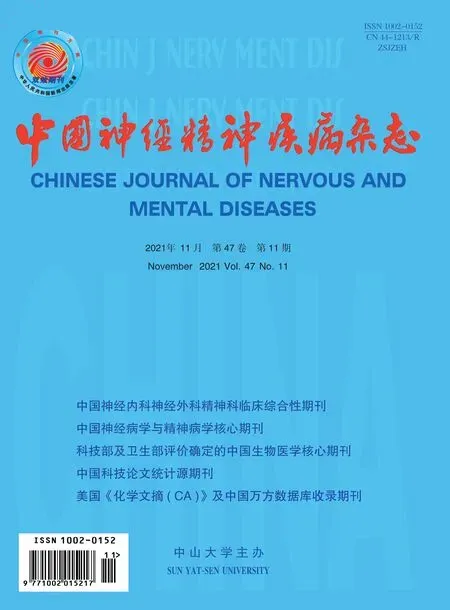自杀与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额边缘系统脑区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黄倩况利
自杀自伤行为因其发生率及相关风险严重性的不断攀升而逐步引起学术和临床领域的共同关注[1]。常见的自杀自伤行为包括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SA)与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二者在青少年时期常共同发生,是自杀死亡的显著预测因素[2-3]。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从神经发育的角度来看,这是前额叶系统和边缘系统发育不同步的时期[4]。额边缘系统由多个脑区组成,包括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PFC)、扣带回皮质(cingulate cortex,CC)、杏仁核(amygdala,Amyg)、岛叶(insular,INS)、海马(hippocampus,Hipp)等,与情绪处理和调节、奖赏处理及认知控制紧密相关[5-7]。考虑到额边缘系统在自杀自伤行为发生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且自杀自伤行为的早期有效识别、预防及干预有助于降低自杀风险,本文对近年来青少年自杀和NSSI的额边缘系统脑区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探寻有效识别二者的客观神经生物学指标。
1 自杀与NSSI的特征及易感因素
自杀个体具有显著的绝望、痛苦、社会孤立及冲动等心理特征[8-9],其患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概率较高[10]。研究显示,13~19岁青少年的自杀风险在性别、城乡及家庭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1]。儿童期受虐待或忽视、精神疾病家族史也与自杀风险较高有关[12-13]。NSSI行为是个体经历了高度的情绪失调[14]、负性情感[15]和自我批评[16]后用于调节负性情绪或直接伤害自己的行为,其发生也常与抑郁症等多种精神障碍紧密相关,儿童期不良经历(如被遗弃、虐待或忽视)对其具有重要影响[8]。
青少年自杀与NSSI的易感因素值得高度关注。“素质-应激模型”认为自杀与NSSI是个体的生物学素质和环境应激源交互作用的结果。神经改变是生物学素质,这可能是导致自杀自伤行为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再加上特定的环境暴露,尤其是急性应激(如同伴伤害、人际关系缺失等),使得产生自杀和NSSI行为的可能性增加[17]。在儿童青少年时期,额边缘系统中的前额叶系统和边缘系统发育不同步,这一过程对动机性行为有直接影响,靠近、回避和调节系统的神经环路尤其起到重要作用。在动机性行为的三元模型中,靠近系统、回避系统分别受腹侧纹状体和Amyg控制,而用于平衡靠近和回避行为的调节系统主要受PFC控制[18]。因此,虽然CASEY等[4]提出青少年的危险行为源于皮质下边缘系统发育相对于前额叶系统脑区更成熟的观点,但自杀和NSSI行为也可能源于靠近、回避和调节系统各个水平上的缺陷。但神经改变不能单独起作用,而是与应激源产生动态交互作用,进而产生青少年期的自杀和NSSI行为。
2 额边缘系统脑区神经改变研究
2.1 神经结构影像学研究
2.1.1 自杀行为相关神经结构改变 腹侧前额叶皮质(ventral prefrontal cortex,VPFC)和眶额叶皮质(orbital frontal cortex,OFC)的结构改变对情绪抑制、决策和自我控制至关重要[19-20]。在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和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青少年患者中,有SA者VPFC和OFC脑区灰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GMV)较无SA者显著减小[21-22]。另外,一项前瞻性研究也发现,基线态VPFC和喙侧PFC脑区GMV减小可能增加了心境障碍青少年将来SA的风险[23]。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额叶GMV减小可能通过改变情绪调节、决策及自我控制过程参与自杀行为的发生。除额叶外,也有MRI研究报告SA者扣带回皮质改变[24-25]。在BD青少年中,SA患者还显示出Hipp、双侧小脑GMV减小[21]。以上研究提示边缘系统脑区在SA中也可能起到调控作用。然而,目前大部分关于SA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精神疾病诊断背景,且额边缘系统脑区的研究结果显示出改变脑区的广泛性及侧性效应(左侧和右侧),表明其特异性较差,因此,尚不清楚这些差异源于SA还是精神障碍严重程度,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单纯SA青少年神经结构的影像学改变。
2.1.2 NSSI行为相关神经结构改变 总的来说,关于NSSI青少年神经结构改变的MRI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关于NSSI青少年PFC结构改变的研究仅有1项。该研究发现,NSSI青少年女性右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的GMV减小[26]。岛叶(insula,INS)作为额边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先参与内部情绪的产生,并作为信号中继站来维持体内情绪的平衡[27]。多项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NSSI青少年呈现出INS的GMV减小[26-2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自伤的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青少年中却未发现此变化[29],提示INS的GMV改变,除受NSSI影响外,还可能与精神障碍诊断有关,例如BPD。另外,多项研究证实,前扣带回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的GMV存在显著改变。在BPD青少年中,过去6个月的自伤次数与左侧ACC体积呈显著负相关[30],关于过去1年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和健康对照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28]。后来的研究还发现,大多数NSSI青少年(55.2%)报告其终生有过SA,再结合前面提到的ACC脑区GMV改变与自杀行为之间的相关性[25],可以推测ACC脑区GMV改变可能参与自杀和NSSI行为的神经生物学过程,这可能有助于自杀和NSSI行为的客观鉴别。然而,这仍需做进一步的纵向随访研究。
2.2 神经功能影像学研究
2.2.1 自杀行为相关神经功能改变 研究显示,SA个体情绪障碍特别突出,每年高达50%的自杀发生在抑郁发作期,MDD患者自杀的可能性是健康对照的20倍[31]。情绪性面孔识别能力是能够正确识别他人情绪性面部表情的社会认知能力,是寻求人际间社会交往的最基本技能之一。研究显示SA个体存在一定的情绪性面孔识别能力障碍[10]。一项基于情绪性面孔识别任务的fMRI研究显示,与基线态相比,伴BD的SA患者显示出双侧Amyg与左侧VPFC(快乐和中性面孔下)、右侧PFC(中性面孔下)的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减少,其中,自杀意念与Amyg-右侧PFC的FC呈显著负相关,自杀方式的致死性程度与Amyg-左侧VPFC的FC也呈负相关关系[21]。另有研究表明,伴自杀意念青少年在主动观看负性图片的情绪调节过程中,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活性显著增高;而在被动观看负性刺激时,右侧丘脑、右侧DLPFC交界处神经活动下降[32]。除基于任务态的fMRI研究外,静息态fMRI研究也发现,伴SA的MDD患者较无SA的MDD患者在额上回、额中回脑区局部神经活动显著降低[33]。以上研究表明,情绪调节相关脑区神经功能改变可能参与自杀行为的神经调控过程。但由于自杀与情绪障碍常伴随发生,横向研究结果仍不足以论证情绪调节脑区功能改变与情绪障碍和自杀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在前期横断面研究探讨自杀意念、自杀未遂神经功能改变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以明确自杀意念向自杀行为转化、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强弱转化的特异性神经生物学特征,这可能为未来实现对自杀的早期预警、早期干预提供了客观影像学证据。
2.2.2 NSSI行为相关神经功能改变 NSSI是减少强烈负性情绪的常见方式,个体通常在实施NSSI行为后表达一种释放情绪压力后的冷静感[34]。探讨NSSI神经功能改变的fMRI研究中使用到多种情绪处理任务。在观看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和自伤图片以刺激情绪反应的实验中,NSSI青少年较健康青少年表现出OFC、顶下叶皮质和额中回/IFC活性增强[35]。在情绪面孔匹配任务中,NSSI患者较健康青少年在Amyg-额叶的任务态FC中表现显著减弱,尽管这与预期相反,但在NSSI组中,每周自伤行为(切割)次数与Amyg-额叶的任务态FC呈正相关关系,提示这一神经环路可能与自伤行为的调节情绪功能有关,进一步地,在NSSI青少年抑郁症状得以控制后,这些发现消失,表明这一神经环路异常可能与NSSI青少年经历的抑郁症状高度相关[36]。此外,DEMERS等[37]还报告在观看面具性恐怖面孔(相比于开心面孔)时,NSSI患者情绪觉察和缘上回、右侧IFC之间存在联系。另有基于静息态fMRI的研究发现,与不伴NSSI的MDD青少年相比,伴NSSI的MDD青少年显示出额上回与多个脑区的FC显著增强[38]。综上,由于上述研究实验范式及样本等因素的差异,研究结果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但以OFC、额中回、IFC及Amyg为代表的额边缘环路脑区神经功能改变可能是未来进一步探讨NSSI情绪调节反应的基础。
冲动控制困难是NSSI个体重要的情绪调节缺陷形式,追求奖赏是冲动行为的维度之一[39]。在NSSI的fMRI研究中,Cyberball范式用于探讨个体对社会排斥的神经反应。既往研究发现,与单纯抑郁及健康青少年相比,伴NSSI的抑郁青少年的内侧PFC和VLPFC神经活性增强,提示其尝试做出监管调节的程度可能增加,但并未成功,因为在Cyberball任务后,与健康被试相比,伴NSSI的抑郁青少年表现更无助[40]。此外,在解读他人的评价性社会反馈时,NSSI青少年也表现出负性偏见,这种偏见可能与对社会评价的不同神经反应模式有关[41]。少有的纵向研究发现,经8周N-乙酰半胱氨酸治疗后,NSSI频率减少与左侧Amyg-右侧补充运动区、右侧伏隔核-左内侧额上回的FC降低及右侧Amyg-右侧IFC的FC升高相关[42],提示这些脑区FC的改变可能是NSSI治疗的有效靶点。另外研究还发现,在基线态时,NSSI青少年额边缘系统脑区FC较健康被试显著降低,经心理干预后,50%青少年报告NSSI次数减少,其中Amyg-PFC连接增强与NSSI改善程度显著相关,表明额边缘系统功能改变可能作为NSSI青少年心理治疗后NSSI行为改善程度的预测指标[7]。上述研究结果提示,NSSI青少年冲动控制困难可能与情绪调节相关脑区的神经功能改变有关,对情绪调节脑区的关注可能激发将来对NSSI发生机制、治疗及临床预后的进一步探讨,这些脑区可能是NSSI的特异性治疗靶点。基于目前研究证据,未来可进一步以大样本、多中心、多检测手段及数据分析方法的方式来补充探讨NSSI青少年额边缘系统脑区的功能,此外,纵向研究仍具有重要作用。
3 小结与展望
目前研究初步探索了青少年自杀和NSSI行为的额边缘系统脑区神经生物学改变,发现了以PFC、OFC、INS、ACC、Amyg等脑区为主的多个可能的自杀自伤行为标志性脑区及治疗靶向脑区。但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第一,在自杀和NSSI行为的研究中,鉴于自杀和自伤行为常与精神障碍伴随发生,研究样本难以纯化,故与健康被试的比较很难将这些神经改变归因于自杀自伤行为本身还是精神障碍,进而差异脑区的特异性较差;第二,研究样本量较小,不足以探讨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大多数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纵向研究较为缺乏;第四,检测技术和分析方法相对单一。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丰富神经检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为探讨神经改变的研究提供补充信息。另外,更大、更具多样性的样本在考虑内在异质性(如行为的频率或方式、潜在疾病、药物使用情况等)的影响方面也更具有优势。最后,考虑到大多数有自杀和NSSI意念者会在一段时间内实施自杀或自伤行为[43],故纵向研究将有机会发现自杀和NSSI意念向行为转变的神经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