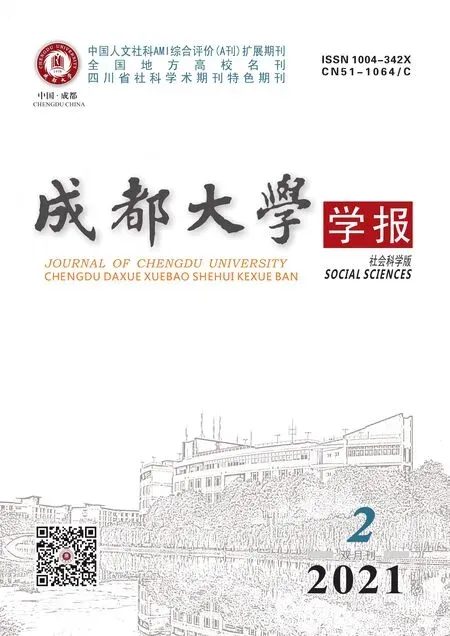除水之害:岷江水患治理与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兴起*
韩 英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历史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72)
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由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标志着定居生活的开始,城市文明曙光初现。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存续与发展高度依赖大自然,特别是在还不懂得利用肥料前,农业经济的持续与兴盛仅能依靠河流泛滥淤积的肥沃土壤。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起源于江河流域的三角洲地带或冲刷平原。然而,大江大河多发源于海拔较高的山地,奔腾于山涧间,随地形蜿蜒曲折,随季节丰枯变化,虽然有饮用通行之利,但也有泛滥成灾之害。因而几乎所有人类早期文明都流传着滔天洪水摧毁氏族部落的神话与故事,如中国有女娲补天与大禹治水神话,《圣经》中有诺亚方舟故事,美索不达米亚有朱苏德拉洪水神话。这些神话与传说是早期先民对江河水患的历史记忆。城市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背后必然会有大型水利工程的支撑:古埃及美尼斯王朝在尼罗河两岸建造了大型堤防工程与灌溉体系,古巴比伦王国在两河流域建造了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工程,古印度人在印度河流域台地上开挖渠道,而大禹则因治水有功而使舜“让天下于禹”[1]158,进而成为夏王朝的开创者。
如同上述城市文明与河流的关系一样,成都平原城市文明产生发展与岷江水患治理密不可分。大约4500年前,成都平原城市文明在岷江孕育下应运而生。然而,岷江水患亦为古蜀文明带来严重灾害,三星堆文明的消亡就与洪水有密切关系,古城遗址上有“厚度约20-50厘米的洪水积淤沙泥”[2]。古蜀国数次易国都同样与岷江水患有着直接关系。秦灭蜀后,将古蜀文明融入中原文明,又以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民修筑都江堰,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岷江水患,使岷江水运交通功能与灌溉功能产生质的飞跃,成都平原自此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3]133的富庶之地,为岷江流域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可见,蜀人及古蜀国对岷江水患的治理及其结果直接影响着岷江流域古代城市的兴衰变迁,这不仅对岷江流域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文明甚至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四川考古发现的推进,学术界对古蜀文明的研究愈加重视,成果日渐丰硕,对古蜀城市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如段渝结合考古学发现研究了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结构与功能;何一民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探讨了成都早期城市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形成过程,进而系统论述了成都“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的都城历史。①但尚未出现以治水为视角,考察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城市兴起变迁的成果。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水患治理与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古蜀文明研究与先秦时期四川城市研究。
一、成都平原自然地理环境与岷江水患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是由岷江、沱江、涪江等河流挟带泥沙长期冲刷堆积而成的扇形冲积平原,地势十分平坦,土质疏松肥沃,平原内河流交错,河网密布,具有发展农业经济的先天优势。然而,也正是因为成都平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水患一直是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重大威胁,尤其是岷江水患对成都平原影响最为突出。
岷江是成都平原母亲河,古称汶江、都江、导江,明代以前曾长期被误认为长江之源,故又称大江水。岷江发源于川西北松潘境内的弓杠岭和郎架岭,由北至南贯穿成都平原,以大渡河为源头至汇入川江全长1203公里。②岷江是长江水量最大的一级支流,支流众多,大多分布在右岸,构成不对称狭长羽状水系,流域面积多达13.35万平方公里。其中以大渡河为最大支流,流域面积达9万余平方公里,此外“流域面积大于5000平方千米的有黑水河;1000~5000平方千米的有小姓沟、杂谷脑河、渔子溪、西河、南河、茫溪河、马边河、越溪河;300~1000平方千米的有漳腊河、牟尼沟、归化沟、松坪沟、草坡河、寿溪河、白沙河、府河、醴泉江、鲫江、思濛河、金牛河、沐川河、龙溪河”[4]97-114。岷江支流又有自身的河流水系,如大渡河有梭磨河、绰斯甲河、青衣江等支流,流域面积达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181条。岷江及其支流构成了成都平原主要水系,为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生产生活用水。但岷江水患十分突出,给位于中游的成都平原造成了巨大威胁。
岷江水患对成都平原影响重大主要缘于四川盆地独特的地形、气候和水文条件。就地形而言,四川盆地四周均有山岭围绕,形成一个四周高、中间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且四川盆地处于第一二级阶梯过渡地带,总体地势西高东低,因而境内河流均从南北两侧山岭沿着下趋势的山势奔腾而下,流向中心盆地,最后自西而东汇入川江,东出三峡。就气候而言,四川盆地地处中国南方,干湿季分明,每年4至10月为雨季,年降雨量1000毫米左右,不仅雨量充沛且降雨量集中,雨季集中了全年80%的降雨量。[5]80就水文而言,岷江发源于川西北松潘境内的弓杠岭和郎架岭,山岭海拔高,终年积雪。春夏之交,雪山融化之际,恰逢四川盆地迎来雨季,因而每当盛夏突发暴雨或降雨连绵时,河水极易泛滥。尤其是岷江从海拔三四千米的川西高山深谷处发育而出,水流湍急,流经都江堰玉垒山后突然越入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海拔骤降至七百米,而“成都平原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坡度千分之四”[6],水势便犹如脱缰野马,夹杂着大量泥沙涌入成都平原,行至平原东部遭到龙泉山脉阻隔,难以排泄,致使每年涨水季节,成都平原一片泽国,而龙泉山以东却干旱缺水,西涝东旱成为常态。
根据竺可桢对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研究,从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7]。考古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四川盆地资阳市,以及原属四川现属重庆的巫山县和铜梁区等地的考古发现,在与人类头骨鼓声的哺乳动物化石群中均有大熊猫、桑氏戳狗、剑齿虎、乳齿象,双角犀、爪兽、云南马、小貘、小猪、巨羊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主要成员,表明旧石器晚期四川盆地的气候类似于今华南地区,属亚热带气候,气温较高,气候温暖潮湿,森林茂盛,草木繁荣,动植物十分丰富。[8]3-4也就是说,先秦时期四川盆地气候比现在更为湿热,降水量更多且集中,有“西蜀天漏”之说,故水患对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威胁更大。因而正如蒙文通先生指出的一样,“成都平原,总须经过治水才能居住,也必须在农业发展时才能显得重要”[9]79。水患治理成为古蜀人与古蜀国重要的政治任务与生活内容,也是成都平原城市文明得以兴起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水与城: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避水”“防水”“治水”
早期人类对城市的选址即是对水与城关系最初的理解与探索。“避水”与“防水”是古蜀先民处理水与城关系的重要准则,深刻地影响了成都平原城址的选择。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依托岷江,城市均分布在岷江流域。如宝墩文化古城遗址沿岷江水系分布,芒城、双河古城、宝墩古城位于岷江支流西河西岸,鱼凫古城位于江安河东岸,盐店古城、紫竹古城与高山古城位于岷江右岸水系南河支流的斜江河两侧,郫县古城位于蒲阳河南岸,三星堆古城位于湔江南岸。③同时出于避水与防水目的,城市选址均与岷江水系保持一定距离。如郫县古城与蒲阳河保持着3.5公里距离,宝墩古城同样距离西河约4公里左右。[10]61为降低洪水对古城的影响,上述城址全部选择在河流冲积扇上地势较高的台地上,芒城、双河古城、紫竹古城3座古城更是直接建在河流上游的近山地带。
城墙是城市的重要标志,而城墙的兴起与先民防水的思想与实践密切相关。相传有崇部落首领鲧善于治水,鲧治水的主要方法是壅堵,即以砂石投水截断洪水或在洪水两岸修筑堤防,鲧治水的壅堵之法逐渐演化为在聚落外围修筑墙体以防止洪水。因此,除长于治水外,鲧还善于修筑城池,即《世本·作篇》所言“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云“夏鲧作三仞之城”。岷江流域诸古城同样建有坚固高大的城墙。虽然学界对古蜀城市城墙的核心功能未形成统一意见,但对其城墙的防水功能基本达成共识。宝墩文化遗址中,芒城、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宝墩古城还建有呈“回”字形的双城墙,[11]无疑与增强古城的防水功能有关。其中,三星堆、宝墩、鱼凫村和古城村特殊的城墙形态尤其引人瞩目。以三星堆古城城墙为例,根据考古发掘,三星堆古城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厚40米,顶部厚20米”[12],且城墙内外两面都是斜坡,根本不具任何军事防御功能,这种形态的夯土城墙应与防范鸭子河河水泛滥有关。
在城市选址中注重“避水”与“防水”是古蜀先民被动适应自然的表现。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他们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开始出现“治水”和“与水斗争”的尝试。考古资料也显示,“成都各考古遗址,多有被洪水冲刷、淹没留下的淤积遗存,甚至有被多次冲刷而反复重建的遗迹”,而在诸多的洪水淤积层之上,“往往又出现若干新的文化遗存”[8]203。大禹治水就是数千年以来古蜀先民探索治水和“与水斗争”的缩影。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剖而生于县。”[13]关于大禹的出生地与发迹地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诸家各执一词且均有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为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大禹来自岷江上游,是古蜀大地一支土著部落首领,与鲧一样以治水见长。在帝舜任用禹治理“平河、洛、济、淮、泗”一带的滔天洪水前,大禹已在率领部族治理岷江水患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
真正使大禹走出岷江上游,名扬华夏文明的历史性事件是尧舜时期中华大地上爆发的滔天洪水,而大禹正是因为治水有功成功取代帝舜成为华夏共主,进而创立夏王朝。据《尚书·尧典》记载,尧舜之际,“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14]11,此次滔天洪水使高山峻岭都被洪水包围分割,平原全被淹没,并且洪水常年不退,使已经走向定居农耕生活的人类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盛,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15]111。在各部族首领推举下,帝尧任用鲧为治水首领。鲧是颛顼后人,善于修筑城池,采用筑堤防水的方法治水,“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16]250。息壤是传说中一种自己能生长且永不耗减的土壤,然而鲧因“窃帝之息壤”且“不待帝命”,而被“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16]250。鲧治水的故事虽极具神话色彩,但也说明在尧舜时代华夏诸族对洪水的认识和治理方式十分原始,治理水患的主要方式为“堙”——鲧率领先民运来泥土和砂石对河流堤岸进行加固加高。然而这次洪水泛滥程度之高,治理难度之大,远超过鲧的治水能力,“鲧用壅堵之法,九年而无功”“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17]5帝舜也以治水失败为借口处死了鲧。
由于明代以前,岷江被认为是长江正源,因此帝及四岳商讨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从洪水暴发的源头,即岷江进行治理。因而他们选中了既有治水能力,又兴起于岷江上游的大禹部落。由于此次洪水泛滥程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治理难度之大,非以一个氏族部落之力能完成,因此禹在奉命治水后召集岷江上游各部族召开“汶川之会”,商讨如何治理岷江洪水。此次会盟商讨的结果,就是各部族放弃了“壅防”之法,另辟蹊径采取“疏导”之法。《尚书·禹贡》说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14]67。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说,“《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18]866。大禹治理此次洪水最大的工程与业绩就是在岷山导江,即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用来分引岷江洪水,提高岷江泄洪能力,这条人工河道称为“沱”。“沱,水别流也”,陆深言“江别流而复合者皆曰沱”,从大江开挖别出一条人工水道,这条水道经过曲折后又还入大江是为“沱”。[19]55一般认为这条“江沱”属于毗河一支,其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东注入毗河,又向东直入金堂峡,汇入沱江后南行还入川江。[8]203大禹治理岷江洪水,就是根据地势和水系分布,尽量把泄洪通道安排在平原中部偏北,方向应与天然水系交叉,采取自西往东的方向,以顺应地势和水情。这样,就便于沿程拦截暴雨径流,向东集中到沱江金堂峡泄出。[20]161此次洪水在禹的治理下逐渐消退,人民得以从高山峻岭重归平原丘陵,农事重新兴起,文明秩序渐渐恢复。成都平原亦因此次治水而大受裨益,为城市文明的兴起创造了良好条件。
大禹治理了岷江上游水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得到开发整治,农业恢复发展,水利兴起,出川交通线开辟,为成都平原城市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与交通基础。《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14]56-58大禹治水后对国家进行了疆域划分和赋税评定,成都平原被划归梁州境,属九州之一。根据《禹贡》记载,通过水患治理,岷江流域产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岷江、沱江等对成都平原影响重大的河流得到疏导,成都平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农业经济复苏。二是水患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四川盆地闭塞的交通条件,加强了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禹贡》记载梁州向中央王权纳贡的线路:首先通过潜水(嘉陵江)经由沔水(汉江支流),进入汉中平原,再由汉中平原东行通过汉水抵达渭河平原,横渡渭河即可进入中原地区。这既是梁州地区纳贡所走的线路,也是岷江流域与汉江流域及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线路。
值得注意的是,大禹治水、鳖灵治水等神话传说是古蜀先民数千年来与水斗争的缩影,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仍十分低下,以人力改造自然、治理岷江水患的能力极其有限,因而古蜀先民对岷江水患的认识经历了从避水、防水和治水的转变,但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发展,而是相互交织的。
三、古蜀国治水活动与成都都城地位的确立
大禹治水开启了蜀人大规模治理岷江的序幕,古蜀人在大禹治水基础上进一步治理岷江水患,三代蜀王时期都曾组织过规模大小不一的治水活动,为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成都地区虽地处平原,有发展农耕经济所需的地形、土壤、水热等先天优势,但是因水涝灾害频发,动辄一片泽国,因而长期以来只是蜀地众多采集捕猎之地之一。随着古蜀先民治水活动的开展和古蜀氏族向岷江中游的迁徙,成都平原农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历代蜀王几乎都将王城建造地点选在成都。
《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21]1三代蜀王统治古蜀国数百年之久,王城选址时有变迁,但几乎都没有离开成都。最早建都成都的是蚕丛氏。蚕丛氏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地区蚕陵县(今茂县羌族自治县),后沿着岷江河谷南迁至成都平原,曾在瞿上建立王城。《路史》卷四《前纪四》云:“蚕丛纵目,王瞿上。”[22]卷四据相关学者考证,瞿上城在今成都市双流区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3]187蚕丛之后为柏濩(当作“柏灌”),不少学者认为柏濩氏是兴起于成都平原的土著部落[23]13,然而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极少,王都选址无法确定。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柏濩时期王城规模小,很可能旋兴旋废,时常迁徙。在今成都市温江区的鱼凫城遗址相传为鱼凫王所建,但鱼凫城遗存中罕见玉器[24]40-53,无大型祭祀活动,可见并非王城。其王城已离开今成都城区范围,迁徙至距离成都约50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三星堆文化第二期与第三期、第四期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演进,[8]34可推测鱼凫氏定都今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年代约相当于有商一代。
商周之际,杜宇击败鱼凫取而代之,号望帝,“望帝积百余岁”,传袭数代以上。杜宇王朝之初当为中原王朝商周之际,王城遗存为金沙遗址,位于今成都城区内,另以郫县古城为别都。[8]147然而至西周晚期,杜宇王朝都城发生转移,迁至“汶山下邑,曰郫(今成都郫都区)”。即《华阳国志》所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迁治郫邑,或治瞿上(今双流)”[3]118。虽然金沙、郫邑、瞿上都在今成都范围内,但是杜宇王朝国祚延续不过百余年,却三次迁都,而迁都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会打破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平衡,如果不是迫于现实原因,一般不会轻易迁都。但是无论金沙、郫邑、瞿上都在今成都范围内,“古代都城的选址并不是一蹴而就,往往是经过多次选择和迁移……一般认为只要在50公里的距离内,都可以认为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25],即三次迁都都想要保持都城的历史延续性,也就是说杜宇王朝迁都的行为并非为了去除前朝的政治影响。那么在古蜀时期,这种被迫的迁都行为只能推测为自然原因,也就是成都平原频发的水涝灾害引起的。可见,虽然大禹导江及历代的治水活动有效地治理了岷江上游的水患,一定程度地提高了成都平原的防水能力,但还未较彻底地解决水患对城市的威胁。
三代蜀王之后,影响甚大的是杜宇王朝鳖灵对岷江水患的治理。杜宇因“教民务农”而广受巴蜀地区人民爱戴,但却因治水无能而丧失帝位。据《蜀王本纪》记载,杜宇氏称帝百余年后,蜀地再次爆发大规模洪水,“时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这次洪水最大的危害不在于规模大,而是洪水长期不退,“蜀水不流”,“壅江不流,蜀民垫溺”,百姓长期浸泡在水中,无法正常地生产生活。此时,“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来自荆楚或黔中一带④的“荆人”鳖灵氏族沿川江上溯至古蜀地区,鳖灵氏族擅长治水因而得到杜宇重用。鳖灵在治理岷江水患的过程中积累了政治实力,壮大了权势力量,“望帝以鳖灵为相”,“鳖灵为刺史,号西州”,鳖灵最终在王权争夺战中击败杜宇,取而代之。
鳖灵治水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凿、疏导了沱江河口金堂峡。成都平原西北高东南低,地表水系几乎都汇集到东南方向,而盆地东南边缘的龙泉山脉形成门槛,阻隔水流流出。但龙泉山脉有三个泄洪口:位于东南部的沱江金堂峡,位于西南部的岷江府河河口与新津岷江河口。正常情况下,岷江上游河水可以通过这三个出水通道缓慢泄出。而在洪水泛滥的异常年份,岷江上游洪水的宣泄主要依靠地势最低的金堂峡。然而金堂峡为狭窄V型河谷,穿行龙泉山脉长达12公里。[26]218群山高矗,绝壁悄然,水路狭窄,两侧岩体又为侏罗系蓬莱镇组砂岩与泥岩互层构成。[27]291岩体并不坚固,容易产生崩塌、滑坡和滚石。同时,龙泉山脉又处在活动断裂带上,“存在着每百年发生一次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28]59。如果该地产生地震,继之以暴雨,则金堂峡两侧极易产生大型岩体崩塌乃至壅塞峡口,使成都平原洪水难以宣泄。杜宇王朝时期发生的洪水最大危害不在于规模大,而在于长期得不到宣泄,严重地威胁了古蜀国正常的农耕生产生活,于是产生了鳖灵开金堂峡的传说,⑤“(帝)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13]卷888,“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29]489,鳖灵“巫山龙斗,壅江不流,蜀民垫溺,鳖灵乃凿巫山峡,开三峡,降丘宅土,人得陆居”[30]117。金堂峡中至今仍有鳖灵峡,峡内有鳖灵迹和鳖灵湾遗址,[31]834金堂县民间还有鳖灵治水开峡的传说。
鳖灵治理金堂峡后,成都平原泄洪能力显著提升,对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成都平原农耕经济由此进入兴旺发达的历史阶段,古蜀国王城选址再也没有离开成都范围,初步奠定了成都的古都地位。据记载,开明王朝最初都城以郫邑为都城,广都樊乡为别都,“开明子孙八代都郫”,“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梦”在荆楚方言中是水泽之意,“梦廓”指郫邑或广都,开明九世(或五世)后王城郫邑被洪水吞噬后,王都迁至成都,此后未见开明王朝迁都的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可见,经历三代蜀王及开明王朝系列治水活动后,成都作为蜀地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由此确立。
另一方面,成都平原早期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古蜀文明从岷江上游兴起,古蜀先民的治水活动推动农业经济随着氏族步伐逐渐向岷江中下游地区迁徙,治水活动的成效决定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古蜀文明迁徙的速度与方向。三代蜀王时期仅有三星堆古城一个早期城市。⑥杜宇“教民务农”推动古蜀国农业从高山农业进入“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稻作农业阶段”[32]。开明王朝传十二世,而鳖灵氏族以治水见长,更凭治水之功而开创开明王朝,可以推测开明王朝必定对岷江水患进行大力治理,使岷江中游地区更加适合农业发展。根据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开明王朝时期水患治理扩大了农业经济的影响范围,早期城市在杜宇王朝基础上有所扩展。除都城成都外,在南安、芦山、宜宾等均有开明王城。《太平寰宇记》引《地志》青衣江上游芦山县,“治有开明王城故址”,《华阳国志·蜀志》僰道(今宜宾)“有故蜀王兵兰”;《太平寰宇记》引《周地图记》阆中县,“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登此,因名灵山”[28]66。
成都平原富庶的农业经济为开明王朝的对外扩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据史料记载,开明二世卢帝曾率军攻打秦国,从葭萌(今广元境)通过嘉陵江河谷与汉江上源,纵入秦国境内的壅城。开明三世保子帝向西南扩张,进攻青衣人,“雄张僚、僰”。经过开明王朝累代开疆拓土,至战国时代,古蜀国的疆域已“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号称西南之长。
四、结语
古蜀文明由岷江孕育而生,岷江水患治理与古蜀文明发展扩散存在高度关联和互动关系。一方面,自早期文明兴起以来,治理岷江水患就成为古蜀国重要的政治活动,岷江流域大型水利工程需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非某一氏族部落能单独完成,其修筑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蜀王朝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古蜀先民治水经验的累积,古蜀文明沿着岷江向中下游地区扩散,而自蚕丛氏建都成都后,历代蜀王通过或堵,或挖,或筑堤,或作堰等多种方式治理岷江水患,成都平原泄洪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古蜀文明最终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中游地带发展壮大,依托成都平原富庶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城市文明,至开明王朝时古蜀国逐步对外扩张,成为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岷江水患的治理对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发展和成都都城地位的确立有重要意义,秦并巴蜀后历代蜀守在古蜀国基础之上继续治理岷江水患,至李冰任蜀郡太守时主持修筑了都江堰,变水患为水利,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岷江水患对成都的威胁。此后川蜀地区历代政府不断拓展都江堰的灌溉体系,使其如同一面巨大的扇面在川西平原上徐徐展开,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推向繁荣,成都平原城市也随之发展扩散。
注释:
①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何一民、《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兴起——论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何一民、陆雨思:《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地位》,《天府新论》,2017年第2期。
②据新华网2013年12月28日报道,岷江以大渡河为正源,发源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满掌乡境内莫坝东山,全长1279公里。详见:《中科院卫星遥感确定长江一级支流岷江全长1279千米》,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3-12/28/c133003591.htm
③有学者根据遥感技术(3S)判定岷江曾在今汶川雁门向东南流,穿越光光山,沿今白水河、湔江流向沱江,只是由于发生于公元前1099年的地震引起岷江河流改道,即言三星堆古城最初属岷江流域城市。详见范念念等:《地震导致河流改道与古蜀文明的变迁》,《山地学报》,2010年第4期。
④对于鳖灵一族来源,参见段渝《四川通史·先秦》,第160页,认为来自今贵州黔中一带;有些学者则认为来自长江中游荆楚一带,如喻权域认为开明氏楚国人,望帝年间来到蜀国,带来了蜀国先进的治水技术,参见喻权域:《都江堰古史新论》,《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冯广宏认为鳖灵确为荆人,详见冯广宏:《鳖灵事迹重考》,《天府新论》,1986年第1期。
⑤冯广宏先生在《鳖灵丛考》中结合地理学、水利学相关知识,认为金堂峡最有可能是开明治水的成果。
⑥赵殿增认为三星堆文化发生期的主人为蚕丛或柏灌氏,繁荣期的主人是鱼凫氏,成都十二桥羊子山遗址的主人则应是杜宇;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详细见《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