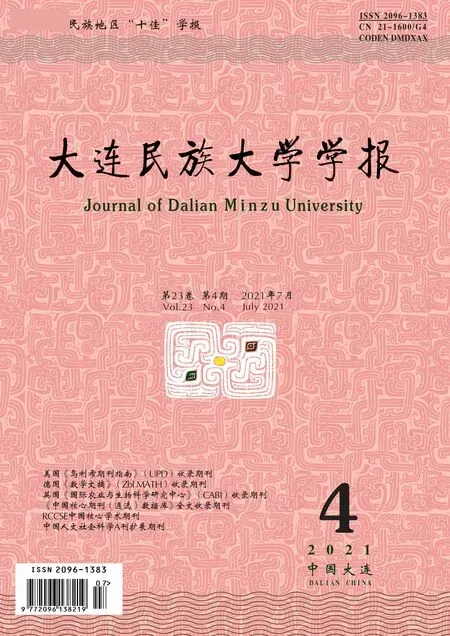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考察与新时代启示
孙守朋,耿靖雯
(大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05)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以中国为主要区域,中华各族人民自觉凝聚而成,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已经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各民族通过不断交流交往交融,最终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形成共鸣,从而对自己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身份产生认同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1],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直存续的,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与实践的历史演进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颇有建树,主要以其内涵和实践途径进行研究,本文意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演进,从古至今各朝代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交流交往交融,并以史实为基础进行宏观的梳理和阐释,从而进一步探索其新时代启示。
一、先秦:“五方之民”格局的形成
多民族共存是中国一直以来的基本形态。五方最早是在《礼记·王制》之中记载: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2]由此可见,“五方之民”是对“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合称,“五方”作为最早对多民族之间关系的认知模式,其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这种认知模式不仅体现在强调以“中国”为中央,对周边地区进行权力征服上,更体现在对中央与地方文化之间的交融。五方将“中国”与其他民族放置在同一地理空间概念之中,这种认知模式一直延续下来,可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滥觞。最早在西周时,夷蛮还只被作为泛称,没有对方位的辨别,就如《诗·小雅·何草不黄》被认为是“下国刺幽王”的诗,其中有“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的诗句,四夷的概念便突出了“中国”的概念。孔孟儒家的民族观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孔子作《春秋》“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至中国,则中国之”[3]。从西周到春秋,这一时期民族的称呼与其所处的方位密切相连,虽然还没有建立整体格局的思想,只是将各方对应关系加以概括和总结,但已为日后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到了战国时期,五方之间相互配合,一统的观念已经形成,对四夷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在先秦就予以实践,这一重要政策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墨子》中明确了“四夷”与“四方”的直接对应关系,整体格局观念初步形成。从《墨子》和《礼记》中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地理观、世界观正逐渐形成等级秩序。自西周以来,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最终形成于《礼记》中《王制》所反映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方之民”的格局,是人们对国家统一大趋势和国家民族地理观的设想。秦汉时期,政治上大统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在一个政权之下有多个民族存在,各民族联系日益加深,多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自然也日渐巩固和发展。《史记》四夷传中,更是突出了中原地区的地位,此后将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按照四夷的标准进行划分,五方之民这一体系的形成,使得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和华夏族的交往融合的过程被记录下来,为后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历史依据。
二、秦汉: 大一统下的各民族融合态势
秦汉建立政权,不仅华夏统一,而且将各少数民族纳入统治之中。自秦统一六国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与“诸夏”一样的管理机构——郡县,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秦朝48郡之中包括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县级少数民族地区称为道,由郡守管辖。西汉在征服的匈奴地区设立了武威郡、酒泉郡,后攻灭南越,设立了南越九郡。秦汉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立的管理机构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
中原地区较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早,边疆地区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农业发展落后,仍处于游牧经济状态。秦统一南越和北假等地后,实行徙民戍边政策,为边疆地区增加劳动力。汉武帝大败匈奴后,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的政策。兴修水利,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戍卒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带动边疆民族发展生产。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将西域的蔬菜瓜果传入中原地区,如葡萄、黄瓜等,中原地区的饮食种类日益丰富。而在家畜类别上,骡、驴的传入,不但使中原地区的耕作能力有所提升,也促进了中国古代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中原的“穿井”技术也传入大宛,“闻宛城得秦人(汉人),知穿井”[4]。
终汉一朝,汉匈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汉朝的民族关系政策。西汉初期,面对社会凋敝、人民急需修养生息的现状,匈奴的屡次侵扰,汉朝不得不示弱以安匈奴,和亲政策正是以此思想为指导的产物。《史记》中记载:“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 约为昆弟以和亲。”[4]汉高祖此后三代君王均延续下来,至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才转变了对匈奴的政策。汉朝取得对匈作战的巨大胜利,所占匈奴之地与汉族边境连成一片。汉匈战争胜利直接使得匈奴国家政权瓦解,匈奴内部划分两部,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政权的崩溃消除了汉匈之间交往的最大障碍,由此,汉匈之间的民族交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彼此间的迁徙、通婚以及经济交流不断加强,双方为增强经济交流特设关市。汉匈各取所需,互利共赢,汉朝精良的铁器和匈奴的优良马匹在市场上备受欢迎。在政治上,汉朝的政策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待匈奴恩威并施,对匈奴首领采取以招降怀柔为主、战争为辅的基本政策。伴随着经济交流的加深以及匈奴上层的归附,汉匈之间的民族融合进程加快。匈奴多接受汉族的文化和礼仪,他们的饮食和服饰也丰富了汉族的日常生活。汉匈之间政策的转变和关系的密切使得其他少数民族纷纷与汉朝建立起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在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使得中华文化多元而璀璨。
三、隋唐:“合同为一家”
隋唐时期的“合同为一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迭代最频繁、民族关系最复杂以及人口迁移最频繁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这种社会状况,促使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经过魏晋时期的积淀,隋唐为中国历史打开了新的局面。隋唐的民族政策在风格上是开放的,对周边民族,以羁縻政策为主,对民族分裂者则进行武力征服,同时辅之以和亲政策,建立互市,加强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以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总之,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为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处理民族问题时基本秉承着“华夷一家”的思想观念,譬如隋炀帝有云:“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5]体现了隋代“混一戎夏”,诸族一家的民族开放思想。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27)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的观点,深入人心。隋唐时期的和亲政策是为安顿边疆而实施的民族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以和亲的方式建立起民族关系网,其成员熟知的有吐谷浑、回鹘、突厥、吐蕃等。在唐朝历史中,共进行了二十八次和亲,当属文成公主进藏最为著名,在政治上通过血缘关系的维系来稳定边疆,免受大规模战争的侵扰,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双方政治经济发展。通过和亲也加强了唐王朝在边疆的影响力,政治上的稳定使得经济、文化稳定发展。随文成公主出嫁的一干人等将农具制造方法传入吐蕃,并且还传授了汉族的耕作方法。当地妇女学会了汉族的纺织、刺绣技术。制陶、冶金技术逐渐传入,吐蕃手工业快速发展。这些都对吐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吐蕃向唐朝定期朝贡,双方开放互市,经济上唐蕃互补。在文化上,吐蕃利用汉文结合民族语言习惯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文字——藏文,对吐蕃影响深远。释佛像和大量佛经传入,佛学文化快速传播,以至于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疏勒、龟兹等乐器传入大唐,丰富了中原地区舞蹈音乐艺术。
和亲政策的推行,使得唐蕃“合同为一家”,达到政治上友好往来、经济上蓬勃发展、文化上兼收并蓄的盛况,德祖赞普曾在给唐的奏表中真切表达了“外甥是先皇帝属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一家”[7]的美好感受。和亲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政治联姻,使各民族亲上加亲,民族融合趋势日益增强,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提供保障。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
四、宋辽金:“华夷同风”
宋辽金时期,契丹、西夏、女真相继建立政权,此时民族关系双向发展,民族斗争虽不断,但随之而来民族交往也在不断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成熟。以辽代为例,无论是政治上的南北面官制,还是经济上学习中原的先进技术、赋税制度,文化上崇尚“华夷同风”的思想,无不体现出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大趋势。宋辽时期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虽无法避免,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迁徙与融合,打破了“华夷”长期不得同步发展的局面。北方各民族加快发展,纷纷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改变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相较南方较为落后的局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更新的形式,更广泛、更稳固的统一基础。辽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其特点以汉文化和契丹文化为主体,兼之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辽文化。正是在这种逐渐多源合流的发展过程中,使得“华夷同风”的思想在有辽一代蔚然成风。
辽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诗献皇太后。“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探;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暴,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8]这首诗宣扬了辽代的国威,并将辽文化发展的盛况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辽朝廷的积极倡导之下,“华夷同风”思想深入人心,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被中原文化所感染。少数民族文化同汉文化相融合,反映了契丹民族以及治下的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向一统,即由多元逐渐融合走向一体。
儒家文化的传播,为“华夷同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一直将儒家思想秉承为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辽建国以来,随着势力不断扩大,与汉族交往密切,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稳定政局,积极倡导儒家文化的传入,契丹提出“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下,契丹本民族逐渐摒弃了以往“好为寇盗”“贵壮健,贱老弱”“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9]这些原始的道德观念,而将“三纲五常”奉为经典。辽以此来考察吏制,约束君臣之间的关系,忠臣升迁、奸臣贬黜。在辽太祖时期诸弟叛乱的事件中,“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10]9除此之外,“三纲五常”也逐渐成为契丹民族约束自身、与他人交往的准则。鼓励孝顺、赡养父母的行为,“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10]112。
儒家文化的传播与融入,使“华夷同风”这一思想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充分体现。早期契丹民族“畜牧与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0]373。随着与中原日益交融,饮食习惯随之发生变化,饮食生活更加丰富。蔬菜在契丹民族日常饮食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大,喜爱面食和黏食。“正旦之时,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10]877契丹服饰也逐渐汉化,“会同中,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後,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後,大礼并汉服矣”[10]908。除此之外,婚丧嫁娶、风俗节日无不被汉文化所影响。 在有辽一代,“学唐比宋”“华夷同风”的思想深入人心,各民族间隔阂消融,民族间更加紧密,民族融合加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五、元明清:“中外一家”
元朝结束宋辽金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疆域空前扩大,政治上的统一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清之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发展的确立阶段,明朝对于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治理上,就有“华夷一家”的思想,明成祖朱棣曾曰:“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11]
至清代,皇太极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12]26对满汉各族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并积极任用汉人为官,在“满汉一体”基础之上,随着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后将蒙古族也纳入行列,提出“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12]556清入关后一直遵循这一政策。顺治时期,在继承“满蒙汉一体”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中外一家”“中外一统”的观念。顺治帝曾派遣使者到朝鲜、外藩蒙古诸国,称“朕荷天庥,缵承祖宗丕业,已敷大赉于国内,兹罔分中外,广沛仁恩”[13]35。在当时“中外”一词已表示与各藩属国的关系。如顺治帝在两次谕礼部时曰:“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13]186。康熙时期,以“中外一体”为指导思想,在敕谕厄鲁特噶尔丹时曾有言“尚毋违朕视四海一家、中外一体至意”[14]。贯彻“中外一体”的思想处理与蒙古的关系,边疆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雍正时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万物一体”的新理念。雍正皇帝提出“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15]147。以“华夷一家”为准则处理民族关系,认为“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15]696。雍正时期对待各民族一律平等,力图通过地域观念协调民族关系。提倡“满汉一视”,雍正称“国家须满汉协心,文武共济,而后能致治”[15]1100,认为对待满汉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在处理与回民关系时,称“朕思考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15]48。强调各民族即使风俗各异,但都是中国人。乾隆时期继承发展,将“中外一家”思想推向全盛。
清后期,在上谕中“外夷”已经不再是对治下少数民族的称呼,而是对沙皇俄国、越南、日本等外国的称呼。例如:“越南贡使陈请为其国王母乞人葠,得旨赏给。而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其使臣欲请改为“外籓”,部中以诏书难更易。”[16]正是在这种“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制度,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相互融合,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与关键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也由此从“自在”逐渐走向“自觉”,为实现国家“大一统”作出重要贡献。
改土归流制度的实施,使诸民族在多方面形成一体化。政治上通过改土归流制度实现一体化,不仅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威慑四方,改变了原土司制度造成的割据局面,而且原土司管辖地正式纳入到国家版图之内,为今日中国的版图奠定基础。经济上,改土归流后,农业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鼓励移民,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不断传入,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农耕技术得到了很大进步。各地之间贸易往来频繁,商业手工业都有所发展。原有的封建领主经济和农奴制经济最终“一统”为封建地主经济。文化上,改土归流后,在西南地区推行儒学教育,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加强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土司地区婚俗汉化,“与汉人渐次化合,习俗变易。如兄弟共妻,械斗为婚,久已不闻”[17],再如改夷服为汉服等各种习俗的改变。各少数民族文化也为中原地区所吸收,丰富发展了汉族文化,各民族相互交融,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六、近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加深,民族意识也逐渐由“自在”走向“自觉”。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昏昏沉沉,妄自尊大,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已深深陷入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危机之中,国家却仍在顽固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踯躅踱步。无论边疆还是内地,都同样笼罩着被侵略的阴云,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共同面临着被奴役的厄运,面对清政府的内忧外患,中国一部分接受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觉醒。
梁启超最早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首次引入并提出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开中国民族主义之先河,随后,又在《新民丛报》中发表了《新民说》一文,文中首次解释了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8]。补充文献出处他所提出的“大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主体,联合满、回、苗、藏诸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抵御列强的侵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深入人心,孙中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指出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
“九一八”事变以来,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都调动起来,朝鲜族、满族、鄂伦春族等族人民以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设。在内蒙古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蒙汉抗日联军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压力,分散牵制了大量日军的兵力。活跃于冀中平原的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以及广泛活动于河北各地的回民组织,如山西灾关的回民游击队、长治的回民营,安徽定远县的清真大队等,为中国共产党抗击日军提供了有力的配合。中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抗日热潮。海南岛的黎族、苗族人民以及有着抗日斗争光荣历史的台湾各族人民纷纷参加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了抗日斗争。抗战初期,中国接收援助的抗日物资主要依赖东南沿海各港口,日军控制沿海港口之后,中国各族人民仅用八个月就修建了长达958公里的滇缅公路。这是一条以各族人民血肉之躯建成的生命通道,为持续接收抗日物资提供了保障,对中国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日军从缅甸向中国云南发动进攻,企图掐断滇缅公路运输线,云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奋起抗争,傣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一方面积极支援镇守滇西的抗日军队,一方面用比较原始的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新疆各族不仅从行动上支持抗日战争,还为抗日募捐大量的战备物资,购买10架新疆号战斗机送往抗日前线,并募捐80000件皮衣、10000架马鞍和一批药材,运往延安。这些事实表明,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奋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强化了中华之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刻画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形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迈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更应该不忘初心,不断推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牢固团结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卓越贡献。
七、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新时代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具有极大的时代价值。费孝通先生曾从“自在”和“自觉”的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9]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环境、文化基础以及社会心态,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正是在不断地分散与融合中逐渐产生的。从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方之民”格局,到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而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直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明确提出,每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历史考察中可以得出:国家统一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民族团结系根本凝聚力,文化认同乃根本向心力,此三点认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能够使我们保持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凝聚各民族的思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今,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有效调动各民族团结奋斗,从而提升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对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发展,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开启新时代伟大征程的思想引领。
八、 结 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虽在新世纪提出,但共同体意识的雏形早已存在于历朝历代之中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方之民”格局,到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而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直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明确提出,每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历史考察中可以得出:国家统一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民族团结系根本凝聚力,文化认同乃根本向心力,此三点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蓬勃发展,各民族相辅相成,大放异彩。本文只是粗略地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演进进行简单的梳理,但对于部分分裂时期并没有涉及,需继续研究发掘,形成更系统更完整的研究,对于每一各朝代的研究也需更加细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