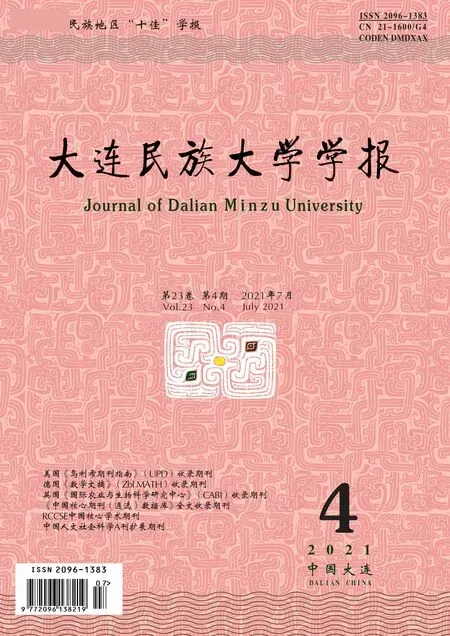《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辑出版等史实考述
金欣欣
(1.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 100081;2.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新华字典》是一部在中国现代辞书编纂、文化教育、汉语规范化等方面有重要影响的辞书。《新华字典》的第一版由叶圣陶先生领导编写,北京大学魏建功教授主编,新华辞书社编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出版。
《新华字典》虽然贡献很大,但它最初的编辑、出版等情况现在人们却知之不多。弄清这些,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教育、辞书编纂等方面的历史都是有意义的。笔者曾撰文对《新华字典》第一版编纂、出版的一些史实做了探讨[1],以下再就这一问题做一些考述。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教。
一、珠联璧合:著名出版家叶圣陶先生与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合作编纂《新华字典》的缘由
魏建功先生曾与金克木、周祖谟、张克强、吴小如四位学者自1948年底至1949年春,就编纂一部新型的汉语字典进行了多次讨论,由魏先生执笔,于1949年4月27日写成《编辑字典计划》[2]一文。《新华字典》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编辑字典计划》的编纂要点编写的。苏培成教授指出:《编辑字典计划》“是《新华字典》在孕育期的写照,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文献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们今天编写规范字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
关于《编辑字典计划》的写作目的,魏建功教授之子魏至先生曾请教金克木教授,金先生说:“那是魏先生为找书店联系出版用而写的。”魏至先生就此感慨道:“可惜对于父亲找书店联系出版和叶先生邀请他‘出山’的经过,现在没人提供情况了。”[4]
本文这一部分拟参照有关资料,对这一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等方面有重要意义的史实经过作一个大致的还原。
吕叔湘先生在《怀念圣陶先生》中回忆,《编辑字典计划》是寄给开明书店的:“1949年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1)吕叔湘先生此文的回忆内容十分珍贵,但是在细节方面略有误。第一,魏建功先生等的《编辑字典计划》在1949年4月27日写成,所以,魏先生把此文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的时间当在1949年初夏。第二,萧家霖先生未参与《编辑字典计划》的讨论与写作。另外,由于叶圣陶先生当时在北京,所以,吕叔湘先生提到的叶圣陶先生的"复信",应该是他在收到开明书店的有关信件后,写给开明书店的答复信件。文中提到,在1948年冬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吕先生正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工作[5]。所以,魏先生把《编辑字典计划》寄到上海开明书店的情况是确定无疑的。
众所周知,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明书店编辑业务方面的领导者是叶圣陶先生。叶先生在1948年年底,即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安排下,由上海先到香港,再辗转到达了北京(当时称为北平),时间是在1949年3月18日[6]。
叶先生既然是开明书店的编辑业务负责人,那么魏先生何以不在北京当面交这份材料,却要寄到上海的开明书店呢?
笔者见到这样一份材料:叶圣陶先生等文化名人从香港出发到北平时,著名学者宋云彬先生是与叶先生一起来的;到北平之后,他与叶先生一起参加了许多政治、文化方面的公开活动。宋云彬先生1949年3月26日的日记记载,在叶先生到达北平的第九天,魏建功先生等的《编辑字典计划》还未写成时,魏先生与叶先生就曾经会面了:
“中午偕圣陶夫妇暨振铎、彬然同赴北大俞平伯等之宴。列名具柬邀请者凡十七人,俞平伯、王重民、朱光潜、金克木、郑天挺、林庚、吴晓铃、季羡林、沈从文、顾小刚、向达、孙楷第、黄文弼、魏建功、杨人楩、韩寿堂、赵万里。地点为孑民纪念堂。”[7]
这次参与邀请叶圣陶等先生的北大学者,在魏建功先生之外,还有参加《编辑字典计划》讨论的金克木、吴晓铃两位学者。这说明,作者方与出版方早就见过面了。
叶先生1949年5月6日的日记说:“魏建功来访,谈渠与同气四人计划开明编字典之事。其字典注重于活的语言,以声音为纲,一反从前以字形为纲之办法,的是创新。有计划书甚长,各点余大多同意。唯须用工作人员至少五人,又有五位主编者(2)引者按:即参加《编辑字典计划》讨论的魏先生等五位学者。,历时又恐不会甚暂,如此规模,是否为开明所能胜,余未敢断言。此须俟上海解放之后,南北通信商量,始可有所决定也。”[8]
这样看来,叶先生虽然是开明书店编辑业务的负责人,但毕竟不是开明书店的主政者;所以叶先生嘱魏先生把《编辑字典计划》一稿寄往上海的开明书店。在1949年5月6日魏先生把《编辑字典计划》的文稿交给叶先生以前,由于两人会面是在公众场合,故未及专门讨论这个选题。正是由于这个编纂新型汉语小字典的选题,使得叶圣陶先生这位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与魏建功先生这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辞书学家通力合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迫切需要一部高质量的语文小辞书的时候,共同领导编纂了这部对国家和民族作出多方面贡献的《新华字典》。
二、审慎选择:《编辑字典计划》最终成为《新华字典》的编纂方案
新华辞书社在1950年8月成立以后,所编写的第一部字典自然称为“新华字典”。但这部字典以什么样的方案编写,却需要仔细研究。当时,叶圣陶先生面临魏建功等先生的方案与吕叔湘等先生的方案的选择。
1.魏建功等先生的方案
魏建功等先生的方案即《编辑字典计划》。这一方案固然很好,但叶先生最初并没有考虑采用。如上文所引述的,叶先生对这个设想的评价是“的是创新”,又认为,“如此规模,是否为开明所能胜,余未敢断言”[8]。叶先生虽然对这一编写计划给予称赞,但又考虑到现实的困难,比较谨慎:字典规模比较大,投入的人力(包括编写者和出版社编辑力量)太多,一时难以做好编辑加工和出版工作。
2.吕叔湘等先生的方案
吕叔湘等先生的方案源自20世纪40年代开明书店的学者们关于语文小辞书编纂的多年努力。
开明书店是一家出版社,所以他们编纂语文小辞书首先要考虑企业盈利的问题;但是作为严谨的学者,他们又很重视辞书的质量。这也是开明书店在20世纪40年代一再讨论辞书编纂问题,却始终拿不出定稿的原因。以上这两方面的考虑,在叶圣陶先生1947年8月11日日记中有明确反映:
“上午,谈小学字典之编辑。营业方面之同事恒言我店无字典,最为缺憾。现届出版界困窘之际,确需一繁销之书,以维店运。因决议不谈理想,务求必成,且速成,但望能比人家较好,即可。我店谈字典已久,皆以理想过高,视人家之作均不佳,而如何方佳亦实难言,遂迁延下来。……因议别作小字典,以今日为开始讨论之期。希望一年而后,即能出版应市。”[9]209
自1947年8月11日起,叶先生在8月12日、15日、16日、18日、23日、25日的日记多次提及编纂小字典的事情,包括讨论字典样张和编写原则等,决定自8月25日起着手编写[9]212。此后,至迟在1948年2月24日,吕叔湘先生参与了这一编写工作[9]261。这部小字典后来是由吕叔湘先生主持编纂、完成初稿的。(3)吕叔湘先生在1948年12月到上海的开明书店工作。叶圣陶先生1948年12月21日日记:“叔湘来信,言渠定于后日挈眷迁沪,即住我店宿舍。”(《叶圣陶集》第2版,第21卷,341页)1949年1月4日开明书店部分学者还为欢迎吕叔湘先生等事宜举行了小型宴会。(《叶圣陶集》第2版,第21卷,345页)
3.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等多位学者关于两个方案的讨论
叶先生最初希望采用吕先生等编纂的小字典的初稿作为底稿,进一步加工,编成新华辞书社的第一部字典。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叶先生当时急于出版新华辞书社的第一部辞书,以尽快满足社会上对高质量语文辞书的需求。《编辑字典计划》规模较大,编写难度也大。吕先生等的小字典初稿是一个现成的成果,可以大为节省编纂出版的时间。其次,这是基于对吕先生学识的充分信任和肯定。第三,也与叶先生对《编辑字典计划》在辞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最初没有充分认识有关。叶先生1950年7月27日的日记说:
“开座谈会讨论小字典如何编辑。建功与其所邀来共事者三人来,又有叔湘,此外我署同人五人。小字典拟以叔湘在开明设计而未经修订之一份字典初稿作底子,此是余数月前之设想。究竟如何,待建功诸君细看后决定,但今日初步一谈,似可成为事实。”[10]120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个初稿不成熟。刘庆隆先生《〈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提及这件事:“开始时,叶先生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遂决定另行编写。”[11]404由此,才决定以《编辑字典计划》为编纂纲要编写《新华字典》[12]317-318。
从以上编写方针的确定过程可以看到,叶圣陶先生等多位学者的态度是极为审慎的。
三、精益求精:《新华字典》第一版出版方面的工作
《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相关出版工作情况,有关文献资料很少。本文以叶圣陶先生日记为线索,同时结合有关回忆资料,略作考述。
一般来说,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两方面:第一,编辑加工,就《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纂来说,包括字典全部内容(正文、附录、凡例、检字表等)的编写、修改、定稿,之后发稿。第二,出版工作,包括版式设计、排版、校对、印制、广告宣传等。但是,由于《新华字典》第一版需要尽快出版,所以有些编辑方面的工作是在正文发稿后才进行的。比如,《新华字典》第一版的凡例、检字表等内容,就是在《新华字典》正文发排后才着手编写的,是与《新华字典》的出版工作同步进行的。
1.凡 例
《新华字典》第一版的凡例是魏建功先生起草的。萧家霖先生参与了讨论,叶圣陶先生修改、定稿。叶先生1953年10月12日[13]40、10月13日[13]41的日记对此做了记述。
2.检索方法
检索方便是中国现代辞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关于《新华字典》第一版的检索问题,叶先生日记主要有这样的记录:
1953年8月22日:“晨间看建功、家霖二位所编之检字表,将刊于字典者。缘字典按声音次第排列,故须附检字表,供不谙拼音字母之人翻阅。此检字表分点、划、直、撇四类,每类之字之排列,亦依笔顺之点、划、直、撇为序,翻检手续麻烦;又以仍顾及部首,属彼属此不易遽定,须碰机会。说明亦甚噜苏,恐为读者所不耐。”[13]20
8月28日:“至建功、家霖所,商量字典检字表之编排问题。二君因余提出问题,谓所定编排法不便,已商量改进办法。大致仍依笔形按笔顺次第编排,唯一律从左上算起,取消以前间或从右上算起之办法。其易于致惑者,则取互见之办法。谈一时许,余觉较胜于前,因请再作研究,务以便于读者为主。建功谓我辈固觉其不太方便,初识文字者习染不深,殆无所谓。余谓恐未必然。”[13]22
第一版检字表的编制工作,以魏、萧两位的意见为主,参考叶先生的意见做了修改。这一版的检字表虽然过于迁就实用性,以至出现一些问题;但是编者不照搬《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中国古代字典的传统部首法,力求探索一个便于初学者使用的新的检索方法,这是令人钦佩和称赞的。
与《新华字典》检索方法相关的是字典正文的排序方法问题。第一版后确定按音序排列正文。对这个问题,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先生也曾参与讨论。叶先生1952年5月19日日记对此做了记述[10]323-324。由此可见《新华字典》在编纂过程中广受关注和重视。
3.出版工作
由于《新华字典》编纂时间历时较久,出书时间又很急,所以在出版方面的工作压力很大。
(1)版式设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版部在编辑部正式发稿前,预先参与到工作中,排出了样张。见叶先生1953年6月15日[10]459、6月29日的日记[10]462。至1953年7月16日,人教社出版部仍然在做版式设计工作。当时为铅排,字典插图又多,排版难度较大。出版部特邀请印刷厂排版工人与出版社相关方面人员参与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见叶先生1953年7月16日、17日的日记[13]8。在1953年7月16日之后不久,字典稿发到印刷厂,印刷厂正式开始排版工作。见叶先生1953年7月27日日记[13]12。
(2)校对。《新华字典》第一版是在1953年10月完成排版工作的。见叶先生1953年10月9日日记[13]40。一般来说,图书编辑不参与校对工作。从这条日记看,《新华字典》的编写者也参与了部分校对方面的工作。这体现了《新华字典》编者们对字典质量的高度重视。
关于版权页上排版时间的标注,国内出版社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标注最初完成排版工作(即第一次校样)的时间,第二种是标注排版工作最终完成(即开始印刷前)的时间。以《新华字典》为例,前者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对1953年版的标注:1953年10月原版,1953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后者如商务印书馆对1957年版(即“新一版”)的标注:1957年6月商务新一版,1957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新华字典》1953年版第一次印刷本的100万册[13]72(4)按照版权页标注,《新华字典》第一版共印刷4次:1953年12月印10万册,1954年1月印20万册,1954年2月又印两次,各10万册。但是叶圣陶先生1954年1月22日的日记记载,《新华字典》第一版在当时已印300万册,还有200万册待印。由此可知,《新华字典》第一版第一次即印了100万册,总共印了500万册。的排版、校对、印刷工作历时3个多月。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困难阶段,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前辈、后曾任人教社出版部副主任的方国楣先生,在他所撰《新中国第一本字典——〈新华字典〉首版印装记》[14]记述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校对情况。这是笔者所见唯一一份关于《新华字典》第一版校对工作的资料。尤其难得的是这份资料来自当事人的回忆,更显珍贵。兹略引述如下:
《新华字典》第一版的校对工作由方国楣先生承担。方先生在人教社原本不从事校对工作,由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文汇报》做过一年半的校对工作,所以被人教社领导委以校对《新华字典》的重任。人教社出版部吉少甫主任向他强调:“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字典”;叶圣陶社长则指出:“字典是典范性书籍,不能有丝毫差错。”[14]
由此可见人教社对这一工作的重视。第一版的校对工作共进行四次:前三次为校对,第四次为核红。此外,人教社校对科对核红样的质量作了抽查,《新华字典》的编者也至少审读了第一份校样。
第一次校对时,前300页校样由方先生和人教社校对科的另一位老师各校对一遍;其后的500多页校样,以及后三次校对工作均由方先生一人完成。此后,出版部吉少甫主任又请校对科的校对专家于凤池先生以通读方式抽查了《新华字典》的300页校样(占全书1/3强),内容涉及正文和附录,未发现问题。一部重点书的校对工作几乎全部由一人承担,可见校对者的工作能力之强。这也是中国现代辞书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3)《新华字典》的宣传材料。一般来说,图书的宣传工作是在图书临近出版时才提上日程的。叶圣陶先生1953年7月15日日记:“建功、家霖草成一关于字典之宣传件,嘱余看之。为逐句推敲,加以润饰。”[13]7由此看来,《新华字典》的宣传工作是提早准备的。这可能与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图书征订工作效率较低有关。
(4)挖改。《新华字典》第一版对“国民”一词的注释,在最初印成书的时候是错误的,编者发现后即做了改正。叶圣陶先生1954年1月21日、22日两天的日记[13]71-72有较为详细的记录。笔者曾撰文[15]对此做了考述,不赘。
四、《新华字典》第一版的审读专家
笔者曾撰文[1]介绍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三位审读专家:吕叔湘、张中行、恽逸群先生。从叶先生日记看,至少还有以下几位学者参与了审读工作。
第一位是朱文叔先生。朱先生是著名学者,自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即任社务委员会成员,1954年任人教社副总编辑。他曾应邀担任《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审订委员会委员。
叶先生的日记有这样两条:
1953年2月24日:“与辞书室同人共谈,外加文叔、黎季纯二人。”[10]425
1953年3月28日:“文叔来谈字典,渠作一‘破’字条与余商量。”[10]436
可见朱先生至少参与了《新华字典》最后一稿的审改工作。
第二位是黎锦纾先生。黎先生字季纯,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教授的弟弟,在20世纪40年代已是平民教育家。他在人教社语文组工作,曾与朱文叔先生一起编辑小学语文课本。上文所引叶先生日记提及他与朱文叔先生一起参加辞书编辑室的审改讨论会,可见他也参与了一部分工作。从黎先生的学识和所从事的工作看,他参与《新华字典》的审改工作显然是很合适的。
第三位是金灿然先生。金先生自1950年人教社成立即任副总编辑,后又兼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局副局长,是叶先生的得力助手。叶先生日记提到,金先生也参与了一些与辞书编辑室有关的工作。其中,可以直接看出与《新华字典》的业务工作有关的,是这样两条:
1952年7月11日:“晨间建功来谈辞书编辑室事,邀灿然共谈。灿然谓观今次印发之一部分字典稿,仍嫌对象不明确,究竟供何等人翻阅,解决何等人之疑难,殊无所主。体例亦未明定,何取何舍,孰详孰略,皆以意为之,殊无准绳。渠意先就印发之稿修订若干条,共同商定,作为标准,供随后修改定稿之参考。”[10]340-341
1954年1月21日:“作书致建功家霖,告以灿然自字典中看出毛病,颇严重,宜急谋补救,作勘误。”[13]73
前者是《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第二稿修改过程中的事情,叶先生认为这一建议有道理,但限于当时的人力条件,没有实行;后者是在《新华字典》第一版正式发行后,金先生发现书内关于“国民”注释的政治错误,于是《新华字典》的编者们及时做了修改[15]。金先生对《新华字典》也是有重要贡献的。
第四位是傅彬然先生。傅先生也是文化名人,当年与叶先生等一起从香港出发来到北平,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后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叶先生日记提到:
1952年7月17日:“晨间彬然来谈小字典事。”[10]343
1953年1月26日:“饭后偕彬然同至社中,彼访萧家霖,谈其对《新华字典》之评议。”[10]411
由此可见,傅先生参与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两次修改稿的部分审改工作。
另外,还有王力先生和辛安亭先生。
关于王力先生,刘庆隆先生说:《新华字典》的编者们“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意见。还分别开了一些座谈会……王力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还单独邀请王先生座谈。”[11]405时间是在1951年11月5日[10]246。显然,王先生曾经审读了《新华字典》的部分初稿。
关于辛安亭先生,叶圣陶先生1953年1月19日的日记:“余又为安亭言,字典总觉拿不出去,尚须修改。渠言当与字典室同人开会商之。昨日邀请可为字典之读者对象者十数人开会,彼辈于字典之评论亦有可采云云。”[10]408看来主持人教社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辛安亭先生参与了《新华字典》定稿前的讨论会,应该审读了部分稿件。
由于叶先生日记只是记录了事情的大略,加上叶先生的日记现在只有节选本出版,所以我们还不能进一步知道以上几位学者对《新华字典》的具体审读情况;但是他们显然不仅仅是做了上文提到的这些工作,贡献应该更多。
此外,由于资料有限,我们还不知道更多参与审读工作的学者。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郭戈先生的《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70周年》是一篇关于新华辞书社的最为权威的论文,我们看到,刘御、王泗原、隋树森、王微、蔡超尘、孙功炎等学者也审读过《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稿件[16]。限于篇幅和研究的侧重点,文内未涉及相关资料。
五、急读者之所急:超常规出版《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修订本
《新华字典》第一版(版权页作“原版”)出版于1953年12月,第二版(版权页作“第一版”)出版于1954年11月。两个版本的第一次印刷本的出版时间相距不到1年,违背了辞书的修订出版规律,显然是有特殊原因的。以下谈两个问题。
1.叶圣陶先生日记所记载的第一版修订情况
叶先生1954年7月2日日记有一则关于《新华字典》1954年版的珍贵材料:

这条日记反映了以下几个情况:
第一,《新华字典》第一版(1953年版)的总印数500万册[13]72在半年内即大致销售出,看来是很受读者欢迎的。第二,叶先生对第一版的质量不够满意。第三,在第一版出版不到一年即推出第二版(1954年版),改动了正文的排列顺序,这是应读者方面的要求。第四,第二版在对第一版做了一些增补、修改以外,还改动了正文排列顺序与检字表。其中,检字表对传统部首的改动、采用“多开门”的方法,这是《新华字典》在实用性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反映了叶圣陶先生学术性与实用性兼顾的远见卓识。第五,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在1954年7月初才启动(当然,有些增补工作应该是此前做的),至同年8月已完成第一次校样的排版工作(《新华字典》1954年版的版权页作“1954年8月第一版,1954年11月第一次印刷”),这样的工作效率在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很高的。第六,这一修订工作由魏建功、恽逸群两位先生负责终审。
2.《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修订原因
关于《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修订原因,有三位学者的4份材料提及,内容略有不同:
(1)叶圣陶先生日记的说法。叶先生上述日记提到的原因是:“非北方话地区反映,以音序排列实难检查。”[13]123*
(2)刘庆隆、方国楣先生的说法。关于《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修订原因,刘庆隆、方国楣两位先生也曾撰文提到。
刘先生《〈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说:“音序本编就后,考虑到方言地区读者对音序不熟,使用困难,就又着手编写部首排列本,听到方言地区的新华书店反映的意见后,就加快了编写进度,1954年春完稿,1954年8月出版。”[11]407-408(5)刘庆隆先生关于《新华字典》1954年版的出版时间的叙述略为笼统,1954年8月为最初完成排版工作的时间,出版时间在1954年11月。刘先生《〈新华字典〉编写修订的历程》说:“音序本出版后,方言地区读者反映,不熟悉普通话,音序排列检查不便。因此,议定另编部首本。”[17]这两篇文章关于《新华字典》第二版(1954年版)的编写动因不同。前者是说,编者们原本已估计到方言地区读者不习惯1953年版正文的音序排列方式等检索方法,所以早已着手编写1954年版,此书于1954年春完稿。后者是说,编者们在得到读者的反馈意见以后,才开始编写1954年版。
方先生《新中国第一本字典》也涉及这个问题。文章说:“字典出版后,不断接到读者来信和书店反映,主要对音序排列还不习惯和对笔形部首检字表提出各种意见,为此,领导上决定再出部首排列本。”[14]
通过比较上述资料可知,《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修订工作,是由于南方读者不适应第一版的正文排列和索引检索方式,临时启动的。这个工作原本未列入新华辞书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1954年度工作计划,至少未在第一版刚出版时即启动这个项目,因为那样不符合辞书的修订周期规律。另外,方国楣先生上述文章以及刘庆隆先生《〈新华字典〉编写修订的历程》的说法,与叶圣陶先生的日记记录也大致符合。由此可见,《新华字典》的编者与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以读者利益为重,急读者之所急,根据读者的反馈意见,及时启动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修订与出版工作。
六、结 语
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编纂新型汉语小字典的学术研究与编纂实践,至1953年12月《新华字典》第一版正式出版,暂告一段落。以叶圣陶、魏建功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希望通过编纂辞书、振兴教育,为祖国做贡献的旧时代的学者,通过这短短数年的《新华字典》编纂实践,思想认识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圣陶先生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魏建功先生应邀担任编审局下属新华辞书社社长。作为国家出版事业领导人之一的叶圣陶先生,与作为国家辞书编纂机构领导人之一的魏建功先生,他们在领导编纂《新华字典》的过程中,对于编纂新型汉语小辞书的目的、任务和意义有了更高的认识。
以往魏建功先生等五位学者的《编辑字典计划》是一份纯学术的辞书编纂规划,叶圣陶、吕叔湘等开明书店学者们的小字典编纂计划虽然有商业经营的目的,但也是以较高的编纂质量为前提的。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这样一部学者们心目中理想的、新型的汉语小字典,因为由国家辞书编纂机构编纂,其编纂意义已从学者们自发的为普及文化教育服务的初衷,上升到国家高度,旨在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新华字典》在编纂、出版过程中的许多曲折经历、许多琐碎的细节才得到合理的诠释:《新华字典》的编纂已属国家行为,尽管它作为中国现代辞书史某种意义上的第一部现代汉语小字典,容许存在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叶圣陶先生等学者对它的编纂与出版工作的要求,标准之高、范围之广,已达到同类辞书难以企及的高度。正因为这样,《新华字典》第一版才会有较高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实用性,才会经过不断修订,成为现代汉语小字典的典范之作,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