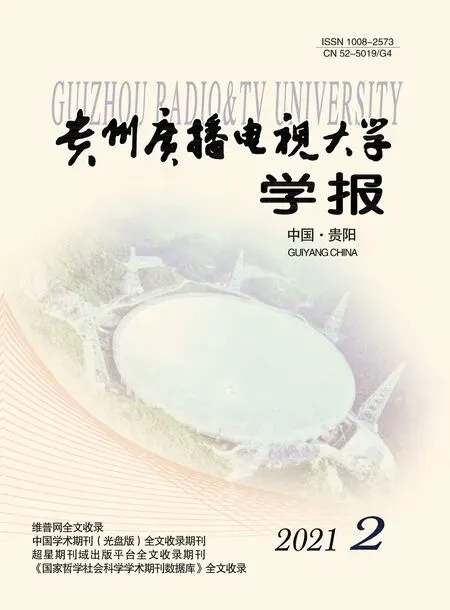论黎渊诗的思想内容及其认识价值
黎 洌
(遵义师范学院 遵义 563002)
黎渊的诗,揭示了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在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并且具备一定的现代性视野后的矛盾心态。他的作品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参照,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态,昭示了沙滩文人的文化坚守。因而,研究黎渊的诗词创作,对探寻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社会转型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化态度和思考,探寻曾蜚声海内的沙滩文化走向衰落的原因,均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黎渊简介及存诗概况
黎渊(1879—1935),字伯颜,黎庶昌的大哥黎庶焘的孙子,其父黎尹融,光绪己卯科举人,庚辰科进士,任吉林农安县知县。黎渊幼时受黎氏家学的影响和教育,聪慧勤奋,清光绪丙申年(1896年)以古学第一入泮(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利用四川留学名额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赴日官费留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毕业并取得优等文凭,之后继续在该大学高等研究科就读,专研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等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光绪朝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奉旨本日学部带领引见之考验游学毕业生陈锦涛着赏给法政科进士……黎渊赏给法政科举人……”[1]5575。严修将黎渊推荐给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时,正值袁世凯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黎渊便被委任为首任监督。作为中国第一所法政学校,北洋法政学堂“自创办起,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2]31,造就了一批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钊等。黎渊后任资政院秘书官,直隶总督署文案。1912年至1916年,黎渊先后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参事等职。由此可见,清末民初,黎渊作为海归活跃于政坛。惜乎黎渊这一时期的诗稿全部遗失,不能从中看到他的政治理念、办学思想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感受。1916年夏,黎渊辞官,谢绝各种政治活动,专心读书、作诗,仅靠少量积蓄生存,在此期间也应邀在松坡图书馆做过短期的编目。1930年,生活难以为继,黎渊受苏象乾邀请“再为冯妇”,出任国民政府河北省财政处秘书,几个月后辞职。“幽居成谢客”,“闭户愁孤坐,支颐入苦吟”[3]337,是黎渊后期生活的写照。最后,他在坚守孤洁中贫困至死,死后竟无钱安葬。
黎渊的诗现存539首,早期的《山居集》《吴帆集》《留东集》共收诗267首,为家居与赴日留学时所作,编为《明致堂诗歌》卷一至卷四。晚期诗歌编为《明致堂诗歌》卷五、卷八,其中,《人海集三》收诗132首,《帡翠轩吟稿》收诗96首,《春蚕集》收诗11首,《鸠寄庐集》收诗29首,而1930年后的《鹪巢集》只收4首,明显是没有整理完成的。缺失《明致堂诗歌》卷六、卷七及《人海集一》《人海集二》,即1919年至1922年、1924年至1928年的诗。黎渊所写的诗,多为闲淡散居、贫穷孤寂生活的写照,以及对时局的伤痛失望。从这一时期的诗中,可以窥见到清末民初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坚守及其与转型期社会的格格不入。
二、传统与现代的艰难抉择
黎渊的诗,展示了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一个传统士子与新型知识分子互斥互融的心路历程。黎渊从小受儒家文化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具有传统士子的孤高气节,而留学日本的经历,特别是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由一个蕞尔小国一跃为亚洲列强,又使他自觉推崇西学。黎渊虽然接受了现代教育,法学学士的履历使他具有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可能,但是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使他并没有如鲁迅、胡适等人一般以西学至上、与传统决裂,而是始终游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因而,建功立业与不愿与时合流的彷徨、矛盾、痛苦以及由此带来的清贫缠绕他的一生。“髫龄随宦出榆关,童试名蜚里社间。岂意抡才停棘院,遂教求学向蓬山。丝纶忝附参知席,珂佩曾趋侍从班。今日市朝随劫换,一椽琴鹤寄尘圜。自注:民国曾任参政院参政兼大总统府秘书”[3]414,即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写照,也反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和矛盾心态。
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青年时期的黎渊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性格平和,重视亲情,渴望建功立业,拯救国难。因此,他外出留学,“此行不为求仙药,要觅奇方起国孱”[3]214,以满腔的热诚到日本学取新的治国良方。
学成归国,黎渊渴望将所学报效祖国,“近来悟得安心诀,一任同胞犬马呼”[3]331。他因良好的学习成绩得到袁世凯依重,被委任为“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并开始运用寻找到的“奇方”施展抱负,“推行北洋新政,而学科就是讲法求治。所以学堂的教师、受业学生都注重学术的研讨、关心国家的命运”[4]。他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北洋法政学堂开设了“《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统计等,多达30余科”[2]31。“从开创起就形成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很少门户之见。学校除聘请日籍教师和留日学子任教外,共产党员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均曾在该校任教授或秘书、主任等职。这种严谨的办学形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北洋法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颇具影响。”[2]32正如北洋法政学堂首届毕业生李大钊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的演讲中所说:“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2]32在黎渊的诗中,对其“储才”效能颇为自豪,特别提及了李大钊、白兴亚、夏敬民等门人,“崔嵬黉舍枕河湄,往迹重寻意尚疑。劫后楼台新市改,眼中冠服旧朝移。百年已着储才效,再到还增化鹤悲。莫怪种花人易老,校内外花木,悉余当年所手植。门前桃李见孙枝。门人白兴亚、李守常、夏敬民诸人皆有声于时,门下受业者甚众,故云。”[3]389正是北洋法政学堂开放的环境,李大钊等人才能在此接受民主、自由等思想的教育,形成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后,黎渊又在北洋政府担任了一系列职务,[5]512获得了“参知席”,进入了“侍从班”,“杯酒论交湖海士,布衣平揖相公庭”[3]357。一系列的要职接踵而至,黎渊心中是充满了喜悦和得意的,不仅作为显宦实现了其“早岁志封侯”[3]285的愿望,而且能将所学所思运用于实践中。
然而,1912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是中国人行走在民主政治探索实践中最艰难的社会转型期,也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化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党纷争、倾轧频仍常常让人无所适从、难以选择,也最考验人格气节。“余生羞作国亡奴”[3]331,黎渊虽然希望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是抛弃民主与共和,恢复帝制,因此,反对袁世凯称帝。然而,他从小接受的忠君爱国、从一而终等传统文化思想,使他不可能放下袁世凯对他的知遇之恩,也无力阻止其复辟行为。“日永槐厅留蟻梦,雨荒苔砌篆虫书。贫交四海谁相忆,狡兔三窟我自疏。廿载尘踪淹薄宦,题桥归志负相如。”[3]337传统士子的心结,使黎渊特别注重传统文人人格情操的坚守。1915年冬,任司法部次长的好友江庸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颇多非议,并抨击其摧残国家,让袁世凯深感不悦,江庸即呈辞职书,避居西山。黎渊对此非常赞赏:“谏书甫上谢朝衣,谈笑辞官世所稀……卫道岂惟全素志,移忠恰好恋春晖。”[3]354江庸所卫之道,显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民主共和之道,他们所效忠的是国家和民族,故黎渊感慨:“愧我依违百僚底,几回循诵重歔欷”[3]354。早在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时,他所依重的黎渊就预感到危机重重,“帝制事起,屏迹者累月”[3]361。黎渊对政坛的瞬息万变深感惶恐不安,于是在1916年5月便避居天津。袁世凯去世后,面对纷争的政坛,黎渊认为“大事尽为朋党误”[3]374,对政治失望至极,他不会“狡兔三窟”,也不愿左右逢源,更不愿改头换面投靠新的权贵,于是选择了退出政坛。退职后,作为法学学士和政法学堂首任监督的黎渊,没有利用他的法学知识和门生故旧四处干营,以致贫困终老。
袁世凯逝世后的北洋政府分崩离析,皖系、直系、奉系的勾心斗角,南北方的对峙,使得中国进入了军阀时代。各地军阀割据一方,城头屡变大王旗,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黎元洪、张作霖走马灯似的串霸政坛,救国救民的初衷遭遇篡改,民主宪政逐步萎缩。面对四分五裂、军阀争权夺利的现实,黎渊更是忧虑:“‘朝野愁闻党锢争’[3]341,‘乡思莼鲈秋又老,党争蛮触世堪怜。神州此日风云恶,谁恤同根煮豆然’[3]339”。黎渊虽已退出政坛,但对军阀只顾自身利益、罔顾百姓的做法十分反感,“吁嗟世事今反常,四维灭绝三纲亡。载胥天下入禽兽,坐见毛羽沦冠裳”[3]342。他对这样的政治时局深感失望:“方今国事艰,群流竞奔走。吾侪习疏放,理合终瓮牖。”[3]341为此,他甚至反对自己的女儿黎寿萱嫁给北洋军将领李炳之的儿子李恭武,不愿参与任何政治集团,选择冷眼看世界,读书、写诗,追求“诗书文章三不朽”[3]337,希望像陶渊明一样躲进桃花源,笑傲江湖,独善其身。
从表面上看,黎渊的诗较少记录时事,也很少表明其政治倾向,但感时伤世是诗歌的主要功能之一,并且诗歌大都“言为心声”,因此,在其诗中,仍然能看到对时局的反映。特别是后期,远离政治的黎渊因为生活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不可能对时事完全充耳不闻,更不可能心如止水,因此,他的诗在吟风弄月、人世感概中仍然反映了时势变化,特别是官场的纷争纠葛,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基本的政治态度。“风雨海内争纷日,棋局长安劫急时。谁识绿荫窗下客,焚香自读剑南诗。”[3]3451917年的中德绝交,总统与总理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斗争激烈,引发了“府院之争”,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卷入争论,各执一词。实际上,是保持中立还是参战,不过是亲日派与亲美派的内部争斗,是争权夺利的结果。曾经厕身其间的黎渊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他已远离政坛,赋闲在家,地位的悬殊和身份的差异使他们恍如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争权结党、趋名逐利的纠葛已与他毫无关涉,面对仍身居高位的朋辈纷纷奔走,而他自已则蛰居斗室,诵诗自遣,看云卷云舒,使其对命运与境况的瞬息万变和政客们的蝇营狗苟不禁哑然失笑,不由感叹“沉渊谁返鲁阳戈,国手棋如末劫何。求治嗟同缘木妄,汰官笑比拣金苛。生涯官食悲强弩,市府泉荒困掘罗。莫叹长安居匪易,故园松菊亦无多”[3]345。1922年,国内政局动荡,内阁总理四易其人,直奉大战爆发,政府缺乏鲁阳式的英雄,衮衮诸公皆不能挽救混乱的时局。天下扰乱,哪有静土?兵荒马乱,故园松菊还馀几何?有节操的人还有几个?故读剑南,黎渊表达出陆游一般的悲愤。在他看来,“异族只今成逼处,豆萁何苦日相仇”[3]345,国家沦入列强的铁蹄,而军阀却互相残杀,专注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和朋党才是真正的民国罪人。
黎渊的诗没有具体对某年某月发生的事进行直白地记录,而是将事件寓于回忆、感叹以及一些历史典故之中,使他的诗看似平淡却意义深藏。与固守乡间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在西化后的日本留学数年的黎渊,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视野,但看得清未必做得到。黎渊虽然没有参加到革命党人之中,但是也没有像他周围活跃着的一大批留日熟识那样成为汉奸。他宁愿清贫至死也不去追逐名利,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体现得淋漓尽致,清晰地展现了转型期传统文人的风骨和矛盾,体现了传统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的许多共性,表现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分化。
三、文化和气节的痛苦坚守
黎渊深受沙滩文化的影响,其入黔二世祖黎怀仁所立家训:“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帅弟子,在朝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党不可一日不以正直化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6]1058。二世黎怀智于明亡,伤亡国之痛,弃家入佛,三世黎民忻立下口头族规“三世不应清朝科举”。黎氏家学要求后人要追求严于律己、自觉向善、讲求礼法、刻苦自励的精神,能守大节、顾大义,注重气节、重视品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讲求民族气节[7]99。
黎渊身处于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军阀割据,政局变动频繁,固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多重出路,但也极为考验一个士人的气节。作为留日的法学学士,黎渊如果愿意泯灭气节、沆瀣其间,自然可以混得风生水起,但受黎氏家学长期薰陶的他早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不愿随波逐流、追名逐利。
“眼底河山蛮斗触,梦中富贵蚁趋膻。”[3]375“闭门樽俎谢时流,朝土贞元几人在?”[3]374有太多的人在利益诱惑面前丧失了气节,黎渊认为这是传统道德观遭受毁灭后的表现,人没有了底线。黎渊要坚持的便是这个底线,尽管贫病交加,故交旧友多身处高位,但他并不攀龙附凤。当周边的留日熟识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告诫家人:“急进从知勇退难,千古宦游同一辙。吁嗟世事今更艰,版籍中原成割裂。十年归计苦不早,此错真成九州铁。行抛轩冕卧松雪,永抱坚贞守孤洁”[3]345。他希望自己和家人永抱坚贞、永守孤洁,不随波逐流。后来,黎渊的留日熟识和亲朋中有不少人成为汉奸,他却始终坚守孤洁,以致后半生被贫穷、感时伤世纠缠,死后竟无钱安葬。他的弟弟黎迈也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工学学士、四川兵工厂副厂长,多次拒绝日本人和亲朋好友的邀请,甘愿在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当会计,自号“工隐”,绝不当汉奸。
传统文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社会动乱、官场污浊的时候,立德、立功已无可能,洁身自好,立言就成为文人的最佳选择。黎氏家族素来强调诗礼传家,黎渊的伯祖黎兆勋、祖父黎庶焘在仕途断绝之后,都追求以诗立言。与传统士人一样,出仕与归隐始终是困扰黎渊的矛盾心理。早年在赴日留学途中,他就发出了“出山纵有为霖志,不待云归兴已阑”[3]340的感叹;到晚年辞官归隐之时,他更是觉得“青衫长谢故山薇,十九年来万事非。惭愧风尘旧司马,题桥虚说锦衣归”[3]391。面对当时社会的动荡,黎渊只能责怪自己才庸力穷、无力挽转,“宦拙未成归老计,时危空抱急难心”[3]288,并将“劳劳歌哭寄文章”[3]346,转而追求“诗书文章三不朽”[3]337。他虽然知道“虽云玩物能销志”,但“绝胜朱门挟策回”[3]337,绝不蝇营狗苟。“未偿天下澄清志,且读人间瑰异书。”[3]349他还自我安慰“花间一醉抵封侯”[3]349,希望“老际太平君莫憾,天教穷散以诗传”[3]359。黎渊的人生经历突显了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中,传统文人对文化的选择、适应以及内心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范本价值。
黎渊赞叹同乡丁纶恩的洒脱,“时衰伤道晦,一笑谢缨绶”[3]344,同时也以此自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黎渊越来越感到盛世难再,贫病越发追人,曾经的“友朋”与他交往越来越少,而他也不愿混迹其中。于是,他更注重亲情,更思念淳朴的家乡,不管是姑父刘子贞、堂兄黎直哉、表兄蹇景潜,还是弟弟黎迈、黎丹雘等,都让他特别的牵挂。在“吁嗟世事今更艰,版籍中原成割裂”[3]411的环境中,家乡、亲情成为黎渊唯一的慰藉。然而,这时“亲友往还最密者,如家子甘从兄、蹇仲常舅氏、王星瑞师、李耀庭、邹怀西、申绪五丈、夏子猷、吴小湄、张仙舟诸君,均先后各登鬼录,存者仅季常舅氏、赵尧生丈及江君骥云、张棣生表兄寥寥数人”[3]411,加上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又病逝,“无多亲旧感凋亡,不独人间海变桑。阅世已枯双泪眼,忧生能耐几回肠。深恩师友惭多负,故业田园早就荒。晚景如斯何所恋,唯应长昼一炉香。年来亲族师友中逝世者甚众,近复得陈氏三姑在渝病故之讣,故起句云之”[3]412,他自感成了“五十孤儿”,因此,写于1928年至1930年的《鸠寄庐集》及后面的《鹪巢集》,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不只是黎渊,和他同时期的沙滩诗人黎树、黎梓、黎楷也有相似的感慨。
从黎渊的际遇可以看出,沙滩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沙滩文人的政治选择,特别是文化选择密不可分。沙滩文化本质上是传统儒家文化性质的区域文化,当这种文化与社会转型不相适应时,面对坚守与趋新的抉择,沙滩文人大多选择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从黎怀仁开始,一直延续到黎渊及其以后的黎焕颐等诗人。因此,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与黎渊同时期的沙滩文人,也多在时代的激流中选择退缩固守,毕业于北洋法政学堂的黎楷,40多岁便告老还乡,曾任陕西褒城县长的黎梓选择回乡办私塾,留学日本的工学学士黎迈任职公司会计。正是这种文化坚守,使他们思想固化,他们甚至认为新式学堂背弃传统,不读儒家经典,不教诗赋古文,就不能从精神到文化系统地培育青少年。黎焕頤、黎培仁、黎培义、黎培炎等走出沙滩的黎氏子弟,都是在1949年后才接受的新式学校教育,沙滩的私塾直到1954年黎梓去世才停办。直到1963年,沙滩才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从坚守变为保守,与时代发展的不相适应,造成了沙滩文化在现代的衰落。由此来看,黎渊的诗对我们了解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以及传统文化惯性中的人生悲剧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