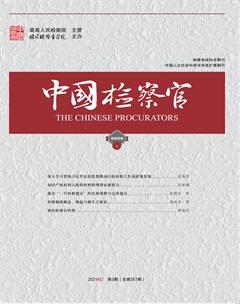检察制度概念、缘起与诞生之新论
杨迎泽
摘 要:中外治国理政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有国必有法,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而法贵在实施,实施贵在执法者,执法者贵在法律监督。因此,在我国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进程中,重新审视认为固有法律监督天性的检察制度及检方至关重要,特别是诸如“中国检察第一书”等检察文献对检察制度概念、缘起与诞生源头追问的回应,也不可小觑。
关键词:检察制度概念 检察制度缘起 检察制度诞生
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中央党校举行的题为《强化新时代法律监督 共同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形势与任务报告会上,再次[1]追问:检察制度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中国检察制度从哪里来,向哪里去……[2]回应此等追问,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难免有些尴尬。究其原因:一因此等追问绝不亚于“世界检察官之问”——“所有奥地利(包括其他国家地区检察官——笔者注,下同)检察官都不断地问一个‘蠢问题:我是谁?我的位置在哪里?”[3]二因“检察”一词内涵的法律监督天性与外延的多元性,从而易将其与“法律监督”“检察法律监督”“检察官”等相关制度混淆。三因检察制度不像警察、审判制度与国俱来,而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年5月5日-1799年11月9日)胜利之后的产物,资历尚浅。四因衡量检察制度确立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五因中国检方未解世界检察官之问,又添“九落九起”[4]余悸……
韦编三绝并死磕“检察故纸堆”之后,立足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检察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国检察第一书”[5](以下简称“第一书”)的证据材料和立论,跳出检察制度依附刑事诉讼特别是刑事公诉制度而生的传统或主流论断(以下简称“依附论断”),重新探究检察制度特别是其概念、缘起、诞生并回应上述追问,也不失为一种逼近检察制度设计初衷蓝图的全新路径。从而坚持好发展好传承好完善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唤醒并发挥其在捍卫践行全面依法治国伟大战略布局中的法律监督天性。
一、检察制度的概念
何谓检察制度?迄今见仁见智。郑言的《检察制度》[6]及熊元翰的《检察制度》 [7]皆认为:“检察制度者,即检察厅之组织及其权限与关于实施检察事务之一切规则是也。”这与我国当前有关检察制度的主流定义概念——“检察制度是关于检察机关的制度”[8],不谋而合。但欠妥:检察制度只管辖治理(以下统称“管治”)检察机关,而不管治检察制度的内设机构、检察人员尤其是检察官的权责能行吗?肯定不行。因为与其他国家制度一样,检察制度也是管治官吏(即检方)及其公权(即检察权)的。而如何给检察制度下一个科学合理的概念?应立足检察制度构成的“三支柱”:
支柱之一,检察制度的“种子”——检察法。检察法即检察法律的简称,是指管治检方权力或行为(以下统称“权力”)之行为规范的总称。[9]因为没有检察法就没有检察制度,有什么样的检察法就会滋长出什么样的检察制度。这一点,在我国当下坚持“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的制度、体制改革过程中,[10]法律包括检察法律对制度包括检察制度的架构英灵作用,显得尤为突出。
支柱之二,检察制度的主体——检方。它是指为检察法所管治的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检察人员的统称。因为没有检方就没有检察制度,有检察制度必有检方。比较而言,检察人员特别是检察官对检察制度及其检方、检察权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检察人员特别是检察官使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使检察权由死转活,并得以发挥作用,
支柱之三,检察制度的对象——检察权。亦称检察权责的简称,是指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之职权与检察人员之职责的统称。因为没有检察权,检察法就失去了管治对象,检方也失去了存在意义。而与其他权力一样,人民是检察制度的原始主体,国家是检察制度的基本主体,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是检察制度的职能主体,检察人员特别是检察官则是检察制度的执行主体;比较而言,作为执行主体对检察制度及其检察法、检察权的左右,尤为关键。正是:“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有其人,然后有法;有其法,尤贵有人。”[11]
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作为检察制度架构的“三支柱”关系:检察法是检察制度的“种子”,也是检方及其检察权得以成为检察制度要素的蓝图;检方是检察制度主体和检察权主宰,也是检察法的管治对象;检察权是检察法和检方血肉联系的纽带,也是检方安生立命之本和检察制度的管治对象。另一方面,检察制度是指规范检方及其权力的检察法,在现实中得以实施、名存形无的客观结果。
二、检察制度的缘起
(一)国家、法律、执法者及其监督
毋庸讳言,人类的进化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猿到人的直立行走到可制造劳动工具到剩余劳动产品出现到私有制和阶级产生再到国家及其法律、制度(以下统称“法制”)和执法者出现的过程。[12]进言之,法制与国家孪生。正是:“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13]“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护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暴力机构、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含立法、创设法律监督制度)把持在自己手中”。[14]換言之,有国必有法制;[15]而法制贵在实施,实施贵在执法者,执法者贵在法律监督。正是诚如《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所言:宪法法律和制度也好,法规制度也罢,其生命力权威都在于实施执行;其实施执行都在于人;“我一直讲,‘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6]
另外,古今中外法制(治)实践表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反之“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17]……一言以蔽之,若漠视法制的生命力和权威——实施执行,那么法制(制)本身所固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作用特点,也无从发挥。
此外,为什么说执法者贵在法律监督?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实践证明,一方面,七情六欲是人之本能,也是驱動人每日行动的内在因素。因此,作为固有七情六欲的执法者,在实施执行法制的过程中,就必然出现实施执行得很好、刚刚好和不好亦即违法的可能。另一方面,预防并管治违法的现实办法,就是加强法制:“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18]易言之,“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还要靠制度来保障,让执法司法权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19]而这也为法律监督制度势必存在的历史性、逻辑性、必然性和现实性,埋下了伏笔。因此,法律监督与法律、法律监督制度与法制(治)不仅共存,其实施执行也都贵在执法者身上;否则,国家代表创建法制的初衷目的就无法实现。
(二)公益及其法律监督
何谓公益?迄今仁者见仁。通常认为,它是指公共的利益,包括国家与社会公益两方面;而熊元翰编辑的《检察制度》指出:“何谓公益?有列举于法律者,有例示之者,因各国立法政策不同故也。”
何谓法律监督?迄今智者见智。应作如下理解:一是它与法律孪生,并非我国专有,国外也有;而实践中常见诸如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广义的法律监督,以及诸如检察法律监督及其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检察官(法律)监督等狭义的法律监督,都是它的子集。二是它还有“监督法律”“法律上的监督”“法律之监督”“法律的监督”等别称。三是对俄语词汇“правовой надзор(法律的监督)”的错误直译,也是我国梁柏台、何叔衡、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人士,对列宁法律监督及其检察、监察思想的抽象概括。四是就其概念而言,宏观上指国家、单位、组织和个人、中观上指受国家委托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微观上指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依法对法律适用情况或结果所进行的检查、督促。而现在看来,它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可或缺内容,也是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制度保障。
基于上述界定与国家及其机关、人员势必保护公益本能不难看出,法律监督也理应属于公益范畴。[20]换言之,国家代表依法创设检察制度之初,就赋予了其检方同时捍卫公益及其法律监督的双重使命。其中的法律监督包括广义和狭义法律监督。
(三)为什么要设立检察制度
国家代表创建检察制度的初衷是什么?迄今见智见仁。从微观上说,为防止“侦检审”三方在诉讼尤其刑事诉讼中“一竿子到底”和恣意滥权。为此,“第一书”不仅规定了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审”三方的制约监督,也在“(检察)事务章程及监督”章节中规定了检方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例如,“第一书”不仅主张“初级检察厅及地方检察分厅,若有监督检察官则以其指挥开始预审;若该监督检察官不令开预审,则申报地方检察长受其命令;若无监督检察官,则主任者专断之”,而且郑言笔述的、熊元翰编辑的《检察制度》,张智远、王枢、王炽昌笔述的《检察制度详考》[21]也有“检察官如何参与民事、刑事及行政之指挥、监督,详检察官权限中”记载。
从中观上讲,为维护国家代表的执政地位。例如,张一鹏笔述的《检察讲义》[22]有“检事局因保护关于司法之国家利益而设”,郑言笔述的《检察制度》、张智远等笔述的《检察制度祥考》有“国家不能自己主张利益,故设立检事局以主张国家利益”诸记载。
从宏观上言,为保护社会公益和国家利益亦即公益,包括法律监督本能。例如,“第一书”不仅连篇累牍地阐释为保护公益,国家才创设检察制度及其检方之立论,也有如下不胜枚举之直白:
——就法国言,检察官初为国王之代理者参与诉讼,以图国王之利益为其职务(西历14世纪)。而今则为国家之机关参与民刑事件,以图公益为其职务。
——在近年之法律思想,凡犯罪皆因害国家之公益而成立。害国家之公益,有同时又害私人之私益者,固不待言。故诉权专属之国家,此“公诉”之称所由来也。
——因婚姻、养子缘组(即收养关系成立)、亲子关系、相续(即继承)人废除、隐居、禁治产、准禁治产及失踪事件等人事诉讼,以及破产诉讼与民商事非讼事件、诉讼上之救助均涉及国家公益,因此检察官理应代表国家参与之……
所以,作为被缔造者的检方,其行动志趣理应服从服务于国家代表创设检察制度的上述“三观”初衷。
三、检察制度的诞生
中外检察制度最早诞生于何时何地?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一,“第一书”认为,世界检察制度最早诞生于大陆法系的法国。[23]这与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不约而合。但它究竟诞生于法国的哪一天?不仅“第一书”莫衷一是,迄今最少包括:中世纪(476~1453年)、中古(500-1500年)、12世纪末叶、13世纪中叶、1285-1314年间、1303年3月23日、14世纪、1489年、16世纪、17世纪、1670年、18世纪末大革命时期、1808年等13种具体观点。[24]究其原因,对衡量检察制度确立与否具体标准的界定掌控不一,突出表现为,只强调或看见检察法或者检方中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检察人员之一之二之三的客观存在,却忽视了检察法与检方之全部成员“四要素”的同在。因为,不尽检察法有束之高阁可能,而且若没有检察法检方必有出师无名风险,若没有检察人员特别是检察官,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也难生法人行为的主观能动性。进言之,只有检察法与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检察人员“四要素”的同在,才能推定出检察制度业已确立的结果;只有“四要素”之一之二之三的存在,也不能得出检察制度客观存在的结果。
因此,按“四要素”同在标准推断,世界或大陆法系近现代检察制度最早诞生于1807年1月1日的法国,并以同日施行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为始;此前所谓的检察制度,则可视为法国古代的检察制度或其近现代检察制度的前身。正是:“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创立”。[25]
第二,英美法系检察制度最早诞生于何时何地?《检察制度祥考》、熊元翰编辑的《检察制度》皆认为:“美國各州创设检察官之时代虽不同,然以皆先于英国也。”而我们也认为,基于“四要素”同在标准,英美法系检察制度最早诞生于1870年7月1日的美国,并以1870年6月21日美国《设立司法部法》的颁行为蓝图。此前英美所谓的检察制度,也可视为两国古代的检察制度或其近现代检察制度的前身。
至于英国检察制度诞生于何时?迄今至少也有诸如1311年、1461年、1515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3年、1908年、1985年等7种主张。[26]但我们认为,“英国于1985年(5月25日)通过了新的《犯罪起诉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建立了皇家检察署,设立检察长、首席检察官、检察官……从而改变了英国‘私人起诉主义的传统”,[27]也标志其近现代检察制度的确立。之前所谓的检察制度,则可视为其古代的检察制度或其近现代检察制度的前身。
第三,《检察制度祥考》有言:“检察制度于中国古无闻焉”。那么我国古代有无检察制度?肯定者或本土自生派认为,诸如御史(台)、司直、禁杀戮、禁暴氏、史官及其官署就是我国检察官及其检察机关的前身。否定者或西方引进派认为,我国检察制度是从西方尤其是日本,并借助“和制汉语”引进的,[28]至于引进的具体时间至少有诸如1905年、1906年2月1日、1906年12月27日、1907年2月、1907年12月4日、1909年1月19日等6种主张。[29]
我们持否定观,并依“四要素”同在标准认为,[30]一是我国检察官制度最早诞生于1843年5月4日英国殖民统治的我国香港。二是我国检察制度依次在1847年8月(或1894年4月17日、1852年11月、1862年)、1895年11月17日(或1896年5月1日)、1897年11月14日、1898年3月27日,葡萄牙、日本、日本、德国、俄国开始殖民统治的澳门、辽东半岛、台湾、青岛、辽东半岛初现。三是我国大陆检察制度,最早诞生于1907年3月23日的天津,并以《大理院审判编制法》(1906年12月27日)、《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1907年2月)为“种子”。随后,又经历了清末(1843年5月4日-1912年10月10日)、民国(1912年10月10日-1949年10月1日)和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至今)三大发展阶段。[31]
另外,按照“四要素”同在标准,主流观点和我们都认为,中国人民检察制度最早诞生于1931年11月20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江西瑞金,并以同日颁行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为“母胎”。但也有人认为,它最早诞生于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而这种观点,恰是照搬照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成立(1922年12月30日)前的做法。
此外,伪满洲国检察制度诞生于1936年7月1日的沈阳,并以同日施行的伪满洲国《法院组织法》为基础。
再者,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制度,分始于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
第四,苏联检察制度诞生于何时何地?迄今至少有1917、1922和1922年5月28日的莫斯科三种观点。[32]
根据《苏联法院和检察机关》(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苏联的检察制度》(新华书店1949年版)以及《苏联检察制度史(重要文件汇编)》《苏联和苏俄刑事立法史料汇编(1917-1952)》《苏维埃检察制度(重要文件)》《苏联和苏俄刑事诉讼及法院和检察院组织立法史(1917-1952)》(法律出版社1954、1956、1957、1958年版)等记载描述,一方面,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在废除沙俄检察制度的同时并未马上建立其检察制度,而建立的是其监察制度,并规定由其监察机关及其人员在履行监察职能的同时,代行苏维埃俄国检察权。另一方面,时至1922年5月28日《关于检察监督的章程》(亦译为《检察监督条例》)的颁行,苏维埃俄国才在苏俄司法人民委员部内创建了苏维埃俄国检察制度。
而我国之所以有苏联检察制度随“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创建的错误主张,一是误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建立(1917年11月7日-1922年12月30日)就是苏联的成立。二是望字生义所致。1956年1月28日,中国国务院颁行《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之前,汉字“检”与“监”、“察”与“查”通用。其结果便是“检察”与“检查”“监察”的混用,进而导致“检察机关”与“检查(监察)机关”、“检察员”与“检查(监察)员”、“检察长”与“检查(监察)长”的不分甚至误认误译。
例如,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院条例》(1920年2月8日)第1条中“在吸引工农参加以前的国家监察机关的基础上,改组中央和地方的国家监察机关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监察机关,定名为‘工农检查院”的“工农检查院”,[33]就属于对“工农监察院”的误写。
再如,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编《列宁论检察制度与监察工作》(新华书店1949年版)中,“检察”“检查”“监察”三者也是混用的,以至1987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列年全集》第42-43卷,所载列宁关于法律监督、检察制度与监察工作的如下代表作中,同样也是“检察”“检查”“监察”不分:《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1921年9月27日)、《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给约·维·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1922年5月20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材料》(1923年1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
因此严格意义上说,苏维埃俄国检察制度是苏联检察制度的前身;而苏联检察制度诞生于1922年5月28日,早于1922年12月30日苏联的成立。
综上所述,在“我们必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4]捍卫践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重新审视自认为固有法律监督天性的检察制度及其检方在我国加快形成严密法治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正逢其时。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并总能给人以深刻启示。
注释:
[1]“再次”,因为至少在48天前的吉林长春等地调研中,张军也有过同样追问。参见邱春艳:《最高检调研组在吉林检察机关调研》,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www.spp.gov.cn/spp/gjyjg/nsjg/201901/ t20190103_40411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
[2]参见邱春艳:《张军:凝聚法治最大公约数 共同深化全面依法治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www.spp.gov.cn/spp/gjyjg/nsjg/201901/ t20190103_40411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
[3]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65-67页。
[4]“九落九起”,泛指中国检察制度在发展中,所经历的1914、1927、1935、1937、1942、1945、1949、1951、1960、1968-1978、1996、2016年检察权被削弱取消、检察院被撤销、检察人员被遣散诸情形。
[5]“中国检察第一书”,专指20世纪初,受重金聘任来华协助清政府变法的日本冈田朝太郎(1868-1936年,刑事学家)、松冈义正(1870-1939年,民事法学家)、小河滋次郎(1861-1925年,监狱学家)、志田钾太郎(1868-1951年,民商法学家)“法学四博士”,1908年3月历时20日,在京师法律学堂(1905-1912年,我国官办第一所法律专门学校)举办的检察研究会(类似于现在的“系列讲座”)上,分别口授的讲义,由与会200名京师司法人员(当时实行“审检合署机制”)中的检察长张一鹏笔述的《检察讲义》(载《法政学报》1908年卷),法官郑言笔述的《检察制度》(中国图书公司1911年版、1914年再版),法官张智远、王枢、王炽昌笔述的《检察制度详考》(检察制度研究会1912年8月编印),法官熊元翰编辑的《检察制度》(安徽法学社1918年编印)4部最早的论述中国检察的书籍。因4部书籍皆源自同 一次讲座的内容,故统称为“检察第一书”。现已由中国检察出版社陆续出版。参见薛伟宏:《检察制度辨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20年版,第308-344页。
[6]同前注[5],第308-344页。
[7]同前注[5],第308-344页。
[8]同前注[5],第27-30页。
[9]而检察权力与行为似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为检察法所承载,均为检方所掌控。
[10]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11]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9页。
[12]而法律和制度,同样也像一枚硬币——法制的两面。其中,法律是制度的书面文字载体,制度则是法律在现实中实施的客观结果,
[13][战国]愼到:《慎子逸文》,《慎子》。
[14]列宁:《论国家》,《马列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15]当然,“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执法者还必须内心确信所实施的法律和执行的制度为良法善治(制)。正是:“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同前注[10],第20页、第54页);执法者无评判法制是善还是恶的权力。
[16]同前注[10],第200页、第74页、第48页、第154页。
[17]同前注[10],第85页、第19页、第45页、第73页、第20-21页。
[18]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19]同前注[10],第48-49页。
[20]诚如柏拉图所云:“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4页)。
[21]同前注[5],第308-344页。
[22]同前注[5],第308-344页。
[23]例如,《检察讲义》称“然现今多数国所采用检察制度之发端,实在中古之法国”;郑言的《检察制度》称“由法国发达之检察制度,除英国法系之外,大概采用法国主义之检察制度”;《检察制度祥考》称“检察制度发源于法国,罗马及德意志之法原无之此,通说也”;熊元翰的《检察制度》称“夫检察制度本发源于法国”。
[24]同前注[5],第81-82页。
[2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26]同前注[5],第89-105页。
[27]陈国庆:《检察制度原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28]所谓“和制汉语”亦称日制汉语,指日本人借用汉字创造或翻译出的汉语新词汇,以及延伸了含义的汉语既有词汇。19世纪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借用汉字大量系统性意译了西方先进概念,其中很多汉语词汇(如宪法、司法、检察、公诉、警察、检事、推事)又传回中国(详见《辨论》第86-96页)。
[29]同前注[5],第86-89页。
[30]同前注[5],第86-89页。
[31]其中,1931年11月20日至1949年10月1日,为人民检察制度与国民党检察制度并行时期;而新中国检察制度又经历了建国初期(1949年1月1日-1968年12月)、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976年10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8年3月5日-2018年11月8日)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11月8日至今)四个时期。
[32]同前注[5],第83页。
[33]参见《苏维埃检察制度(重要文件)》,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
[34]同前注[10],第19页、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