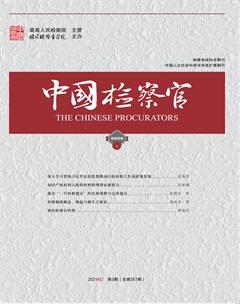浅议串通投标罪的解释路径与适用
邱远典 黄怡璇
摘 要:由于刑法对串通投标罪的规定较为概括,司法实践中对刑法条文作完全形式意义的诠释,导致该罪认定面临诸多困境,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法纳入刑法评价范畴。串通投标罪作为行政犯,具有“双违性”特征,因此应当把握串通投标罪的危害本质,借助行政法律规范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从而解决串通投标罪的疑难问题,全面提升对招投标领域犯罪的惩处力度。
关键词:串通投标 行政法律规范 刑法解释
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串通投标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大多违法行为无法通过刑法规制,一些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违法行为也被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其原因在于刑法条文对于传统投标的界定并不清晰,多种串标行为未被考量。串通投标罪属于行政犯,所涉及的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各种合同法律关系复杂,招投标代理、监理机构、中介机构等主体繁多,给界定犯罪带来了一定困难。实践中行为人为了规避惩处已经衍生出多种串标、围标、贿标行为,对刑法条文的刻板理解已无法有效规制上述各种“非典型”串通投标行为。招投标行业的行政法律法规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在刑法条文的理解适用时引入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刑法解释的依据,对于规范串通投标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一、串通投标罪抽象规范的局限性
(一)刑法对串通投标罪的界定不明确
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了串通投标罪,但条文并未细化定义投标人、招标人,如评标委员会成员、挂靠单位、监理单位、组织串通投标的中介机构、掮客等能否被评价为行为主体值得探讨。刑法亦没有界定串通投标的具体行为,对实践中常见的恶意挂靠、评标失衡、中介机构串通评标成员、掮客拉拢投标人等行为没有评价。现有司法解释也无细化规范,实践中不同法院对刑法条文存在不同理解,易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二)限缩解释的弊端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司法人员对法条的理解较为保守,在规定不明确时尽可能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解释,实践中犯罪主体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投标人、招标人,即招投标合同中的具体单位。为了规避串通投标罪,实践中已经出现多方挂靠、联合投标或投标人、掮客串通评标委员会成员的情形。根据限缩解释,上述单位或个人都无法被评价为招投标行为中的适格主体,不属于投标人或招标人,其行为也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串通报价行为。而各种各样的“非典型”串通行为对于招投标秩序的破坏不亚于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标价,放纵该行为既不利于对市场秩序进行妥善维护,也不利于规范具体的招投标行为。
(三)扩大解释的担忧
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招投标行政法律法规体系,包括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还制定了一系列部门规章,详尽规范了招投标领域内各种串通投标行为,对于招标人、投标人、报价、串通投标行为等有明确的界定。串通投标不仅是指串通投标报价,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其他联合行动也视为串通投标的行为,串通投标主体不仅仅是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也有可能是掮客,以及为实现传统目的但不参与投标的人如评标委员会、行政监督部门、仲裁和司法机关人员。[1]行政法律规范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对投标人、招标人及串通投标的行为进行相较于字面意义上的扩张解释,更有利于公平公正打击招投标违法行为。在刑法条文规定较为抽象的情况下,利用行政法律法规解释刑法条文是否属于扩大解释,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在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刑法条文肆意扩大,不宜采用行政法律法规的标准对串通投标行为进行界定。[2]司法实践中,上述观点较为常见,直接限制了行政法律规范对刑法中串通投标罪的主体和行为进行解释。
二、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刑法解释依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行政犯“双违性”特征的要求
串通投标罪为法定犯,即不同于自然犯的行政犯。法定犯的产生本身依赖于国家的行政法律规范禁止,本质上属于违反了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规定而应当受处罚的犯罪[3],法定犯的刑事可罚性取决于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或者行政机关的决定。串通投标罪既然是行政犯,则不能脱离行政法律规范的意义和范围而单纯界定其刑法属性。对于法定犯的惩处属于二次评价范畴,串通投标罪首先具有行政违法性,其次是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不是对行政违法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在行政违法基础上的二次评价,由行政领域递进到刑事领域的违法,具有双重违法性。[4]刑法在规定行政犯要件的时候,对同一种事实当然得采用和行政法规相同的用语,这样才能够真正表现行政犯“出行入刑”的特点,保持行政违法行为和同类型刑事犯罪行为之间质的一致性。为了使两者这种联系在司法中继续得到贯彻,对刑法中行政犯用语的解释,当然也应当尽量保持与行政法规的含义相同。[5]
(二)有效保护法益的要求
串通投标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险性和法益侵害性被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法律规范所不允许,行政法律规范所保护的法益内容与刑事法律规范一致。在串通投标罪中,违反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给其他招标人或国家造成损失,扰乱市場秩序是行政法律规范所要遏制的,市场秩序也是刑法所要维护和保障的法益,所以本质上说,刑法与行政法所保障和维护的法益具有一致性。[6]将行政法律规范作为串通投标罪的解释依据有利于对经济市场秩序这一法益进行更为充分的保障。
(三)不违反刑法解释原则
对刑法条文进行解读是否属于超过法律允许范围的扩大解释,主要在于该解读是否超过刑法条文的解释边界。界定一个概念应当将其内涵作为定义某个对象最为实质的特质[7],只要解释范围不超过概念内涵,则可认定为合理解释。行政法律规范作为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其中对于串通投标行为的解释往往根据实践中的行为判断,本质在于对招投标市场秩序的保护,对于投标人、招标人的范围界定也是根据各行为主体在招投标活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来确定,能够体现串通投标行为的概念内涵,即行为人伙同他人联合串通,扰乱招投标市场公平公正的行为。同时,刑法条文的解释不应超过文字字面上可能具有的含义,也就是文义最远的解释范围,既包括了一般规范对于该文字的理解,也包括了学理上对于该文字的解读。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最远含义并不意味着必须死板地限制文字的概念,而是一般人解读该文义能够接受的范畴,可以认为是文义可能达到的范围,即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解释。[8]就串通投标罪而言,行政法律规范中将招投标代理、中间掮客、评标委员会成员纳入招投标犯罪的主体中进行考量,本质上来说并未超过一般人能够接受的文字意思理解范畴,上述主体之间的串标,在一般人的理解范围内也属于串通投标行为。
三、行政法律规范作为串通投标罪解释依据的理解与适用
(一)把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认定犯罪的前置性要素
串通投标罪属行政犯,单纯从刑法条文原文出发并不能对实践中的串标行为进行准确把握,应将体系较为完备的招投标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刑法解释的依据,纳入刑法的评价体系中。我们应将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前置性要素,在此基础上对行为人的串通投标行为进行评价,确保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规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能够找到相应的条款作为依据,这是基于法定犯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的要求。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某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根据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认定为构成犯罪应当满足的条件。不成文要素存在,关系着法律漏洞的补充适用、法律解释结论的准确性等根本问题。[9]不成文要素对于犯罪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是认定某类犯罪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了对于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也就缺乏了对某种犯罪本质属性的认知。[10]也就是说,只有在违反招投标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某种行为才能作为串通投标犯罪的评价对象,即刑法条文中默认串通投标犯罪应当以“违反招投标行政法规”为前提。
(二)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解释串通投标罪解释依据的具体适用
在认定串通投标行为的性质、主体、对象等构成要件时,将行政法律规范中对于相关概念的解释和理解作为刑法条文的解释依据。首先,在犯罪主体界定方面,根据招投标法、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理解。对招标人的理解不局限于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具有与招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还包括评标委员会成员、组织者,如果发现评标委员会成员具有串通行为,应当认定为具有串通投标罪的主体资格。其次,在犯罪行为界定方面,招投标行政法律规范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列举了串通投标的表现形式,为认定查处串通投标行为提供依据。一是从投标人之间的串标行为来看,不仅包括了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还包括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二是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行为,包括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信息泄露给其他投标人,招标人直接或者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
注释:
[1]参见李金开:《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构成串通投标罪》,《中国招标》2015年第8期。
[2]参见刘艳红:《法定犯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之实践展开——以串通投标罪“违反招投标法”为例的分析》,《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
[3]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4]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
[5]参见张绍谦:《试论行政犯中行政法规与刑事法规的关系——从著作权犯罪的“复制发行”说起》,《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8期。
[6]同前注[2]。
[7]参见董梦晴:《法律解释中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研究》,安徽大学2019年碩士学位论文,第16页。
[8]同前注[7],第19-20页。
[9]同前注[3],第57-58页。
[10]参见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