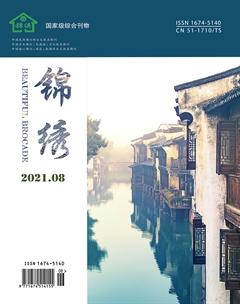解读张强“踪迹学”体系
张一琤
自四川美术学院二级教授、两江学者、世界实验书法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当代水墨艺术的实践先驱与艺术理论家张强最初提出“踪迹学”的概念已经整整有了三十个年头。至今,张强把他的实验水墨实践与理论分为三个系统分别是:“张强踪迹学报告”(1990—2009)、“张强+liawei双面书法”(2009—2019)以及“云自在书”(2020—)。这三个系统无疑都是建立在与“踪迹”这个概念相关的思考之上,而张强的“踪迹”概念在这三十年中,已发展为由四十多本著作构建的理论体系,蔚为大观。那么,张强试图通过“踪迹学”实现怎样的一种理论图景呢?笔者试图通过联系张强的实验水墨实践作出一种解读。
张强教授在《踪迹学》一书的开篇就将他的思考设立在一个文明起源的时空环境中。张强写道:“起源是指某种事物或者是某件事情滋生的原初状态,踪迹的起源就是踪迹作为概念的确立,踪迹是语言与概念对现象的指称与命名,尽管在命名之前踪迹已经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而概念的命名,使得踪迹成为一个自在之物——独立的文化概念。”张强试图从两个方面论述踪迹的文化“本源性”:首先,踪迹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起源的必然前提,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当我们为了探索而度量迹象或痕迹时,已进入了“踪迹”状态。其次,踪迹是文化发生的方式,与艺术发生有必然的关系。人的意识能够成为文化的前提是具备能够接受、流传的条件,当踪迹痕迹是人为有目的的被认识,或者是认识者充满了目的性去“加以认识”的,那么就是文化的本源性发生,也成为集体智慧产生的可能。同时,回溯这种文化发生的本源,也是踪迹学实践的一个指向。
这里所提的“踪迹状态”与“踪迹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有着独特的共鸣,被称作“笔墨表征”。中国书画艺术通过漫长时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精妙完善的笔墨系统,作为视觉的外在语言,而意指的是内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即对人格理想的终极追寻。笔墨书写的经验作为一种古代日常的经验,因此与形而上的追求有所联系。我们观赏笔墨形态、万物意象、符字意解、气韵形神、笔力势遒;从而我们体悟创作主体的心性跃动、内在精神,文化涵蕴、此在思辨。当我们今天看待“笔墨表征”如何对个人经验进行哲学提升与意义还原,如何可能成为跨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有效中枢,跨学科系统下的一个汇通。《踪迹学》对此提供了颇具份量的思考。
首先,张强在《踪迹学》一书中对“踪迹”显现的第一个层面“笔墨”进行了梳理分析。在“笔墨”创制之前的“前笔墨时代”,古人们对绘画的观念从“模拟物像”到追求“笔墨内涵”已经有所端倪,例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录:“夫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到了宋代,笔墨的意识随着苏轼文人画的成就,而趋于成熟。由元代赵孟頫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叶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可见,笔墨踪迹在具体的物象表现的途径之中由于笔法形式的独立而获得另外的价值。而清代石涛《画语录》中将“笔墨”上升到“一画”的思考才是对笔墨作为书画的踪迹作了彻底形而上的思考。其云:“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画法就建立在一笔一画的一画上,天地万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所谓“文彩已彰”的典故,既玉林通琇曾问本月禅师:“一字不加画,是什么字?”本月答曰:“文彩已彰”。这种禅机的话,大意可能是从无到有,既然有一字,就不难有许多字。一字虽然不多笔画,但字形已具备,文字已经开始,所以说“文彩已彰”。
其次,张强“踪迹学”所探讨的踪迹并非停留在“笔墨”的层面,那尚处于古典书画时代的价值范畴。趋向近代,对墨迹本身的趣味与观赏,时而超逸出“笔墨”的约束。不论米家山水的“墨戏”还是徐渭“由草入画”的墨葡萄,审美共情具有某种“自省”“自赏”的特点在墨迹中突显。张强称之为“艺术主体”意识的介入。画面呈现为一种对客观形象的极大程度消解和仿佛侵蚀般地对形象出离,褪去其美化、装饰的视觉表象,悬置起绘画的伦理教化与致用功效,而充分成全绘画行为的本质与主体意识的本真性,达成一种主体的介入性的参与、相互生成与通感情境。这种取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宋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卧游”、“畅神”的审美自觉,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看,这遇见了海德格尔从主体间性层面上“此在”对存在本真的领会。这种主体交往互生贯通、自然美与人格美的整一、天地神人化归一体的际遇才是艺术本真体验的植根之处。那么,艺术进一步将墨迹逐渐从形象中解放出来,乃至突破笔墨的范式和主客陈规,甚至是在书法领域抹去其认读的功能而实现对墨迹的纯粹观赏,可以说同时实践着两个方向,其一是向此在达乎本真存在的藝术本源归复,另一是向着对普遍性有所探求的他者文化与他者系统敞开。
张强认为西方绘画中形象呈现的过程从踪迹学的角度看是“形象由踪迹的意图与踪迹的形式来构成”。[1]西方油画传统中的笔触肌理基于介质不同和布局的迥异,表面的组织结构、排列造型各不相同。这种相互嵌合、映衬的触觉品质能够使观者通过视觉肌理模拟物质感向心理的传达一种意境与美感。尽管西方美术史惯常被用风格学或图像学的方式进行,但从绘画笔触的角度亦可以牵联出绘画观念变迁的线索:从尼德兰的精致到文艺复兴的和谐,转至巴洛克的笔触,进而印象派的点彩,直至德库宁、米罗、塔皮埃斯、克莱因的当代姿态。正是从“踪迹”的视角出发,具象与非具象不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成为相应的顺延观念与形式对接。一方面踪迹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另一方面踪迹作为理念则是对形象的抽象超越。
“笔墨”与“墨迹”都还是作为主体表现的踪迹,我们再来看作为“表现缺场”的踪迹,即没有主体的表现意识而留下的“痕迹”,是否也可能具有艺术或踪迹学价值。张强认为涂抹的痕迹具有原生性,它与人类意识中最本能部分的相互联系,它先于任何书写或绘画技法的出现,比如启迪象形汉字“出现”的蹄迹爪印就是非可以而为之的“痕迹”。我们对于痕迹的识别仍然是视觉层面的,并指向更精微的视觉。痕迹作为表达与表现的缺场,是一种非表达或表现之物,那么这种表现意蕴的离去是否是存在者之存在的缺席呢?显然并不。从突破既有陈规的表现到对表现意识的取消,绘画的主题变成没有表现意识的痕迹,而到达一种无的状态,这些痕迹不是为了表现而诞生的,而是对在世界敞开的视域中作为存在涌现的见证。它在视觉层面时时刻刻指向创始伊始的混沌原初,并暗示在运动之中、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让存有成为敞开的作品。这种“敞开”褪去笔墨结构与墨迹材料带来的符号与标识解读,更进一步揭示对特定艺术经验的认同。对此,创作主体甚至难以主观任意做选择或改变潜意识层面的艺术经验认同。
那么,“墨迹”与“涂抹的痕迹”究竟是不是笔墨表现的缺场?或是从“劣笔”、“败笔”中加以挖掘的所谓表现力?答案是否定的。笔墨在离开了既有范式的系统之后就不再被称之为笔墨,在离形解象中组成了新的“踪迹网络”的实际情况是:笔墨虽缺席,但笔墨的经验却被训练有素的书法家化用进了“踪迹网络”之中,因此笔墨范式虽离去却在新的视觉形式中留下了无固定形态的“痕迹”。同时对以往传统中“书写行为”充分体验的创作者,将书写行为进行强化而消解对笔画关系的雕琢,势必会呈现外行眼中的“劣笔”、“败笔”,而书写行为本身的老道与练达所带来的迹化形式却逃不过最专业的眼睛。这样一种“剥离”与“返真”的过程,如果没有创作者内在的训练有素与学识见解,那么可能就会产生出真正的“劣笔”与“败笔”,即便假以“观念”之名也难以负载中国艺术价值中的内在份量。而领会中国艺术中的“气息”、“神韵”呈现出形式内在的生命力与道家文化中“大象无形”的境界才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家的书写中所欲加以通达的,也是张强认为的以抽象艺术的准则来取舍中国现当代书法实践可能带来的“误读”所在。
然而,即便 “痕迹”层面也非“踪迹学”的全部内涵要旨。因为,如果说痕迹尚关注于视觉层面,那么张强踪迹学真正立足于宏观而抽象的思索。
“踪迹”涵义在于将踪迹看作是资源,面对数以万计的艺术名作;面对东西文化的眼中挤压的焦虑;作为当代语境中的艺术家,应怎样超越地创造的艺术与文化?仅凭借一股人文热情与历史的责任是不够的。艺术本身不是文化的重负,也非创造理念的堆积;具有历史感的艺术必定要对现实与历史对人性的双重遮蔽具有穿越的力量。这种穿越又不仅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对抗阶段。[2]
其中的“穿越”与“对抗”两词简要锚定了张强的思考:在我们经验当下文化之时,我们同时置身于西方文化体系与东方文化体系。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与艺术价值系统原本没有转译的可能,即便是通过语言的翻译相互理解,也势必在实践中只能遵循一种价值体系。显然张强思考的是“穿越”,使它们有各自思维系统的同时又有共同的经验支点。这种穿越恰是对对抗均质化的深化,也是他对艺术形式与意涵的思考。
而张强在思考踪迹的普遍性的同时,用创作展现他的关注视角,给踪迹作出他的定义,也给理论话语打开多向的活力场。其中以互动书写作为代表的典型,涉及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与当代书法与水墨语境的思考。
通常的书写是书写的主体在纸上留下了可读解的痕迹,目光所及,纸上的痕迹被“所指”化了,它可以是一个词、一首诗、一封信等等传达着语言的内容。而张强实验水墨的互动书写,着重于双重主体的“互动”。在互动中所发生的一切,那些物质形式中未保存下的内容,恰恰也纳入踪迹的范畴。其中对于女性合作者的邀请,呈现出女性作为书写客体与能动主体的双重身份。她抛去日常的装束与社会意识的映射,而在笔墨痕迹中将容姿涂抹,这是一种消隐抑或显现?或许这些女性个体因此而得以遇见真正心灵深处的自我。张强说,互动书写的合作对象之所以都选择女性,是因为她们更倾向于尽情自我表现。
当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艺术家团体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在大街小巷贴满“猩头裸女”的海报,上面写着“大都会艺术馆里的女性必须是裸体吗? ——现代艺术家中的女性不足5%,但是85%的艺术品中的裸体都是女性。”之时,这种呼声从未在水墨实践中得到表现,甚至是审视。其中原因是中国书论画论中从未有此传统。写到这里,张强互动书写中的女性载体,当真只是一个人的形象,抑或她可以是一种隐喻,一种对书法艺术的隐喻。在此,张强使古典的书写经验缺场为一种踪迹,是缺场却不是缺失。张强说:“我所关心的是当代经验” ,“当代书法大师是什么?用自己的书法经验给书法重新下定义的人。”[3]以“书法”命名的艺术形式仅仅只能在“书论”的范畴中成为自身吗?它是否有可能主动地面对一次“无语之境”的文化碰撞?再看张强的“双面书写”系统与“云自在书”系统,书法成为两个主体之间充满偶然与默会的“踪迹”体会。从而这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文化系统本身。
综上所述,踪迹的概念在张强的理论体系与水墨创作中可以具体化为“痕迹”、“墨跡”、“笔墨”多个层次,而踪迹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甚至已然溢出视觉的层面,而指摄存在在时间中的维度。那么踪迹学,即有关踪迹的学说集合,试图要容纳关于艺术,关于存在于时间中敞开为作品的各种理论思考,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下即刻的,无论是系统的还是零星片语的,它们自身无异于一种踪迹。因此踪迹学仿佛是一个不可见的空间场,有关艺术的起源与发展的众学科边界在此得以取消,而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在踪迹学的空间场中分门别类找到相应的坐标。同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这些坐标在阵形上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它们又是在不断生成演进的,因为艺术家用实践在对踪迹学扩容。当不同的艺术家对踪迹做出理解的时候,“踪迹”的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得到闭合。正如,本文的写就亦可被视为“踪迹”层面上的实验。
注释:
[1]张强:《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M].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2]张强:《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M].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3]张强:《世界实验书法读书会》讲稿
参考文献:
[1]张强:《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3]道济:《石涛画语录》[M].俞剑华点校注释,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王庆节、陈嘉映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5]张颐武:《互动书写的激情》[J].东方艺术,1997年第三期
(中国美术学院 美术学、文艺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