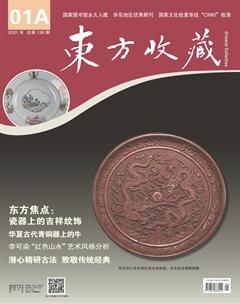博物馆大众传播模式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浪潮的不断推进,新媒体持续发展,博物馆行业本来就因为其极高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往往易局限于有限的专业领域之内传播。伴随着新媒体浪潮和外国文化入侵的冲击下,博物馆作为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够进行广泛、有效的大众宣传工作,势必将会对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增强民族认同感、增进民族凝聚力,甚至树立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博物馆向公众传播历史文化知识,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传播关系,是当下重要的时代任务,博物馆在新媒体时代的大众化传播模式革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
关键词:新媒体;博物馆;大众传播;传播模式研究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2007年于维也纳召开的第22届大会的会议章程中,对博物馆的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有形及无形遗产。”在新博物馆学的浪潮之下,建构二十一世纪博物馆的目标由“藏品立本”转变到“公众体验”(1),因此,构建博物馆新时代的大众传播模式就变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浪潮的不断推进,互联网加入大众传播的行列,新媒体持续发展,大众传播的媒介和内涵被不断地丰富。
博物馆行业本来就因为其极高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往往易局限于有限的专业领域之内传播。伴随着新媒体浪潮和外国文化入侵的冲击下,博物馆作为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够进行广泛、有效的大众宣传工作,势必将会对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增强民族认同感、增进民族凝聚力,甚至树立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博物馆向公众传播历史文化知识,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传播关系,是当下重要的时代任务,博物馆在新媒体时代的大众化传播模式革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
博物馆的大众化传播发展概述
新中国的博物馆大众化传播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际传播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博物馆,主要是以宣传历史文化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館,虽然已经对传统博物馆进行了改造,并适时增加了一些新型博物馆,但因其规模甚小,对博物馆的内涵和大众化概念意识不强。同时,受政局动荡和国外势力排挤等外部因素影响,导致博物馆的建设动力不足和创新意识不够,博物馆基本是一体化模式。在传播模式方面比较落后,仍然属于人际传播模式。
第二阶段:大众传播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博物馆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仅数量激增,而且种类更加多元,除了综合类博物馆持续发展以外,艺术类、自然类、民俗类和科技类博物馆也都逐渐呈发展之势。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博物馆的大众化传播手段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在这一阶段主要依靠报刊、电报、电影、广播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大众传播的诞生,结束了人们以口语和手抄文字传播为主的漫长时代,提高了传播效率,扩大了传播规模,使人们能更为直接地了解文物与博物馆管理,向博物馆的大众化发展迈出了一大步。
第三阶段互联网下的大众传播的新阶段。20世纪末,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互联网也以磅礴的气势加入了博物馆的大众传播,它与以往的大众传播相比,具有传播速度实时性、传播内容海量性、信息形态多媒体性、信息检索便利性、传播过程交互性以及传播范围全球性等优点(2),博物馆通过对互联网的使用,使博物馆更加贴近群众,经常性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增进了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以更接地气的宣传方法扩大了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的传播,提高了人们的关注度。
博物馆的大众化传播现状分析
目前,从总体上来看,新媒体时代博物馆的数字化传播走势较好,比如较之以往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对博物馆的传播价值的认知更加深刻、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尽管如此,依然还是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在此处,拟运用拉斯韦尔经典的“5W”理论,对现阶段博物馆的数字化传播模式进行全面深度分析,探究目前发展博物馆数字化传播模式的机遇与困境。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五个层面:
1.从控制分析也就是传播者(who)的层面来说,新媒体时代的博物馆数字化传播存在着大众化社会化程度低、娱乐化倾向严重,传播者对博物馆信息的解读浮于表层,对其文化价值剖析不够深刻、用户思维意识淡薄等问题。
2.从内容分析(what)的层面来说,博物馆的数字化传播存在着缺乏创意,创新驱动不足,博物馆创意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3.从渠道分析(by which chancel)的层面来看,依赖于平台和技术的博物馆数字化传播,存在着博物馆文化价值有些层面难以用数字化来展示,尤其是人们对历史的情感无法直观表达出来、个性化传播机制尚未形成、平台缺少把关,由此导致的不实信息散播、大众错误解读博物馆信息、信源传输渠道狭窄、平台技术缺乏活力、对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智媒体应用不成熟等问题。
4.从用户分析(to whom)的层面来看,我国网民数量庞大,CNNIC第45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因其媒介素养层次不齐,存在着占比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对数字化博物馆产品和信息鲜有关注的边缘用户群体、部分用户持猎奇和攀比心理接触博物馆信息,导致博物馆信息对受众的精神涵养价值大打折扣。
5.从传播效果分析(what effect)的角度来看,新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受众注意力有限,博物馆的数字化传播效果更多地停留在微观的认知和接触层面,引起态度改变和行动的宏观传播效果微弱。
探索新媒体时代博物馆的大众化传播更优模式
1.从控制和内容分析而言。以河南博物院为例,其作为现代化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有着丰富的馆藏文物,其中一、二级文物五千余件。河南博物院要想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充分彰显自身丰富的馆藏优势,必须从传统的藏品收藏研究、展览展示,向更主动和开放的对外传播模式转变,如互联网服务和文化传播数字化等领域,做到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从而实现数字化传播的更优模式。虽然河南博物院于2013年开始建设和部署“河南博物院数字资源管理系统”作为全院数字资产管理平台,但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数字资源缺乏关联性、连续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数字资源“共建共享”还处于比较松散型的阶段。要想实现数字化传播的更优模式,博物馆需要不断提升对外服务水平,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分析”等现代化数字手段,可以根据既有数据,以及需要从数据中获得支撑决策和判断趋势的分析结果,主要集中在优化和决策层面,大到明年博物馆要举办多少场活动,需要多少志愿者,小到某次展览策划的方案是否合理可行等。博物馆作为文化资源的生产和提供者,特别是我国博物馆当前正在进行“以服务为导向”的职能转变的前提下,把博物馆的文化数字资源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观众需求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的对接,以推动博物馆所代表的文化有效传播和对观众文化需求的持续追踪,创建博物馆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实现更优的传播模式。
2.从传播的媒介来看。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博物馆的网络线上传播“两微一端”等手机APP已经成为了信息传播、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2020年持续的疫情,也使线上展览加速进入了大众的生活,在疫情期间,由于各地博物馆被迫因故闭馆,线上展览成了博物馆展示的唯一的新途径,逐步形成了“线下闭馆,线上开花”的态势。在利用媒介推广博物馆的过程中,创建在“两微一端”的官方账号,与公众进行良性沟通,扩大观众群,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博物馆的关注度,在提高关注度的同时,做好对博物馆观众意见的反馈;对博物馆文创商品进行推广,提高博物馆设计水平的同时开设网络店铺、开展网络带货直播等,增加文创产品的购买渠道、推广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可以拓展体验式教育、推动生活化教育、拓宽展览受众群,也是促进博物馆大众化社会化的手段之一;承担起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公共科普性质的讲座,在网上举办相关的传统文化的宣传活动,增加博物馆的群众参与度,发挥其社会服务的职责。
(作者覃覃,壮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郑州大学,研究方向:先秦丧葬礼俗研究、博物馆观众研究)
参考文献
(1)沈辰,构建博物馆:从藏品立本到公众体验,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