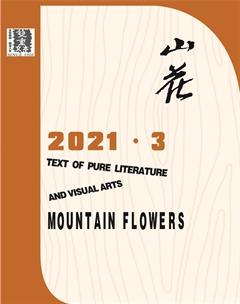幼少时代
乐水

永心油醋坊与私塾
村东头的永安、永心、永范上一辈开油醋坊,子承父业。解放前我上的半年私塾,就是在永心家西屋。当时,早晚两顿饭后,先生好一阵子不来,屋里便是弟子们临时的天堂。八仙桌上放着乌油油的戒尺,鲁迅那篇写乡间私塾的文章简直就是我们那会儿的写照,虽然相隔这么久远,但时代也会有着前后的重叠与类似。我在那间白天不见阳光的土屋里,半年读完半部《论语》(《上论》)和先祖陈略所撰的《胡打算》,继续习学毛笔字,写大仿,练小楷。男女少年,晨昏苦读,咿唔一室,至晚不散。
有时早晚出入时会看到沥醋和晃香油的情景。沥醋似乎只须在缸里泡上米谷高粱等,灌上水置于向阳处曝晒,醋水由竹管内一滴滴沥出来。晃香油,先把白生生上好的芝麻上锅炒香,掌握好火候,焦糊和不熟都会直接影响香油的香味儿;然后磨成芝麻糊,再舀到一口铁锅内,放在堂屋地面上左右摇晃,这时表层便有一层香油浮出,再用小铜勺撇进油壶里。刚晃的香油,浓香四溢,或拌蒜末黄瓜,或浇在萝卜盐豆里,或滴几滴在热汤面和泡烂煎饼的碗里,美味无比,南面王不易也。我小时家里来客临时被指派端个小茶碗去打香油,今日记忆犹新。
永心大爷双妻,和西邻两家各有异同,但不是因为正妻不生养,而是图享受。这样说也许不为过。小婆子是开封人,也是因上黄水那年流落我乡,遂购之为小星。外号小蛮子、小美人儿,肤色浅黑,鼻官秀挺,一绺S状的鬓发始终耷拉在鬓角。我偶见她井畔弯腰汲水,一边不住将那一缕青丝撩向耳边的娇态,留下鲜明印象。设想一下这样一位美人儿,怎么会一直委身于整天光着上半身赤脚干活儿的粗汉子。解放后随着妇女翻身,她便回河南老家了。
永心家境较为富足,在村里人缘很好,但有时做事也惹人不悦,他不在乎这些。我上私塾那年,他家养了一头猪,过年请杀猪匠来家,经宰杀、鼓吹、剥皮、开膛,直到徒弟小刀手将整猪倒挂在横杆上割肉,一直围着一圈子人。小孩子看热闹,大人等着买肉。永心始终不开口,不报价。到最后,他打算尽量留作自用,遂将肉价定得很高,以至于等待多时准备买肉过年的村中邻里失望而回。永心家人将整个猪头腌制起来,每顿饭吃一碗炖猪头,竟然一直吃到收麦。他自以为乐,倒也得罪了不少人。
永心的两个堂兄弟永安、永范,他们的爹也溜乡卖过醋和香油。老大永安老实,一生默默务农,老二永范极为聪明、能干。解放前后,永范在家乡“创人物”(“物”读若“武”,三声。“创人物”系泛指树立个人才能与威望的行为),最早知道延安有朱毛,最早使用自来水钢笔,平时插在上衣口袋里,纽扣上拴着一条小链子。他给村里人写状子,编顺口溜,为庄上青年人找工作写介绍信,不用毛笔,都用钢笔。他写字笔杆直立,笔尖在纸上吃吃拉拉划过去,转眼间一封介绍信作成。我二哥小学五年间辍学找工作,就是请永范写的申请书。不过在我幼小时,他老是欺负小孩子,无缘无故辱骂我们,庄上少年都很讨厌他。
永范夫人和我母亲娘家都是苏口人,生女二人。长女桂玲妹妹待人亲切,腮帮两边长着两个可爱的小酒窝儿。小时碰到有人结婚,大多都能在迎轿队列中看见她。后来她嫁到台儿庄镇上一户商家,我在北京上学时,暑假回家,曾路过她那里。记得那天酷热难耐,她和她阿嫂妯娌俩下面条待客,忙得不亦乐乎。盛夏的小院,阳光刚退,暑气蒸逼,一碗热汤面,火上浇油。为了赶路,我也不再等到稍稍凉一凉,心急面热,吃得我大汗淋漓,溻湿了短袖衫。接着,她们忙着为我洗衣服,竟不小心将上衫洗破了,嫂子很觉得很过意不去,又不好意思跟我说,两个人嘀嘀咕咕,最后妹妹走到我跟前,说:“三哥你可别生气,嫂子把你的小褂揉破了。”我说,“那小褂穿了好几年,丝丝缕缕,早该扔掉了,我包里还有一件,不妨事。”
永范妻病逝后,他前来我家商量购买早年为我祖母准备的楠木“物件”,当时迫于生计,祖母首先提出转让予她,以致后来1959年祖母去世,听大哥说,仓促中临时购一薄材入殓,成为孙辈们永久的遗憾。
说起这件“物件”,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很早购置好几条高级楠木棒,腾出牛屋,专门留给木匠师傅当作业场。木匠划线锯开,木头的清香立即弥漫农家小院,数日不散。棺材板很厚,越厚越好,价钱也越贵。过去家乡要说人死后只有一副薄匣子,那就是命苦。有钱人家花巨资为先祖送大殡,用白绫子扎彩球,宾客盈门,热热闹闹。小时我见过学运老爷,为他父母送殡,就是非常气派。按习惯,有钱人家父母一方亡故,入殓后灵柩先保留于墓地地面之上,护之柴帐,以避风雨,谓之“停厝”,待另一方死去,一块儿送殡,掘坑(窀穸zhūn xī)土葬,地面堆个坟头。就像鲁迅小说《药》中华老栓儿子的那种墓,有的书上叫土馒头,我们老家叫“林”,意思是居于树林之中。“一抔黄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坟头杂乱地分布于农田各处,耕作中也是一种障碍,犁耙要提起,牲口要绕圈儿走,反复耕作耙地,有些坟墓幾乎“夷为平地”了,只好等清明节或过年时好好挖新土修补。
兄弟书笔挑子
我的私塾先生学先老爷,一副标准的封建时代文人知识分子模样,酷肖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家三个儿子,老三永念叔是我少年时代的挚友,两个异母哥哥都是跑纸笔生意的。农闲时从徐州贩货回来,平日到周围乡镇赶集。宿羊山逢集,弟兄俩及早吃完早饭,两副挑子一前一后出门,在东门内约五十米远的明文烟店对过摆摊子。夏日两副雪白的帐篷,在太阳底下闪光。兄弟各自弯腰笑脸应对前来买纸买笔的学生。当时,除了写毛笔字的仿纸、毛笔、黑墨、砚台外,还有现在很少看到的墨盒子、压仿圈等学习用品。当时的小学生,从学龄前就学习写毛笔字。起初描红,也就是先由老师或别人写一张标准文字,放在仿纸底描摹。我们那会儿就叫写大仿,是日课,天天写。我村的小学生常写的就是那人人熟悉的数字短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当时以为就是老祖宗陈略公作的,长大后才知道是北宋的邵雍。四五年级,不再描摹,改为临帖,即选择一种满意的字帖,大体不外乎柳体或颜体,仿纸下垫一张只划着方格子的纸,将字写在格子内。老师每天批阅大字,凡是写得好的字,用朱砂红笔在右肩上“发圈”,整篇字按级别“超、优、中、可、劣”,或“优、上、中、下”或“甲、乙、丙、丁”等评定好坏。自打踏入学校大门,毛笔字天天写,假期也不中断。在我来说,一直继续到高小毕业。上初中时,先是废除写大仿,继而废止用小楷字写作文,后来全部改用钢笔。
除了上述几种副业外,小陈庄还有过豆油坊、酒厂等,但大都于我出生前衰败停业,我又不熟悉当年情景,不说也罢。
另有于农闲时跑开封贩点儿洋布、笔墨纸砚和洋红洋蓝,还有唱玉鼓的,也是幼时之常见。我父亲也到开封跑过生意,小时我家里有一叠开封到碾庄的火车票,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小时握在手里觉得很长,后来想想,小孩子手小,才会有如此感觉,其实和后来比纸牌短一些的硬纸板车票相比大不了多少。
叫 魂
日伪时代,我因年小,只留下一些梦幻般的模糊记忆。我们庄除了东台子有汉奸刘老斐子为伪团部参谋长警卫员之外,村子中段人家的长子永品也在镇上当过小队长。永品结过两次婚,前妻麻子,红红的脸,一直受婆婆、丈夫的歧视,后来上吊死了。我记得那是个秋夜,我睡在门口過道屋里。半夜,突然被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惊醒。我赶紧爬起来,外头月明星稀,寒气森森。只见小队长的草屋顶上,站着一个人影,手拿一把扫帚,一边呼喊一边抡起扫帚砸屋脊:“大尹来——家来喽!大尹来——家来喽!”夜阑人静,声震四乡,听起来头皮阵阵发麻。我知道了,那是在叫魂。什么是叫魂?旧时传说,人死了魂就离开肉体走了,这时赶紧高呼此人乳名,借此将离开不远的魂儿重新叫回来。在我们家乡,多半用在女人上吊的时候。茅草都被砸烂了,一团团掉落下来。过一会儿,叫魂的人累了,这时屋内走出一个人来,仰首说道:“下来吧,不行啦。”
这位麻面媳妇死后,葬在东南湖刚刚耕过的地里,传说是天狗星,坟头上扣着一只涂成白粉的陶罐,周围插了一圈儿白色木头杆子,说是为了防止夜间恶狗盗尸。
前妻死了一年,永品又将街上一位姿色动人的女子娶回家中。结婚那天很热闹,喇叭班子点灯演大戏,细吹细打,惹得小孩子围成一堆儿,听到半夜不肯睡觉。这种喇叭班子,一伙四五个人,一个喇叭(唢呐)手,两个吹笙的,一个敲小糖锣的,有的再配上个敲梆子的。白天为婚礼吹打,晚上在门口场边大显身手。一般都是喇叭手为主演,大都以河南豫剧为基础,运用手中大小唢呐,模仿各种人物的道白及歌唱。男女老少,惟妙惟肖,比起真实的舞台,更加充满幻想与浪漫。有时舍弃唢呐前段的竹管子,直接将哨子连在最后的铜喇叭口上,一只手扣住,腾出另一只手,拎起一只茶碗,盖在喇叭口前,一开一合,模仿老生净丑,无不惟妙惟肖!别看三五个汉子,也能吹出个《百鸟朝凤》《抬花轿》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名曲来……
永品后来大病一场,右腮长痈,数年都不好。记得冬天,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门口晒太阳,静听乡人们拉呱。上世纪后半,我从北京回乡,返京时经过县城,偶遇永品于公交车上。他肩背一副渔网,问他到哪里,他说到外地撒鱼。看他神情有些颓唐,我也没再说什么。自那之后不知所终。他有两个弟弟,老二参了军,老三比我小两三岁,考初中未取,后来去了西北,听说在兰州铁路局任职。
挨 淹
大概是1946或1947年,那年大旱,好几个月不下雨,夏天汪塘涸(hào)干了。乡人们虽然为缺水发愁,但老天作孽,实出无奈。老百姓除“竭泽而渔”之外,趁机起土垫台子。各家都在属于自己的塘底下挖泥土,将崖(yai)头垫高些。记得那都是松软的沙泥土,摸在手里凉阴阴的,舒服极了。这种土晒干了正适合做婴儿穿的土裤子,许多妇女也都借此存满了货,以免小孩落生时为缺沙土犯愁。
大旱时节,村中小孩子们都到挖过的水坑里洗澡,玩泥巴。几天后下了一场暴雨,积聚了半汪水,土井子淹没了。一天,我照旧去玩水,不小心滑进去,立即水没头顶,拼命挣扎也毫不顶用。当时,只觉得两耳时沉时浮,水声哗哗,除了被迫大口大口喝水,只好等死,别无他法。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只听一位妇女高喊:“有小孩掉汪塘里啦——!快救人哪——!”喊了几遍都没人应,过了几分钟,那妇女又高叫:“干文,干文,快快快!”我知道干文熟悉水性,他会踩水。不能死,得坚持一会儿。但好一阵子没动静,又过了几分钟,眼看就要喝饱了,突然,有人搂住我的双腿,用力举出水面。这时,我的肚子宛若一只白色大气球,在夏日的阳光下闪耀。当干文将我抱上岸时,我几乎衰竭了,两腿绵软无力,站都站不住。乡人们都说,要拍打,使劲拍打,叫他大哭吐脏水。但说归说,祖母、父母、兄嫂都没有当回事儿,全家忙着煮玉米吃。西邻大奶给我母亲出点子,说把大锅揭下来扣在地上,叫孩子趴上去,用鞭子狠抽,这样我就会一边哭喊一边大口吐脏水。所有这些,家人都一概未予置理,竟使我逃过一场应得的惩罚。孩子受淹,再挨一顿揍,哪里受得了。这就是当时家人的心态吧。谁知,喝了一肚子水,尿了几泡尿,肚子瘪了,顿时觉得饿了,吃起煮玉米来比昨天甘甜得多。我知道,这是天地神祇的赐予,生命再造的馨香。
挨了一次淹,觉得很没面子,不大好意思出门玩了。因为一旦同别的孩子有矛盾,人家动辄就将胳膊举过头,挤眉弄眼,模仿水里挣扎的样子。我也只有二话不说,赶紧灰溜溜离开现场。
这次灾难也教育了我,以至于多年后重新回忆起来,又增添了新的感悟,遂作小诗一首以志喜:“人生可宝贵,坚韧知多久。危难不当死,暗中神来助。”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不寒而栗。多少个必然死亡的要素凑在一起,都没能战胜几条相聚一处的偶然因素的护持,致使生命之树蔚然不凋。例如,我滑入泥塘、水没头顶拼命挣扎时,正巧没有人在汪南的田里劳动;即使有人劳动,他或她只顾干活儿,目不旁顾;或只是草草瞥一眼,并未注意有小孩子被淹;或即使发现后大喊救人,而附近没有别的人;即使有别人他或她都不善于游水;即使会游水,又是半吊子本领,不像干文那般会踩水,能腾出双手,举我过头……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巧合,这么积极地铰结成一条生命的锁链,将我从鬼门关前硬生生拽了回来。
其实,我心里有数,我在水里挣扎喝水的时间,决不是五分钟,也决不是十分钟,凭我后来的感觉,肯定接近一刻钟或更长些时候。那次被淹的耻辱持续很久,时时有人提起,直到我到宿羊山上学才渐渐被乡人淡忘。
初小时代
大约是1946年,永汉利用他家昔日残留下来的破酒厂子,私人开办了小型学校(就是一座屋子),只有他一人任教。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庄上二哥一辈年龄稍大的人,编入高年级,初级班就是我们这些年龄幼小的少年儿童……上课分为两拨,永汉交叉为学生讲课。当时,我们低班学生写算都用铅笔,我二哥他们都用蘸水钢笔。一枚梭子形状的带沟儿的笔尖,内含蓝墨水,写几个字没有墨水了,就得插在墨水瓶里蘸一蘸,继续写。写下的字水棱棱的,鲜明,好看,老大一会儿才干。有时墨水瓶里的墨水不多了,笔尖插进去,便需哗啦一晃荡。等墨水用光了,花三五分零钱向西邻永柏大爷买一点颜料(他是贩卖颜料的,时常担着杂货挑子赶集卖颜料),回来自己兑水和一和就成了。永柏大爷用什么秤称那一点儿轻如鸡毛的颜料呢?用小戥子。杆子是鱼骨头做的,细如鹅毛筒儿,上面镌刻着刻度,黑红相间,非常悦目,简直就是一件精细的工艺品。
和墨水也有讲究,先加少量井水,待颜料慢慢化开,反复试试浓淡,达到满意为止。否则,水加多了,会发生“化学”反应,几乎变成全纯白水,还得向大人要钱再买颜料。那可不是容易获准的。
当时的语文课本至今记得不少:第一课是“进学校,进学校,学校里,真热闹……”,还有一篇,几乎全部记得,“荷花红,荷叶青。飞来一只大蜻蜓。大眼睛,亮晶晶,身体一挺像根钉。一会儿,飞起来,好像飞机在飞行……”除了国语,就是算术,学的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每天写一张“大倣”。
永汉是老师,但他最不像老师,他教他的,你学你的,不急不躁,任你成绩好坏,都没关系。师生十分相得。他把高级班的七八个人刚刚说的媳妇,都分别凭借想象画上一系列肖像画,标上文字说明:“徐楼小姐”“桃园姑娘”“刘庄美人”“岔河女士”……悬挂起来。那年夏天,麦熟季节,他还带领全体学生到套种的麦地里偷摘豌豆吃。那豌豆刚刚鼓胀起来,尚未长成,也未发黄发硬,甜脆爽口。大家蹲下身子,远处根本看不见。豌豆角含在嘴里,猛一咬,“啪”的一声脆响,别提多享受了。吃个够,悄然回家,谁也不知道。其实,主人很难发现,因为豌豆结果繁多,吃不尽,摘不完,过两天又会多生出一些豌豆荚来。种豌豆的人家谁也不在乎,任你吃个够。豌豆一旦黄熟变硬,采摘下来,上锅煮了,非常美味,那是吃不够的美食。此种享受,只可回味,不能再得。
我们的邻村阴庄也有一座类似的学校,也只有一位姓杜的老师任课。学生不仅限于本村,还招收了一部分外乡人。他们其中有我们村子东南角何庄子的几名男女学生。他们上学放学,每天打汪塘南岸经过,我校几个调皮鬼,还经常向人家挑衅,惹是生非。何庄子学生中有个女生,叫何彩丽,长得很漂亮,说话嗲兮兮的,好可爱。有一次,有人朝汪塘扔石子,水珠儿溅湿了她的红裙子,她竟然没生气,还友善地嫣然一笑。后来竟然双方隔岸对起话来。哦,“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何彩丽告诉我们说,她家种了好多玫瑰花和月季花,请我们星期天薅草时顺道去看看。但我们一直没有勇气去何庄子找那些先是冤家后是友人玩玩,只能在薅草时有意绕道东南湖,朝何庄子多望几眼,偶尔也能看到一闪即逝的红裙子。
总之,酒厂初小时代给我留下不少愉快的记忆,给我苦难的童年稍稍增添了亮色。
第二年,我又读了半年私塾,念完半部论语,后来还和二哥一起到宿羊山小学北校读了半年。他读三年级,我读一年级。年底迎来解放。记得当时,我还到学校找成绩单,扛回方桌。老师都跑光了,校内一派狼藉。
寒风呼呼,灰沙满地。
童年的游戏
乡间百姓生活清苦,大人为全家生计奔波,小孩子也力尽其能,下湖割草喂牲口,帮助大人干农活。但毕竟年小体弱,有父母兄弟照料,可以自娱自乐。除了一般的过年过节,同大人共享有限的热闹之外,也有作为儿童的特殊游乐,诸如:玩会挑旗、踩高跷、放风筝、打老瓦、馱布鞋、弹琉子、甩泥蛋儿、踢毽子,以及捉麻雀、网鸟、粘知了、摸鱼儿……
除此之外,我个人“创造”的游戏有:打电话,捡两只空火柴盒,穿孔,拴线,两人各持一端,互相对话,似有嗡嗡之声。我便大声问:“听见没有?”对方有的回答“听到了”,也有的回答“没听到”。问话人对前者,自然高兴,对后者则稍有不悦。这种线电话,我随身携带,逢人必定打一次试一试。还有一种游戏“插汽车”,用高粱秆外皮作篾子,折成圆形作车轮,内瓤纵横组合成车箱,车头糊彩纸,兜风疾驰,自得其乐。
农家的孩子,自有农家孩子的玩法,冬天踢毽子,春天放风筝,秋天捕虫逮鸟,夏天摸鱼捞虾……快乐无穷,一时是数不清的。
殷庄小学
1949年春,村中几个具有高小以上学历的青年,鼓捣着建立初级小学校,校址选在殷庄西头一家地主的空宅子里,几间大瓦屋作为教室。教师大都是我们庄上的,东台子的法文、化文,村西头的永汉,我大哥,后来还加入了孟宪珍,陈秋文的姨太太。殷庄上只有一位叫杜什么坤的,一个成天病怏怏的青年。计划报到兰陵县临沂地区教育部门,很快获得批准,当即将大瓦屋粉刷一新,制定课表,摇响铃铛,上起课来了。
殷庄小学成立后,我即转学过来上三年级,二哥继续留在宿羊山原校上五年级。周围几个庄子的男女少年都来上学了。上课时,人声嘈杂,下课后更是热热闹闹。老师同学都很兴奋,西大院里热火朝天。
1949年秋天,新中国宣告成立,全国欢腾。学校里学唱国歌,几个班主任老师同时在三个年级的教室里教唱国歌。一时间,到处都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歌声震荡着小村庄沉睡的土地,红旗照亮了故乡河川池沼的角角落落。
记得我当时有个红布面的笔记本子,封面封底都印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我当时对着作曲者的名字默想过好久,觉得很新奇。后来我上初中,一开学也是唱国歌,初见聂耳像,嗬,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于是立即成了“聂粉”。这是后话。
初小时代的生活平静而清苦,由于家中经济状况不佳,我也经常不上学,在家干农活儿。农忙时节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冬天,上学的时间比较多些。我们家乡一天两顿饭,上午课间操,回家吃煎饼。冬季里没菜吃,将干辣椒放在锅底下烤焦,红黑两色,趁热塞进在蒜臼里,放些盐加点儿水捣烂。吃时,将高粱煎饼烤软和儿,卷起来,沿着蒜臼口儿,一边擦一边转着吃。辣椒只要放进盐,又拉馋,又下饭,倒也吃得有滋有味。这是农村少年较为普遍的“午前间食”。
来回都要经过两村交界处,靠近中间公路西侧姓席的一家,开办牲畜配种站,场地上喂养着马、牛、驴等种畜。起初还有一道柴帐遮挡,后来一切交易完全在空场上进行。逢到宿羊山有集市或庙会,周围村庄上的人都对这家配种站咒骂不止,但作用不大,即便临时收敛一个时期,过一阵子又回到老样子。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方便了周围村子的百姓,因为在那个时代,普遍喂养牛驴,耕地拉车推磨都少不了这些牲畜。即便养不起两头牲畜,多数人家也都有一头毛驴。因为三天两头都要推煎饼,磨糊子,除非阴天下雨,才凑乎擀一顿面条儿,包一次饺子。庄户人家很少有那样奢侈的时候。
录取分为两步走,根据笔试成绩,发布草榜,刷掉大半,凡是榜上有名的考生应接口试和体检。两项完成后,回家等候通知。
此后的事,不想多费笔墨,引一段旧作搪塞之。
1953年小学毕业后,到八义集考初中。一同赴试的有街上的小跛子和本庄的平文哥。暂时放下畚箕和镰刀,洗洗满手的草垢,背上一摞煎饼,挟着一把油纸伞,上路了。
草榜公布了,上面有我和小跛子,没有平文。他死了心,先走了,我和小跛子参加了口试和体检,然后回家静等着好消息。一想到就要上中學了,心中好不兴奋。再见了,我的畚箕和镰刀!再见了,那满湖青青的野草!对不起了,还有我的牛驴们!
该轻松一下了,于是赶集就去听大鼓书,讲的是郭子仪征西,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节使我欲罢不能。一天,我正站在大布篷边上听得入迷,衣服忽然被人拽了一下,回头一看,是小跛子。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刚接到了录取通知,邮局的人对他说,还有一份是陈庄的,正等人拿哩!我连忙跑到邮局,看到墙上信袋里插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露出半拉“陈”字来。邮递员立即交到我手中。一看,傻了,上头竟然写着“陈平文”三个字。这是怎么回事?肯定是搞错了,平文不是连草榜都没上吗?这通知无疑是我的。
于是赶紧到八义集查问。母亲又为我包了煎饼,怕我路上渴,往口袋塞了个香瓜。我带上那把油纸伞,蹚了三十里泥水路,赶到了学校。挂着“校长室”木牌的房子里坐着一位胖乎乎的老头儿,他就是校长吧。我在门口逡巡良久,壮着胆子走了进去。校长看了看那信,亲切地对我说:“没错,没错,上头有了新精神,要照顾军属嘛。”
我绝望地走出了校长室,眼泪刷地淌了下来。一回到家,就把信交给平文。他正坐在石碌碡上,仰着脸望天。他接了信,傻愣愣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散文《秋草》)
班长梁丽燕当年考取山东兰陵中学(兰中,校址台儿庄)。暑假某日,父亲有事路过梁口村头时,偶遇一女孩儿,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对父亲说:“大爷,叫他别气馁,明年再考。”父亲很疑惑,那女孩儿怎么知道我们是父子?怎么在路上偶然一见就如此熟悉?自从毕业之后,我一直再未见过梁丽燕,这个疑问始终悬在心里,一直没有解决。
后来,我又在孙老师的围追堵截和街上几个同学的强拉硬拽之下,回校复读一年,考取八义集初中,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初中生。
(本文系作者文学自叙传《无奈人生》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