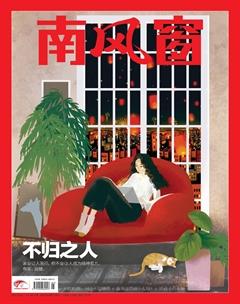爸妈,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回家吗?
刘肖瑶

年初北方的一波疫情出乎意料地袭来,“就地过年”成为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的春运,被抹去了熙攘。
许多人都着急。核酸检测、隔离,种种繁琐程序都不是问题,回家路漫漫,抵不过绵绵乡愁。
但另一些人,则是“正中下怀”。“就地过年”给了不想回家过年者最正当的理由,且不必承受“不孝”“冷漠”“矫情”“自私”等指责。
在他乡工作,身体劳累,回老家过年,精神疲惫。“就地过年”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是一次真正的休息。
2020年12月,北京大山子疫情复燃,乔山委婉地告诉母亲,为配合疫情防控,减少人员流动,不给国家添麻烦,今年就不回去了。
意料之中,母亲立刻坚决反对,埋怨她“宁愿一个人在外地过年也不回家探望父母”。数落一番后,母亲指责女儿丢人,因为“无法向亲戚朋友交代”。
在一个名为“春节恐归族”的豆瓣小组里,有这么一句说明:恐惧并非源于对回家本身有所抗拒,而是在节日回家的种种烦心事折磨之下,一种本能的反应。
潜意识里被与“春节回家”挂钩的诸种“烦心事”所困扰,包括“囊中羞涩”“逼婚”“风俗习惯难以接受”等主客观原因。
乔山形容自己这些年和家人的相处就像“螃蟹在水里慢慢被煮熟”。她多希望家人之间能真正互相理解、坦诚沟通,而不是为了一幅和睦的家庭图景,去回避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积弊已久的矛盾。
“有谁不愿意回家呢?如果真的称得上是家。”
“家是我羁绊最深的牢笼”
这几年,乔山过年回家的唯一活动与理由就是陪父母吃年夜饭,不想回家的原因却攒了很多,比如父母爱攀比、爱面子,很多话小时候听不觉得有什么,越长大却似乎越敏感。比如,每年回家,刚进家门爸妈就会劈头盖脸地问她:“你怎么又胖了?你看看谁家的女儿多瘦多白!”“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别人的孩子都结婚了!”
从5岁到25岁,在自己家里却始终逃不了“别人家”的压力,乔山哭笑不得。尽管在父母眼里,这些都是关心,但乔山依然不能回避内心最真实的感觉:“每次回家就像要上刑场一样,家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放松的舒服地方。”
有一年,乔山因事没能回去,表哥表姐立马找上她一顿数落:“ (你)父母活一天少一天。”“等他们死了你才知道回来过年多好。”“去上海北京上班有啥用?你也没存到钱,还不如回老家结婚。”……
代际之间,对生活价值与目标的理解差异,是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不愿回家的一大共通阻力。大学毕业后半年内,陈思都没有在北京找到工作,于是她去了天津,却不敢告诉家里人,索性今年不回家过年,“不想再顶着压力撒谎”。
每年回家,讨论母题都一样:被催促考公务员、早点结婚。“多大的人了还在外面漂?”每一次陈思试图向他们談及自己的职业打算、人生目标,但都会因为不在父辈心目中“稳定职业、尽早成家”的价值公式里,从而不被理解,更不被认可,交流沟通的机会一开始就直接被堵死了。
“不想回家,是因为自己心里始终有一道跨不过去的、不想面对的坎。”今年25岁的陈思说。
陈思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打压教育”下,责怪、辱骂是成长常态,家里常常紧绷着火药味,稍犯错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可不一会儿,父母又会和声细语来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
“父母对孩子有没有‘PUA?”陈思未曾对谁说起这荒谬的问句,因为她知道,类似独生子女、父母双全、家境不算糟糕这些要素加乘下,她已经是大多数家庭眼里的佼佼者了。
每年回家,讨论母题都一样:被催促考公务员、早点结婚。“多大的人了还在外面漂?”
但旋即她又陷入困顿:“家庭是用来比的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谁来听我这本经呢?”
因为父亲经商,小时候,陈思一家三口全国奔波,换了好几个城市居住,直到五六年前才回到母亲的家乡定居。对于那个情感上陌生的小城市,陈思的确感受不到归属。
但她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始终生疏,离家后更是“好几年没说过话了”。父亲是9个兄弟姐妹里的老大,“总是有种传承香火的感觉”,可惜陈思不是个儿子。“但不是就是不是啊!”陈思苦笑,从小到大,她偶尔会因为自己的女儿身份自卑,继而逐渐演变成委屈和愤懑。
26岁的小柒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百分之九十的眼泪都是父母给的”。
她说不上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过年回家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她无奈而无助地感受到,“我就像一头马戏团的狮子,永远逃不掉这个囚笼”。
从小到大,她认为自己在父母面前“就像一个高度封装的人”。记忆里关于“家”的片段,当然有数不清的爱与温暖,有严厉与责任,这些都是无可否定且深明感激的方面,但因为是最亲的人,小柒亦无法否定父母给自己带来的羁绊,甚至是阴影。
比如,小时候,父母不希望小柒与同学朋友交往密切,外出玩耍不能超过半小时回家,也不让她到同学朋友家里去玩,理由是“同学家不会对你多好”,依据则是,父母在他们的小时候,亲眼看到同学父母把好吃的藏起来。
而当小柒长大后念中学时,想到市里去玩,却再次被阻拦,理由成了“连个能陪着你的同学都没有”。
“是啊,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小柒在心底哭。但没有地方哭,站在父母角度,这都是为孩子好,在外人看来,也不过一句“不懂事”的指摘罢了。
小柒的奶奶也不希望她离开家太远,理由却是:小柒是个女孩子,奶奶希望她能留在家里,留在父母身边。
小柒哭笑不得,自然不敢在家人面前吐露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的酸甜苦辣,对待家人热切的“企盼”和“关怀”,也越来越无话可说,到最后只能摆出一副笑脸相迎,至于这一年来在外面积累的诸多心事和感言,再也不敢说出口。
她很羡慕那些可以和父母无话不谈的人,哪怕做不到无话不谈,至少能和睦相处。有长辈训斥她:“你是没经历过苦!对父母这般那般不满的,自己生一个娃试试,自己去体验一下做父母有多难。”
无从反驳。只有无止境的失语和自视理亏。
疫情暴发后,家里的弟弟告诉陈深,父母又冷战了,几天几夜没说话。
这是陈深成长记忆里的常态。自嘲为“新时代下青年腐化的极端典型”的他,自从2013年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有再回家过年。他在南方一座二线城市工作,工资不上不下,工作不咸不淡,也没有结婚生子的想法,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与家人的联系一直很淡。
这些年来,陈深一个人在外面走过失业、失恋,做手术,负债,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不愿意跟家里说,因为父亲从不关问,母亲则过度焦虑,在家里,父母常年爆发激烈争吵,一回家就是大型战争的观摩现场。
借着疫情,当陈深准备再发微信告诉父亲不回家过年,顺便发了一个拜年红包时,却发现自己被删除了。
一定程度上,“不想回家”的理由或许是千篇一律的,有主观上的疏离,有客观上的家庭矛盾。然而,这些撕裂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代际之间理解的错层,还是说,这一届年轻人,真的变得越来越敏感、“玻璃心”了?
回家热情似火,一催就熄
今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观澜园区挂出了一则走红网络的标语:“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春节留守,才是归宿。”此标语被网友戏称“宣传语秒杀月薪三万的文案”。
理解的不对等、观念的不同步,让更多“恐归族”面临着另一个共通的痛点—催婚、催生、催房三件套。
老家在东北、工作在北京的胡静今年33岁,硕士毕业后,她曾谈过一段持续4年的恋爱,结束后单身多年至今。然而,30岁以后,母亲开始焦虑不安。“催婚成为近几年我们母女之间矛盾的焦点”,但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所以矛盾通常在春节的7天假期里激化。
比如,尤其漫长的2020年春节,由于疫情而被困在家的小半年,胡静和母亲的交锋可谓一触即发。只要母女俩同时待在家中,任何话题最终都会被引向结婚、找对象。含沙射影的,春秋笔法的,直白明了的……无论胡静如何解释“还没遇到合适的人”,都会被母亲劈头盖脸地统归为“不上心”,她啐道:“等过几年嫁不出去了就孤独终老、寂寞死去吧。”
胡静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亲人不像亲人,不会体己理解,倒像咄咄逼人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地手刃母女二人之间难得的相处时光。
理解的不对等、观念的不同步,让更多“恐归族”面临着另一个共通的痛点—催婚、催生、催房三件套。
刚进入2021年,河北石家庄就暴发聚集性疫情,紧接着,北京燕郊出现确诊病例,河北与北京的通道封闭。
胡静把通告病例、政府通知都转给母亲,像转交一份“不回家合格证”,然后长舒一口气。“虽然远隔千里思念亲人,但只要想到我今年可以过个安静的年,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对“安静”的需求偶尔会掩盖对“团聚”的需求,这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无可奈何下,互相妥协、体谅的关系。
今年30岁的小楠与同性女友同居,在她多年的坚持与感染下,父母已逐渐接受了她的女友,但老家的姑姑、叔、姨仍在年复一年地为她找相亲对象,还不厌其烦地在其父母耳旁悄悄劝说:“女孩子还是要找个人嫁了。”
小楠能预料到,只要回家,心里紧绷多年的一根弦会立马溃决,父母救不了她,女友救不了她,无数“善意”却充满偏见的声音会如乱箭从四面八方飞来。“不回家是为了不对回家产生‘PTSD(创伤后心理综合征)。”
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
除了老一辈的催促,哪怕已经结了婚、完成了“人生大事”,已近中年的大雄也面临着另一种恐惧:没完没了的酒桌寒暄,同辈间的相互攀比、暗中较劲。
在哪里发财?
今年赚了多少?
换房了吧?开什么车?
在外面赚大钱,可不能忘了兄弟啊!
这些话大雄都要听烂了,年年如一,除了笑脸逢迎,别无他法。
这些年来,大雄慢慢感觉到,回家过年的喜悦其实早在他步入社会那一天就开始消淡了,儿时的快乐也被岁月浪潮冲走。“现在的过年只是一种形式,被迫攀比,炫富,聊天三句不离房、车、钱。人情世故而已。”
年味年味,年年无味
除了“过年回家”本身承载的压力,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春节承载的年味,的确有所消淡了。
疫情让29岁的杨天终于有了逃避一系列古老“乡俗”的机会,比如挨家挨户磕头拜年。“工作后劳损导致的腿疼是真的,为了防疫也是真的。”她苦笑。
杨天的老家在一个南方小城市,她记得小时候,对那些象征年味的习俗都是期待大于抗拒的,也许是自己变了,也许是老家变了,随着成长、工作,家里的老人老去,孩子们纷纷远走他乡,慢慢地,杨天感受到“亲戚间的勾心斗角”“老一辈的矛盾”越来越多,同一屋檐下,家人之間的交谈变得越来越冷漠,甚至是针锋相对。

这些都是很难细化、描述得具体的,但她十分肯定,那些潜伏在“温馨家庭”表面下的暗涌,并非错觉。
又比如,当“过年回家”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上的必要,这个“年”到底要怎么个过法,个体的支配权被某种程度剥夺了。
有人想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旅游,却碍于亲情的捆绑,情感上迈不出。比如刚年满30岁的阿豪。
因为工作地与家乡相距不远,防疫压力小,阿豪只好放弃春节的独自出游计划,回到广东南部边陲的县城家乡。
这些年来,家乡的景貌已经天翻地覆,“不是说发展得多快,而是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却没找到合适的来替代”。
在那个曾以浪漫著称的海边小岛,当路边摊老板说着纯正普通话卖给阿豪鱼丸粉的时候,当老人们把习俗带进城里的房子、却“怎么都显得别扭”的时候,当电视里的春晚越来越难看下去的时候,阿豪忽然“很矫情地”理解了“近乡情怯”四个字。
“怯”,是害怕对曾经熟悉的、怀念的东西产生抵触,害怕对家乡的失望大于期待。
这些年来,家乡的景貌已经天翻地覆,“不是说发展得多快,而是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却没找到合适的来替代”。
然而,当除夕前夜朋友问起阿豪今年怎么过,他苦笑着脱口而出:“怎么过?熬过呗。”
被迫也好,主动也罢,就地过年,不管理想中多么自由潇洒,有些东西始终是换不回来的。
“只有在外面流浪过,才知道回家的好。”对于那些主观上不愿意回家的年轻人,32岁的外卖骑手阿泉哭笑不得。他不否认,感觉得到这些年的“年味”正在丧失,不能放烟花爆竹了,很多传统仪式都在日渐消亡,春晚也越来越不好看了……
“但真正想回家过年的人不会在乎这些。”
阿泉眼中的“就地过年”,不是自由和朋友,不是轻松和惬意,而是接不到外卖订单从而失去收入。在阿泉居住的房屋对面,肉眼可见的工地停工、工厂停产,宿舍清空,食堂不开门,没有福利补贴,没有安置政策,还要自己支付房租。
“为什么‘春运成了中国的特色,而不是‘劳动运‘国庆运?”阿泉发问,“因为很多人是没办法在劳动节、国庆节回家的。”
对那些薪水微薄、工作艰苦的城市漂泊者而言,春节团聚,是他们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可以卸下一整年孤独与艰辛的安全堡垒。
“这是一种血脉里的追求。”阿泉这么总结,“不是要去指责那些与家里关系不好的年轻人,但希望他们别就这样放弃‘春运。”在阿泉看来,“春运”两个字,蕴含着一定机遇—重新倾听、凝视与拥抱家乡的机遇,要放在其他节假日,还真不一定能有。
同样,我们谈论家庭关系的矛盾、年味的消淡等等,也不是要否定年本身的意义。代际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成长、塑造的,一味逃避和沉默,只会让这种掣肘越深、隔阂越厚。
“回家过年”其实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短语,它蕴涵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與情愫,至少绝对谈不上清晰分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假,但这很难成为情感上回避与懒惰的借口,更并不能一棍子消解春节团聚的意义。
纵使“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至少,对那些主观逃避过年回家的年轻人而言,踏上春运的路,就已经迈出了愿意为理想状况作出努力的第一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