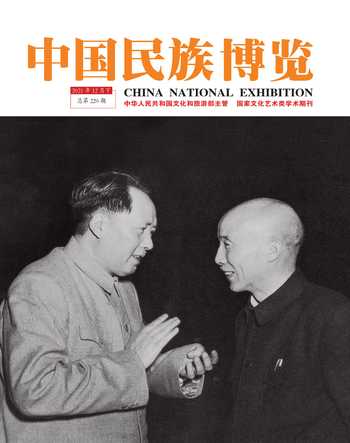中国山水画本体创新之浅论——以综合材料为例
【摘要】20世纪以来,“综合材料”及其表现与应用已然成为当下视觉艺术的一个热门话题。材料不仅是视觉艺术的媒介,更关乎着技法与形式、语言与表达、审美观念与精神内涵等的构建与发展。作为中国山水画核心内容的“笔墨”本身就既是工具,又是形式,更是精神。本文将以山水画的继承核心、山水画的创新原则、综合材料的有机介入及其具体方案探讨为框架,对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山水画本体创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当下山水画的创新实践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综合材料;中国画创新;山水画
【中图分类号】J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4-179-03
【本文著录格式】毛谷溪.中国山水画本体创新之浅论——以综合材料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12(24):179-181.
中国画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与人民文化的最佳载体与艺术形式,在构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点。山水画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在中国画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更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传统文化符号。它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生命观、自然观、美学观,更包含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形态与情感形式。随着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国文化、各类知识史无前例地汇聚在了一起,网络又将信息传播与多元运用推向了高峰。这对传统山水画产生了强烈冲击之余,更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新可能性。
当人们谈论山水画的创新,就必然要探寻人们究竟要继承什么。中国画带有极强的文化自律,因而具有自我生长的特性,其核心便是“笔墨”[1]。“笔墨”包含了三重含义:作为媒介材料的笔与墨;作为表现形式的笔墨语言与笔墨构成;作为文化内涵的笔墨精神。自古至今,“笔墨”的形制、款式、技法、效果、内容、含义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首先,毛笔与墨的物理特性为笔墨语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王微说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叙画》)中的“一管”指的就是毛笔。作为工具媒介的笔和墨,逐渐发展出关于“笔墨”的理法与程式,例如谢赫的“六法”与“六品”,“骨法用笔”的“骨”就因于那“一管”;又譬如历代山水画作品中的皴法,董源的长披麻皴与范宽的“钉头鼠尾”小斧劈皴都是对笔墨表现力与创造力的求索与总结。并且,在对笔墨理法与程式的不断继承创新中又慢慢构建起了“笔墨”精神以及中国画独特的笔墨审美趣味与品评鉴赏规制,比如“气韵生动”与“神妙能逸”。由“笔墨”所生成的又一个核心概念是“写意”,这也是与中国书法艺术血脉相连的。“写”是笔法的行为,是墨法的结果,是强调过程性的,还是书写性的,不生硬、不板结的;“意”是意象、意思、意气、意蕴、意境等,表达了“写”所需要承载的那些“形而上”。两个字都是发于主体与本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其目的是达到“气韵生动”。本雅明的“Thought-image”(“思想—图像”),正是表达“写意”克服了西方固有的“形象”与“思想”的对立,创造了一种“形而中”的“第三者”即“意象”[2],意象也体现了中国画体系中主客观的和谐统一。再由“笔墨”“写意”与“意象”共同生成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则是“意境”。意象是写意与情景的交融,意象的组合形成整体的氛围,即一种“境生象外”的诗性。“意境论”是受到魏晋玄学、老庄道学以及禅宗思想的共同影響所形成的中国画审美理论。宗白华曾说“中国是生命的体系,它要了解体验世界的意趣(意味)、价值”,因而往往有一种“哲学的美”,这种美、这种体系,便是“意境论”所集中体现的中国艺术的特点[2]。
那么,如何创新?从主体出发,当下的山水画创作者的身份、年龄、性别、背景等都与前大不相同,直接影响了审美表达的多样性。从客体出发,当下充斥着过载的信息与图像,目不暇接又不停变换的新事物、新景象,加之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参与了山水画的研究与创作,山水画的题材、对象、范围、功能等都得以持续拓展。本体关乎媒介、语言、技法、形式等,从本体出发,便是与主客体、与山水画的内在核心最为密切联系的。例如从宋到元的山水画巨变,这个巨变不仅是技法上,更是观念上的巨变;巨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材料的革新与发展。两宋时期主用绢本,偶有纸本。对书画颇有研究的明代文学家屠隆就曾提及“宋纸,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画多用此纸”(《纸墨笔砚笺》),例如李公麟的《白描罗汉卷》。最早用生纸“游戏笔墨”的是米芾,他所推崇的“天真平淡”与“信笔”都可在其《珊瑚笔架图》中窥见一斑。这对之后元代文人画“以书入画”“逸笔草草”的审美观念,注重枯湿浓淡的笔墨变化的表现技法,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4]。回到当下,媒介材料空前繁多,综合绘画亦相对成熟。“材料的选择在画面中一旦被确定,并融合于形象的整体表现中,便成为作者表达情感体验的语言载体”[3],综合材料对中国山水画的有机介入,为当下审美观念、表现形式以及社会风貌、时代精神带来了积极的探索意义,是全球视野下山水画创新的有力突破口。
所谓“综合材料”,即“mixed media”,指的是在视觉艺术中,混合运用多种媒介材料来进行创作的形式。与多媒体艺术(multimedia art)不同,综合材料的作品主要以传统视觉艺术为主,多媒体艺术则会将视觉以外的元素混合应用。综合材料艺术萌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远离了自然,于是这种对自然本能的亲近与神往最终走向了作为艺术本体的媒介材料,并开始关注其更具存在感的物质性以及由物质性所产生的特殊又多样的表现力。综合材料作品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拼贴(Collage)、组合(Assemblage)、现成物(Found objects)、变更的书籍(Altered books)、湿介质(Wet Media)和干介质(Dry Media)等。毕加索的《静物和藤椅》(Still Life with Chair Caning)被认为是第一件综合材料的现代艺术作品,这件作品就运用了现成物和拼贴的手法,试图打破二维的空间,以绘画的方式反思了“什么是绘画”。因此,运用综合材料的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其物质性的独立意趣与多元隐喻,从本体上获得对传统视觉形式的重构与拓展,以实现艺术表现和艺术形态的突破与创新。在艺术接受的理论中,有一个“陌生化”理论。这个理论是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1916—1985)提出的,他是20世纪俄国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形式主义理论的贡献者。他认为,创作者需要运用各种方式将其所描绘或表现的对象或内容变得“陌生”,这个“陌生”是相对于接受者的传统、习惯、固有的知识系统、稳定的审美经验等,并以此不断打破接受者原有的审美心理定势和思维惯性,来保证接受者能够持续且长久地获得对美的感知与体验。那么,从艺术接受的角度上讲,综合材料的介入,无疑是使其他视觉艺术形式增加“陌生感”的最佳手段。综合材料并不具有固定的、确定的边界与内容,相反,它是动态的、广泛的,它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是与时俱进且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因而,对综合材料的运用本身就是对时代精神与当下性的主动关注与思考。
有机介入,是立足于山水畫传统的,基于内在联系的,深层且和谐的介入。例如胡伟认为基弗(Anselm Kiefer,1945-)的作品《PIG》“看上去类似装置,但它却散发出绘画的意味”,基弗作品中的绘画性也并未因那些枯枝、花草、灰烬、金属、毛发等“现成品”而有丝毫减弱,“相反,这些‘别材’推动了作品的审美流向,打开了‘架上’的空间,使空气流淌”[8]。基弗的作品具有两个重要启示。首先,其作品对绘画本体构成了复杂的内涵与反思。由此,或许有另一个与山水画更为紧密的例子,即徐冰的《背景的故事——万里江山图》。这件作品是由亚麻、玉米麸、干花、垃圾袋、纸、玻璃等综合材料完成,借鉴了皮影的呈现方式,以光与影替代了水与墨,从正面观看作品,其水墨的淋漓晕染,笔墨的意韵、画面的意境与纸本的山水画别无二致。这种用“陌生化”的材料表现熟悉的视觉形式的创作动机,不仅是对山水画“笔墨论”与“意境论”的一种新论,更是对山水画本体的一种打破与探索。他所使用的材料均来自日常所处的生活环境,现成的自然物与人造物,这种物质与精神、形式与内容的多重表征又产生了极强的艺术冲突与文化深省。传统山水画“澄怀味象”“迁想妙得”的创作方式,自我与生活空间、社会自然的物我观照与人文关怀,正是以这种“观物载象”的匠心巧思得以被重新诠释并赋予更为微妙深刻的象征与寓意。或许可以说,基弗或徐冰的这种“装置性绘画”或“绘画性装置”,延伸了山水画创作的本体空间,增加了另一维度的视觉美感与内容层次,是因于“笔墨”又不限于“笔墨”的一种创新尝试。
基弗作品的第二个启示,是其充满了材料与形式自身所蕴含的抽象美感与晦涩诗意,这种美感和诗性,与传统山水画中的笔墨自律是相通且共融的。波洛克(Paul Jackson Pollock,1912 — 1956)的“行动绘画”与吴冠中的“抽象中国画”皆是对“有意味的形式”的有力践行。吴冠中曾说:“‘有意味的形式’,这‘意味’是什么呢,是情意、是诗意,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意味’,那么形式美失去了灵魂,空洞了,虽美,却乏味。”[4]他的作品中,往往形式的节奏与内心的感受相呼应,例如他的《逍遥游》,水墨的线条勾斫往复,环环相抱,疏密相间之中,又点缀着各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彩墨点,丰富变化却自有一套秩序。这种秩序,好像是“离经叛道”,不合章法,但恰恰与山水画的传统“程式”是一脉相承的。波洛克的作画过程与吴冠中——或者说与传统中国画正相反,是完全脱离画面的。那些自由落下的颜料,或跳动飞跃,或随性冲撞,却与画家的情感及无意识的审美观念相契合,充满了微妙的“不确定性”,又似乎达到了形式上的平衡与和谐,构成了“‘坠落’的妙趣”,这种“妙趣”正是“真正的‘笔笔生发’”[6]。也就是说,笔墨自律应当是“用笔”在心中,不只是在手中。因此,综合材料的有机介入,也不该是机械生硬的“照搬”和“嫁接”,而该是合乎胸中笔墨的“生发”和自律。
除此之外,综合材料的第三个突破点应当在于构成。关于中国画的构成,可以是笔墨构成,可以是色彩构成,亦可以是画面构成。国内最早将西方平面构成体系引入中国画的是林风眠,他融合东西绘画之长,将现代性的画面构成与中国画的东方意蕴相结合,从本体上拓宽了现代中国画的语言技法和表现形式。卢沉也是这一理念的继承者之一,他将“构成”作为单独的课程加入了中国画本科教学大纲中。他认为学习“构成”是为了以现代人的观点重新认识传统,“用形式法则这把刀从造型的角度解剖作品,汲取营养”,这样才能在自然空间与画面空间之间获得自由与平衡,从而达到“既会从笔墨方面欣赏,也会从造型方面分析”,从而“丰富我们的形式语言”的创新诉求[5]。综合材料对山水画构成的介入,其最典型的个案要数胡伟。胡伟始终坚持“把古典带到今天”的创作原则,“从传统绘画出发”,既善于发现材料,更善于运用与改变材料。例如他的《海礁》系列采用了传统山水画的横构图,并以平面构成的方式重新安排设计。所用到的主要材料是宣纸、麻纸、矿物、植物、土质颜料和金属渣等,是花了数年时间积累的,他在采访中说“除了海沙和珊瑚石是大海边取来的,其他的海礁、海水、潮涌等都是用宣纸做的,这些素材都是我在宁波现场做的,吸纳了宁波的空气和水。”可见这些材料,不只是“现成物”,而是成为了带有他个人情感与思考的特殊材料。他又以水与色的相互渗透浸融和这一过程中再造了自由流淌的色墨渍迹,从而表现出海水、浪花、烟云等意象,并唤起了其意涵的某种转化。胡伟所倡导的就是让绘画回到本体,让材料自语,水墨与宣纸是其材料美学的本体意识,构成便是融汇材料的视觉形式。
最后,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主体在变,客体对象在变,审美需求与观看方式在变,“笔墨”和“法”也在变,但其中的“理”是不变的。综合材料对中国山水画本体创新的有机介入,究竟怎样才能更具有内在的生命联系,如何去能扬长避短、去良性发展等,都是将中国山水画之于世界文化之林时,一个需要长期研究并付诸践行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牛克诚.中国画:生长的传统[J].美术观察,2008(1):9.
[2]马欣.本雅明对中国书法的美学阐释及其笔迹学背景[J].中国比较文学,2019(2):59.
[3]叶朗.再说意境[J].文艺研究,1999(3):109-110.
[4]胡光华、李书琴.论绘画材质之变与元代山水画观念和技术之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艺术与设计版),2007(1):20-21.
[5]陈守义.材质·构成·表现[M].杭州:杭州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60.
[6]胡伟.综合材料绘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J].西北美术,2018(2):39-40.
[7]吴冠中.文心独白[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1.
[8]胡伟.综合材料绘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J].西北美术,2018(2):44.
[9]北京画院编.卢沉论水墨画[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134-138.
作者简介:毛谷溪(1991-),男,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艺术硕士,主要从事:美术学、中国画理论研究。
3768501908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