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七岁起,就向往成为作家
图: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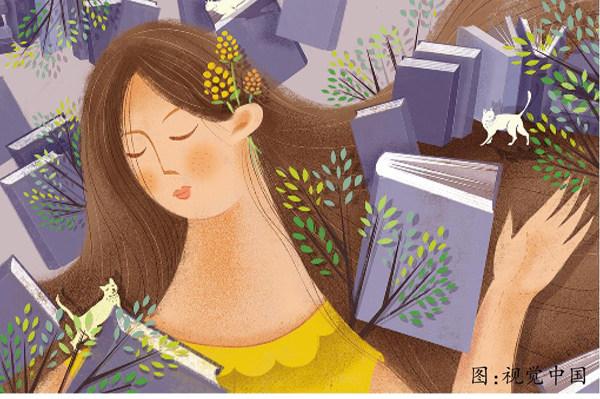
我有一位朋友,一直对父母心怀愧疚。
她父亲是学物理的,母亲是学农业的,二老至今还会对着书架上那一长溜专业书感慨,本来都是留给她的——她学的是新闻。
她为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而愧疚,我对朋友说:我家,也有过这样一长溜专业书。
我的父母学的都是无线电,他们不仅是高材生,还是动手能力很强的能工巧匠。我家早在1976年就有了电视机——是我父亲自己组装的。从小到大,修电器,打家具,房屋装修,疏通下水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是他俩不能搞定的。我母亲经常说:“这些都很容易,只要有零件。”我父亲的口头禅则是:“荒天饿不死手艺人。”
可以想见,我的父母完全没有“女生不能学工”的偏见,他们的想法非常清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希望我长大后当一名工程师,这是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都能养活自己的选择。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我准备了一整套木工工具,父母借助一切机会教我使用锯、刨、斧……但我只想看书,只想进入文学的世界。
在父母的期许里,我高中读的是理科,虽然我很想读文科;我大学读的是工科中的工科——机械制造。高等数学、制图测绘、工程力学……每门课都是我当年的噩梦。
大二那一年,我像所有工科生一样去实习。老师要求我用一个星期锉出一把锤子的8个面,我用了40个小时才锉出一个面。老师一看不行呀,叫来一个男生,他用2小时就锉出了其余的7个面——工作效率是我的140倍。
这种无能,在某种意义上反而让我解脱——都差到这种程度了,去工厂,去实验室,最好的可能也是浪费国家财物,万一出啥事故,还连累生产和众人。最终,我走上了另一条路——写作。
作为作家,我从来没红过。
有一年,我看了李长声的《日边瞻日本》,他在里面说某作家“没什么名气,像众多的作家一样,是给著名作家和流行作家垫底的,不然,就那么几本名著或畅销书可构不成文坛”。我就笑起来,觉得那像在说我一样。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质疑自己的写作能力。
行年至此,我已经明白,我其实没有才华。承认这件事,多少有些令我难堪。但才华真是上天给予的大红包,给你多少你就得到多少。我写了这么多年,写得也不好。我心想,这世上的垃圾書已经满坑满谷,何必再多我这一本?
直到有一次,我走进人生的幽林。最痛苦的时候,是阅读给我以安慰。我不能看艰深的著作,因为痛令智昏,我的脑子不够用了。我就随便翻看心灵鸡汤,忽然被一句话击中,掉下泪来。
那一刻我明白了:只要我曾经安慰过一个人,我的写作就是有意义的。只要有一个人曾经从我的文字里有所收获,我就没有白写。
文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共情的可能性”。读者可以借助他人的故事,甚至虚构的人物,来了解其他人是如何想的,让自己有部分“设身处地”的能力。
比如,你觉得乱臣贼子罪不容诛,不妨看看《麦克白》,到最后,你很可能是同情他的。麦克白有才干、有权谋,只因为不是法定继承人,他就不能当国王。
以我自己的立场,我以为只有文学作品能带给人这种想象、这种对他人的怜悯,以及对自己的洞见——你最黑暗的念头,原来早已经被写在书里了。你不是独一无二的“恶魔”,你只是个普通人;你最见不得人的经历,原来也有雷同。
很好,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不孤单。写作与阅读的意义,就在于这精神的慰藉。
除此之外,音乐、绘画、雕塑和文学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对朋友说:扔下愧疚吧。父母的期许,不该成为你的枷锁。
而如果有机会重返高二分班时刻,我会勇敢地对班主任说:“不,我要学文科。不是你说的那样,只有成绩差的人才学文。我成绩够好,但我从七岁起,就向往成为作家。”
3890500338291
——他者形象的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