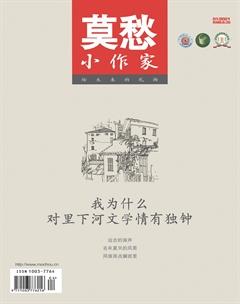那房子,妈曾住过
晚上,和父亲通话,不知不觉聊到以后买房的问题。父亲似乎很理所应当地说道:“到时候我把房子卖了,给你付首付,我回老家住去。”
我一直很逃避这类现实问题,却没想到父亲早有打算,一时间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说道:“你卖了干什么啊,那房子,好歹,妈以前住在里面……对啊,妈住过,你卖掉干什么。”话刚出口,眼眶就有些湿了。父亲可能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一时间,电话两头尽是沉默。我急忙岔开话题,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那房子,妈曾住过。”我望着窗外的夜色,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目光不自觉地低垂了下来,垂到了黑夜最寂静的深处。
母亲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已经习惯了和父亲相依为命,习惯了没有母亲的家庭和生活,但那份思念只是退避到一隅,不曾凋谢。
它就像是伤口上的痂一般,平日里显出枯树皮的模样,让日子从上面安然地路过,但一旦被撕开,累积的思念就会喷薄而出,让人先是沉默,然后哭出声来。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越来越硬,泪腺越来越不敏感,但在那一刻,我也只是一个思念妈妈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动过卖房子的念头。
家,本来就已经散了,只剩下两个人。房子是家的物化,也是原来那个完整的家最后的痕迹与守望。
所有和母亲有关的记忆,都在这个房子里发生。因为残疾,母亲几乎不出门,每一个房间的每一块地板砖上,都有母亲的脚印。也只有在这个房子里,母亲还一瘸一拐地行走、生活,在过去,在光的上方,在时间的镜像里。
人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要靠联想的。正所谓触景生情,有一些深埋在岁月中的回忆,一些简单、微小,却足以让心脏重重一跳的细节,只有在我们重回到那些地方时,才能解锁,才能透过灰尘,摸到钥匙。
只有这个房子还在,我才能让自己相信,母亲始终陪伴着我。那份我只拥有过十几年的母爱,那份我还没握紧便失去的母爱,只有在这个房子里,我才能触摸到它的余温和轮廓。如果我连这个房子都失去了,那我就真正地、永远地失去了母亲。
我们终究要在一些事情上妥协和抉择。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失去这个房子,等我再回到这里时,该是什么心情。我连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回忆和痕迹,留给我的最后一份馈赠,都没有守住,多年之后,我拿什么去见黄泉下的母亲。
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新房子吧。但至少,在我年老的时候,不会望着用老宅换来的新房子空流泪。或许我会一生潦倒,但我不是一无所有。
那房子,妈曾住过。再大的伤痛,在房子里睡一觉,都会得到治愈。那房子,简陋却温暖,它记得我们在里面流过的或酸楚或幸福的泪水,然后倔強地站在时光的隧道里,成为我心灵永远的港湾。
仇士鹏:江苏省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 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