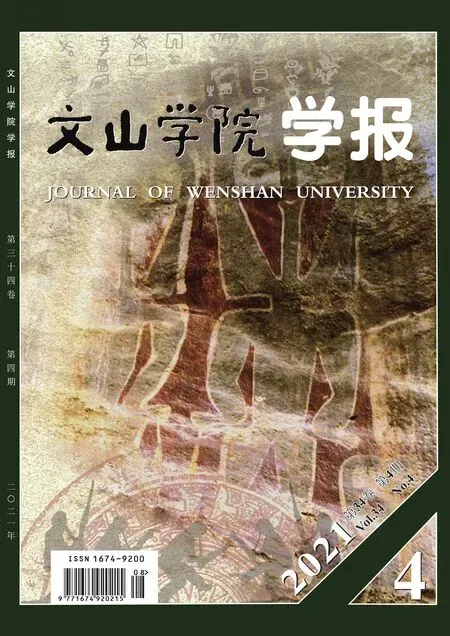有《山本》,无“山魂”
——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的创作问题
周小东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自陕西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公开出版以来,随即便收获着广泛的关注,好评者盛赞,甚至有论调认为“《山本》可与《白鹿原》相媲美”。然仔细审视却会发现,被“鲜花与掌声”簇拥着的《山本》实则问题颇多。它的价值取向比较混乱,叙事结构松散失衡且涉嫌自我重复,人物形象又偏类型化,扁平化,某种程度上是一部缺乏创新点与突破意识的作品。
一、主题价值的混乱
仔细梳理作品便会发现,《山本》所描绘的三个主题,即革命历史主题、爱情主题、秦岭风物主题偏于琐碎,彼此难以协调统一。按照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谈,他最初是以为秦岭动植物“写记”的目的去谋划取材与布局的,但后来因能力与体力的不足而转向去写发生在秦岭山中的众多传奇故事。由此不难看出《山本》创作所具有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首先便反映到作品的主题价值取向方面。通过作家以充满象征与写意的笔法,曲折表现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思考中,读者难以把握最真实的秦岭生活,也未能体会作品真正所要传递的思想价值内涵。
作品首先表现的是革命历史主题。在《山本》中,贾平凹希望以土匪、国民党武装力量、共产党游击队三方势力的争斗结构起秦岭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但作家还原这段历史所采取的方式却出现了差错。他认为革命历史斗争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流血杀戮,于是便在作品中付诸了密集的暴力死亡的书写,反复通过“血”“肉”“性”“脑浆”等词汇冲击着读者的视神经线:游击队转移来到云梁寺,游击队员随意杀害因不了解情况而惧怕逃散的无辜百姓;土匪五雷袭扰涡镇大肆烧杀抢夺,侮辱妇女,国民党保安团内部却在进行血腥的权力争夺,任其逍遥法外;农民协会会长使强耍狠用滚烫的蓖麻油残忍杀害当地财东;井宗秀为给哥哥报仇,活生生将刑瞎子剐死……随处可见的“暴力流水账”式的叙述与无理性的杀戮场面难以让读者相信涉及秦岭的历史故事便只是这样,历史的神圣性全然消解在了这些鲜血淋漓的文字之中。其次,依据作家在作品后记中所谈的“(秦岭——文章注)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①“《山本》里虽然到处都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他记述的既是秦岭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中必然寄寓着自己批判的玄思与“形而上”的人类意识。贾平凹美好的创作意图当然值得肯定,但至少在《山本》中,作家创作的构想与批判的雄力被他那混乱的话语准备与价值取向淹没了。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之路我们知道,自《废都》始,作家便有意识地模仿明清市井小说的叙事语言与叙事方式。此类型的行文选择成为他中后期作品鲜明的个人特色,但应当看到,这样的个人特色对作品主题价值的阐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山本》中,“那山叫莲花山,山头上一簇五个峰,峰上都长着红豆杉树,更有成片成片的绿叶黄花的棠棣,又还是太阳要落,晚霞烧起,万般艳丽,两人就在草窝里做起那事。杜英还在经期,血把他们的腿上、肚子上都弄红了,也全然不顾,待折腾完,像鱼晾在了沙滩上张口喘息。就看着远处的鹤雉一边走一边鸣叫,后来飞到一棵红豆杉上了,将尾巴直竖起来,尾巴竟然长六七尺。”“他没有松手,一直在掐,一直在掐,他觉得力气都快用尽了,但这时候蛇的身子也软了,绽开了扑沓在地上。井宗丞拿了枪再打,打了三枪,蛇断了四截,他喊着杜英,杜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左腿开始发黑,人昏迷不语了。”井宗丞作为游击队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头脑清晰,有勇有谋,具有十足的英雄气概。但如此重要的人物竟会突发奇想,与配偶在山林间行快活之事。读者通过此种类型的叙述方式很难感受到革命的严肃性与崇高感,而只留下粗俗,荒诞的印象。再则,井宗秀一行人蛊惑傀儡县长将县政府搬迁至涡镇的描写明显也是作家价值取向混乱的明证。试想,即便是在战乱年代,县政府驻地的选择与搬迁也要进行多方面周密的考察,怎能随随便便盖几间房子,拉几支队伍便将政府机构搬离。《山本》明显承认了历史的虚构性与荒诞性,且作家采用民间化,个人化的写作视角书写下一段“一地瓷片”的历史。但事实上这种话语方式所阐述下的历史文本却无法真正诠释出 “山”为何物的主题思想。
《山本》第二个主题或许可以称为爱情主题。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谈道:“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显然作家对秦岭山中酝酿出的“爱之花”是抱以呵护心态的。我们知道,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对它的歌颂是文学永恒的母题。而纯美如水的爱情在贾平凹此前的多部作品中均有所呈现,如《满月儿》《带灯》《秦腔》等。作家在这些作品中建构出一个个纯洁柔美干净的明亮世界,供小月和才才,带灯与天亮,引生和白雪们的爱情“自由生长”。但反观《山本》,作为同样涉及爱情主题的文本,作品中爱的美好质素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段段“爱欲失范”的庸俗琐碎画面。恰如鲁太光所评价到的:“就《山本》来看,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情感描写的失败,即在情感上,作者不能给人物以出路,也无法给读者以出路。”[1]
作品主要记述了秦岭山深处一个名为涡镇小山村的现代历史进程,以陆菊人与井宗秀的“乱世爱恋”为主题。陆菊人本为寿材铺老板杨掌柜为儿子杨钟收养的童养媳,与涡镇的正义英雄井宗秀并无瓜葛。但一块充满神秘色彩的胭脂地却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继而生发出一种模糊的畸形暧昧关系。文本中,陆菊人虽为杨钟的妻子,剩剩的母亲,但她对这两位亲人的感情却十分寡淡,反而全身心迷恋起了井宗秀:“那夜看了耍铁礼花,陆菊人的脑海里就一直是井宗秀浑身火光的样子……她真的高兴,井宗秀当上团长了。”井宗秀光辉潇洒的身影令陆菊人生发出一种异样的无意识心理。这种无意识驱使陆菊人完全放弃了对自己那不成器丈夫的管教,遗忘了儿子已经摔成跛子的悲惨现实,却整天做着井宗秀因为她的三分胭脂地而飞黄腾达的“黄粱美梦”:“井宗秀怎么就当上了团长,或许三分胭脂地起了作用?自己就暗暗有了些得意。”随着故事的推进,依照前文的叙事逻辑,杨钟死后井宗秀会顺理成章的与陆菊人结为夫妻。但作家却无意于此,后文出场的美女人物花生成为他为井宗秀所挑选的妻子。“花生突然听陆菊人说出找婆家的话,回过头来,脸就很快红了。陆菊人说‘咋不能,我慢慢教你么。’”“小往大长哩么,你要愿意,我慢慢给你养着”“我给你养着她的时候,你不要吓着她”。为了给井宗秀安排一位“像自己一样的女人”,陆菊人(贾平凹)“规训”着花生的一言一行,却也一步步将“花生下的单纯”女子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因井宗秀的性无能,成婚后的花生生活倍感压抑。加之井宗秀怪异的性格,花生根本没有享受到丈夫带给她的爱与幸福。陆菊人当然明白花生的处境,但她对这个美丽女人的同情却也只是流下几滴苍白的眼泪而已。花生凄惨的遭遇映现着陆菊人的自私,更反映出作家情感描写的无力与价值取向的混乱。一男两女三人充满悲剧的怪异情感完全将贾平凹欲意借情感主题揭示深刻人性内涵的愿望吞噬。这种粗糙的情感呈现方式对作品主题的伤害是根本性的。
作品第三个主题叙写的是秦岭自然风物。贾平凹在后记中记述:“曾经企图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这便是说,深受《山海经》影响的贾平凹最初的计划是创作出如《山海经》一般伟大的作品,只是后来意外地改变了初衷。不过作家还是“通过塑造麻县长这个人物形象以潜隐的方式呈现着自己的创作初心”[2]将秦岭的自然世界展示给读者。一方面,秦岭作为“最中国的一座山”,其人,情,物是必不可少的存在要素,作家显然深知此点;另一方面,将秦岭山的优美与神秘共同结构为作品的主题思想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将“庞杂混乱”的材料巧妙与文本融合却不显得突兀,生硬,这考验着作家的创作功力。就阅读《山本》的感受来说,作家并没有恰当的处理这些素材,《山本》中的秦岭风物只是大量动植物材料的堆积与“贾平凹式”的介绍:“白起说:这是连翘,没长叶子就开花,花黄得像金子,果实还生着的时候是青而圆的,一旦熟了是黄的,大张口。这是绞股蓝,延蔓生长,五片叶子攒在一起,结的籽有豌豆大……”“一只林麝在奔跑,牙齿露在唇外,呈镰刀状,跑到一棵树下了,将屁股在那里磨,印出浅褐色的腥味东西来,留下了标记,然后就在草地上晒着腹下的香囊,香囊分开来散发出浓浓的奇香,蚊虫飞来,香囊又合起来,包裹了那些蚁虫。”必须明白我们阅读的并不是“动植物百科大全”,此种类似直接摘抄科普读物的语段扣不住文本的主题,更构建不出作品的深度,广度与超然的普世价值。《山本》看似翔实丰富实则单纯直白的动植物罗列介绍与整部作品所要阐明的精神气韵的关联暧昧不明。从侧面看也显示出贾平凹“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进而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3]
作家在题记里写着:“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作为从秦岭大山走出的精英,贾平凹一方面计划为这座山留下一部光辉的纪念册供后人瞻仰;但另一方面他又欲以秦岭为“核心元”,建构出一部反映历史变迁,文明发展的民族史诗。如此宏伟的创作意图需要作家倾注巨大的精力与耐性。比较遗憾,贾平凹在《山本》中虽然安排了多个主题对 “山之魂魄”进行阐释,并生发自己的关怀意识,但此举能否将“山”隐秘的本质内涵揭示出来仍尚存疑惑。
二、叙事结构的失衡及重复
优秀小说的叙事结构能够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但《山本》却在叙事结构方面存在着失衡与重复等问题。作品开篇交代陆菊人带来的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制造悬念,并围绕此点结构小说,铺陈出一系列人物事件与矛盾。贾平凹通过对这些人与事的叙述,描绘出涡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及其历史进程。应该说,这样的布局选择还是比较容易编写出一部情节丰富,悬念迭起的故事文本。但缺憾之处在于,作家并没有以良好的艺术手段对这种结构布局做出巧妙的安排。
首先,《山本》中人物形象及情节的设立与作品结构的架设并不平衡。井宗秀作为贯穿整个文本的关键人物之一,无论是他阴差阳错获得胭脂地后睿智地谋划事业,使自己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乡里能人”,风光无限;还是周旋于土匪五雷与王魁之间的圆滑算计,巧妙获取麻县长的信任出任预备旅的旅长,并最终成为涡镇实际的管理者,作家对他的蜕变过程倾注了大量的笔墨,欲将井宗秀塑造为一位似白嘉轩一样串联全篇的“灵魂人物”。但这样一位机智果敢,拥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形象却最终被糊里糊涂的暗杀,性命草草收场。或许作家认为故事的发展脉络已经推进到此种地步,只有安排井宗秀的死亡才能保持叙事的张力,彰显主题。但即便如此,鉴于井宗秀是串联整部作品脉络的关键人物,作家又花费许多精力着重塑造此人,便有理由对他的死亡结局预先进行文学化的铺垫与渲染,以平衡作品结构。而不是将主要人物的命运出路突兀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写法很容易使读者产生阅读的阻断感,极大地降低了作品的可读性。
其次,三分极具神秘色彩的 “胭脂地”以及涡镇由弱至强的蜕变历程是《山本》的两条关键线索。前者在作品绝大部分篇章均有所涉及,但却在井宗秀成为预备团团长后对其提及突然减少,似乎这块风水地已经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井宗秀仰仗着胭脂地出人头地),可以按下不表了;后者则贯穿全篇。在此,作家有意将涡镇设立为一个形似“仁义白鹿原”一般的文学场域,供众多人物活动,制造冲突。于是他便对其由乡镇发展为县城再到军事重镇的蜕变过程着力进行了表现。这一过程占据着相当大的篇幅:井宗秀未发迹之前,涡镇只是秦岭东部一个不起眼的小乡镇。伴随着井宗秀的成长,涡镇摇身一变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县城,拥有商业街、学校、驻防军队以及足以匹敌正规军事要塞的强大防御工事。但就是“铁桶”一般坚固的涡镇却在红军仓促且简单的几轮攻击下顷刻化为乌有,烟消云散。在此,作家对这些材料的架构使用上明显出现了偏差,因而借战争外衣所搭建的文本结构的失衡才会在《山本》中暴露得如此清晰。
《山本》在结构上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对读者所熟知作品结构的拼凑模仿与重复化使用。小说开篇便提到一块极富神秘色彩的胭脂地,但此种手法与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安排白嘉轩利用骗局“换”来风水宝地,并依仗宝地成为塬上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布局方式竟然如出一辙。同样性质的一块地,对人物命运的发展与作品结构的架设几乎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不能简单归因于巧合。再则,《山本》中作家借多位人物性格面貌的展现去组织故事,结构文本的做法与《白鹿原》也比较相似。每每读到涉及井宗秀的叙述片段总会情不自禁将他与白嘉轩抑或鹿子霖进行比较。两部作品同样围绕这些男性形象从小人物到地方权威的奋斗历程串联起整部作品。但差别在于,陈忠实为白嘉轩与鹿子霖安排的情节事件与人物契合程度比较高,使人物完全能够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里充分施展拳脚。而白嘉轩也完全可以成为作品灵魂之所在,从而支撑起整部小说。反观《山本》,井宗秀作为统领小说的关键人物,形象是否立体,性格内涵是否丰富暂且不谈,仅仅是那些围绕人物形象结构的故事框架也是漏洞颇多。试想,战乱年代,一个水烟店老板的二儿子,起初仅仅是位卑微的画匠,庸庸碌碌,但却在父亲埋入“胭脂地”后惊奇地迎来了逆天改命的好运势。这种为了安排叙事而勉强为之的写法以及过于理念化的阐释着实将严肃的叙事逻辑与文本结构进行了消解。除此之外,作品看似情节丰富,主线明晰,又以多条线索共同推进叙事,但这些线索并不像蛛网一般密集紧凑。就以秦岭游击队为例,这支队伍完全成为一个游离于作品之外的尴尬存在。作家在需要它登场之时便将其随意拉出,而后却又突然中断这条线索,跳去讲述与之不相关的其他事件。这种缺少全局视野,忙于局部应付的创作姿态从某种程度上审视也暴露出作家在灵活运用前后照应,巧妙安排文本结构等方面能力的欠缺。
此外,只要比较系统地翻阅贾平凹十几部长篇小说,便会清晰的生发出一种似曾相识的阅读感受,即作家涉嫌自我重复,以致一些叙事片段与故事结构重复性出现。《山本》中,井宗丞和杜英在野外行事,不料杜英被蛇咬后毒发身亡,懊悔不已的井宗丞“竟解开裤子,用手扇打,要把它扇死。没有扇死,又想杀它,但没有刀子,就从口袋摸出火柴点着了去烧。毛是烧焦了,烧伤了皮肉,他倒在地上哼哼,眼泪流下来。”这种自虐生殖器的叙事选择与《秦腔》中疯子引生偷白雪内衣被发现羞愧难当,从而挥刀自宫的描写模式完全如一:“我掏出裤裆里的东西,它耷拉着,一言不发,我的心思,它给暴露了,一世的名声,它给毁了,我就拿巴掌扇它,给猫说:‘你把它吃了去!’猫不吃。猫都不肯吃,我说:‘我杀了你!’拿了把剃头刀子就去杀,一下子杀下来了。血流下来,染红了我的裤子。”[4]陈先生多次安慰白起给生病的胃说好话的语段在《高兴》中刘高兴同样对五富说过:“不要一天到黑都想着我有胃病了。而要不断地感谢胃,它出了那么多血,现在还每天给你装了饭呀菜呀消化着,你要给它说好话哩。”作品中其他雷同的结构现象还有许多。花生在嫁给性无能的井宗秀后因情欲得不到满足而饱受折磨的苦痛情形便与《五魁》中的相关结构安排大同小异。此外,带灯时常在镇政府大院发现的神秘人面蜘蛛在《山本》中依然出现,且这种蜘蛛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完善文本结构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与《带灯》相比几乎毫无二致。这些雷同化的书写频率如此之高,显然不能轻易判定《山本》具有创造性。因为创新所产生的基础和土壤必定源自生命感受与生活积累。不幸的是,贾平凹在这方面却呈现出一种尴尬的“贫血”状态。受此影响,《山本》失序的文本结构也必然不会对何为“山之魂魄”做出确切的回答。
三、人物形象的扁平化
人物形象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意图与载体。某位作家之所以被载入文学史画廊,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语言与题材方面做出了创新性贡献;但更重要的在于他所塑造出的人物形象立体且典型。若以此标准观照《山本》却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够典型和丰满。作品中,贾平凹主要从“自然”“人”以及“人的生活”入手,表现他对“山”的理解。作家首先通过对秦岭自然风物的展示为读者还原出一个自然化,生态化,野性化的秦岭。此层面的秦岭纯粹是自然的,其内涵本质并不突出。而作为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仅仅从自然入手结构文本,阐发主题,显然难以将深厚隐秘的“山”之内涵表现出来。这就需要作家赋予“自然山”“人与生活”,借助人物的活动及其他们的生活从更高层面展示一座“人化的山”。我们知道,优秀的小说家均是通过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去组织故事结构,彰显作品价值的。关于这点,陈忠实在他的创作随笔中曾做过相应的表述:“不是先有结构,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述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5]想必贾平凹深谙此道,于是他才在作品中有意识的塑造出大批人物形象,欲通过他们达到触及“山”之灵魂的目的。但遗憾的是,作品对这些人物及其相关生活的书写是失败的,作家并没有真正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揣摩他们。因而《山本》中类型化、扁平化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而立体,具有丰富人性内容与文化内涵的形象却难以寻觅。
《山本》中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达190余人。考虑到为如此之多的人物逐一取上名字,组织他们的行为活动确实是一件颇费心力的工作,因而作家为超过半数人物安排死亡结局的做法倒也情有可原。其实作品真正的问题在于,作家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与逻辑性要求。先谈主要人物。井宗秀起初是以涡镇守护者的面目示人。他善良儒雅,讲道义,重感情,懂得收买人心。但这些可贵的品质后所隐藏的狰狞面目才是他的真实本性:设计杀害与土匪有染的结发妻子;修筑城墙时将捉来的保安队员活填在了地基中;为封口而残忍杀害孙举等等一系列的恐怖手段让人在不寒而栗之余不禁疑问:井宗秀这些行为的深层心理动机与他所表现出的性格特质是否一致?其次,作为整部小说的关键人物,作家着重渲染了井宗秀的才气,匪气,霸气,但却在文本后半段突然将他的死亡通过一场杂乱,诡异的战斗草草地呈现给读者。而读者显然对于井宗秀抱有极大的阅读期待,作家将这个人物的起点设置得如此之高,最后却又安排给他一个平淡无奇的死亡结局,甚至连必要的悲凉气氛都未能为之营造。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在过于草率。
作品中另外一个主人公陆菊人形象的塑造同样是比较失败的。陆菊人作为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子,却诡异的展现出极具现代意识的商业头脑与超强的企业管理意识,共同运营着几处大茶行。仅仅凭作家认为她是金蟾的化身这般简单的交代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此外,作为杨家的童养媳,陆菊人因为出嫁时带来的三亩胭脂地而将她的命运与涡镇英雄井宗秀连接在了一起。而后经过一系列的动荡她竟然一跃成为井宗秀最为得力的助手,涡镇实际的“女掌柜”。但在这个过程中,贾平凹先入为主地让人物服从理念与情节的需要,并没有对陆菊人从童养媳到女强人身份的巨大转变之间做出必要的事件交代以充实她的面孔。事实上,陆菊人形象的 “形销骨立”一定程度上隐藏着贾平凹矛盾的创作态度。一方面,作家想让陆菊人成为一名能撑起整部小说框架的亮色人物;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恰当地赋予这个亮色人物闪光的必要质素,使其丰满,生动。缺少骨架作为支撑,“站立不起来”的陆菊人犹如一潭死水——无色无味,“波澜不惊”。除此之外,作为一位几乎每个章节都要出现的高频人物形象,宽展师父也是一个缺少意味的存在。经作家处理过后呈现出来的这个形象却只是一个会吹尺八,会念经,没有主体思想,缺乏生气的哑巴尼姑符号。她既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也没有突出的性格特征,更没有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任何推动作用。
《山本》中几位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不具备立体之感,他们均被作家随意的“使唤着”。五雷作为土匪大架杆,刚登场时显得有勇有谋,对属下的领导也比较得力,但后来却窝囊地命丧二架杆王魁之手。五雷的性格表现与他前后行为的巨大不对等显示出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缺乏统一性考量的弊病。再看另一位出场较多的人物陈先生,他被作家当作一位颇具道家气质的智慧人物而着重表现。但这个形象的出现却让读者不得不将他与《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进行比较。陈先生虽时不时地说出一些智慧的话语,并自觉与外界的争斗保持客观距离。但与朱先生相比,他的智慧气质与传奇属性仍是比较薄弱的。陈先生看似精明的话语更多讲的只是因果报应,宿命轮回这类“鸡汤式”的大道理,缺乏更深层次的思想性,指向性。这样的人物与作品的内涵呈现“两张皮”,各说各话。此外作品中出现了太多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例如杨钟,蚯蚓等人。杨钟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游手好闲,猴气十足。他的性格始终如一,没有发生变化。而蚯蚓则完全成为井宗秀的跟屁虫,被井宗秀强大的个性气质所笼罩,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念或特征。在准备进一步揣摩他们之时,却立刻发觉这些形象的心灵特征实际上是一望即可的,并不存在更深层的奥秘。纵观整部小说,这样单薄没有亮色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他们好似无根的浮萍,随风飘摇。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过: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写作呈现出的部分问题在于他们均不能良好的集中于某一人物的灵魂。像王安忆90年代写作的小说只集中于一两个人物身上的作品如今越来越少。当下作家们的小说中看似人物成群,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人”。此言非虚,许多读者在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均希望在作家智慧的结晶中发现“人”,进而发现他们自己。这是对一部作品最实际却也是最严苛的要求。若以此审视贾平凹的创作便会发现“贾平凹小说里的人物,几乎都不会说‘自己’的话,也不会‘自己’说话。他们都在说着贾平凹的话,老在那里‘贾平凹’‘贾平凹’着。不管什么人,不管他们说什么话,都是贾平凹的话。”[6]长久以来,贾平凹的创作很难在人物语言与他自己的叙述语言之间寻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与融合。同时他也难以将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彻底剥离,因此许多人物形象均可以视作他精神气质的投射,是镜像化出来的贾平凹式的人物,他们共同“说着贾平凹的话”,喜好着贾平凹的喜好。作品粗看人物众多,内容翔实,但真正经得起品味的“人”并没有多少。《山本》虽写秦岭,但我们识别不出真正具有“秦岭”内涵的秦岭人。有山无本,“失却魂魄”的《山本》,毫无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根本无力承担作家“为秦岭立传”的伟大关怀意识。
四、结语
总之,《山本》虽以反传统的书写描摹出秦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并“挑战了既有的叙事思维和表现方法”“对历史的叙述展现出新的途径和审美性开拓”。[7]但应当看到作品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却不幸出现了偏差,然而这样的作品却仍被盛赞为“经典”,此举是否会间接导致作家陷入“自我迷失”的泥沼?行文至此,我们对贾平凹《山本》所存在的问题简单进行了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山本》看起来仍像是作家艺术驻足期与风格探索期的作品,拥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正如陈思广所言:“适当的驻足是为了更好地前进。”②显然作家真正能够被铭记的作品仍没有出现。而另一方面,对于读者来说也殷切期望曾经登顶文学之巅,如今仍有希望再次登顶的贾平凹能够静下来,慢下来,积极深入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从而创作出一部真正“有山本亦有山魂”的伟大作品。
注释:
① 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以下所引原文均出自此书,不再标明出处。
② 陈思广在第二届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