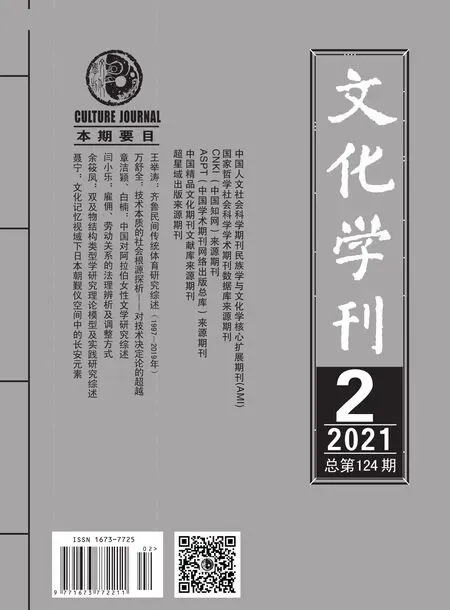“文如其人”命题的模糊性与重实际倾向
——从中国思想传统角度分析
杨 琪
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命题“文如其人”的讨论大多立足于对“文”“人”含义的分析,或基于一位作家的生平及作品来阐释“文”“人”,或与西方相似命题如“风格即人”进行比较,或运用西方文学术语对此命题进行阐释,或从跨学科视角如心理学等角度切入。目前,学界对“文如其人”命题的研究,重点在于从文论史角度对其进行梳理,以及在当代视野下,尝试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重建[1],缺乏在宏观文化层面上对此命题的探讨。邓心强谈到目前“文如其人”命题研究存在的不足之一便是“缺乏从宏观上对该命题为何如此顽固并深入人心的文化学探讨”[2],因此,从宏观层面的思想文化角度,对于此命题的分析尚有不少空白。而用西方理论阐述中国古代文学命题时,必然面临着思想文化基础和语汇系统不同等问题,因此,应当注意结合中国的传统语境,辅之以适当的中西比较进行研究。蒋寅认为:“‘文如其人’的命题成了一个模糊判断,随便说说倒也简单明白,一加以推敲,就发觉其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明确。”[3]
本文基于邓心强和蒋寅指出的“文如其人”命题尚未解决的问题,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文如其人”命题的产生与流变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传统,从“文如其人”命题所体现的中国命题的模糊性,以及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实际倾向对“文如其人”命题的影响这两个部分展开论述,以期为“文如其人”命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文如其人”命题的“模糊性”
“文如其人”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命题。对“文如其人”命题的讨论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本身的模糊性带来了巨大的讨论空间。事实上,“模糊性”是中国传统文学和哲学的一大特性,冯友兰就曾提到中国哲学“不够明晰”[4]。下面将从中国思想传统对寻求精确定义的忽视和中国文论术语本身的特性两个角度,对“文如其人”命题的“模糊性”展开论述。
(一)中国思想传统忽视对精确定义的追寻
宇文所安提出:“现代学者,无论中西方,经常为中文概念语汇的‘模糊性’表示悲叹。其实,它们丝毫不比欧洲语言中的大部分概念词汇更模糊;只不过在中国传统中,概念的准确性不被重视……中国读者或许始终不能确切说出什么是‘虚’‘文’‘志’等等,但只要它们一露面,他们就知道是它们。二者的差别在于:在西方传统中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张力:一边追求精确的定义,一边追求它们在文学术语中的回响(1)即这些定义在各种参照标准中的应用。;而中国传统只看重‘回响’。”[5]导言3宇文所安提到的“回响”是指由术语到应用的过程,他认为中国文学术语“模糊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思想传统对于精确定义的忽视,即跳过文本分析层面,更看重意境的领会和实际操作。对于精确定义的忽视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其一,中西传统对“真实”的理解存在差异;其二,借助余英时先生的理论,西方传统走“外在超越”的道路,通过宗教信仰穷究宇宙万物的存在和价值的明确答案,借此实现对现世的超越和对天国的追寻,所以更注重定义的精确性;而中国思想传统走“内在超越”的道路,认为“道”在于人伦日常,“重视现世实践,将重点放在每个人的内心自觉,让个人的修持成为关键所在,故而重视意会,因此对于精确定义的重视不如西方文化传统”[6]10-20。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超人间”的起源,“但当我们审视‘超人间’和‘人间世’的关系便会发现‘中国人对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西方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砂锅问到底’。柏拉图的‘理型说’便是要展示这个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柏拉图也承认这个真实世界是不可言诠的,但他毕竟还要从四面八方来描写它”[6]8。可见,西方传统对用言语描述真实世界的不信任以及其力求确切的努力;而中国传统则将真实世界与“文”的呼应关系当作不证自明的常识,于是在这方面的论述便有普遍的模糊性。
(二)中国文论术语本身的特性
从中西文学理论术语差异的角度比较中国"文如其人"和西方"风格即人"等相似命题时,需要考虑所借用的西方词汇的所指与中国语境下的词汇内涵是否吻合。“一种文学思想传统是由一套词语即‘术语’构成的,这些词语有它们自己的悠久历史、复杂的回响和影响力。这些词语不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意义载体的集合,它们不过是相互界定的系统的一部分。”[5]导言2刘若愚认为中国文论词汇本身的特性给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增加了难度。宇文所安也认为:“一词多义因而具有多种所指,这是中国文学思想话语的一个优点,但也造成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5]238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现象也并非中国文论独有,关键在于“中国批评家习惯上使用极为诗意的语言所表现的,不是知性的概念而是直觉的感性;这种直觉的感性,在本质上无法明确定义”[7]8-9。
首先,中国文论所使用的词汇本身有较强的模糊性,汉语词汇复音化则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就单音节的汉字而言,意义不明确的问题已够严重,至于双音节的词,那就更复杂了,因为两个音节在句法上常呈现模棱两可的关系,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无法确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句法上的还是语形上的……例如‘神’这个字本身可能意指‘神明’‘鬼神’‘精神的’‘神圣的’‘神妙的’……‘韵’这个字可能意指‘谐鸣’‘和音’‘押韵’‘节奏’‘声调’或者‘个人风韵’。‘神·韵’合在一起,在理论上可能以令人迷惑的各种方式加以解释,其中有些合理,而其余的毫无意义。”[7]8
其次,中国文论所使用的词汇的本义常常影响后人的文学观。“传统中国思想比较推崇那些把抽象物和实物统一起来或把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统一起来的词汇”[5]68,中国文论词汇大都由借用他物得来,显现出“模拟”的原始思维,这些他物通常与人的身心或自然社会有关,如“气”“性”等本是人的生理或心理词汇,而用它去描述一个文学概念,本身就具有与“人”紧密结合的意味。在“文如其人”命题中,“文”这个词也不例外,“‘文’包含一系列(2)“文”的含义经历了“记号—样式—文饰—文化—学问—著作—文学”的变化过程。光谱般的意义”[7]32,“‘文’的语义范围过于广泛,从‘书写的文本’到‘装饰’都属于‘文’。‘文’的模糊性刚好表明了宋代以前,中国文学思想的强大力量——希望世界和文学创作之间保持一种有机的关系”[5]117。
我们谈论“文”时,难免受其在历史流变中形成的不同含义的影响。甲骨文及殷商后期青铜器上的“文”型记号,以及许慎给出“文,错画也,象交文”的定义,都表明“文”原是指身上的记号或事物的花纹,即“装饰”,后来,先秦时期出现了“文”的抽象意义。在历史上,“文”作为“装饰”的原始意义对其抽象意义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扰动:在“装饰”和“实用”、重形式和重内容的含义之间来回摆动。“《论语》中‘文’有几种不同的用法,有时指‘文化’或‘文明’,有时指‘文雅’或‘文饰’,有时指‘学识’或‘学问’。”[7]导言10由此可见,“文”在早期的含义并不等于“(纯)文学”或“文章”,且“文”本身带有强烈的表象色彩,用于为人或物增加美感;汉代的“文”作为具有修饰性的对偶与押韵的“文章”,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转换。即便是审美的“文”,也与人的本性息息相关:刘勰不止一次谈到人在文学作品(文)中显示出他的本性,就如动植物借着外表的美(文)显示出其本性一样自然。魏晋唐以后,“文”的抽象意义缩小,出现“文”“笔”对立、“文”“诗”对立的狭义的“文”的内涵,即便如此,“文”的原始意义,以及后来广义的“文学”“文章”、狭义的“韵文”“散文”义仍然相互纠缠共存[7]导言9-12。古代的批评家也常常在一篇文章之内自由切换“文”的诸多含义,如刘勰在《原道》中利用“文”这个字的多义性,以强调文学与文饰之间的模拟;萧统在《文选》序篇中以“纯文学”的概念定义“文”,而在“世质民淳,斯文未作……文之时义远矣哉”一段中,他又以广义的“文”(即文化与文章)的概念,保持天“文”与人“文”之间的模拟,由此证明狭义之“文”(即文学)的正当性。换言之,作为“纯文学”概念的“文”的合理性需要原始概念和广义概念的“文”来支撑。因此,在论述“文”的具体内涵时,任何企图排斥甚至抛却“文”的多义性和历史性的行为都是没有道理的。
二、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实际倾向对“文如其人”命题的影响
“中国思想有非常浓厚的重实际的倾向,而不取形式化、系统化的途径。”[6]6以下从中国思想传统对人的内外关系的理解、创作层面的“诗言志”传统、阅读层面的“观人”与“知言”传统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实际倾向对“文如其人”命题的影响。
(一)对人的内外关系的理解
探讨“文”与“人”之间的“如”或“不如”,是在追求一种呼应关系。这种关系用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连接,也就是探讨作品与现实中的作者或作品与作者的艺术人格之间到底有多少“真实”的问题。中西思想传统对于文学“真实”的理解显然不同。首先,从书写他者的角度来看,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指的是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是否的确存在过;西方文学传统所追求的真实则指历史表象之下埋藏着的本质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必然性,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是怎样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挖掘其隐含的本质,从而将其再现于文字形象中;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8]。若从书写自我的角度来谈,中国思想传统是如何理解“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品性,以及文与其二者的关系的?这分别关注外在与内在的说法是否有相通之处?
宇文所安在分析《论语·为政》一篇时,针对孔子提出的“善”,不是认识“善”这个概念,而是如何在具体的个案中知善、识善,“它是一种关于‘知人’或‘知事’的‘知’……它引发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意在揭示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的解释学。中国的文学思想就基于这种解释学,正如西方文学思想基于‘诗学’”[5]18。术语的提出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具体的人的种种复杂情形,王阳明在《别诸生》中的“不离日用常行内”一句,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中国文学思想与揭示、解释人的言行密切相关,人的言行与文学作品构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由此,便不难理解人们将对“文”的评价与作家个人的实际言行挂钩的传统。
除了将“人”理解为人的外在言行,学界也有不少观点(3)例如蒋寅:“文如其人是如人的气质,而非如人的品德。”等等。将“人”解释为人的道德性情等内在因素。“文”作为一种向外的表达,是如何与人的内在品性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上文引用的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寻求内在超越”理论[6]10-20,宇文所安也提出中国思想传统中内在真实和外在真实的互通:“《论语》这段话(4)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论语·为政篇》)提出了若干值得思考的基本假定。首先,有两种真实,一在内,一在外:虽然对外在真实的观察有可能导致对内在真实的误解,然而,它同时也假定,通过对外在真实的某种特殊的关注,完全可以充分地深入到内在真实之中……在具体的内在状态和外在表现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5]18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人的内外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一种近乎线性的信任之上的,也就是说,内在的东西向外流露时不受太多阻碍,外在言行揭示了其内在思想。
西方传统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倾向,尤其体现在对外在和内在的理解上,若换成更贴合西方语境的词汇,即表象与本质的对立关系。“柏拉图思想认为‘绝对真理隐藏在世界欺骗性的表象之下’体现了这一传统,强调表象的偶然性和变化性,对于从外在看到内在充满怀疑。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分裂和紧张在后世的康德哲学中达到极致展现。”[6]11-12在这里,理解内与外的通道是受阻碍的。这样看来,西方语境下的“真实”本身就带有对抗和否定性的意味。从拉康到齐泽克,“真实”是作为对象征秩序的一种对抗而被反复谈论,它是一种坚硬的阻力,同时,也光滑而不可捉摸,充满一种类似于“轮扁斫轮”的不可言说的意味:“真实因此是坚硬的也是不可穿透的内核,是拒绝象征化和纯粹的不真实的实体……在我们即将牢牢掌握其特性时,它就自我消散了。”[9]869西方认为,真实与现实难有重合,它们是悖论性关系,真实瓦解现实也产生现实,“现实总试图以一种基本的连续对抗性对抗真实的瓦解效果,但现实又总是趋向真实的现实(reality towards the Real),现实中有创伤、缺失与焦虑等真实之物,这类否定性事物无不表明,现实的每种形式都表征着摆脱真实之威胁的意图”[9]870。如果我们把外在言行看作一种现实,那么真实不包含(并且对抗着)外在言行与内在品性。作品与外在言行的真实性和作品与内在品性的真实性并不等同,作品的真实性并不属于人的外在言行或内在品性,因此,西方没有类似中国对“文如其人”命题中纠缠“人”是指“人”的哪一层面的讨论。基于此,我们或许能回答邓心强在《“文如其人”研究评述》中的发问:“为何批评史中既有论文人‘道德品行’的一面也有论其‘气质个性’的一面,并且这两面始终共存并呈胶着状态?”正因中国思想传统对现世中的“人”的重视,中国的作者和读者才对“文如其人”抱以巨大的期待和极度的敏感。
(二)创作层面的“诗言志”传统
考虑到文学生成年代与中国文学总体发展的关联,大致可以说中国文学起源于“诗”,谈论“文”不妨从“诗”的传统入手,而谈论“诗”不妨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入手。《诗经》基于“采诗说”,从口头民间歌谣到作为“诗歌总集”,这出自一种文化意识或代表着一种明确的历史需要。李洁非认为《诗经》是一个围绕天子、道人(采诗官)、民间歌谣(社会原生形态)的“文化规范”,“一种社会性、政治性的世俗生活主题结构”[10],这种主体结构因其“无宗教感”而与西方文学源头相区别,“重实际倾向”明显。
刘若愚提到“中国原始主义诗观结晶于‘诗言志’一句”时,借用了朱自清先生“‘诗’和‘志’是同源的字,即使并不是相同的字”的观点[7]136-137。后世批评家对“志”这个字作了不同解读,大致有两种理论流脉:一是认为“志”是“心愿”或“情感意旨”的批评家提出了表现理论,二是认为“志”是“道德目的”的批评家导向实用概念。情感和道德的分流从“诗言志”传统发端,便不难理解为何学界热衷于辩论“文如其人”是指向“情感的人”还是“道德的人”。学者洪涛对“志”的语义嬗变进行了梳理;“‘志’在先秦典籍中有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意义用法,即作为史的‘志’和作为心理的‘志’。”[11]无论哪一层面都导向作品的非虚构性,可见,其重实际倾向,从中也可以窥见,“文如其人”是指向“人的外在言行”还是指向“人的内在性情”的论争的思想发端。
(三)阅读层面的“观人”与“知言”的传统
蒋寅认为“文如其人”表达的或许是一种读者对作者的期待[3]。而笔者认为,从期待这一层面来看,对象并非仅指向作者,也可以指向读者自身,是对读者的要求以及对合格读者的筛选,而不只是对作者的要求,即“文如其人”是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何理解“人”的一种期待,作者是如何在读者的阅读中被充分而全面理解的,而不仅仅是在对“文”的表层阅读中期待和证实作者应该是怎样的。这隐含了社会对“知音”式读者的期待,体现了儒家“观人”与“知言”的思想,“在孔子看来,观人确实可以观到这一层:阅读一篇文本也可以读到这一层,它提醒西方读者注意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事实——文永远是人写出来的”[5]20。在孔子那里,任何一种内在真实都有可能被错综复杂的环境所遮蔽,而只要掌握观察的方法便会发现,“内在的真实其实就在外在现象之中”[5]20。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知言’描画了一种(与西方)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试图去理解另一个人。读者的兴趣渐渐发展成为更广泛、更复杂的对‘他人’进行理解的尝试。”[5]22此处的读者和作品并不是封闭的关系,而是作品寻求“知音”的关系。刘勰首先将“知音”引进文学批评领域,并在《文心雕龙·知音》开篇即喟叹“知音难求”。“一个文本从千百万读者的手中传过,它所寻找的永远是这个或那个人,即一个‘知言’的人。”[5]22“知音”式读者是中国古代读者理论与西方不同之所在,先秦诸子哲学中蕴含的“圆融性,使知音论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互动关系……作者通过文本表现我思,读者‘振叶寻根’,通过文本去发现作者的我思”[12]。刘勰提出读者可以用“六观”的准则来考评作品(5)《文心雕龙·知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固定的,“衡量它价值的标准是‘位体’‘通变’等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因素,作为‘知音’就是要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地位做出客观的评价与考察”[13]。对比西方读者批评理论,即“文学文本的客观性正是它最终所要破坏的概念”[14],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实际倾向尤为明显。
三、结语
“文如其人”命题在中国经久不衰,原因在于,这一术语本身的模糊性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讨论空间,这一部分基于中国哲学追求“含混”的美感,另一部分由于中国思想传统相对忽视追求定义的精确,将重点放在每个人的内心自觉,重视意会,对于精确定义的重视程度不如西方文化传统。此外,中国文论术语本身的特点是诗意而重直觉的,古汉语词汇复音化加重了其含义的模糊性。对“文”的语义嬗变的梳理也可见中国古代将对“文”的理解与“人”的本质和“人”的活动相关联。
“文如其人”的“如”可以视为对“真实”的理解,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实际倾向影响了中国古代对“文如其人”的理解。从文学本论的角度看,西方传统认为内在真实与外在真实的沟通是受阻碍的,而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中讲究“史传传统”,并且,认为人的内在品性和外在言行可以相对顺畅地互通,因此,批评史中既有论文人“道德品行”的一面,也有论其“气质个性”的一面,且这两方面始终共存。从文学分论的角度看,创作层面的“诗言志”传统可见“文如其人”是指向“情感的人”还是“道德的人”论争的思想发端;阅读层面的“观人”与“知言”的传统以及中国古代“知音”式读者原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文如其人”不仅包含对作者创作的期待,还包含对读者的要求以及对合格读者的筛选,即“文如其人”是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何理解“人”的一种期待,注重“作者”是如何在读者的阅读中被充分而全面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