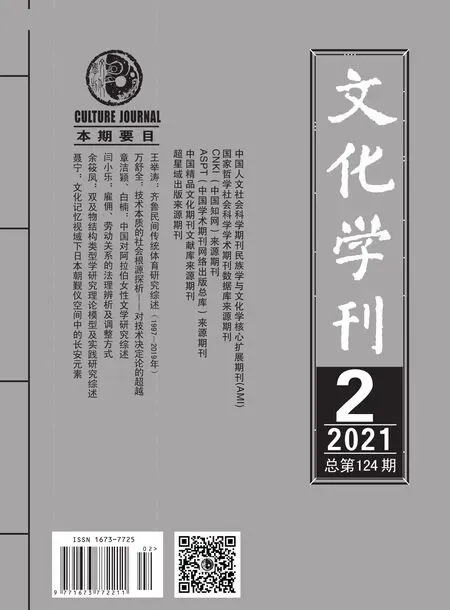信仰与爱:桑顿·怀尔德《圣路易斯雷大桥》中的女性寓言
汪 雪
一、《圣路易斯雷大桥》研究要略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是迄今为止唯一同时荣膺普利策小说奖和戏剧奖的美国作家,《圣路易斯雷大桥》(TheBridgeofSanLuisRey)是其代表作之一。此书一经发表,就“引起极大轰动,成为当年的全国畅销书”[1],并于1928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颁奖词将其评为“近代灾难文学和电影的先驱、作家的文体写作手册、完美的道德寓言”。“围绕它的最大争议,或许在于《圣路易斯雷大桥》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坛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大主流的疏离。”[2]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喧嚣的20年代”(the Roaring 20s)。这是一个经济不断繁荣、社会经历剧变的时期,旧的价值观被颠覆,妇女得以解放,是一个全民狂欢、文化多元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美国作家也被称为“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小说体现出创作题材的现代性,“它同意识流小说一样旨在揭示现代经验,即战后弥漫于西方世界的异化感、孤独感和绝望心理,并深刻反映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性格认同危机”[3]。彼时,怀尔德却“专注于古典文学的复兴”[4],他的作品中充满古典文学的元素。左翼批评家高尔德(Mike Gold)就曾指责怀尔德将此书的故事背景置于18世纪的秘鲁,“未能紧紧把握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潮”[5]。另一种批评声音强调“怀尔德的问题不仅是运用‘意此言彼’的寓言叙事,更致命的是他在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20世纪文学写作中,竟然固守了某种普世价值,竟然试图对转向‘一切都无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读者进行某种道德意义上的‘说教’”[6]。
然而,怀尔德不仅使用了《圣经》般的语言风格和古典的寓言叙事讲述了宏大恒久的人文主题,也通过《圣路易斯雷大桥》表达了“他对美国人和20世纪美国的关注”[4]。“他(怀尔德)的小说和戏剧是传统与创新、乡土与都市、现代与古典、美国与欧洲、适时与永恒的奇妙结合。”(注:笔者译)[7]普利策小说奖的评奖标准为“授予当年发表的美国小说,该小说最好能反映美国生活的整体风貌”[8],然而将背景置于18世纪秘鲁的《圣路易斯雷大桥》却摘得此奖,这就暗示了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美国社会特质的映射。《圣路易斯雷大桥》以秘鲁为背景,但是故事中夹杂着大量秘鲁与西班牙关系的描述,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及其对美国文学地位的思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美国文学独立于英国文学取得民族文学独立地位的关键时期[9]。此外,这部“近代灾难文学的先驱”探讨在无妄之灾降临时,我们应该如何理性面对亲人逝去的悲痛与哀伤,与一战后大众心理与社会氛围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通过对不同生活背景下的女性的刻画,勾勒出了当时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群像,从个体的角度来隐喻女性的整体生存状态。这些女性人物在追求信仰与爱的痛苦中挣扎,在顿悟后觉醒,她们的身上体现了矛盾与永恒的人之特性,即我们的人性。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女性意识在不断觉醒,但时代的通病困住了女性觉醒的步伐,因此,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坎坷命运也是时代的写照。
二、蒙特马约尔女侯爵
布斯(Wayne Booth)提出的“不可靠叙述者”(the unreliable narrator)概念一直被看作通过文本分析探寻隐含作者意图不可或缺的范畴之一。其经典定义在叙述学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细化和修正:费伦(James Phelan)与玛汀(Patricia Martin)将不可靠性分为事实/事件、价值/判断、知识/感知三条轴,并得到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和不充分评价六种不可靠性类型[10]。在小说的不可靠叙事内容中,即从朱尼帕的叙事视角来看,蒙特马约尔女侯爵被认为是一个面容丑陋、不被女儿喜爱的笑柄,是个被抛弃的可怜人。但从全知叙事视角可以得知,“在她逝世后的一百年里,她写给女儿的书信已经成为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丰碑,她的生平事迹则在此后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11]11,人们试图赋予她很多荣耀。显然,在不完全了解女侯爵的情况下,人们对女侯爵产生了不充分解读和不充分评价。人们仅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来解读和评价她,完全忽视了她在其他身份上体现的人生价值,这种解读视角正是长期的父权制社会统治与近代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大背景的产物。同样,女侯爵在后世被大加赞誉的原因除了她写给女儿的书信是充满“妙语连珠”的“精妙绝伦的篇章”之外,也因为这些书信体现了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深情。
哦,我的心肝宝贝,你的感冒拖了这么多个星期,你要遭多少罪啊?文森特啊,我恳求你让我的孩子好转起来。神的天使啊,我恳求你让我的孩子好起来。一旦你有好转,我求求你,当感冒的症状刚一冒头,你一定要好好蒸个澡,然后上床休息。[11]17
她的书信完全符合主流价值观对女性的要求——做一个完美的“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家中天使”得名于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Conventry Patmore),他在其诗作《家中天使》(TheAngleintheHouse)中称女性为“人人仰慕的完美者,头戴桂冠、犹如天使”,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完美女性形象。“家中天使”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主流文化,对各阶层妇女均产生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蒙特马约尔女侯爵能成为伟大的女性不完全是因为她本身的成就,也是因为她的书信诠释出了主流价值观赞同和需要的女性形象,即一个一心一意爱孩子的完美的母亲形象。
但真实的蒙特马约尔女侯爵绝不仅仅只是一位母亲,她一直在试图反抗周遭的压迫和不公,也在努力追寻自己的信仰,努力去施与自己的爱并渴望被爱。女侯爵童年容貌丑陋,说话结巴,不被家人关心,被大众嘲笑,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成年以后,“她独自生活,独自思考,竭尽所能与世俗习规进行抗争,很多追求者找上门,但她已决意保持独身”[11]12。尽管她极尽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无法与父母和强大的世俗抗争,最终“不得不委身于一个傲慢、堕落的贵族”[11]12。在女儿出生之后,她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虽然她对女儿的无疆大爱可以囊括爱的一切,但这爱却带着几分专制的色彩:她对女儿的爱不是为了女儿,而是为了她自己。她渴望将自己从卑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这种感情过于强烈,以致无法驾驭。”[11]16此时,她早已不将自己看作一个母亲,而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一直生长在被压迫的环境里、不曾被爱的个体,她为女儿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希望“苦难在她的心脏组织中留下的印记”[11]15能够被看见。她渴望自己能够得到肯定,即使被人敷衍地夸奖“宅心仁厚”,她都会十分惊喜;她渴望能够真正地享有爱与被爱的自由,“尤其渴望能回到那种简单的爱当中”;她渴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是“一切都听天由命”。她对女儿看似疯狂的付出和爱不是她对母亲和妻子身份的妥协,而是她试图反抗多年来受到的压迫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便是她的信仰,是一直以来支撑她的动力。
在自己的爱长期得不到女儿的回应后,她开始酗酒,爱上了醉酒后的“幸福状态”。文学与心理学分析者喜欢把酒神视作人性解放、反抗礼教束缚、追求身心自由的象征,酒有着冲破习俗、颠覆礼教的力量[12]。此时的女侯爵已经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心中的信仰。她不再相信自己有改变周遭、改变命运的能力,她彻底陷入了爱而不得的悲剧之中。直到看到佩皮塔修女的信后,她才真正顿悟,才发现一直以来追寻的信仰并没有错,错的是她表达爱的方式,错的是她将自己困在了寻找爱的牢笼之中。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长期在被压迫的家庭中成长的女性大多会加强对孩子的统治支配,这是一种悲剧的循环[13]。女侯爵终于明白,将自己的爱投射在女儿身上并不能让自己得到解脱,更不可能弥补自己一直以来被亏欠的爱和关怀。“上帝也是麻木不仁的。人没有什么力量去改变自然规律。”[11]33“我不再奢求任何改变。一切都听天由命吧。”[11]37她终于将自己从卑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只是在她彻底想通后,便从桥上掉了下去。
女侯爵一生的遭遇是绝大多数女性命运的缩影。在父权制社会下,她们在童年与青年时期受到家庭的束缚和压迫,在婚后困于家庭之中,必须努力成为世俗标准下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尽管女侯爵一直在竭尽全力追寻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自由,并在人生最后实现顿悟,但其终究打破不了时代的局限,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三、卡米拉·佩利绍莱
卡米拉从十二岁开始跟随皮奥叔叔学习戏剧表演,对古典戏剧有着极大的热忱。她如饥似渴地训练,对表演有着极高追求。每当有人暗示她是一个存在局限的艺术家,她就会为之抓狂。“必须完美才行,必须完美”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卡米拉常常会为了表演细节和皮奥叔叔讨论到天亮。渐渐地,她成为西班牙语世界里最出色的演员。她和皮奥叔叔仍旧对古典戏剧及表演有着近乎完美的追求。他们早已不是为了取悦利马的观众,而是在殚精竭虑地尝试在秘鲁建立戏剧的标准[11]89。尽管早已成名,在见到伟大的古典戏剧大师的孙女时,她仍然因为在其面前表演一段戏剧而心脏狂跳不止。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卡米拉逐渐失去了对艺术的执着。她不时会对表演产生轻视,这让她有些心不在焉,这与西班牙古典戏剧本身和当时观众的审美风格有极大关系。西班牙古典戏剧“一直缺乏对女性角色的真正兴趣……只关注他们的男主人公,关注那些被各种责任和荣誉相互撕扯的绅士”[11]89。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两性地位总是不对等的,女性长期被看作“他者”。“女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和诗歌,她们仍然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她们崇拜的是男人创造的天神。男人创造出伟大的男性形象来自我歌颂:赫拉克勒斯、普罗米修斯、帕尔齐法尔;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起次要作用。”[14]男性以自己的观点来描绘世界,同时表现出对女性的蔑视[15],他们不屑于去丰富女性角色,去研究女性的智慧、魅力、激情和疯狂。与此同时,利马的观众却逐渐爱上了那些讲日常俗语的新式嬉闹剧,古典戏剧被冷落。就连通读过所有古代文学作品的利马大主教也早已忘光了古典文学,只能大致记得沉醉和幻灭的感觉。此外,女演员一直受到社会的轻视,“表演就是她们的罪”。卡米拉在逐渐意识到西班牙古典戏剧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女演员的态度之后,选择渐渐远离舞台的决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不愿再生活在一个对女性充满极大蔑视的环境里,她开始探寻生命的其他意义——寻找爱。
卡米拉早期曾对皮奥叔叔心生情愫,但她更像是皮奥叔叔一生追求的古典戏剧的接班人。遇到总督以后,她体会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并将这种新奇感受当成是爱,于是她彻底离开舞台,努力扮演一位贵妇的角色。结合这部小说的写作背景,“喧嚣的20年代”是自私轻浮、摈弃传统的10年。“在这10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由于厌恶战争,因而对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淡然视之,只是热衷于追求享乐,追求金钱。”[9]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繁荣发展,国民却日渐精神贫乏。卡米拉的行为或许也是当时美国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射,“她想成为一位贵妇,她渐渐对社会地位产生了一种觊觎”[11]98。于是她精心包装自己的身份,努力学习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也开始享受各种特权。但是,在她得到了想要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后,却没有获得原以为的幸福和快乐。大病一场,毁容过后,她更是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认为美貌尽失就真情难再,变得更加孤傲。卡米拉想要通过成为总督的情人实现改变社会阶层的美梦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经济”一般,最终还是破灭了。直到皮奥叔叔努力打动她,在准备将她的孩子带去利马培养的路上掉下桥时,她才真正顿悟。她从未意识到除了男女之情,其实还有别样的爱存在。“我被封闭了起来,我没有心。我让所有人都失望了。他们都爱我,可是我辜负了他们。”[11]123
前半生,卡米拉·佩利绍莱都在追求将古典戏剧演绎到极致,但是她终究无法力挽狂澜,无法改变古典戏剧对女性角色的忽视,也无法改变古典戏剧逐渐被新式嬉闹剧取代的局面。后半生,卡米拉·佩利绍莱在追寻爱的坎坷过程中终于理解了爱的本质——爱并非只有男女私情,它“慷慨施与、体恤周到,能诞生伟大远见和诗篇”;“只有经历了长久的劳役,经历了自我的仇恨,经历了热嘲和冷讽,经历了漫天的怀疑,它才能立足于被信任的行列”[11]106。卡米拉的一生是矛盾的,她的思想在压迫与觉醒之间挣扎,她的行动在拒绝平庸与随波逐流之中徘徊。她的观念与行动终究还是受到了环境的极大影响,她放弃对戏剧和表演的追求转而投向消费与享乐之中,美梦幻灭时她最终幡然醒悟,可彼时已经失去了人生中的太多“珍宝”。
四、德尔·皮拉尔院长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16]马利亚·德尔·皮拉尔院长就是一位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她身上有当时很多女性不具有或者不敢具有的品质。她将女性的解放事业作为自己的追求,将所有人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相连,对所有人都施与最博大的爱和关怀。
皮拉尔院长是虔诚的基督徒,追随上帝是她的信仰。在寻找接班人时,她选定了那个“一边指挥别人在木盆边干活,一边还和她们绘声绘色地讲着利马圣罗撒那些匪夷所思的奇迹故事”[11]30的十二岁女孩佩皮塔。欧洲“发现新大陆”后,罗撒是第一位被册封为圣人的妇女,她拥有所有圣人皆具备的一个特点,即遭逢逆境却仍保有信德。圣女生命的最后几年,在自己的家中设置了一个专司照顾无家可归的孤儿、老人与病患的房间,这可以说是秘鲁最早的慈善事业。皮拉尔院长也有同样的品质,她以对芸芸众生的博爱实践着对上帝的爱。她长期维持着医院、孤儿院和女修道院的运转,锲而不舍地开展慈善事业;她总是禁不住地想为聋哑人做些什么,以帮助她们之间的沟通;她也习惯于去重症病房陪睡不着的人聊几句。在双胞胎伊斯特班和曼纽尔被抛弃后,她给予他们最大的关怀和照顾;在曼纽尔死后,她想出一切办法安慰伊斯特班,增强他活下去的信念。为了锻炼佩皮塔成为合格的接班人,也为了增加她的见识,她将佩皮塔送去蒙特马约尔女侯爵家做侍女。即使强大如皮拉尔院长,还是会有矛盾甚至崩溃的时刻。在无法打动伊斯特班时,她深感无力,“气愤地大声说道:‘我已经祈祷获得智慧,但是您什么也不给我。您没有给我哪怕一丁点儿恩宠。我不过是一个拖地的……’”[11]66。她渴望自己能参透上帝的旨意,渴望自己能帮助身边所有人战胜苦难,但现实总会给她当头一击。
皮拉尔院长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是时代的先驱。她兼具女性的柔和与刚强,是男权制社会的反叛者。她本人十分独立,完全具有一个当家人的能力。在同时代的大多女性还在依靠男性和家庭而生活的时候,她早已实现了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独立,并致力于帮助更多陷入苦难的人们。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并对自我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生存目的做出深刻思索。她也有强烈的自审意识。“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这易于使女性产生对男性的依附心理、谄媚心理、顺从心理”[17],但是皮拉尔院长对女性的自我认识极为清醒。她致力于对抗时代的顽疾,渴望能赋予女性一丝尊严,希望女同伴哪天能够组织起来,保护她们自己。她全然不顾这个旧时代对她公然的敌意,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她看到了女性所受的压迫之苦,意识到了女性与男性本不该有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她将提升女性地位奉为自己的终身理想,并尽力去探索和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就算有20个同她一样的女人,也同样会失败,因为那个时代不会受到她们的丝毫影响。
慈善事业上遇到挫折,无法唤醒那些沉睡的女性,尤其是继承人佩皮塔的死给皮拉尔院长带来巨大冲击,“这段经历让她脸色苍白,但却心志坚定。她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即她的工作是否继续下去并不重要,她已经干够了。作为护士,她去料理那些永远不会康复的病人;作为牧师,她去永远维护神台前那个没有信徒朝拜的祷告之所”[11]122。她不再困于工作和信仰之中,不再总是陷入深深的自责。她明白自己曾经完成过一项伟大的事业,即使这份事业后继无人,“对于上天来说,在秘鲁曾经有这样一份无私的爱由盛而衰,似乎就已经足够了”[11]122。她不再是那个全心全意只关注上帝、慈善、工作的人,她的感情开始多了几分颜色,她也领略了人生的意义。皮拉尔院长不再被宗教信仰和责任所撕扯,她也回到了那份简单的爱当中。“在爱当中,我们的这些错误似乎都不会持续很久。”[11]126这是一种最普通也是最宏大的爱,它包含了所有感情,也是人们的心灵中最细腻的情感的反映。
五、结语
在《圣路易斯雷大桥》中,读者看到了很多体现当时美国社会背景的元素,尤其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和隐喻极具时代和民族特色。书中这三位主要的女性人物的性格、经历和命运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女性意识觉醒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她们渴望从被安排、被束缚、被忽视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渴望自己能享有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自由,渴望体会到最纯粹的爱与被爱,渴望能为自己而活。
蒙特马约尔女侯爵的一生是大多数女性生存状态的写照。她受到父权制社会的压迫,想要反抗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只能将自己生活的所有希望和追求放在孩子身上,期望在孩子那里得到认同,体会被爱,却终究因为这压抑的爱太过炽烈而伤害了彼此。卡米拉·佩利绍莱渴望演绎出古典戏剧的魅力,宣扬古典戏剧的价值,但时代的动荡带来人思想上的变化,她无法阻止古典戏剧发展的式微。深受时代的影响,她也逐渐陷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陷阱,但最终仍然无法通过财富和地位来实现人生价值,弥补自己从少女时代就被忽视的情感关怀。皮拉尔院长是时代中那一小批先驱者的代表,她们致力于对抗时代的顽疾,渴望用博大的爱来抚慰人的伤痛,渴望能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最终也无法与时代抗争,反而将自己困在了责任与使命之中,忽视了自身的发展和内心最细腻的情感涌流。
她们都体会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之苦,也都在痛苦中挣扎,渴望解放,渴望自己的需求能被满足、绝望过后,她们得以顿悟,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不过就是人类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情感——爱。它“是唯一的幸存之物,它是唯一的意义”[11]129,爱是她们所有人的信仰。“爱说到底,的确如弗洛姆所言,主要出于一个事实,就是要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如果人与人无需建立任何关系也可以满足生存的需要,爱根本不重要。但是事实表明人一出生就需要有依靠、需要提供无条件的被爱才能活下来。”[18]对于自身主体性被长期否定,生存的社会环境不如男性的女性群体来说,爱显得更加重要。
同时,从更加宏大的人文主题来看,这些女性在追寻信仰和爱的过程中展现的复杂心理体现出矛盾与永恒的人之特性,即我们的人性。悲剧过后,那些追寻信仰与爱的主体不复存在,但是爱这一幸存之物跨越生死,给各自苦闷的人生增添了几缕色彩。时代的局限注定女性无法彻底冲破枷锁,但是在寻求自由的路上,她们都在寻求爱与被爱的过程中顿悟,某种意义上,她们都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19]。
《圣路易斯雷大桥》从未被定义为一本女性主义小说,但其中对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的刻画,却真实地传达出怀尔德对当时美国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复杂心理的观察与思考,体现出怀尔德对美国人与20世纪的美国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