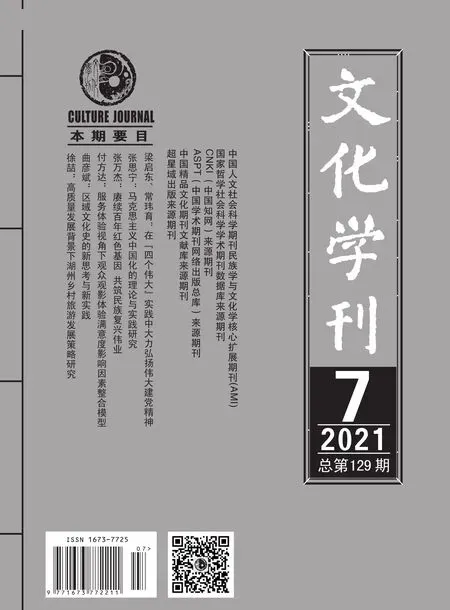论人性与自由的关系
——基于哲学史的思考
黄新佼
哲学的终极奥义是探寻世界的本质,在这一探寻过程中,作为寻找主体的人,首先要清晰地认识自我。在漫长的哲学发展史中,哲学家们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且趋向一致,由此对人的本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而自由是与作为主体的人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在人的本性与追求自由之间,哲学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作用与意义?是否可以将自由和本性这二者相等同?基于哲学发展史,本文将从其产生及发展过程来进行思考和探寻。
一、对人性的探究
希腊哲学早期建构世界的方式是神话故事,用古希腊神话解释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现象。公元前6世纪,第一批哲学家开始探寻更为真实的世界,将目光从神话转向了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不过早期哲学家更多的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进行思考,如世界的由来、构成等,从自然的角度入手,忽略了人自身。
到了智者学派时期,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人。古希腊哲学家探讨人事问题时关于人事相关内容的争论产生了“自然说”与“约定说”的两个观点,首次提到了人的本性。“自然说”中的自然特指人的本性。“自然说”认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该受到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1]。这里的人的本性即人性,“自然说”中用“自然”一词来形容它,但是并未对这一词做出更多的说明。按照“自然”来理解,这里的本性应该是指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纯自然的动物性的欲望、渴求,人想要如何生活,就可按照自己的这种本性去追求。这种本性是自由的,不应受外在约束。这一时期对人性的看法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动物性的特性,也可以算是人原初的状态。刚出生的婴儿所具有的就是这种纯自然的动物性的渴求。在这里借用“自然状态”这一称谓,但是这一“自然状态”并非是霍布斯原意上所说的那种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出于自己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互相杀戮。这里的“自然状态”更多的是想强调一种自然性、原始性和动物性,有的只是单纯的原始的欲望。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里说,据说神在造出各种生物之后,又分配他们适合其本性的生存手段,唯独人没有得到护身的工具。人类从普罗米修斯那里得到火之后,分散居住,无法抵抗凶猛的野兽,人类之间也相互为敌。为避免人类灭绝,宙斯派赫尔墨斯把尊敬和正义带到人间,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他要求把这些德性分给每一个人[2]。柏拉图的论述本意是想通过人性来说明国家是如何组成的,通过他的论述可知,他认为尊敬与正义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且尊敬与正义是神所赋予的,这时柏拉图的人性已经脱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纯自然的动物性,多了道德与政治的内容,有了社会性。这样的人性是伦理人性、政治人性。
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关于善和幸福的内容时,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它出自人的自然禀赋和本性,人独特的自然能力是理性,即人性中含有理性的成分,理性指导人分辨是非善恶并趋善避恶。在这里,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德性被分为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自然意义上的德性是一种潜在的倾向,未必能够实现。在人的本性中含有对幸福的向往,而这种理性并非是动物直觉,与柏拉图一样,是一种社会伦理取向,都是伦理上的人性。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发现人的价值包括尊严、才能和自由,人文主义者关注抽象的人性价值,包含尊严、才能和自由,当转向社会政治中看人时能看到人的政治本性。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恶,他说,“关于人类一般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3]。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也都认为人的本性已经全然败坏。“我们的本性不但缺乏一切的善,而且罪恶众多,滋生不息……”
到了康德那里,他认为人性与道德密不可分。道德是人性的基础,人性服从于道德[4]。康德把人分为感性的人和理性的人。感性的人就是像动物一样追求感性肉体官能,理性的人高于动物,具有理性能力。这样来理解,人性就有了更细化的分层,可以称为自然人性与道德人性。在这一过程中,理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理性的存在,给了人向善去恶的可能性。
历史上对人性的认识发展,经历了从无知到知,从简单认知到复杂认知的过程。这里说人性的发展,实际上是想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人性,而非道德伦理的角度。因此,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人性本应该是最初纯自然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纯动物性的渴求,可以称这种人性为人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不能简单地用善性或恶性来概括,它既有向善的可能也有作恶的可能。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性逐渐被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人的政治性、伦理性。人们理所应当地从道德伦理人性层面出发考量人的一切活动,却忽视了人的一切行为一定都是从本原的人性出发,就算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人,在行为时多了别的考量,这样的考量也一定与自己的本性有关,然后又受外界影响,在人性的基础上多了社会因素。
二、自由的萌芽
自由一直是哲学、伦理学中重要的命题,人似乎是与生俱来地对自由充满了向往。而自由究竟是何时被人所认知的,什么样的状态才是自由的状态,从哲学史中可见微知著。
晚期希腊哲学的斯多亚学派,虽然并未直接表明自由是什么,但谈到了自由选择。人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对表象的态度。斯多亚学派用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人选择表象的自由:
不要被表象弄得急不可耐,对自己说,“表象啊,等一会儿,让我看一看你是谁,要干什么,让我考验你一下”。不要让表象牵着你走,不要把你要做的事想得栩栩如生,否则你就会受到它任意支配。要用另外一个美丽高尚的表象与之相抗衡,把这个卑鄙的表象排除[5]。
斯多亚学派的这个例子所表达的选择表象的自由,着重强调不被外界所左右的选择就是自由的选择。这个外界的范围很广,可以理解为,只要是经由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表象都是不自由的,由此人极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真正自由的选择非常稀少且珍贵。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发现,对于人来说,最高的价值是自由,这个自由是指选择和造就人自己地位的力量,自由是神赋予人的礼物。皮科借上帝之口曾表示过,上帝造人时人没有任何的规定性,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做出任何自由的抉择。人文主义者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可以凝视世间万物。人在这样自由的境地中,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任意的形式。人文主义时期的这种自由着重强调人在世间独一无二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所以人是自由的。
斯宾诺莎认为,自由是人自觉顺应自然,当人不自觉被自然必然性所驱使时,他是被迫的,奴役与自由是相对的。这里的自然必然性不仅指外在的自然界的规则,更重要的指人的内在自然本性,在这种自然本性中会有自发产生的自然情感,如果人能对这些情感和欲望产生的外在原因及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有正确的认识,那么人就是自由的,即自由就是能够认识、克制和管辖从人的本性中产生的各种自然情感。
卢梭在其政治学说中论述了何为自由,人生而自由,即人在自然状态时是原初的自由状态。当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人逐渐丧失自由,自由是一种原初的状态,但是这种自由状态是不持续的。卢梭的自然状态指没有人际交往、语言、家庭、住所、技能的人类最初的状态,当人逐渐进入社会状态时,自由就已经开始逐渐丧失。
洛克在谈论到自由时,认为人有自然自由。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任何人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为准绳。洛克的自然自由是与处于社会中的人的自由相对应的。处于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意志的管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这里的社会自由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不是无限的,是在法律的范围内的自由。
三、人性与自由
在人的本性之中,与生俱来地包含着对自由的向往,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不难发现,人性的具体内涵尽管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这一过程无论如何变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由这一因素,自由与人性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是以下思考的重点。
(一)人的本性即自由的状态
古希腊时期所探讨的人的本性,即一种纯自然的状态,这种纯自然的状态没有任何指向,不具任何道德性,就是事物最初产生的一种自然形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下的人是自由的,不受外在社会世俗的约束。这里所谓人性的自然状态恰好与卢梭所指向的自由的自然状态和洛克的自然自由相契合。没有外在的社会世俗对人的本性的影响,也就没有对自由的奴役,因此可以说,在这样的阶段,人的本性即自由,人生而自由。这样的状态是一种原始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但我们只能认识,却无法恢复。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无法卸载的枷锁,使人类社会成为社会应有的样子。
(二)自由的丧失与人性的泯灭
当人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随着伦理哲学的发展,自由在不断地被限制,人性也在不断泯灭。这里的人性就是本体论上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就是不具理性因素的,没有限制和约束的状态。随着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在表象的左右,人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在表象的覆盖,于是自由状态不复存在。人性还是人性却也不再是人性,人性成为道德的附庸。人纯自然的本性被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赋予了善、恶等道德意味,所以这时的人性已不再是原初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性。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探寻如何达到平等的路径时,其中之一是回到自然状态。回到自然状态,不仅可以达到平等,也可以恢复人的本性与自由,但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路径无法实现。其中之二,即用社会契约来保障社会平等,这样能建立一个保障人们自由和平等的国家政权,但这恰恰是使人丧失自由和人性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契约将人从自然状态全权脱离出来,受社会的左右和约束,交出人的本性与自由,组成了国家和社会。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是政治动物或称社会动物,恰是泯灭了人性,再无自由可言。
(三)自由与伦理人性并存
在康德道德哲学语境中,自由即自律,是一种理性。人在社会生活中,能认识外在各种事物,了解其产生和发展。人能够自觉主动地适应各种外在事物,自觉行善。人的本性中同时就含有善和恶的因素。当含有的善的因素处于领先地位时,自由和人性相契合,在善性的指导下,人自觉主动地行善,这时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人。当恶的因素处于领先地位时,自由的人是理性的,可以纠正恶行,向善靠拢。
但是从实际层面来看,人并不是一直自由,即人并非可以一直自律。不论是善还是恶,生活中我们都有失去理智、打破自律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不管是善还是恶都将倒向恶或更恶。同时这样一种并存的状态,是建立在对自然人性的泯灭基础之上的。打破自然状态,建立社会状态之下的人性,依赖于道德哲学将自由和人性并存。
四、道德对人性与自由的重要影响
人性与道德的关系是复杂的,现在我们探讨人性时,常将人性分为善、恶等其他不同的类型。然而人性是先于道德的,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所认为的应然的人性和实然的人性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此看来,人们常常说人性的善与恶等其他类型的划分,显然是一种应然的状态。而实际上,人性本无道德划分,只是一种纯动物性欲望。在这种欲望下所导致的各种利益冲突之中,产生了道德规范,借以约束彼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时才赋予了人性善和恶的区别。所以可以说道德是从为人性服务出发,最终又复归人性。
自由与道德的关系在不同哲学体系中有不同的类型。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表现为自由受制于道德。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道德规范是在社会习俗中渐渐形成的,并非在人的自由意志中形成。人的本性中本没有这些克制与伦理,所以归根结底,自由受制于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学中,自由和道德是辩证统一的,其中康德关于自由与道德的思想尤为典型。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道德法则视为自由的法则,他提出“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前一个自由是一种他所认为的消极的自由,指不受干涉;而后一个指自律,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康德还有一句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前一个就是康德所指的消极的自由,后一个就是一种高级的自律。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和道德是辩证统一的。道德赋予了人性和自由不同的等级,道德使人性与自由更加规范化和社会化,但同时,就是因为道德的产生,将人性本自由的状态打破,人性与自由分裂开来,成为人性和理性。
不论人的本意如何,都是产生于自然,由他的自然本性所决定,这种自然本性即人性。当人在自然状态自主自觉地活动和选择时,人就是自由的。当人已经无意识地被外在事物所驱使时,自由就不复存在。而伦理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和人性的约束和限制更多。因而,当人进入社会时,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再自由地行动了。正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