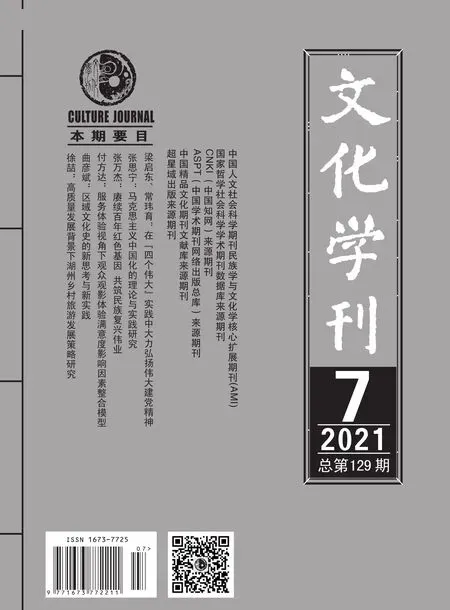粉丝群体的审美免疫研究
郭正为
审美免疫是文化免疫的一种表现,所谓文化免疫即特定文化对于异质性文化的识别和处理能力,审美免疫则是指拥有特定审美趣味的共同体对于异质性审美对象的识别和处理能力,审美趣味是审美免疫的生成和工作机制,也是对于审美对象识别和处理的标准[1]。媒介技术的进步对粉丝群体的审美免疫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提供丰富的审美对象诱使粉丝群体让渡了审美的免疫权,这在降低粉丝群体审美免疫力的同时,也给群体的审美趣味带来了一定的异化风险。
一、粉丝群体审美免疫的表现
粉丝群体的审美免疫表现在对于具有相同审美趣味的事物的接受与同化以及对于不同审美趣味的事物的破坏与排斥,这种免疫表现诠释了粉丝文化以“热爱”为旨归的评判标准,也体现了审美活动的感性的力量。审美趣味是粉丝群体对审美对象取舍的标准,而审美趣味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群体内成员对于审美对象的选择往往遵循爱即正义的原则,对于喜欢的内容往往不会考虑它的性价比等因素,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基于喜欢而对产品进行消费。有的粉丝群体对某一审美对象甚至达到了痴迷、疯狂的程度,轻视主流审美文化的引导,公开发表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做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行为举止,这也是粉丝群体审美趣味异化的表现,也是审美过度免疫的表现。爱本无罪,为了喜欢的事物付出时间或金钱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喜爱一定要在主流审美文化的引导下进行。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粉丝群体往往还会为自己树立 “假想敌”,与自己审美趣味相左或对立的审美对象都有可能成为他的“假想敌”,这也是审美免疫的力量所在。例如粉丝群体喜欢某一影视作品,与这部影视作品价值观念相左或对立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粉丝群体的“假想敌”,粉丝在欣赏或评价这部影视作品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成为“假想敌”的作品来举反例,以此表达对于群体审美趣味的认同和对群体的忠诚。詹金斯曾对粉丝群体进行过深度研究,他曾提到粉丝群体很注重文本的再生产,即同人写作,作品质量越高在群体内就拥有越多的话语权,同人展的作者也会看重同人文本的版权,这也体现了粉丝群体维护审美趣味纯洁性的决心,而对于与群体趣味不同的文本,粉丝们也会采取漠视或敌对的态度[2]。审美免疫是维护粉丝群体最有力也是最深层的机制,正常的免疫有利于粉丝群体良性发展,每个粉丝也都会因此受益,但免疫过度也会增强粉丝群体的封闭性,使得粉丝群体因循守旧或思想行为偏激。
二、粉丝群体审美免疫的工作机制
粉丝群体的审美免疫主要表现在对外来审美对象的识别和处理能力上,这种审美免疫是通过粉丝群体的审美趣味起作用的,具体表现为审美趣味对同质性审美内容的接受和同化以及对于异质性审美内容的破坏和排斥。粉丝群体是基于趣缘形成的,具有同一性的趣味使得群体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判断,这种审美趣味在一次次的审美活动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强化,并形成了免疫机制。审美趣味为群体的内容选择和内容生产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而粉丝的每一次审美活动又为趣味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即审美趣味表现为一种审美鉴赏能力,面对外来文本,粉丝首先会评价其形式和内涵是否与既有的审美趣味相符合,对于相符的文本,群体会加以接受和同化,用群体的接受仪式和解读规则消费文本,最终使文本成为群体新的议题,强化群体的审美趣味;而对于与群体审美趣味不相符的文本,群体则会对其报以敌对的态度,运用群体的解读规则解构文本的合理性,或者通过对内容的排斥重申既成的审美趣味,强化对既成审美趣味的认同。粉丝群体当中的每个粉丝对审美趣味都是认同的,在这一审美共同体内,群体的趣味就是个体的趣味,群体趣味为个体构筑起一道围墙,使得个体免受异质性审美内容的侵扰,当个体趣味遭到侵蚀时,可以从群体当中汲取力量,个体也会因害怕偏离趣味受到孤立而固守着群体的趣味;而个体趣味也为群体趣味的巩固贡献着力量,同一粉丝群体的粉丝可能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但他们共享着群体提供的审美产品,预演着群体为他们设定好的审美体验,对于群体内的审美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着体验和解读,这也从不同维度为群体审美趣味的合法性提供了解释,增强了粉丝群体的审美免疫力。
三、粉丝群体审美免疫的失效
(一)算法推送:媒介对审美免疫系统的置换
詹金斯把粉丝的文本阅读行为比喻成游牧,四处奔走围猎与群体审美趣味具有同一性的文本,这种围猎行为是具有主动性的,围猎的目的也在于获取更多的文本巩固和发扬群体的审美趣味。而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粉丝的围猎行为逐渐被媒介所取代,算法推送机制在这一取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介会记录粉丝的阅读行为,根据粉丝的阅读行为为粉丝贴上相应的标签,并向粉丝承诺会根据粉丝的阅读兴趣向粉丝推荐相关的内容。[3]粉丝在媒介技术提供的便捷之下,逐渐放弃了“游牧”而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更关键的是由于算法机制强大的运算能力,可以更快地向粉丝推送源源不断的内容,这让粉丝在享受内容福利的同时也对技术产生了一种崇拜。如果说“游牧时代”,粉丝审美趣味的形成是经由复杂的互动积淀而成的,那么定居生活粉丝的审美趣味则是由同质化的内容堆砌而成的,“游牧”允许异质性对其侵犯,即使异质性的东西无法被接受或同化,也有可能倒逼粉丝群体修正或强化自身的审美趣味,“定居”则从根本上消除了异质性的东西,不符合粉丝趣味的内容往往不会被推送。传统粉丝群体的审美免疫要经历“接种——免疫”的过程,即群体形成了一定的审美趣味,面对异族的文本会产生一种应激的反映,而媒介为粉丝群体建立的“免疫系统”则缺少了“接种——免疫”的过程,算法直接通过为粉丝推送同质化的内容,在粉丝与异质文本之间建立了一道围墙,粉丝的审美免疫行为不再是一种主体的排异,而是媒介承诺给粉丝的保护。这种“免疫系统”是不牢靠的,换句话说,媒介所给的承诺是不牢靠的,因为媒介承诺的背后是资本市场,媒介对粉丝群体审美免疫系统的置换给粉丝群体带来了不稳定性,同时也给群体的审美趣味带来了异化的风险。
(二)快感体验:主体对审美免疫主动权的让渡
媒介技术的进步为粉丝提供了更多的审美对象,这看上去为粉丝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实则是在动摇粉丝群体的文化根基,使得粉丝群体的审美体验更倾向于对形式的消费而忽略了对内涵的感悟。媒介在为粉丝提供丰富内容的同时,并没有剥夺粉丝搜寻内容的权力,粉丝仍可以通过搜索栏搜索自己喜欢的内容,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异质性的内容丰富自己的审美体验,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趣味。但媒介化的审美让粉丝将这种搜索的权力在默许的状态下主动让渡了出来,媒介化审美给主体的审美活动带来了更强的快感体验,这种快感体验诉诸视听的满足而忽略了精神的愉悦,粉丝在享受着媒介提供的内容带来的快感的同时养成了一种怠惰的态度,不愿意再消耗过多的精力进行内容的搜寻与思考。这种对于审美快感的推崇弥漫在粉丝群体当中,媒介技术借由对粉丝个人免疫防线的攻破,使得粉丝群体的免疫系统失效。视觉文化带来的奇观转向使得媒介空间内充斥着各种视听奇观,受众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审美对象应接不暇、乐不思蜀,这些审美对象将受众的快感满足到了极致,却降低了美感的体验,即使得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失衡[4]。粉丝在享受着快感体验的同时,作为一种等价交换,回报给了媒介一种信任,相信媒介推送的内容就是自己真正需要和喜欢的,这种信任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三)追求奇观:粉丝群体审美趣味的异化
从粉丝一词的起源来讲,其最早的解释就含有“疯狂、不理性”的感情色彩,随着粉丝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矫正,粉丝一词才逐渐回归了中性,但由于粉丝群体生成过程中的趣缘特性,这种“疯狂、不理性”的基因一直残存在粉丝文化的基因当中,并且在媒介技术和审美文化发展的支持下,这种基因疯狂“繁殖”“变异”。前面提到媒介的作用使得基于审美趣味建立起的审美免疫系统失效,在媒介内容的怂恿下,审美趣味不仅不再起作用甚至被异化。媒体经常报道粉丝不理智的追星行为,例如《青春有你3》曝出的粉丝疯狂倒奶打投应援事件。这一事件折射出粉丝的审美鉴赏力不断下降,失去了对追星行为理性的评判标准,这是粉丝群体审美趣味异化最直接的表现,对于偶像的追求不再是基于一种人格的认同或是作品的认可,而是疯狂地追求各种形式,打造各种“奇观”,这种不理智的审美行为是一种畸趣的体现。粉丝感兴趣的点不再局限于“同人展”“同人写作”,而是乐此不疲地分享转发同质化的内容,对于奇观的追求纵容媒介内容生产者生产出更多、更具冲击力的内容,受众的审美需求与生产者对利益的追求实现了合谋,使得受众的审美需求在被满足的同时也被资本市场所操控,粉丝群体的审美趣味也不断被异化,频发的粉丝圈乱象就是这种审美趣味异化的明证。
媒介通过为粉丝群体提供丰富的内容,让粉丝群体主动让渡了审美免疫权,媒介通过不间断的内容供给为粉丝群体建构起了新的免疫层,这也使得粉丝群体的审美趣味被资本市场所操控,给粉丝群体的审美趣味带来了异化的风险。因此,要加强对于粉丝群体审美活动的引导,传递多样性的文化产品,引导粉丝树立崇高的审美理想,建立新的免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