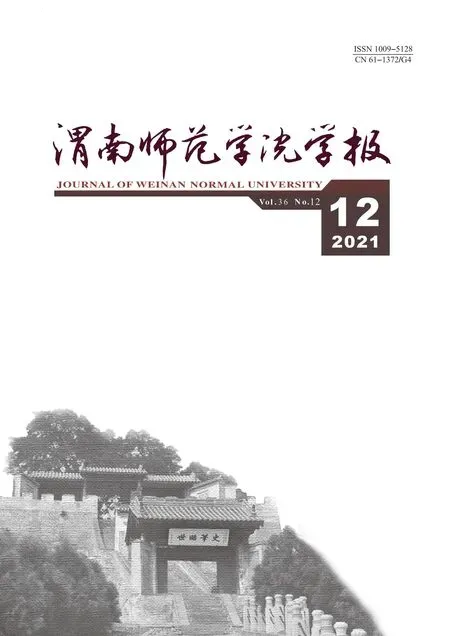《科利奥兰纳斯》的两个伦理问题分析
杨 康 恩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罗马剧,讲述了公元前5世纪罗马将领科利奥兰纳斯与平民发生冲突遭到驱逐,其联合外部势力对罗马复仇,最终惨死他乡的故事。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根源与人物形象等被中外学者反复阐释,其中观点各异甚至大相径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评论家自身的立场之外,根本原因在于《科利奥兰纳斯》中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返回到科利奥兰纳斯时代的历史伦理现场,对《科利奥兰纳斯》中突出的伦理问题进行客观的阐释,能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该剧的悲剧性成因。
在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13。同时,“伦理”又以人的社会活动各方面为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政治关系构成政治伦理,家庭关系构成家庭伦理,人际交往关系构成人际交往伦理等。对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就是分析作品在政治伦理、家庭伦理以及人际交往伦理等方面涉及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秩序的变化,进一步分析这种变化背后的伦理动机、伦理选择以及伦理困境等,以获得更广泛的伦理价值意义。[2]14在此意义上,《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伦理问题突出表现在政治伦理的重建与家庭伦理的异变两个方面。
一、政治伦理的重建
政治伦理具有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含义,指“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亦包括诸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3]5。《科利奥兰纳斯》在制度、行为和观念三个层面均具明显的特征。
首先,政治制度的变化。科利奥兰纳斯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彼时的罗马刚推翻王权、结束王政时代不久,随着不断的军事扩张和对外征战,政治和军事事务大量增加,社会政治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下层平民由于战争往往失去土地而沦为债务奴隶,贵族形成封闭的特权阶级,通过元老院掌握国家大权,元老院通过执政官处理国内外政务。[4]235-254因此,此时城邦的权力集中掌握在贵族手中,政治制度属于贵族制。
由于战争的需要,平民在城邦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以离开城市、退出战争为主要手段,争取到护民官的设立来维护平民群体的利益。《科利奥兰纳斯》开场就展示了罗马城邦设立护民官这一事件。其中,贵族和平民是城邦中两股最主要的政治行为主体,贵族之中又有温和派和强硬派之分,贵族中的强硬派以科利奥兰纳斯为代表,温和派以米尼涅斯为代表。护民官则在议会中替平民发声,代表平民的利益,平衡执政官的权力。因此,护民官的设立是贵族和平民达成政治契约的产物,城邦权力不再由贵族单独掌握,城邦的政治制度转变为共和制。在政治制度层面,城邦由贵族制走向共和制,这是政治伦理重建的最明显的特征。
其次,政治行为的选择。政治制度关系着每一个政治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在不同的政治目的下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因此,政治伦理的重建过程必然伴随着新旧政治伦理维护者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科利奥兰纳斯与平民之间。二者的冲突主要有两点:一是平民是否可以参与城邦的治理,二是科利奥兰纳斯是否可以做执政官。
冲突一,平民是否可以参与城邦治理。科利奥兰纳斯否认平民具有参与城邦治理的资格,在他看来平民不具有治理城邦所需要的政治德性。在科利奥兰纳斯眼中,平民只是一群好吃懒做、党同伐异、胆小怯战、反复无常、忘恩负义的多头怪兽。科利奥兰纳斯从德性的角度否定了平民参与城邦治理的合法性。他看到平民参与城邦治理对贵族统治的危害,却看不到平民的力量是维持城邦存在的前提。与之相反,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温和派,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支持平民参与治理国家的权利,因为他们考虑到城邦的现实处境,那就是城邦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与伏尔斯人的战争。平民的政治选择同样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争取自身的权利。他们反抗的目的只是满足生存最基本的需求而不被饿死,而不是为了推翻贵族的统治,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过多的要求,在元老院答应设立维护他们权利的护民官之后随即散去。因此,平民争取政治参与的权利,最初目的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出于生存的权利。
冲突二,科利奥兰纳斯是否可以做执政官。罗马人有把执政官的职位当作奖赏有功于城邦之人的惯例,在科利奥兰纳斯为了当选执政官到广场征求平民的同意前,就有市民认为“要是他把他的伤痕给我们看,把他的功绩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就应当替他的伤痕说话,告诉他他的伟大的功绩已经得到我们慷慨的嘉纳”[5]423。同样,科利奥兰纳斯不愿意为了当选执政官乞求平民同意,他宁可饿死也不向别人乞求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得的酬报。无论是平民还是科利奥兰纳斯都把执政官的职位看作是一种奖赏,是对有功于城邦之人的回报。这种观念属于伦理学范畴中的“回报论”,是“不论结果如何都要令人得其应得的行为”[6]113,科利奥兰纳斯与平民最初都认可这种“回报论”。随着冲突的发展,平民在功利主义的趋势下转变了观念,不再基于行为本身而是基于行为的结果来考虑选择科利奥兰纳斯作为执政官这一政治行为的利弊。两个护民官对科利奥兰纳斯当选执政官对平民危害的认识,代表了平民中这种政治观念的转变。虽然两位护民官被莎士比亚塑造成为以一己之私刻意煽动民意的权谋家,但是他们看到了科利奥兰纳斯对平民德性的否定、对平民自由的剥夺、对平民权利的压制。考虑到科利奥兰纳斯的种种行为,可以说这种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最后,政治观念的变化。科利奥兰纳斯代表贵族强硬派,坚持政治与德性的内在关联性,其政治行为基于政治德性与“回报论”;元老院代表贵族温和派,其政治观念出现变化,不再以德性作为政治参与合法性的唯一准绳,最终与平民达成政治契约。元老院极力维护城邦整体利益,因为城邦整体利益包含他们的自身利益。平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城邦集体利益,因为旧的政治伦理之下的城邦利益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伦理。当元老院和平民在功利主义驱使下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观念,达成新的政治伦理秩序时,科利奥兰纳斯作为旧的政治伦理秩序的代表,成为被选择的“替罪羊”。
在第三幕第一场中,护民官要求把激怒平民的科利奥兰纳斯处死,米尼涅斯为科利奥兰纳斯向护民官求情时说道:“与其卤莽倴事,不如循序渐进;否则他也不是没有人拥护的,要是因此而引起内争,那么伟大的罗马要在罗马人自己手里毁掉了。”[5]446冷静下来的护民官同意米尼涅斯的提议,让科利奥兰纳斯接受合法的审判,这是元老院与平民达成政治契约的又一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科利奥兰纳斯表示如果自己接受平民的审判,很有可能被暴怒的平民磨成粉,米尼涅斯和考密涅斯却坚持让他接受平民的审判,他们已经决定了通过牺牲科利奥兰纳斯来换取城邦稳定。
“精疲力尽的英雄主义粗俗的傲慢必须屈服于一种新社会秩序谦恭、温和的价值观”[7]79,科利奥兰纳斯代表维护旧政治伦理的力量遭到驱逐,也标志着政治伦理重建的完成。新的政治伦理具有新的特征。在政治制度方面,贵族制转变为一种复杂的混合政治体制:执政官代表君主制、元老院代表贵族制、护民官代表共和制。在政治行为方面,基于政治德性与“回报论”的政治行为遭到排斥,基于功利主义的政治行为得到认同。在政治观念方面,平民不再因为德性的原因被排除在城邦治理之外,取得了政治参与的合法性。
二、家庭伦理的异变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小组成单位,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法律和道德观念所承认的”[8]308。家庭作为一个伦理实体,以亲情为特征,其伦理关系既包含婚姻关系,又包含代际关系。家庭伦理是指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伦常秩序及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在处理与其他成员之间关系所信守的伦理理则和价值信念”[2]162。在本剧中,以科利奥兰纳斯与母亲伏伦妮娅的母子伦理为代表的家庭伦理,被莎士比亚置于特殊的戏剧情境下,深度参与城邦政治伦理的重建过程,呈现为异变的状态。
首先,伏伦妮娅对科利奥兰纳斯自然情感的缺失。伏伦妮娅自一出场就表现出一种缺乏传统母性德性、执着于追求荣誉的卓绝姿态。在第一幕第三场,科利奥兰纳斯率军出征后,伏伦妮娅告诉因为牵挂科利奥兰纳斯的安危而闷闷不乐的维吉利娅,她在科利奥兰纳斯很小的时候,就让科利奥兰纳斯出去追寻危险,为的是在危险中博取声名。在维吉利娅关于科利奥兰纳斯有可能战死的追问下,伏伦妮娅丝毫不以为意:“那么他的不朽的声名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裔。听我说句真心话:要是我有十二个儿子,我都同样爱着他们,就像爱着我们亲爱的马歇斯一样,我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不愿一个儿子闲弃他的大好的身子。”[5]389在伏伦妮娅看来,不能为国家征战就是浪费身体资源,为国征战效命疆场成了人生存在之目的。
与伏伦妮娅母爱的缺失相对,维吉利娅所表现出的对丈夫的关心与担忧,让我们看到了正常家庭伦理中应有的温情。在伏伦妮娅因为科利奥兰纳斯受伤而兴奋时,维吉利娅为科利奥兰纳斯流血感到惊惧与担忧,为之祈祷。婆媳二人对待科利奥兰纳斯态度的明显反差,在剧中多次出现:
维吉利娅 请您准许我进去。
伏伦妮娅 不,你不要进去。我仿佛已经听见你丈夫的鼓声……他用套着甲的手揩去他额角上的血,奋勇前进,好像一个割稻的农夫,倘使不把所有的稻一起割下,主人就要把他解雇一样。
维吉利娅 他额角上的血!朱庇特啊!不要让他流血!
伏伦妮娅 去,你这傻子!那样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武的雄姿,远胜于那些辉煌的战利品……(第一幕第三场)
米尼涅斯 他没有受伤吗?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总是负着伤的。
维吉利娅 啊,不,不,不。
伏伦妮娅 啊!他是受伤的,感谢天神!(第二幕第一场)
可以看出,莎士比亚高超的戏剧创作技巧,用维吉利娅的温情反衬伏伦妮娅的冷漠,用夫妻间的自然情感凸显母子自然情感的缺失。
很难说伏伦妮娅不爱自己的儿子,她只是认识到名誉在当时社会中对于人的重要性。彼时的罗马城邦正处于四处征战之时,“英雄社会隐含着的认识论是一彻底的现实主义”[9]163,这种现实主义以城邦生存为第一原则,勇于参战和敢于牺牲成为公民最主要的德性之一。荣誉作为对勇敢者的奖赏,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各阶层追求的对象。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伏伦妮娅督促儿子追求荣誉理所当然。然而与普通母亲祈祷儿子在战争中免于受伤不同,伏伦妮娅不顾科利奥兰纳斯的生死,把受伤的程度与荣誉的大小等同,将战死沙场看作最高的荣誉而刻意追求。此时,家庭伦理因为荣誉受到军事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当时的罗马,执政官掌握着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被认为是全国最荣誉的官职。伏伦妮娅期待科利奥兰纳斯当选执政官获取最高的荣誉,家庭伦理又因为荣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伏伦妮娅身上,我们看不到母亲对待儿子的自然情感,母爱德性被追求荣誉之心挤占,她把科利奥兰纳斯当作追逐荣誉的工具。可以说,伏伦妮娅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期待是他前行的动力,他们的家庭伦理生活明显受到军事、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特殊的境遇下,他们做出的伦理选择又反过来影响着城邦的政治伦理变化。
其次,伏伦妮娅基于城邦利益做出牺牲儿子的伦理选择。在科利奥兰纳斯立功归国后,按照惯例应当被选为执政官。然而科利奥兰纳斯骄傲的性格,促使他不愿履行向平民示以伤疤这一当选执政官必要的程序,加之他对平民一贯的蔑视,终于激怒了平民。面对平民强烈要求审判科利奥兰纳斯的诉求,在明知这一行为的危险性后果的情况下,元老院从功利主义出发,为了城邦整体利益选择牺牲科利奥兰纳斯,让他向平民道歉。然而以米尼涅斯和考密涅斯为代表的元老并不能使科利奥兰纳斯让步,于是迫使他委屈意志、冒死去向平民道歉的使命,依然要伏伦妮娅来完成。伏伦妮娅首先语气委婉地请求科利奥兰纳斯接受劝告,在被科利奥兰纳斯拒绝后又循循善诱地告诉他,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利用权谋示之以诈的必要性。在科利奥兰纳斯说明此行有性命之危时,伏伦妮娅却丝毫不为所动,由温柔相劝突变为冷漠决绝:“那么随你的便。我向你请求,比之你向他们请求,对于我是一个更大的耻辱。一切都归于毁灭吧;宁可让你的母亲感觉到你的骄傲,不要让她因为你的危险的顽强而担忧,因为我用像你一样豪壮的心讪笑着死亡。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的勇敢是从我身上得来的,你的骄傲却是你自己的。”[5]451在伏伦妮娅软硬兼施的逼迫下,科利奥兰纳斯终于答应去向平民道歉,他没能够控制自己骄傲的天性,在护民官肆意的言语挑拨之下恶意攻击早已怒火中烧的平民,最终被驱逐出城邦。
科利奥兰纳斯被驱逐标志着罗马城邦政治伦理重建的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伏伦妮娅在家庭伦理异变之下的伦理选择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果说伏伦妮娅第一次伦理选择的结果是科利奥兰纳斯遭到驱逐,那么她的第二次伦理选择则是把他推向死亡。
在科利奥兰纳斯联合伏尔斯人兵临罗马城下之时,相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在罗马城邦中各方势力出场均不能劝说科利奥兰纳斯罢兵之时,伏伦妮娅又一次为了城邦的整体利益扭曲科利奥兰纳斯的意志,彻底地把他推向了悲剧性结局,而这一次,伏伦妮娅选择以下跪的方式用最自然的母子伦理来逼迫他。伏伦妮娅长篇大论地指出科利奥兰纳斯违背人伦之处:“没有一个人和他母亲的关系更密切了;可是他现在却让我像一个用脚镣锁着的囚人一样叨叨絮语,置若罔闻。你从来不曾对你亲爱的母亲表示过一点孝敬;她却像一头痴心爱着它头胎雏儿的母鸡似的,把你教养成人,送你献身疆场,又迎接你满载着光荣归来。要是我的请求是不正当的,你尽可以挥斥我回去;否则你就是不忠不孝,天神将要降祸于你,因为你不曾向你的母亲尽一个人子的义务。”[5]496伏伦妮娅用“孝敬”“不忠不孝”“义务”等词语直指科利奥兰纳斯败坏的家庭伦理德性,讽刺的是,这种指责却是在她自己家庭伦理德性缺失的情况下做出的。显然,伏伦妮娅没有想过被逼退兵的科利奥兰纳斯在伏尔斯人面前该如何自处,这也不是她关心的。
正是这样,“以自然情感为根基的母子伦理在外在的、更高意义上的社会理性伦理挤压下支离破碎”[2]186。在城邦利益与母子伦理相冲突时,伏伦妮娅做出了牺牲儿子的伦理选择,并且以母子伦理之名逼迫儿子一再做出违背其意志的选择。伏伦妮娅在特殊境遇下所做的伦理选择,在将儿子推向死亡的同时,也参与了罗马的政治伦理重建过程,影响了罗马城邦的命运。
三、结语
无论是政治伦理还是家庭伦理,都是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把政治伦理与家庭伦理割裂开来,尤其在《科利奥兰纳斯》这部被哈兹里特认为最具政治主题的作品中。“在科利奥兰纳斯的身上集中了各种政治事件……莎士比亚以一种诗人的热情和哲学家的敏锐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少数人的特权和多数人的要求,自由和奴役,权力和滥用权力,和平和战争。”[10]55这些政治事件,明显受到家庭、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罗马家庭、军事、政治的三位一体,政府的地位相当于父母的地位,一个好孩子是一个好公民的必要条件。因为战争的需要,彼时的罗马实行全民兵役政策,“一个好战士是一个好公民的必要条件,一个好将军也是一个好政治家的必要条件”[4]221。家庭生活、军事生活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每个公民同时拥有不同的身份。伏伦妮娅以作为母亲的家庭身份和作为贵族的政治身份参与了以上政治事件,她的伦理选择却完全是站在贵族温和派的立场以政治身份做出的。可以说,该剧所表现的家庭伦理的异变是政治伦理重建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科利奥兰纳斯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家庭层面都成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