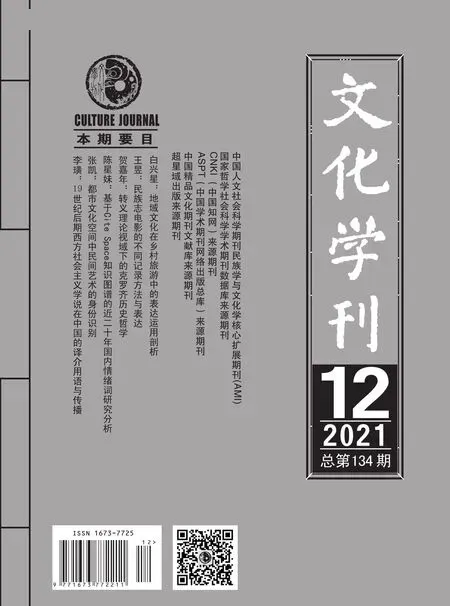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铭文背后的文化沈州
宋 巍
一、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及石函的基本情况
(一)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的基本情况
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45巷15号,原沈阳电缆厂二分厂以东约100米处的黄土岗上。其东连昭陵,南临沼泽,古色苍然,塔南地势平坦开阔,古时为浑河故道,现有北运河自东向西流过,故又称塔湾舍利塔。
该塔始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通高34.75米,由地宫、塔座、塔身、密檐、塔刹五部分组成。塔座为八角形仰伏莲须弥座,通体砖砌,周边嵌石条,高1.7米,每面宽5.5米;塔身每面都辟佛龛,龛上雕有卷草、海棠花纹图案及造型美观的伞盖、飞天等,龛内凸起的莲座上有身披袈裟的坐佛,龛两侧立有协侍。
1985年文物部门对舍利塔进行维修时,发现其具有独特的三层腹宫(中宫),即直径2米的空心结构,这在全国同类建筑中所罕见。在腹宫出土有鎏金铜释迦牟尼佛、错金银铜鼎、舍利子、经卷、瓷器等大批文物,并在方形地宫中出土一大型石函[1]。
(二)舍利塔石函的基本情况
石函,棺形,通高61.5厘米,长84厘米,前宽54厘米,后宽56厘米,黑褐色砂岩质,外表略经研磨,子母口对合,上盖的右侧与函身相合处有两处约20厘米的缺口。
石函上盖及函身四面均刻有楷书汉字铭文,共五千余字。其中上盖顶面中部刻:“维南瞻部洲大契丹国辽东沈州西北丰稔村东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大壬辰朔蓂生十五叶,葬佛舍利一千五百四十六颗……”字样;函身前面刻:“奉为太后皇帝皇后太后万岁诸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禄位州尊太师福寿延长雨顺风调国泰人安万民乐业,邑人李弘遂等百余人见武家庄东埚上地维爽凯平坦如镜以此众邑人请到前僧政沙门云秀为功德主转请到僧法直为塔院主共同发愿造无垢净光舍利佛塔一所……”,其余皆为题名。石函内容包括建塔缘由及参与建塔各界人士的姓名与职务等,是研究舍利塔和辽代沈州地区社会、文化、宗教等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石函铭文的整理与分析
石函铭文中,大都是施财施地修建舍利塔者的题名,涉及的名字较多,本文选取对该塔营建有重要影响的耶律庶几和李弘遂两位进行简要分析:
(一)耶律庶几
石函铭文共有两处有关耶律庶几的内容,一处位于石函函盖顶面:“昭德軍節度,瀋嵒州官内觀察通置侍使,崇祿大夫,檢校太師,使持節瀋州諸軍事,行嵒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涿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食封一百五十户,耶律庶幾……”。
另一处位于石函函身前面:“奉為太后皇帝皇后太后萬歲諸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祿位州尊太師福壽延長雨順風調國泰人安萬民樂業……”,其中的‘州尊太師’即为耶律庶几。
对于耶律庶几,《辽史》无任何记载。所幸在上世纪60年代,《耶律庶几墓志》在辽宁义县高台子乡出土[2]。结合墓志并《辽史·皇族表》记载,我们可以对耶律庶几身世及其仕途经历进行解读:
耶律庶几,契丹皇族,属大横帐季父房,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四弟寅底石的后裔子孙。自辽太平元年(1021)进入仕途,至辽清宁五年(1059)病卒,38年间共历17任官职,最高至上京留守,一生地位显赫。
墓志记载,耶律庶几曾任上京留守,也是其历任官职中最高者,即《耶律庶几墓志·序言》中所谓“论道经邦,曾任京师之主”。辽代,上京乃皇都,是契丹耶律氏家族兴盛之地,也是辽朝之立业所在。上京留守的衙署称上京留守司,下辖临潢府,即称“上京留守行临潢府尹事”,在当时可谓权势极盛。
对于耶律庶几的先世,辽史失载,墓志只有零星记录,亦未交代清晰。根据朱子方、魏奎阁及郭德胜等先生的考证,提出其世系大致为寅底石——刘哥——耶律阿烈——耶律惯宁——耶律庶几——耶律斡特刺[3]。但近几年的出土及研究资料显示,就其世系关系仍存疑问需进一步考证与商榷,姑置阙疑。
另据墓志记载,耶律庶几妻子刘氏被封为彭城郡夫人,可知其应属汉人名门望族之一刘氏家族。辽代,契丹与汉族只限在一定范围内通婚,因此,皇族耶律庶几迎娶汉人大族刘氏在当时可谓一件大事,也是契丹皇族与汉人大族世家通婚的一个实证。
(二)李弘遂与沈州李氏家族
石函铭文有关李弘遂的内容有两处,均位于函身前面,铭文一:“……邑人李弘遂等百余人见武家庄东埚上地维爽凯平坦如镜以此众邑人请到前僧政沙门云秀为功德主转请到僧法直为塔院主共同发愿造无垢净光舍利佛塔一所……”。
铭文二:“都维那李弘遂弟弘仙妻霍氏贾氏男用副维那节度推官王筮从妻李氏弟德从妻刘氏弟指挥使可从妻李氏男匡佐高五国胜奴高六……施院地主李匡顺妻田氏施院地主李匡友妻刘氏指挥使李匡受妻傅氏男文政施地主董斌序妻李氏……”。
邑人李弘遂之‘邑人’,非官名,乃佛教信徒为修功德而组织的邑社中人。
铭文中的‘都维那’,同样不是官名,而是佛教寺院中管理僧众庶务的僧人。
铭文中将李弘遂记为‘邑人’,亦记为‘都维那’,则李弘遂应为佛教信徒无疑,或为佛教寺院中管理僧众庶务的僧人或是沈州城内的居士,也是建舍利塔邑的邑首。但无论是何身份,这座舍利塔的修建,李弘遂都是主要发起人,以他领衔,说明其在沈州佛教界有相当高的威望与地位。
另据铭文记载,为修建舍利塔而捐施土地的“施院地主”有李匡顺,李匡友和董斌序妻李氏三人,且在参与营建舍利塔施财题名中,李氏人数也是最多的,由此可见李氏家族在沈州有财有地亦有势,实力可谓相当雄厚。
三、石函铭文背后的文化沈州
(一)辽代沈州地区的佛教
辽代契丹族最初只信仰萨满教,后来受汉人影响,也开始信奉佛教和道教。耶律阿保机深知佛教可以稳定他的统治,因此,他在龙化州和上京地区相继修建佛寺以安置中原来的僧尼,这也使得被掳掠来的大量汉人的佛教信仰有所归依,不再思念故土[4]。
通过对石函铭文的整理,我们可以对辽代沈州地区佛教的发展有以下几点认识:
1.沈州地区重视佛教且信徒众多。从最初发起人李弘遂等一百余人至后来自报“芳号”参与舍利塔捐资的一千五百余人,可见沈州地区佛教影响之广泛,信徒之众多。同时,大量官府人员的参与和捐资,说明修塔在当时的沈州城是一件大事,州府亦非常重视。
2.沈州地区佛教信仰普遍,信奉民族众多。铭文所示,在参与捐资的提名者中,很多以家庭为单位,人数上两人至四人,有的将已逝的故人也纳入其中进行提名。这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捐资的情况并不多见,反映了沈州地区佛教信仰的普遍性[5]。另外,佛教信徒除了汉人之外,还有契丹人、渤海人,甚至鲜卑人亦或高车人,说明沈州地区信仰佛教的民族众多。
3.沈州地区佛教团体众多,邑社林立。通过铭文及考古资料可知,辽代沈州地区邑社众多,常见有“钟楼邑”“升天塔邑”“建塔邑”“上升邑”等等,活动十分频繁。其以“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数。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为宗旨。事实上,作为佛教组织的一种,邑社的存在往往加速了佛教的发展与影响范围的扩大;而作为邑社的邑首或邑长,则是每次佛教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带头人。同时,佛教对沈州社会及百姓生活也有很大影响,诸如:“起名字”“子女出家”“下葬习俗”等等都与之相关,在此不一一例举。
(二)辽代沈州地区的居民与文化
1.沈州居民与儒家教育。通过舍利塔石函铭文、《辽史·太祖纪》及朱子方先生《辽代沈州官吏小考》可知[6],辽代沈州居民以外地迁居至此的汉族为主,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占少数。而在汉族居民中,李、刘、张、王、康是大姓,人口较多,为官者也较多,在已统计的329名捐资者中,共有官员28人,其中五大姓氏家族占据18人,占比达64.3%。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统计的人物中,契丹族只有两人,其中一位是大横帐皇族耶律庶几,时任沈州节度使,铭文称之为“州尊太师”。同比在沈州府衙任职的汉族官员,人数不少,但从品阶来看,六至八品居多。即便是官职最高的“节度副使”和“检校国子祭酒”,虽是从三品朝官,但勋爵却在七品下阶。由此可见,汉人从官者的居官级别普遍较低。
同时,在目前已考证的20位沈州节度使(节度副使)中,有契丹族16人,汉族4人,其中节度副使1人,即李克永(又称李尧永)。在19位节度使中,有皇族2位,国舅族7位,驸马2位,由此可知契丹用人之谨慎,沈州地位之重要。
另外,从石函铭文记载的人名命名习惯和规律中可知,沈州居民当时所受的文化教育主要是儒家思想教育。如兄弟间的命名排行、妇女称某门某氏和以弘俊、继全、守道、匡睿、延福、希进、德从、国佐、日新、元纪等命名都与中原习俗相一致。
2.沈州地区的文化特点。辽代沈州地区文化的最大特点便是多民族共存,多种宗教并存,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官员百姓,亦或城乡市井,大家均各取所需,任意供奉。宗教信仰与传统教育对提高沈州地区各族民众的文化素质、缩小契丹与汉族间的文化差异、加强其政权管理与阶级统治均起到重要作用,也有力推动了辽代沈州地区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
不仅如此,辽代沈州居民对文化与艺术的追求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舍利塔腹宫及地宫中发现的壁画,特别是绘于地宫四壁白灰面之上的彩色壁画,其保存完好,线条粗犷有力,运笔流畅自如。表现人物肌骨、眼神,用笔皆准确。画人物须发,密而不乱,笔笔带锋;画衣褶飘带,飞扬舞动,极其自然;画主像身着铠甲,片片结构严谨,一笔不疏,堪称辽代时期壁画之精品。同样精彩的还有无垢净光舍利塔自身的砖雕艺术及营造工艺。这些所谓“胡汉交融”时期的艺术作品,充分体现辽代沈州地区各民族艺术家、工匠们高超的创作水平。通过这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一件件精致而又不失民族风格的雕塑,向世人展示了辽代沈州地区的文化特点与底蕴,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
通过对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铭文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对辽代沈州地区的文化、宗教与社会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与了解。我们发现辽代沈州地区文化建构合理、社会体系完备。生活在沈州的居民正在接受多民族地区文化碰撞、多种宗教并存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与变革。在经过不断的杂居聚集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显示出辽代沈州地区特有的质朴与醇厚、聪慧与灵秀,逐渐造就了与中古时期中原及江南地区文化迥异、具有“胡汉交融”地方特色的“沈州文化”。随着这种地域特色浓郁的文化世代传承与发扬,为沈阳地区未来都市文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及文化领域的自信与开拓,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条件,也为打造“文化沈阳”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