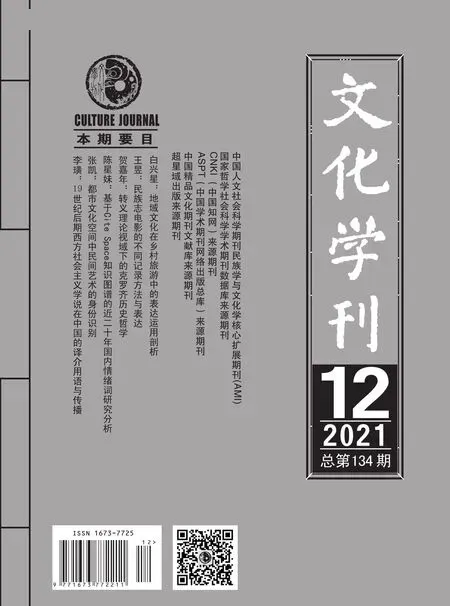感受距离的共性别择与文化精神的个性发展
——张爱玲与毛姆小说比较
朱扬清
张爱玲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个例,在主流文学史上一度处于无处安放的尴尬境地。在“重写文学史”思潮兴起后,怎样评价与定位张爱玲成为了学界的一大重点议题。在这一问题的推动下,我们在英国文学史上找到了与她时代相近、处境相似,同时也是为她私淑的作家——毛姆,与她相对应。事实上,张爱玲与毛姆的比较研究已为前人涉足之地,但现在学界较多研究成果仅是浅尝辄止地探讨张爱玲在创作上与毛姆一致的方面与表现,而相对忽视了考察张爱玲与毛姆创作基于共性上的独特个性,以及分析产生分歧的文化背景与个人特质原因。人性、人生、社会在古往今来就是文学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张爱玲与毛姆在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观照之时,都展现了理性客观的叙事态度。究其根本是由于他们与这三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们的共性所在,而构成距离的因素则牵涉到二者的个性分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选择从张爱玲与毛姆创作中与人性、人生、社会之间的距离出发,以期透视张爱玲与毛姆比较研究的新维度,探究对本土作家与域外作家比较研究新方法,从而更好地理解与阐释20世纪以来不断发生着的东西方文学视界的碰撞、交融与改变。
一、与人世的距离造就的“人性的洞察者”
毛姆与张爱玲的小说素以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著称。这是因为他们不论是与现世之人还是笔下人物始终隔着一段距离来打量,“在很大程度上,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站在一旁,观之笑之,这比一味介入要强得多”[1]。而毛姆和张爱玲,就是远远置身事外而洞若观火的人世看客。所以,毛姆恰当地自称为“无所偏袒的观察者”,相似地,胡兰成也曾将张爱玲比作“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2]。正是这样的一种距离,为毛姆与张爱玲的客观叙事态度留出了空间,从而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理性叙事手法,即不对笔下人物做出任何带有褒贬性质的评价,客观理性地还原真实场景事件中的人和物。
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二者理性叙事最为突出的体现,同时,女性自身的弱点也是人性本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同性恋者的毛姆,在某种程度上或能更好地体察女性心理,同时其男性身份又为其客观塑造女性形象提供了支撑。其代表作《人性的枷锁》中的米尔几乎集结了女性现存已知的一切缺陷:爱慕虚荣、平庸粗俗却又自命不凡,面对菲利普这样值得信赖和尊重的伴侣,她不但没有珍惜,反而对其嗤之以鼻,在陷入绝境后才想起向菲利普求救,其冷酷自私的本性可见一斑。当然,如果毛姆像传闻中那般有着严重的“厌女”倾向,那么米尔一类的女性形象或许就是出于偏见的产物。但事实上,毛姆心中的理想女性也曾隐现于其笔下,那就是《寻欢作乐》中的罗西。由此可见,毛姆刻画女性缺点,应该是在冷静观察后通过理性分析的结果,人们对他由“厌女”倾向引出的偏见怀疑,便不攻自破了。
同样是揭露女性个性弱点,张爱玲没有因为自身的女性身份而对女性群体有所偏袒,相反地,她以其敏锐的感知与细节的捕捉为读者打开了女性隐密内心世界的大门:葛薇龙的为情所困、曹七巧的自私阴毒……“无可讳言的,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观沾染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色彩,她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言明她的女性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活牌位”[3]。然而,“狡猾的求生者”也好,“祭祀的活牌位”也罢,张爱玲对她们都没有任何道德评判的兴趣,她关注的只是特定环境中人的生命境遇与真实、舒展的人性。她曾表示“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4],总比刻意的人为雕饰要高明许多。虽然两人同样推崇理性叙事的故事技艺,但毛姆与张爱玲的行文风格及其给人的阅读体验却有些微妙的差异,这区别或要追溯到两人对待人世的不同态度。
张爱玲欣赏并借鉴了毛姆具有理性意识的叙述手段,但她采用这种技艺的出发点却与毛姆不同。作为簪缨望族的后裔,没有见证家族的显赫一时,却偏偏赶上日薄西山的暮霭,她这样敏感脆弱的女孩,看着如何不心生悲凉,只道:“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过去,我没份了。”因自身与时代的错位,她选择去探寻那逝去的光阴里注定要为时代所抛弃的人,并“不动声色地与现实拉开距离”“用审视的目光编织着自己的传奇”[5]。或许是她这样的想法分了些给笔下的人物,又或许是这些人物的嬉笑怒骂正合了她的心意。“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点“悲”本来只是对自己的身世之悲,然而张爱玲却推己及人,以一种对众生皆苦的深深懂得,将其化为对一切在历史与时代的泥泞中无谓挣扎的人们的哀矜,“悲悯”由此溢满了她与人世的间隔。需要注意的是,这“悲悯”并不是“同情”,而是超越了一切个人感情,对人类无比宽容与理解的大爱,或者说,是“老灵魂”看破了人世种种的萧然尘外。如此也就不难解释相比于毛姆文风的棱角锋利,她更柔和,带着点撞破了人间疾苦的抱歉,低眉顺眼之际似有“地母”般的神之光晕隐现。
不同生存体验导致的个性特点差异如毛姆由生活经历形成的“愤世嫉俗”和“冷酷”立场及张爱玲以身份血统引起的“悲悯”态度,分别填补了他们与人世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的理性叙事选择也就推动了他们“人性观察者”地位的最终确立。
二、与生命的距离造成的“人生的虚无主义”
在19世纪,虚无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具有明显思想导向的阶段性影响。Nihilism(虚无主义),在《牛津词典》中对应的解释是“the belief that life has no meaning or purpose and that religious and moral principles have no value”,也就是说,它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信仰缺失,人们从而对自我存在和生活意义产生怀疑,乃至于引起普罗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现状。毛姆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价值标准已然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建立。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的阴霾笼罩着整个欧洲,空气中弥漫着“世纪末”的绝望气息,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就此来临。此外,在大学时期曾接触过的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给了毛姆极大的启发[6],他意识到:人生只是镀了金的空果壳,其本质是虚无一片。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行舟,拨开层层的迷雾,人们看到的不是孜孜以求的永无岛,大雾背后不过是海市蜃楼幻象罢了。于是,对于生命贫瘠、空虚的本质,毛姆和叔本华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达致了一致的认识[7]。
在西方世界精神危机和叔本华哲学的双重作用下,毛姆结合他不断发展着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认识,创作出了令他享誉文坛而至今热度不减的“三部曲”:《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其实,不妨将这“三部曲”看作“崩溃—逃离—重建”的系列过程。《人性的枷锁》作为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其主人公菲利普与毛姆一样经历了信仰崩溃的痛苦迷茫过程。带着这样的怀疑与恐惧,《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逃离了现存的价值体系,不顾一切地奔向南太平洋一个名为塔希提的小岛,以抛弃全人类及与之背后千年文明相决裂的勇气,将整个的生命倾泻于灿烂辉煌的画布之上。他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如果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人类究竟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终于在“三部曲”的末尾,即《刀锋》中得到了答案。主人公拉里在战友去世的偶然契机下踏上了寻求人生意义的旅途,最终从印度的《奥义书》中得到了关于瑰丽人生的启示:幸福的取得依靠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精神[8]。这或许就是毛姆游历半生,对菲利普、对思特里克兰德乃至对全体经历着精神危机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最终答复:若想抵抗漫长虚无如黑洞般的人生,必先重建人类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若用一个中国成语来形容,那么“不破不立”或许能够最为妥帖地概括毛姆不断追求生命真谛的漫长过程。
与西方世界精神危机后理所当然产生的对人生的绝望情绪不同,中国人从不太去想生命,“他们的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也正因如此,中国人一旦接触到了实际人生与“虚无”的结界,便不再往前一步。所以实际上,他们早已对“虚无”的存在熟视无睹,却可以与之和平共处而不至影响到自己平实鲜活的人生。
这种适应性的差距不难从东西方不同的宗教崇拜模式看出些端倪。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前,西方的宗教往往都具有完备且单一的规则体系,“服从”在某种程度上是多数人生命的意义所在,但随着近代西方对一切信仰的推翻,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就此摧毁,动荡带来的是无所适从的多疑和不安。然而中国人向来就有着模糊不清的心理背景,儒、释、道加以近代基督教等的传入,他们的宗教是由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构成的,数千年的多疑倒形成了一种坦然,无论各路思想如何混乱他们都自能将其纳入到中国化的背景中去,这是唯中国人所有的奇异智慧。无可讳言的,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深谙此中法门的张爱玲便是“中国式虚无主义”的忠实拥趸。
但是,“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所以,从对“物”的喜悦中生发出许多对“生”的喜悦,便成就了张氏特有的“物质耽溺”,这其中以对服饰装扮的浓墨描绘为最:正午阳光里,面前垂下镶着绿宝石蜘蛛面网的毒辣的梁太太;着磁青薄绸旗袍,一壶装在青瓷中半泼不泼牛奶似的葛薇龙……同京戏唱角的行当规矩一样,张爱玲也要让她笔下每个人物的衣着打扮都与她的地位和性格特征相吻合,如此才能保证那些人物“一寸一寸都是活的”。不仅笔下的人物以物为生,张爱玲本人也是一样。她的思想背景里始终潜伏着“惘惘的威胁”,认为一切不过是被“虚无”吞噬前的一瞬,于是,“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便成了唯一的救赎——这是她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得到的启示。对于张爱玲“中国式的虚无主义”,王安忆有句评价放在这里很是恰当:“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 ,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 ,便回缩到俗世之中 ,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9]。如此说来,张爱玲所秉持的人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或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庄子“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的处世态度有些许异曲同工之妙了。
同样是“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念,毛姆的“虚无”产生于西方精神危机的大崩溃情景之下,而张爱玲的“虚无”则是中国式的,能将一切怀疑不动声色地融入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想底色中去。根据“虚无”产生的源头不同,毛姆与张爱玲也分别形成了对待“虚无”的不同解决方法,前者选择重建精神家园以抵抗“虚无”入侵生命,后者选择用物质实在来填补生命里广袤无际的虚空。在这里做出优劣高低的判断都是不妥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身后是东西方各成体系的历史背景。
三、与中国的距离形成的“异乡社会的看客”
对毛姆和张爱玲稍有了解的读者就会知道,二者对中国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情结和浓厚的兴趣,这使他们笔下的故事多有以中国为背景的痕迹。如毛姆的游记《在中国屏风上》提供了一幅幅鲜活的中国生活画卷,以中国题材为中心的戏剧《苏伊士之东》以及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小说《面纱》,而收录了张爱玲代表作的小说集《传奇》,其故事地点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国的上海和香港。当然,仅凭二人采取的相似创作题材,并不足以说明张爱玲与毛姆在该方面的创作共性,然而相似的“异乡人”立场,却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毛姆在《在中国屏风上》中直接点明了自己心理和生理双重意义上的“异乡人”身份:“但是你对他们的陌生,正如他们之对你陌生一个样……你也有可能正如望着一堵砖墙,你对着它一无所获,你不知道关于他们起码的事情,于是你的想象受到阻碍。[10]”
如果说毛姆作为英国人,以一个“异乡人”的目光来打量中国是理所当然,那么张爱玲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又如何会以“一个西洋旅客的眼光观赏着这个古旧的中国呢”[11]?这或许与张爱玲的西式教育背景有关。对于长期浸染在英国文化中的张爱玲而言,这种距离的收缩也就是自身与西方心理距离的缩短而拉大其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从而接受西方作家的文化视野,最终在阅读心理上对“异乡人”身份产生某种认同。毫无疑问地,她把这种心理也带入了其创作过程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开头对梁太太宅邸的描写便将其“异乡人”的目光暴露在读者的视线之下:“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儿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12]。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装饰陈设似乎与毛姆笔下的女主人在中国的客厅如出一辙:“房间后壁有一个凹处,原先供着一尊入定的佛像,前面摆着一张很大的上漆香案……她只能在中国买地毯……这种手工制成的毯子没有英国货那么光滑……她只好买一架中国屏风……”无怪乎应贲这样评价张爱玲:“通过她,我们闻见了毛罕姆(引者注:毛姆)特有的神秘东方性洋味。”
虽然毛姆与张爱玲同样是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以“异乡人”的目光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古老的中国,但二人观察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毛姆与中国之间的距离让他对其产生了某种潜意识里的期待,这也就导致了他邂逅的其实是西方文化视野中的“想象中国”。在经历着精神危机的绝望中,与西方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毛姆把视线移向了东方,其“目的是想通过东方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13]。诚然,中国,在空间上代表着东方,在时间上象征着过去,是西方知识分子理想中的精神栖息地和文明避难所,而毛姆笔下以隐喻东方信仰和文化疗救的格格,在他们眼中则手握诺亚方舟的船票,是面临末日审判的西方人逃出生天的最后希望。
怀着这样的目的,毛姆在亲临中国之前,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就必然带有某种倾向性。然而,当他真正踏上中国大地,却不得不面临这样尴尬的处境:无论是由呈现出衰败光华的商店街,背着沉重货物乃至身体畸形的苦力,腐败渎职、寡廉鲜耻的内阁部长及烟雾缭绕中散发着腐烂气息的鸦片烟馆组成的令人难堪的污浊画面,还是玫瑰色的黎明下,伴随着泥土中升腾起的醉人芳香,小溪里的点点星光与稻田中的朦胧光晕交相辉映,不辞辛劳的农民与嬉戏打闹的孩子生活其中的清明图景,都是中国。不出意外地,他在破败的现实和理想的乌托邦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并感叹“心灵的眼睛会使我完全盲目,以致对感官的眼睛所目睹的东西反倒视而不见。一个人竟能完全被联想的法则所摆布,这让我自己很吃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像性制作”[14],毛姆笔下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度,不如说是毛姆自我欲望的投射,这样一种个体性想象,最终参与了整个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创造性虚构,即古往今来西方文化视野中的“想象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恰好借笔下人物范柳原之口,道出了同毛姆一样的外国人或华侨对待中国一厢情愿的心理状态:“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不只范柳原,张爱玲的故事里常常出现这一类男性的影子,像耽溺于长安古中国闺秀文化符号的童世舫,抑或是对出国前时兴的旗袍样式念念不忘的章云藩,都对古老玄异的中国抱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幻想性情结。然而,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明确地否定了这种特殊心态:“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祟拜着神圣的祖国。”并表明了她认为中国人对待中国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毛姆等人的方式相反,那就是“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看个仔细”。如上文提到,这种态度所建议针对的群体是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人,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早已把“爱国”当作一种文化基因深深地刻入到一代又一代的骨髓当中,却往往“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吧。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只有将中国看了个真切,才能爱上真正的它。实际上,张爱玲本人就是她所提倡态度的践行者,身在中国让她能够也愿意去了解“真实中国”,但又能与之保持心灵上的距离,那就是一种对于本民族深邃的好奇,从来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作理所当然[15]。这使中国在她面前如同一颗蒙尘的明珠,她看到了它的真实现状,却丝毫不影响她对它的喜爱与欣赏,只有抱定如此心态的人,才能发出如“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的感叹。
四、结语
在复杂人性的塑造上,毛姆与张爱玲都认为世上没有“彻底的人”[16],所以“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的写法”,以此形成了选取非典型人物进行描绘的写作偏好;在人生观念的流露上,二者都秉持着“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从而区别于他们所处时代那种昂扬向上的文风格调;在现实社会的描绘上,虽然毛姆与张爱玲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成分,但那也只是在理性叙事态度下有节制地表达,他们没有以小说实现社会批判功能的想法,更没有用文字参与民族社会伟大构建的兴趣,这也就造成了他们二人在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的现状。张爱玲则是五四以来以启蒙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文学形态所延伸出的“异端”,也是游离于京派、海派、左翼文学流派之外的奇特分支:不似京派对冲淡自然的逝去故乡的执着,不似海派对声色犬马的十里洋场的耽溺,更不似左翼文学对黑暗污浊的社会人生的批判。可以说,离开张爱玲笔下的“沪港世界”,人们通过文学认识到的20世纪中国也将是不充分、不完整的[17]。”毛姆与张爱玲居于大时代之外的边缘位置,以民间文化的视线打捞20世纪中英社会历史的另一些维面,而这些维面的存在将证明历史主流之外的另一种文化。他们互为坐标,成为了中英文学史上遥遥相对的两颗孤星。此外,由张爱玲与毛姆的比较研究,我们或可得出本土作家与域外作家比较研究新方法,即在共性的基础上发现幽微的个性差异,并通过进入异国文化语境与个人精神内宇的途径探讨分歧产生原因,从而在中外文学交融互动的视界下为不同比较对象找到恰如其分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