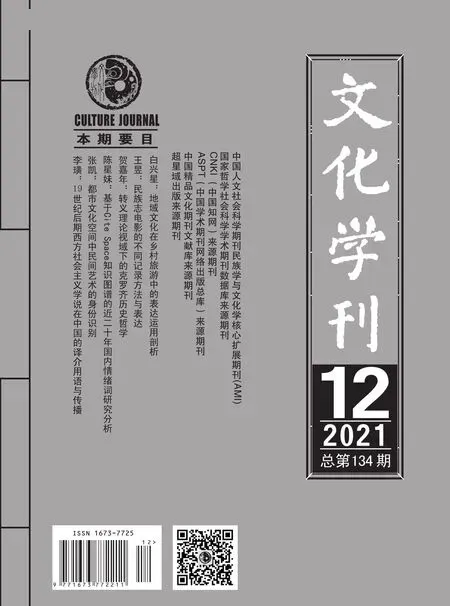“白条”与“暗号”:巧妙结构的乡土叙述与现实批判
——读李佩甫《生命册》
梁盼盼
2012年,李佩甫出版《生命册》,依然是写乡人的生命状态,写乡土经验与城市文明的对峙与碰撞,写人的异化。然而,作为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生命册》显然希望能为乡人/现代人的奋斗提供希望。
小说面临着守成与突破的双重难题:乡村/城市的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在小说中如何布局与体现?主人公吴志鹏的乡土记忆与城市焦虑是何种关系?小说要如何同时对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展开批判与分析?小说寻找到了意象化与结构性的呈现方式:“白条”与“暗号”。“白条”是源自于恩义的债务与责任;“暗号”是警训与教训,是“我”反思前行的精神资源。
一、“白条”与“暗号”——两个核心意象
小说开头就提出了人活着的“背景”与“关系”,但并不止于讨论人情为表、利益为里的权力网络,而是延伸至乡土民众性格、人伦、人情及它们对个体的影响与形塑。那么,乡人构成了“我”什么样的“背景”,“我”与乡人们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小说的第一个核心意象与叙事线索是“白条”。“我”出生后第三天就成了孤儿,在支书老蔡主持下吃百家奶、百家饭长大;学费由各家平摊,读大学是村人逼着老蔡找的关系。一切恩义与债务总领于老蔡;乡人来找“我”办事,经常手持老蔡书写的白条,托“我”办事的电话亦可视为“白条”的变体。然而“我”曾为逃离请托的电话辞职远行;“白条”几经辗转,时有延迟,却终能抵达,提醒我往日的恩情与永恒的债务。
“白条”成为了小说的叙述线索与结构方式。单数章主要叙述“我”与突入城市后的友人(骆驼)、情人(梅村)的生活;双数章(第十二章除外)主要叙述乡人们的人生经历。两种平行叙述以“白条”作为纽结:自老蔡为寻找三女蔡苇香向“我”求助,白条便源源不断发到“我”手里;梁五方每次都能带来一张,有伪造之嫌;虫嫂五张,“一张是二国考大学的时候写的,另一张是为三花找工作时写的……还有三张是虫嫂收破烂时,她的三轮车数次被工商局没收的事”;有关杜秋月的五张,两张帮他“跑事”,三张帮其妻刘玉翠跟他打离婚官司;帮春才推销豆制品的七张。“白条”将乡人的活动与“我”的生活,将“我”的历史与现实纽结到一起,标示为恩义与债务的关系。
另一核心意象与线索是“暗号”:“我”以乡人的人生故事编制歇后语,以提醒规劝骆驼。这套暗号诞生于“我”与骆驼制订向书商老万讨债的策略的时刻,其应用却远超出这一事件。实际上,这套语码的编制方式非“我”独创,而来自无梁村的风俗,可理解为“我”对乡人思维方式的继承。这种由个体命运构成的警训,成为了“我”的精神资源,使“我”与骆驼走上了不同道路。
“暗号”使对乡人的叙述与对“我”、骆驼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叙述构成了相互对照关系,使前者成为审视、反思与批判后者的参照与资源。由此,小说在结构上更具整体性,其反思更具厚度与力度。
二、骆驼与“我”——乡土经验对城市文明的现实批判
“我”与骆驼是相互对照的一组人物。二人都有着艰苦的过往、强烈的欲望、报答乡里的意愿。但骆驼身有残疾,身负兄长为保全他而死的精神重负,具有重构宏伟的自我形象的意欲;并未背负如此之重的来自乡人的恩义与债务,也未谙熟乡人们平凡卑微却又极具悲剧性的人生,因而未能从中获取警讯。于是,骆驼难以把握分寸,难以察觉“过头”,不设“底线”,不知何时“面临危险,立即回头”。其人生的失败,印证了“白条”与“暗号”的有效性。
小说将骆驼的心理与行为模式概括为“抢”,认为这源于其天性的急躁,亦来自时世氛围。应当说,小说对骆驼的急躁性格与“抢”的塑造让人印象深刻,对于情绪氛围的渲染极具感染力,但其现实性与可信性却存在可商榷之处。小说所叙述的骆驼的“商业行动”,主要是钱权交易,不仅通过名、利、色,更可能通过满足其“行善”之志,攻陷干部。这恰如对《羊的门》的官场故事的重述,只是视角由“守方”转移到“攻方”。但仅以此类叙事塑造“商界”,却显得单薄了:一是缺乏对“权力场”的叙事建构,无法指明这些行为的结构性,二是正常商业活动的缺席,无法构成“商界”。于是,骆驼的“抢”,无法真正落实为对“时世”的有效指认。
另一方面,“平原三部曲”所长,在于以乡土作为人的性格形成的地场。然而,骆驼的乡土与历史仅以三言两语交代;“我”的主观视角叙述又限制了对其内心的刻画。这使得骆驼的急躁性格与焦灼欲望,缺乏个人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支撑,显得乖戾而空荡。这一形象的虚浮,使得小说的批判难以落到实处。
借助“我”于车祸中视力受损的隐喻,以及在眼科病房内邂逅的病友的形象及病因,小说对“抢”这一“时代病症”作出了象征化的表现。然而,与其说“抢”是时代的病理机制,不如说是其最直观的症候。仅指出其危险性,未深究其社会结构性成因,则“乡土经验”也仅帮助“我”在价值判断上对此进行翻转,未真正成为分析性、批判性的思想武器。
三、作为精神资源——乡人群体与乡土经验
小说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未能尽如人意。所幸其以“暗号”引出的对乡人的人生叙事,并非仅是上述批判在乡土世界的投影,而有具体与丰富的内涵。
老蔡、梁五方、虫嫂、杜秋月、吴春才,都曾有跨越城/乡的经历,都曾因爱情/情欲陷入困境。老蔡本是战斗英雄,自愿到无梁村当了上门女婿,成为了无梁村的支书与乡村社会中的“老姑父”,然而,爱情迅速消磨,二人在仇视与争斗中度日。匠人梁五方因参建“龙麒麟”出名,与李月仙恋爱结婚,建了新房,却因为“各色”遭遇“运动”,失去房子,与妻子离婚,走上了上访之路。最后,这位“上访专业户”住进了镇上的福利院,却又俨然变成了算命高人。虫嫂家穷,靠小偷小摸度日,并靠出卖身体逃脱,后来“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了”,遭到丈夫与儿子们嫌弃。即便后来改变了行为模式,到城里收破烂,三个儿女全成了城里的大学生,最终仍是逝于乡里。杜秋月本是城里的老师,因恋爱被指为“作风问题”下放,与寡妇刘玉翠成婚;平反后重新当上了老师,设计离婚,然而作派早已被村人同化,并因此失去教职;中风后复婚,依靠妻子生活。反倒是其妻生意成功,改头换面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吴春才本有一段朦胧的初恋,因对性的羞耻与犯罪感阉割了自己,在孤独中生活,后来竟当上了豆腐大王,在镇上开工厂,因不掺假反而在市场竞争中落败,又回归到豆腐坊的生活。五个乡人,都曾跨入乃至穿梭于城市空间,终被此方乡土深刻形塑了性格,乡土显示出了生命力与浸染力。
五个乡人的生命状态与精神内涵远超出小说赋予的警示意义。在遭遇突变后,在颓唐、卑微、困苦的生活状态中,其灵魂中仍可能存在顽强、执拗、温暖、善意、安然。五个乡人的形象独特鲜活,但在乡土小说的流脉中显然存在着其原型,更增添其意蕴。他们五位一体,组成了乡土人物群像。
相较于骆驼,小说对这五个乡人的叙述要控制得更好:活泼之下的沉实,荒诞之中的谐趣,质朴之外的华彩;能够构造微妙的细节与情景,酝酿与推进情绪和气氛,写出人生之中真正的无奈,透彻而又酸软。
相较于对城市文明与时代病症的批判,小说的乡土叙述要更为丰富与深厚,显示出其作为精神资源所应具备的生命力。
四、愿景与乡愁
小说不仅把吴志鹏塑造为观察者与叙述者,更试图让其成为行动者,以体现乡土经验在城市文明中的生命力,以及这个时代自我批判、自我疗救的希望。骆驼死后,“我”成为了厚朴堂最大的股东,面临选择:是否回去执掌厚朴堂?但“我”是否能建构自己的行动方式,走出自己的道路?小说屡次让“我”以一个“慢”字作为药方,然而,如何慢下来,而又立得住,向前进?
小说描述了困境,叙述了期望,却未能提出解决方案,相反在第十二章提到了一种“仅凭着意念,让筷子在锅排上竖起来,走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的“阴阳术”。而“我”把自己寻找的道路,比拟为“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并许下世代去寻找的心愿。这一方面强调了志愿的诚笃,另一方面却提前否定了愿景实现的可能性。
为应合此种希冀,缓和迷惘与焦虑,小说最后三章沉浸于渐浓的乡愁意绪里。这启始自第十章吴春才未发生即已夭折的青春爱情故事:村庄的夜晚,有神秘的望月潭,家畜与鸣虫有各自色彩的鸣叫,而春才在田野里游荡;白天,则是以豆腐坊亘古不变的劳作填满的日子。这是萧红一脉的乡土书写,有着落寞与悲哀,亦建构了一个似乎永远可以复归的前现代时空。而至第十一章,当“我”因车祸住进眼科病房,对乡愁的渲染达到了高潮:以十二个“我怀念”,总领十二个自然段,怀念十二样家乡风物,描写细密精致,优美渺远,情绪上一波推动一波。
这几章引入乡愁书写有着相当重要的功能:骆驼已死,那种急躁焦虑的情绪也随之退散,此时若无新的情绪进入,小说的感觉可能就散了,回落了,乡愁的引入保证了小说的情绪饱满推进至高潮。而在骆驼死后,“我”将要占据行动者的位置,要走出新路,方案却无从知悉,此种决志便容易显得“空”。乡愁则以情绪上的强度与张力,填充着这强烈的“愿”,以召唤尚未现容的“景”。
乡土叙述与现实批判是相互缠绕的两大文学主题。而在乡土叙述中,恩义/债务以及精神资源是乡土经验的两个理解方向。《生命册》以“白条”与“暗号”两个意象,组织与结构小说的叙述,指明了乡土经验的两个理解方向,又使乡土叙述与现实批判合理而机巧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对人生中悲凉与无奈境况的理解与叙述,对细节与情景的营造,对情绪氛围的经营酝酿,见出了作家的功力,也生发了作品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