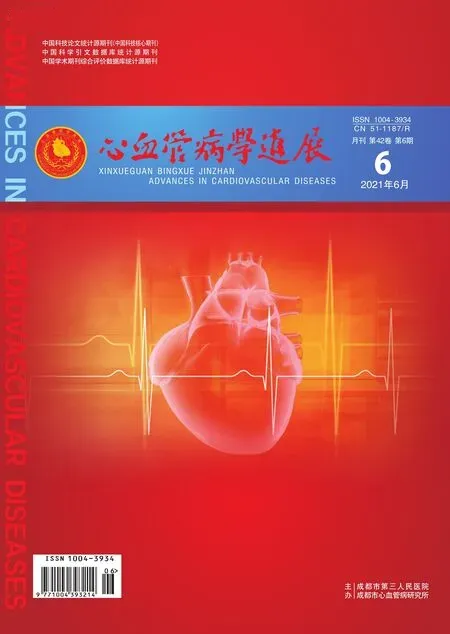基因多态性与心力衰竭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进展
臧童童 沈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上海 200032)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是指心脏的收缩功能和/或舒张功能发生障碍,不能泵出足量血液以满足身体需求的一种病理状态。HF病因复杂,冠状动脉疾病、压力超负荷、心肌病和心脏毒性药物等都可能导致HF[1],其关键在于回心的血量与泵出的血量之间急性出现的不平衡。
HF的机制复杂,与心脏重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和炎症反应等有关[2]。尽管公众对HF的认知度提高,医疗水平进步,如心室辅助装置、心脏移植等治疗新手段的出现为HF患者带来希望,但解决HF的手段仍有限[3],HF仍是临床上面临的一大问题,中国HF现患人数为450万[4],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HF患者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近年来对HF的研究逐渐深入,一些研究报道HF与遗传密切相关[5-6]。当基因突变频率在人群中超过一定比例并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就被称作基因多态性。基因多态性普遍存在于生物当中,它通常分为三类:DNA片段长度多态性、DNA重复序列多态性和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SNP是基因多态性中最常见的一种,常用于分析药物遗传学或某些特定的疾病[7]。随着技术发展,检测基因多态性成为可能。基于基因多态性的新研究和新发现,为个体化诊断和治疗HF提供了新思路。
1 基因多态性与HF的发生和发展
多态性是指处于随机婚配的群体中,同一个基因位点可存在两种以上的基因型,它们之间互相组合可产生物种基因的丰富性。在人群中,个体间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存在差异性称为基因多态性。
HF过程中,神经体液调节机制激活,主要是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RAAS和内皮素(endothelin,ET)系统,心脏发生代偿,最终心室重塑。炎症细胞因子也参与这一过程,在此过程中涉及的基因多态性都有可能影响HF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1.1 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
交感神经活动产生于中脑孤束核和腹外侧神经管,它直接刺激髓质嗜铬细胞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全身组织和器官。当交感神经激活时,向心脏发出的信号使心输出量适用于外周应激情况。长期交感神经激活,心脏结构重构,导致肥厚和纤维化,最终导致HF[8]。
β1肾上腺素能受体(β1 adrenoceptor,ADRB1)在人群中存在基因多态性,常见有ADRB1 Ser49Gly和Arg389Gly。Luzum等[9]的研究发现,携带ADRB1 Ser49Gly的射血分数降低性心力衰竭患者比携带Arg389Gly的患者其左室射血分数能更好地恢复。Johnson等[10]在非裔美国人HF试验中发现,基因之间也可能存在协同作用,ADRB1 Arg389Arg基因型携带者可放大G蛋白β3亚基825 TT基因型的影响,携带者的无事件生存期更长。β2肾上腺素能受体(β2 adrenoceptor,ADRB2)也存在基因多态性,目前研究较多的为Arg16Arg、Arg16Gly和Gly16Gly。携带有G等位基因的患者(AG型和GG型)与AA纯合型患者相比其预后更差[11]。
1.2 RAAS
RAAS在HF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主要通过抑制体内RAAS活性,抑制血管紧张素Ⅰ转化为血管紧张素Ⅱ,减少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抑制缓激肽降解,从而达到降压和改善心肌重构的作用。大部分研究的关注点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基因的插入和缺失(ACE I/D)与HF的关系,因ACE I/D可能会影响血浆中ACE的水平。
目前各项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同。大部分研究发现ACE DD型与心肌梗死有关,但ACE I/D与HF的关系存在较大争议。在中国广东进行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ACE I/D与HF发生密切相关,DD型人群慢性HF发生率高[12]。DD型人群发生左心室肥大的概率也比其他基因型人群要高[13]。但Bai等[14]的meta分析发现ACE I/D与HF风险无关,其亚分类中缺血性心力衰竭和扩张型心肌病导致的失代偿性心力衰竭风险和ACE I/D也无关。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1(angiotensin Ⅱ type 1 receptor,AT1R)是血管紧张素Ⅱ的主要受体,与血管紧张素Ⅱ功能的发挥密切相关,是RAAS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AT1R与HF的关系的结论也存在矛盾。Starzhynska等[15]发现AT1R的等位基因与血管内皮的状态有关,进而与HF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同时Moe等[16]的研究发现,AT1R rs5186突变与不良结局有关,其HF发生率显著上升。但Zhang等[17]通过meta分析发现AT1R与HF的发生和发展无关。结论的不同可能与研究对象和试验设计有关,RAAS与HF的关系需深入的研究。
1.3 ET系统
ET具有强力而持久的收缩血管的作用,同时促进细胞生长,促进有丝分裂,对维持基础血管张力和心血管系统稳态十分重要。ET-1可刺激受体引起一氧化氮合成增加,从而引起心室重塑[18]。因而探究ET系统中的基因多态性和HF之间的关系具有临床价值。
Douvaras等[19]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与健康人群相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因多态性并无统计学差异,但在对患者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携带VEGF CC型基因的患者发生HF的概率是其他患者的7倍。除VEGF,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基因多态性也与HF的发生和发展有关。酪氨酸激酶受体4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成员之一,它是由原癌基因erbB-4编码的细胞膜受体。它的多态性可能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HF的发生及发病严重性有关。rs10932374和rs1595064与较低HF风险相关,rs13003941和rs1595065与较高HF风险相关[20]。
而Colombo等[21]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发现,ET-1和内皮素受体A的基因变异均与HF有关。ET-1 Lys198Asn和内皮素受体A H323H对HF的发生和发展有协同促进作用。
除ET及其受体等的直接作用,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NOS)也是ET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NOS是一种重要的同工酶,在内皮细胞、巨噬细胞和神经细胞中均有分布。内皮中的NOS被称为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它在血管内产生一氧化氮,协调血管功能,近年来对eNOS基因的研究逐渐深入。Oliveira等[22]发现在eNOS的G894T位置携带G等位基因的人群发生HF的风险更高。且Fares等[23]发现在外显子G894T位置携带G等位基因的HF患者有更大可能发生心房颤动。G894T位置负责编码eNOS第298位的氨基酸,如该位置的核苷酸从G突变到T,该位置对应的氨基酸会从谷氨酰胺突变为天冬氨酸。这可能会对eNOS的活性产生一定影响,从而造成HF发生率的差异。但也有研究者发现eNOS的基因多态性与HF无关[24],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种族和试验设计有关。
1.4 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是HF的重要病理生理机制。多种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γ干扰素、白介素(interleukin,IL)-1β和IL-6]和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均参与HF的发生和发展过程[25]。关于IL的研究较为全面,近年来对免疫反应过程中涉及的其他分子的研究逐渐深入。
IL-6是一种重要的炎症调节因子。Markousis-Mavrogenis等[26]通过对BIOSTAT-CHF队列研究的分析发现,超过50%的HF患者出现IL-6水平升高。IL-6基因、IL-6受体基因和IL-6信号转录因子基因在人群中均存在基因多态性。Hansen等[27]对IL-6基因、IL-6受体基因和IL-6信号转录因子基因的SNP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析,发现5个IL-6受体内含子SNP和1个IL-6受体编码区SNP与不良心血管事件结局有关。随着对IL-6信号通路了解的深入,它有可能成为严重HF的独立预测指标。
酪蛋白激酶2相互作用蛋白1可调节M1和M2巨噬细胞的极化[28]。Li等[29]研究了酪蛋白激酶2相互作用蛋白1在汉族中的基因多态性和HF的关系,发现酪蛋白激酶2相互作用蛋白1的非同义替换rs2306235(Pro21Ala)与慢性HF有关,尤其在高血压患者中。因此该基因多态性可能是汉族人群中HF的危险因素。
除免疫调节与巨噬细胞极化,巨噬细胞的迁移在HF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ion factor,MIF)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因子,参与心血管疾病和多种免疫系统疾病的免疫过程。在临床研究中发现,MIF与射血分数降低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30]。MIF也与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有关。El-Mahdy等[31]发现携带MIF rs755622的人患HF的风险更高,尤其患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的概率更高。
2 基因多态性与HF的治疗
目前HF治疗的主要药物有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blocker,ARB)、β受体阻滞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利尿剂、正性肌力药以及新兴出现的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ngiotensin receptor-neprilysin inhibitor,ARNI)[32]。不同人的药物敏感性和耐受性存在差异,基因多态性可能是其原因。如在心血管等多个领域,基因检测已广泛应用于指导华法林的剂量,维生素K环氧化物还原酶复合体1和细胞色素P450 2C9的多态性已被证实与华法林的代谢速率有关,通过基因检测,可实现对患者的精准治疗[33-34]。HF患者的用药复杂,患者个体差异大,因此研究HF中的基因多态性对指导临床治疗方案有一定意义。
2.1 基因多态性与β受体阻滞剂
2.1.1 药物敏感性
如前所述,ADRB2也存在基因多态性,带有G等位基因的患者预后更差,但他们对β受体阻滞剂的敏感性更好,且与G等位基因呈剂量相关性,AA纯合型患者则无这一趋势[11]。Wu等[35]发现ADRB1的基因多态性也与治疗效果有关。与ADRB1 1165CG患者相比,ADRB1 1165CC的患者对β受体阻滞剂的敏感性更好,预后更佳。但具体机制仍待探讨。
2.1.2 药物耐受性
细胞色素P450 2D6(CYP2D6)是一种重要的氧化代谢酶,参与美托洛尔的代谢。与不携带CYP2D6*4的患者相比,CYP2D6*4携带者对美托洛尔的耐受性更低[36]。临床医生可根据不同患者对β受体阻滞剂的敏感性与耐受性综合给药[37],对于β受体阻滞剂敏感性高且耐受性低的患者,需减少剂量;对于β受体阻滞剂敏感性低且耐受性高的患者,需适当增加剂量以维持药物效果。通过检测患者对β受体阻滞剂的敏感性与耐受性,可更加个性化和合理化地给药。
2.2 基因多态性与RAAS抑制剂
2.2.1 基因多态性与ACEI
ACE I/D不仅与发病风险相关,也可能与治疗效果有关。Hristova等[38]的研究表明,在接受RAAS抑制剂的患者中,ACE DD型患者血清中的ACE水平最高,I/D型次之,II型患者血清ACE水平最低。由于血清ACE水平是高血压、HF等的保护因素,且ACE I型人群ACE酶活性更高[39],因此可认为ACE DD型患者的RAAS抑制剂治疗效果最好。
另外一项包含158例患者的研究发现,ACE基因多态性对培多普利的治疗效果有影响,其中DD基因型者对药物更加敏感,且对其预后有明显改善作用。而CYP2D6基因多态性对培多普利的代谢无明显统计学影响[40]。这与前述的CYP2D6基因多态性影响美托洛尔耐受性的结论不同,这可能与不同药物的不同化学结构等有关。
2.2.2 基因多态性与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作为细胞色素家族的一员,CYP11B2是重要的醛固酮合成酶,它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多态性[41]。Sarhan等[42]的研究表明,在同样服用6个月螺内酯后,AGT rs699 CC型和CYP11B2 rs1799998 TT型基因携带者的心功能改善情况最好,其左室射血分数回升最多,同时左室收缩末期内径和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减少。这可能与TT型患者使用螺内酯后,血清中醛固酮水平更高有关[43]。
2.2.3 基因多态性与利尿剂
噻嗪类利尿剂在临床上有广泛应用。eNOS作为一种重要的调节血管功能的同工酶,其多态性与利尿剂的作用也存在关系。Turner等[44]的研究表明,eNOS的氨基酸残基298位点的多态性与噻嗪类利尿剂的疗效有关。298位点的多态性共有3种:Glu298Glu、Glu298Asp和Asp298Asn。在均使用噻嗪类利尿剂的情况下,与其他多态性的患者相比,Glu298Glu型患者的血压水平降低更多。在HF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疗效。
3 总结与讨论
根据已发表的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已证实许多基因多态性与HF的发生和发展有关,主要是RAAS、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和ET系统中涉及的基因。随免疫反应在HF中的作用被逐步发现,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炎症反应中的基因多态性。这些基因的多态性与疾病的患病、预后和治疗等都存在密切联系。但不同研究者得到的结论有时互相矛盾,可能与试验对象的人种、年龄、性别以及试验设计有关。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研究基因多态性与HF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ACE2是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进入细胞的关键受体[45],关于是否应继续在患有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中使用RAAS抑制剂一直存在争议[46]。Gómez等[47]的研究表明,ACE的基因多态性可能影响COVID-19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Yamamoto等[48]的研究表明,SARS-CoV-2的感染和COVID-19导致的死亡与ACE I/D存在关联。因此研究基因多态性对COVID-19大流行时期的HF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对基因多态性的研究在阐明疾病临床表现多样性、药物治疗敏感性和疾病易感性与耐受性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对肿瘤等疾病的基因多态性的研究为精准治疗提供靶点,同样的,对HF的基因多态性的研究也可能为个体化治疗HF指明方向。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的基因型选择用药,调整剂量,防治并发症。研究HF的基因多态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