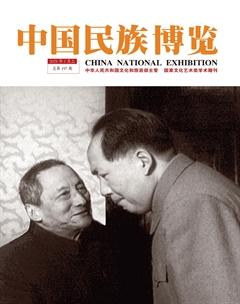拆解时空的差异性存在
【摘要】本文旨在对音乐发生时的时空状态进行描述、分析,表达了作者对音乐的存在方式及结构问题的部分看法,并对该选题的来源做进一步的补充。
【关键词】拆解;时空;原子论;音乐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1-131-04
【本文著录格式】刘约仑.拆解时空的差异性存在——音乐的时间、空间与神[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131-134.
“当每一个音符的流逝以点的方式留存下来,逐渐地,这已不仅是一段旋律,而是流淌的星河……”
《拆解时空的差异性存在》(以下简称《拆解》)作为一套分析方法,其立意的基础来自“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这一普遍的认识。文章借助物理学与数学工具性的特点并辅以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将关于音乐的命题置放在时间与空间中进行讨论。它的分析思路,参考对“原子论”在广义上的诠释,即:把事物理解为彼此独立的单元机械结合的产物(黄敏 2018)。这套分析方法与逻辑原子主义有相近之处,即:语言和世界存在对应关系,但《拆解》中着重分析的是用语言描述的世界中的物和事件。与“逻辑原子”不同,《拆解》中的原子或分子以闵科夫斯基所描述的世界点为准,每一个事件或事实的发生记录为一个点,每一个点对应一个事件,每一个事件按其在时空中的属性进行关系排列,相同属性的点为同一级,根据空间中的点具有离散性的论述,不同属性的点按照这一规则可与相邻的点进行转换,同时,如果将这些时间点以几何的方式构画出来,也可以根据数学中的点集论进行推衍,而以这些点为基准形成的连续区就是对应某一个或多个音乐命题的空间图像。以这些图像为参照,进行关系的推导,就可以得出原命题的真或假。这与数学中证明一个命题的真伪的过程是相似的。罗曼·茵加尔顿将音乐的时间称为对应于物理时间的“内在时间”(或称“主观时间”);卡西尔认为,艺术世界具有所谓的“两极性”,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库尔特·勒温把宇宙分别看成心理的和物理的。以此为依据,我们把音乐发生时的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的,另一种是客观的,即心理宇宙与物理宇宙,但二者皆统一于时空当中,并按照时间流逝的方向顺次排列,无分主次。这也符合了恩斯特·马赫关于要素的一元论的论述,认为最后的部分——一切要素都是等价的,物体的要素、身体的要素、心理的要素相互依赖、互为因果。
一、观测之外的客体
音乐的开始源自于我们对于这一客体的观测。要注意到,它的本质不是作曲家的笔、演奏者的乐器,更不是欣赏者的耳朵。“假定我们看到一棵树,然后我们把头转开去。我们怎样知道这棵树在我们不去看它时仍旧在它的位置上呢?如果我们回答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头转向这棵树,从而证实它并没有消失,这是无济于事的。这样证实的只是:当我们去看它时它总是在那里;而这并不排斥如下可能性:当我们不看它时它总是消失了,只是在我们把头转向它时,它才又重新出现。我们可以做后一种假定。按照这个限定,观测使客体发生了某种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变化的变化。我们无法证明这个假定是错误的。(H.赖欣巴哈 2018)”这是赖欣巴哈在论证客体会受到观测干扰时用到的一个例子。这里的客体,应有别于胡塞尔的“意向对象”,二者间最显明的差别是界定它们的方式:观测的客体重在“观测”,它更倾向于实证性,而“意向”更多的是由“心”到“物”的趋向作用。这是作为“介质”的一种区别,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作为“客体”本身的不同。比如,树与音乐。请予以足够的关注:音乐的发生,一定是运动的,不论它以何种方式运动着,它必须具备在时空中的可持续性,即它必须满足构成连续区的条件。据此可以设想,音乐不仅仅以音响形式出现。如果作为音乐的对象本身就是绝对静止的,那么它如何以运动的方式让我们感知?但这也提醒了我们一点,和赖欣巴哈一样的观点,我们只能确证自己所能确证的,至于那些静止的在别处是什么样状态,始终只能存疑。
二、关于“不稳定性”的陈述
我们的心理宇宙与物理宇宙从构建基础来看都是统一于时空的,音乐的发生一直游走于这两个宇宙之间,却似乎始终无法实现单个点的独立留存。(请注意,这个点一定遵守不可再分的原则。)“无论如何,心理学不能如物理学一样,讨论一个单独的联系的空间,用以代表它的宇宙的全体。相反,心理学的题材为多数分立的空间,或许多各自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人或动物的完整体。物理宇宙在动力上为一封闭的统一,心理宇宙在动力上为开放的统一(库尔特·勒温 2013)。”在《拆解》中,我们把音乐置放在宇宙中来讨论,这个宇宙包括了宇宙本身以及所属于它的宇宙。然而,我们不能把心理宇宙与物理宇宙完全割裂开来解释,因为心理宇宙的生成往往源自于物理宇宙的刺激,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忽略“走入”与“走出”这一“经过”的过程。当我们以时空中的世界点勾画音乐中的一件事或者多件事时,物理宇宙与心理宇宙的联系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在一个相对的前提下,对于音乐时空间的封闭问题,我想借鉴舒茨提出的“全醒”这一概念。“只有当我们离开对日常生活的完全注意,使意识脱离‘全醒的张力状态,不再与外界世界打交道,内在生活才能变得可见。”(于润洋2012)也就是说,当意识自身的张力发挥到最强时,客观空间与意识空间各自的封闭性最好、稳定性最强。但是,我们很难估量作为“非全醒”的张力的标准,却能比较容易地理解自己与另一事物在意识上产生聯系的感受。比如:我打开电脑,准备写一篇文章。当我在自己的思维指示下不断地敲击键盘时,我的意识的状态就应该属于“非全醒”的。原因在于,一个普通的人很难以两条不同方向的意识流去完成不同的两件事。就像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同步地写文章和看书,这似乎难以做到。我们只能交替着去做这两件事。这实质上已经证明人类的意识在常规的情况下只能支持我们与一件事交流。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意识以独立的状态与一件事产生联系时,便是“非全醒”的。如果我们在音乐播放的同时又与旁边的人积极地聊着天,这时对于“聆听音乐”这件事而言,就不具备封闭的条件了。
三、音乐——作为中轴线的时间?
以下将要讨论的问题,都以意识的“非全醒”的状态为前提展开。
通过《拆解(一)》,我们了解到音乐发生时人处于两个空间,一个是物理的空间,一个是心理的空间,并且这两个空间的维度极为相似。当意识与音乐产生交互时,对应于这段音乐的心理空间得以产生。这时,划分开这两个空间的就是作为音乐的一维时间,它的存在形式与物理时空中的时间相似,不同的是,音乐是有限的时间,而物理空间中的时间是无限且延绵的。音乐的发生决定了它所对应的心理空间的存在,它的长度决定了这个空间崩塌的时间。作为音乐的时间充斥在心理空间中,同时它也成为划分两个空间的边界。如果我们把这段音乐的长度从物理空间中截取出来,似乎会有这样一个错觉:一个物理空间相似或相同地对应一个心理空间,它们以音乐的时间为中轴线对称分布。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并且远比此复杂。
我们知道,音乐在流逝的同时,物理空间中的时间也在流逝。我们以物理空间的时间为参照基准,做如下推论:在“非全醒”的状态下,每一个存在于音乐的物理空间中的点都能找到一个与它相对应的心理空间的点。站在时空间的角度上,从仅仅讨论“音”与“心”的关系看,音乐在空间中呈现的形态是曲尺形的。
心理空间在时间轴上的点始终稍晚于对应的物理空间中的点。同时,我们也发现,作为发生于空间中的事件,它们都代表着在时间中物体在某一刻的运动,可是,实质上这些事件按照我们前面讲到的“层级”的准则进行排列,却不在一个平面上。“我们知道,宇宙中存在着无数的点,这些点往往代表着不同的事件,闵科夫斯基将它们称为‘世界点。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点不仅是‘一,它也是多个一的集合。”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根据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对空间的“一”与“多”的论述来论证。但我想用更直观的方法让大家来理解这个区别。比如,我正在操场上跑步,这是一件事,与它同层级的事件是我正在看书,或者我正在享用晚餐。在这一层,个体为单位的主体实践着一件只能以一个谓语动词描述的句子的事件。但在宇宙中,这些事件分别以一个时间点的方式留存着。请注意,绝不能以此为唯一确定“层级”的标准。原因在于,当我在操场上跑步时,如果以腿的运动为参照,把它看成运动的主体,我们可以把每一步看成一个事件,这样,它相对于“我正在操场上跑步”而言属于第二层级,在排列上,应该另当别论,我们也可以说,第二层级上的点从属于第一层级的点。这也遵循了逻辑原子论的推衍方式。同理,如果以目光落在书本文字上的运动和筷子的运动为参照,就能够看到第二层级的呈现。所以,事件的主体的属性也影响着“层级”的划分。相同层级的主体应该满足同一属性的诉求,要参考毗邻它的上一层级和下一层级进行划分。
由于音乐这一维时间的出现,时空间的单一属性被割裂,但也是它让两种属性的空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系。如果我们仅从时间上辨析这两个空间和它们的关系,似乎事情会显得容易许多,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在时间中留下了足迹,那么这个足迹一定也留存于空间中。这假使在一个坐标轴上横向代表时间,纵向代表空间,我们可以根据所选取的音乐发生过程中的点的先后顺序和间隔确定它纵向上的位置,但它在空间中的位置却需要专门进行讨论。
我想先强调一组概念:参照和相对性。我们想要在空间中确定一个点的位置,往往要以另一个点作为参照,这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有过相关的陈述。由此就引出了与它双生的“相对性”。当我们做出如下的描述:A在B的左边。这时,B是A的参照物,我们对A的位置的确证来自B,它是相对于B而言的。所以,对一个点的位置的确证,源于对参照物的确证。当参照物改变时,相对位置随之改变,但相对位置的改变并不仅依赖于参照物,还有它所属的坐标系的改变。这一个坐标系也可能是另一个坐标系中的其中一个,同时,这个坐标系中又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坐标系。其实,这也是整部《拆解》中始终不会脱离的一组哲学范畴:有关于它的所有命题,自始自终,都需要参照,都是相对的。至少,在我们的这个体系中是这样。对于不同属性的空间而言,这种参照和相对性又有所区别。如果我们想要限定相对性,那么,请拒绝对任何事物的定义。这样看来,一切都陷入了混乱。我们能做的是在不同的参照与相对中找到有效的规律,使其在一套有序的系统中获得客观的存在价值。即使是公理或定理都离不开成就它们的那一套系统。
物理空间中的点应有外在与内在之分。在这个空间中,有不同的参与者,而不同的参与者会有不同的行为轨迹和机体动态,这些都将导致分析上的异化。从时间上讲,音乐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中是错位且对称分布的。但从时空间上讲,“对称”只是音乐于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中迷惑人的假像。所以,我们要严谨地去看待音乐的“镜像”问题。如果是“镜像”,意味着镜中之人与镜外之人几乎一般无二,至少镜中之形与镜外之形是统一的。但心理时空间中的“形”与物理时空间中的“形”無法统一,它们映射出的“像”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说音乐如镜般映射出其“像”,我们似乎称其为“境像”更为合理。以上可见,物理空间中音乐发生的位置的确定,依据的是它的实在位置的一个参照,而心理空间中的位置需要根据或经验的或关系的、甚至或规则的前提条件来获得,而这些经验的、关系的、甚至规则的,又要求我们以更多的实例来加以判断和归类。
四、音乐时空场存在的可能性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们将音乐时空场的力学基础进行了初步的阐明,由于目前的研究对时空场这一概念还存有些许争议,相关的资料也比较有限,我将在这里结合先前已有的观点和论证来阐述我们所要使用的“时空场”的界定。引用爱因斯坦的“时间是我们用时钟测量”的格言,底部时空(各种束的基本空间)是一个构造,从片段上观察逆向工程。因此,虽然时空(作为基础的基础空间)本身不是一个字段,但是我们收集信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字段,因此,在这个“物理”意义上,用字段定义。实际上,在时空中有一个与重力相似的存在,即时间。可以明确,时间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进的力。在它行进的过程中,必定会改变周围的某些结构。虽然我们不能在时间本身中看到量子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场引力”的存在,也正是有了这一“场引力”才有了支持时空场存在的根据。可以看到,时空本身就是一个场,我们只知道如何处理在非常理想化的情况下将时空作为一个领域来处理的复杂性,然而我们期望这样的公式存在而有意义,并且是时空和几何的最基本的表述。因此,时空中任何物都无法逃脱这一“场引力”的影响。我们所讨论的任何一个问题,只要是在时空的领域内,就一定有一个力是朝向时间的。在对音乐的时空间问题的讨论中,这一点始终需要被注意到。由此可以基本确定,我们以时空间为基准勾画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属于黎曼的。
在时空中,音乐作为一维特殊期间的时间而存在。如果我们把宇宙看成一个大型的时空场,那么根据空间中还有空间的论断,一个场中也可能有多个场存在。这里,我想通过两个例子加以证明。第一个例子,一位钢琴家正在演奏肖邦的夜曲。这时,基于几何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他所处的演奏厅看成一个场,基于时空的角度,这位演奏家正处于整个大型的时空场中的一个或者一部分中,我们用H表示它。以鋼琴家奏响第一个音符为界,在H领域中又可以分化出相对于音乐发生时的前域、域内以及后域。它们并不完全占据H领域,前域、域内和后域可以被看作属于H领域的一个领域。第二个例子,我们在时空中选取三个点,创作者写作音乐作品时、演奏者演绎音乐作品时以及欣赏者聆听音乐作品时,当这三个点在时空中发生联系,就定义一部音乐作品从有到无的一次比较完整的过程,这一段期间的时间充斥在这个连续区中。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看到以事件为单位的时空场具有独立与交互以及互相转化的关系,这一关系止步于不可再分的终极命题上。
从谱面上看,在音乐的发生中,横向向后力是始终存在的。同时,相对于每个音的前一个音而言,在它们的纵向上有一个垂直向上的力,在这两个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这些音的斜向上行的趋势。这时,我们把这不同的音的时空间位置放置在一个坐标系中,坐标系中的坐标轴t代表时间,坐标轴s代表空间,当两个音之间间隔的时间越长,它们在坐标轴t上的距离会越远,这就是时值;当两个音在听觉感受上差异越大,它们在坐标轴s上的距离也会越大,这就是音程。同样,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推论方式沿用至其他的乐谱当中。只要我们所标识的音存在于这个坐标系中,就应该会有在这个空间中与它所适应的推论方式。当矢量从一个坐标系变换到另一个坐标系时要进行线性变化,对点来说也要进行仿射变换。这也就是我们在《拆解(二)》中提到过的“中心位移”的解释。这时还需考虑几个问题:在同一个坐标系中的音的坐标所要转换坐标系的前提是什么?不同的音乐的坐标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不同坐标系之间是否存在调性关系上的转换?不同的调性是否共存于一个坐标系中……
五、神与神性
我们对直接事实之外的潜在性的理想认知,都源自神的魅力。留存在时空中的点是以“逆向工程”的形式被经验着,正如阿尔弗雷德·舒茨所说:“正在发生的经验,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处在经验之中时,它并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回视过去的经验时,它才具有意义。……过去的经验对于反思的态度具有意义,这意味着它们是在采取反思态度的‘现在中被感知的。(于润洋 2012)”而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是神让我们具备了反观时空间中的连续区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音乐与神是对等的。虽然音乐似乎也具备这样的能力。毕竟,音乐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先验存在的产物,即使它玄妙于时空当中,我们也无法否认这一点。因此,音乐本身并不是神,但它却具有神性,我们可以说它是神之形与气的体现。同时,音乐与神相通,可以在广袤的空间中在神的影响下不断地转化与进阶。
六、结语
在《西方音乐美学史》中,福比尼在他的最后一章《未来会怎样》中写道:“……在当今的音乐美学领域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和广泛的多样性。凭借这种丰富性,未来将会出现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论,一方面包容了我们已经证明了的过多的分裂性;另一方面去除了那种能够想象到的弱点,即当过于以预设的体系为基础时思想将会遇到的危险。(恩里科·福比尼 2005)”我们通过解构与重构,在不同的封闭的体系中找寻着一个新的、能够解决足够多问题的封闭的体系;我们借助物理学和数学的理性思维来平衡哲学思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我们的《拆解》还处于成长当中,却也努力地一步步靠近理想的那一部分。假如时间是过程的转化,空间是不同存在形式相互交织而形成的静止的必然性,那么我希望在这两者融合的时候,找到属于音乐的“生命和运动”……。
参考文献:
[1]黄敏.哲学分析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德)H.赖欣巴哈.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M].北京:商务图书馆,2018.
[3](德)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北京:商务图书馆,2013.
[4]于润阳.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6]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北京:商务图书馆,2012.
[7]恩里科·福比尼.西方音乐美学史[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刘约仑(1987-),女,汉族,四川自贡市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音乐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