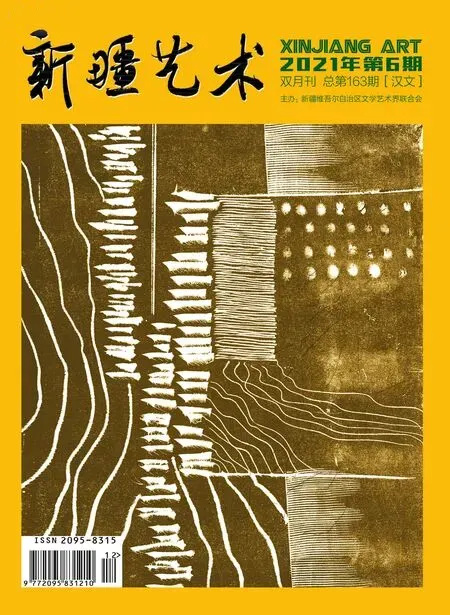欲望的高度
——关于长篇小说《珠峰海螺》的辨析
□ 黄 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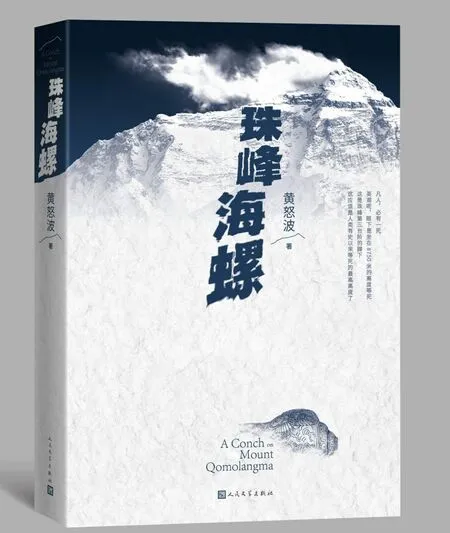
这是一部有着类似欧美电影气质的小说。故事紧张、刺激,叙事环环相扣,又不乏温婉的抒情。
小说一开始就制造了一个悬念,主人公英甫在海拔8750 米的高度等死,并强调“这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等死的最高高度了”,就像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一开始写到的那样:“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的最高一座山……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这是多么相似的一幕!他一下就抓住了读者,急需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在那样不同寻常的高度去等死的心理。这是个欲望的高度。显然,作者对好莱坞电影开场的引人入胜、先声夺人的悬念手法是非常熟稔的。

珠穆朗玛峰
小说的展开其实并不复杂,以英甫登顶珠峰,然后下撤的2013年5 月17 日至2013 年5 月19 日的三天结构全篇,分别以第一天:大难临头,第二天:雪上加霜,第三天:绝地恐狼,三个小标题概括了一个人在珠峰极地极难、极险、极恐的三天生死历程。而这些只不过是明面上的文章,作者用了两条线索,类似于蒙太奇的手法交织进行,一条是英甫登山下撤受挫,围绕着救援展开的种种行动,恶劣天气、肆虐的风雪、峰顶旗云、飑线天气、低温缺氧、脑水肿、阴谋者设计的一步一步的危险、命悬一线的挣扎。诡异而超乎想象的山神启示;另一条是英甫在危难之际对商场你死我活争斗的回溯,此次登山貌似是一次被逼无奈的选择,实则是整个谋划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亦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甚至有以命相博的意味,是赌就有输赢,谁也不能保证一定会赢,只不过英甫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各个环节基本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人有时在极端的境遇下,才会激发出潜能,忽生慧心,也只有在这特定的高山缺氧情况下,半醒半梦和亦真亦幻中,求生的本能使之必须对眼前做出基本判断,思绪缥缈、瞬息万千中,顺带着也会对过往有个理性的辨析,如此这般,纷繁复杂的事件渐渐被梳理出头绪;一个在所有人看来必死无疑的登山者,能够生还,是一个奇迹,也应是一个意外,而他的起死回生则宣告了一干人的毁灭,这种反转既符合小说的逻辑,也符合读者的期待。
小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还原一个物质世界,一种世俗生活。显然作者是有着这方面的考量的。这个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对文学的理解自不必多言,况且他完成过世界七大洲的攀登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三次登顶珠峰,同时他又是国内房地产的大佬,大名鼎鼎的中坤集团的创始人。可以说,他将此生最拿手的三件事组合在了一起,用文字将房地产商业与户外登山串联起来,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阅历生涯的碰撞,迸发出了耀目的华彩,形成了层层迫近的关系,其结构的张力自然呈现出。
大多数人中,某人可能具有写作的天赋,但不具备商业和登山的生活体验,而也可能你是一位登山家,却不会侍弄文字,更不具商业实操,抑或你是一个商海沉浮的地产商,却与文学、户外毫不搭界。只有同时拥有这三种生活体验和能力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与众不同的小说。毕竟,写攀登珠峰那样世界级的山峰不是靠道听途说或者想象就能够完成的,那么细致专业化的描写,那么扣人心弦的氛围的营造,那么精彩的特定环境下人物心理的调动,如果没有登遍七大洲高峰的经历,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数十年房地产开发的风风雨雨,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 年逐渐做大做强的所谓“暴发户”,对在商场如何立足,如何发展,如何守成,有着最直接的体验,他们面临的种种艰难也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他们的付出,有时甚至是包括生命在内的所有身家。不要只看到这些新贵是如何的有钱,这些光鲜的背后,哪一个没有一肚子苦水?同行的觊觎,劳资双方的斗智斗勇,金融机构的冷漠,黑社会的威逼,腐败官员的贪婪,时时受制于人,又时时低三下四、曲意奉承,处处提防小心,又防不胜防,步步惊心,步步疼痛,没有这样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积累是难以完成此部小说的构建的同样它也不是靠想象所能形成的坚实而可靠的小说基座。
这部小说的象征和隐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别以为这只是一部以登山为故事构架的小说,其实它也是写另一种攀爬,在商业社会的打拼中,每一步不比登山容易,即使是攀登像珠峰这样的世界第一峰,高海拔带来的一系列凶险,仍不如商海缠斗的种种可怕,登山中你如果训练有素,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体能、坚定的意志,再加上好运气,往往是可以登顶的,但想要攀上商业高峰成为第一,就算你绞尽脑汁使出洪荒之力却是千难万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自然的斗争,彰显出的是疏朗的人的精神与气度,而人类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的争斗,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折射出的则是混沌的欲望与贪念。可以说作者用登山的故事写尽了商业社会的复杂与凶险,他是在讲述这个时代,讲述这个时代的记忆和经验,把当下物质世界与世俗社会这些活着的历史表达得淋漓尽致。
小说除了物质的还原,还必须是精神的容器。有人说,小说要解释世道人心、探索人性,为人类的精神作证。
作者在小说扉页上赫然摘录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骇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了灵魂的深。
在这个变革的伟大时代,谁能是审问者?审问者与被审问者之间总是不断变换着角色,令人目不暇接,最终的结果是对人性产生深深的怀疑:这世上谁是好人呢?究竟有没有好人呢?坏是建立在好的对立面上的道德划分,而好又是基于何种范式定义的呢?你认为的黑不一定是黑,你判断的白也不一定是白。我们的小说家和读者,更愿意看到非白即黑、非好即坏的人物,那样既简单又容易理解,就像琐罗亚斯德教所推崇的黑暗与光明的二元论一般,黑和白代表了这世界最基本的元素,也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对抗与协调。但小说写作却有所忌讳,好人坏人的界限愈分明,愈缺乏人物的深度,黑白之间的过渡色杂色愈多,人物的价值就愈大。
以英甫、罗布、牦牦、吴菁、朱玫等为代表的形象,是好的正义的一方,以吴亦兵、叶生、西门吹雪、施副区长、伊行长、齐延安、吴铁兵等为代表的形象,则是坏的邪恶的一方,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在这两大壁垒中,读者很容易做出道德判断,划分出他们心目中的黑与白,这对小说家来说是欣喜还是悲哀呢?
英甫这个人物,显而易见有着作者的影子,或者简直就是在写自己,这种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人物,或许更容易把握。作品中英甫是一个商业的奇才,有眼光、有谋略、有胆魄,既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又有温婉柔情的一面。果断与勇气是他突出的行事风格,从做人做事及品格上衡量,英甫似乎没有什么大的缺陷,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瑕疵,如此完美的一个人,却让人不那么信服,他在危难之处总能化险为夷,总有意想不到的人出来为他出头,原因并不是他的仗义豪情,有着强烈的人格魅力,而是他处处施舍,做慈善,出手阔绰大方,动辄几千上万,对他的信任与好感,皆源自他背后的巨大资产,钱的力量仍然是驱动一切的原动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钱密不可分,当英甫的氧气行将告罄,命悬一线时,甘米从尼泊尔一侧冒险将氧气送来,救下奄奄一息的英甫,以他们之前登山结下的友谊,甘米大可不必为此冒险,但英甫是一个金主,他为甘米的“尼泊尔青少年基金会”慷慨解囊,解救被沦为妓女的尼泊尔农村女孩,为拯救牦牛、秃鹫他勇于承诺,对甘米们来说,他是一个“有用”之人,这样的人必须救,救得有价值;当叶生带着青年杀手准备掏枪时,青年却发现英甫就是26 年前在一个慈善晚会上从一个和尚手中用了十几万救治自己兔唇的恩人。钱是万能的,这也许是英甫们经过奋斗最终跻身社会精英阶层的这群人最终得出的真理。
倒是吴铁兵和齐延安这两个人物塑造得较为丰满。这两个当年造反的红卫兵,逼死了他们的女班主任,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在草原上山下乡,美丽的女孩为了赎罪,开始学习油画,临摹18 世纪俄罗斯名画《春天里的耶稣》,但这幅画却因为吴铁兵对齐延安的嫉恨而被吴铁兵毁坏了,连忏悔赎罪都不能,女孩彻底绝望了,在一次草原的大火中,女孩葬身火海,这对吴铁兵和齐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也因此结下了一生的恩怨情仇。
两人日后都成了高官,都是在社会上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曾经有个理想,但理想破灭了,他们以为找到了方向,最后发现,愈走愈迷惘,他们曾付出真爱,但真爱被付之一炬,两人的书房里都壁悬着相同的三幅油画,其中一幅的内容就是女孩被大火包围,在烈焰中如花蕊般的面庞,他们的内心都珍藏着那个时代弥足珍贵的一点点可怜的爱,其实,他们的心已死。为了子女的营生,他们动用自己的势力,几十上百亿资金在他们掌股中玩弄,各自的信托基金会都成了他们发挥余热的趁手工具,他们贪婪无情的本质,其实是扭曲灵魂的再现,是对他们逝去美好青春的招魂,是对社会的不仁不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讲故事。如此说来,优秀的小说,一是要对物质的还原,二是要有对精神的探索,必须二者高水平的综合,才能称得上一部杰作。
语言的冒险,是当下小说创作最值得研究的现象,实际上它是进行着如何叙事的探索,这种探索的意义,才更能接近小说的本质,还原文学的初衷。作者曾经是一个出过几本诗集的诗人,多年的诗歌训练,使他的语言干净、节制、漂亮,与其他小说家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小说中的语言基本保持了诗歌的弹性,节奏张弛有度,画面感强烈,如果将此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应该有不错的基础。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小说的结尾部分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完美结局,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纪委的介入使一切变得清晰和简单起来,这样的结局契合了国人的心理预期,是中国读者最希望看到的,也是符合当下的需要,它释放了一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善恶结果的情怀,说不上是久违的宣泄,但一定是提供了某种渠道,只是,现实中正义的伸张,往往比我们期待的要来得迟一些,至少比小说中出现的会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