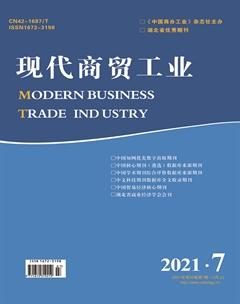《墨子》人才管理思想探析
周叶玲 雷志柱
摘 要:墨子提出了“列德尚贤”的政治主张和人才管理思想,在中國人才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贤者政之本”的人才价值思想,“德为先、能为本”的人才选拔思想,“察能授官、量能而用”的人才使用思想,“赏当贤、罚当暴”的人才激励思想,“全面考察、量功分禄”的人才考核思想,“上说下教、以行为本”的人才培养思想,构成了《墨子》内容丰富而体系完整的人才管理思想。这对于新时代做好各项人才工作、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子;列德尚贤;人才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07.025
1 “贤者政之本”的人才价值思想
墨子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墨子提出,“夫尚贤者,为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首先,尚贤“取法于天”,是天神的意志,也是古圣王的为政之道。“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尚贤上》),如尧举舜于服泽,禹举益于阴方,汤举伊尹于庖厨,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等。古代圣王正是由于重用了这些贤能人才,国家才得以安定富强,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其次,君王是否尚贤,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尚贤上》);“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尚贤上》)。贤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君主不重用优待他们,在危难时刻就无人献策效力,国家就会有灭亡的危险。而任用贤者治国,则“国家治而刑法正”,提拔贤者长官,则“官府实而财不散”,采用贤者治邑,则“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因此君主只有尚贤亲士,国家才会兴盛发达。再者,贤者举而尚之,有利于教化民众,改变社会风尚。君主对当今贤士“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使得天下世人皆知“欲富贵而恶贫贱”者 “莫若为贤”,这样他们中就会有更多的人“相率而为贤者”。另一方面,尚贤可以向人们传输“仁爱”“贵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兼相爱,交相利”的良好社会风尚,“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尚贤下》)。因此,墨子得出结论,尚贤任能是国家行政的根本,选拔、使用和培养人才乃是当政者的第一要务。
2 “德为先、能为本”的人才选拔思想
墨子认为,贤良之士应该“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尚贤上》),从“德”和“能”两方面对人才提出了标准和要求。“贫则见廉,富则见义”(《修身》)。厚德,是墨子提出的人才的首要标准,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贤者应具有“怀兼爱之心,行仁义之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兼爱中》)。贤者应兼爱与公义并举,既怀有兼爱之心,又能践行天之大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有力者助人,有财者分人,有道者教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穷,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兼爱中》)的大同社会。二是“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亲士》),作为贤士,只有不安心,不足心,天下才会安足。墨子认为,为了实现兼爱交利的理想社会,贤士要时刻居安思危,存而思亡,勤政于民,不自安,不自足,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为了实现墨家治世理想,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三是克勤克俭的牺牲奉献精神。墨子认为贤者为人处世要遵守两项基本原则:一项是“凡足以奉给民用者,则止”(《节用中》),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特别提倡“节用”,反对奢侈浪费,教育弟子要勤劳从事,吃苦耐劳,注意培养节用勤俭的品质;另一项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节用中》)的原则。贤者应以实现“万民之利”为理想,以是否对人们有“功利”作为判断是非、善恶、智愚的标准,做到“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
除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墨子还要求贤者拥有必要的社会实践能力。首先,墨子十分重视言辩的作用。他认为,辩术不仅可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同时又是“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的重要手段,可以达到“处利害,决嫌疑”的目的,是贤良之士开展“上说下教”“教以劝人”救世活动的必备本领。说教者只有思路清晰,言辞犀利,语言缜密,表达自如,才能做到以理服人,使对方口服心服。因此,墨子既要求弟子有兼爱的道德情感,爱人如己,又要“辩”于言谈,学好“辩”的技术,将“辩乎言谈”作为塑造理想人才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贤者还要“博乎道术”,多才多艺,拥有参与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的“从事”能力。墨子谨记“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辞过》)的信条,倡言“凡天下群百工使各从事其所能”。与儒家所理解的人才是一个追求至高无上的“仁”的理想主义者不同,墨子所理解的人才应是一个为了“万民利益”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实干家。所以,墨子不仅要求弟子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与手艺技巧,“赖其力者生”(《非乐上》),而且最好成为耕作之行家,百工之能手的全面型人才。
由此可见,墨子提出的人才标准就是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实践能力,能够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一标准,既突出了“以德为先”,又立足于“以能为本”,从德与能两方面对人才提出要求,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无疑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3 “察能授官,量能而用”的人才使用思想
贤才既得,该如何使用才能使之发挥相应的作用呢?《墨子》将“尚贤使能”的核心直接落脚到执政者对人才的使用上。
一是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墨子认为,世间有谗人、利人、恶人、善人等各色人种,有谋士、勇士、巧士、使士等各类人才,由于每个人的德行、能力、性格、经历差异较大,因此,统治者应该“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杂守》),即仔细考察他们具备哪些品性或特长,以便名副其实的接纳使用。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如何知人呢?墨子说:“听其言,迹其形,察其所能”(《尚贤中》)。通过“听其言”可知其人是否真有治国安民之道,通过“迹其形”可知其人是否顺从天志、言行合一,通过“察其所能”可知其人是否仁义道德,是否符合人才的能力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把各类人才安置在合适的职位上,可使治国之才使治国,可使长官之才使长官,可使治邑之才使治邑,合理分工,各尽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二是要以德就列,量能而用。人的德行有高低、能力有大小,大材小用或者小材大用都是错误的。大材小用造成人才浪费,无法发挥人才的长处,而小才大用不仅于事无补,甚至把原来的局面越弄越糟糕。所以墨子提出要依照德才大小安排职位,反对让“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尚贤中》),否则,即使夜以继日地执政理事,也只能“治一而弃其九”。
三是能者上、庸者下。贤者不是永居其位,人才是流动的,有能居之,无能则下。在墨家看来,兼爱交利谓之大义,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的伦理原则,统治者任贤使能也必须符合这一“天之大义”,因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能者上、庸者下,取法于天,当在自然之理。每个人,包括平民百姓在内,都有凭借个人本事出仕参政出人头地的机会;同时,即使位居高爵的权贵之人,若不行仁义之事,不能为国为民治政理事,也会“抑而废之,贫而贱之”。“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胜绰)”(《鲁问》),便是例证。
4 “赏当贤、罚当暴”的人才激励思想
怎样才能让天下人争当贤士,让贤士勤政于民呢?墨子主张“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尚同中》),充分运用赏罚手段,对贤者实行重赏,对不肖者实行严惩。墨子认为,对待贤良之士,不应该在乎其出身是否卑贱,都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不仅要给予贤士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还要满足他们社会地位和政治需求,即“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这样,使他们“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而且,墨子还认为,高爵厚禄并不是给予贤士的恩赐,而是“欲其事之成”所必需的,因为“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贤士出仕参政,官爵不高,百姓就不会尊敬他;俸禄不丰厚,百姓就不会信任他;行使政令不果断,百姓就不会畏惧他,所以,高爵、厚禄、重权三者对于贤者完成其工作任务来说是缺一不可的。而且,“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尚同中》),如果不将名与利统一起来,只有高爵而无厚禄,百姓就不会相信,尊贤尚贤就会是一句空话。“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尚同中》)假借尊贤尚贤之名来博取好名声的君王,人们怎么会亲附于他们呢?因此,统治者想要真正任贤使能,既要“事则与”,大胆使用天下贤能之人,又要“禄则分”,给予他们较为丰厚的物质待遇,这样,天下贤良之士才会“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
对于人才不仅要有正面的激励,同时还需辅以必要的惩罚和约束机制,不仅要“赏当贤”也要“罚当暴”。为了建立一个民众平等、互助兼爱的理想社会,墨子希望君主选用人才时不必考虑亲疏贫富贵贱,以贤能与否为唯一标准,主张“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对于贤者要“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对于不肖者要“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从正反两方面激励人才发挥作用。由于人们都愿赏而畏罚,故民皆“相率而为贤者”,这样,国家的贤良之才才会逐渐地多起来。
5 “全面考察、量功分禄”的人才考核思想
如何客观地评价各类人才的德行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尽可能地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墨子从兼爱交利的政治理想出發,提出了一系列人才考核思想与方法。
一是“合其志功而观焉”(《鲁问》)的考核原则。即评价一个人或一种行为,应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同样一种行为,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所以,在分辨人们做事是否是出于正确动机之前,不宜轻易地对他的行为作出评价。
二是德、能、勤、绩全面考核。墨子的人才标准是德为先,能为本,除了高度重视对品德和能力评价之外,还特别重视考核任职者的工作态度以及工作效果。墨子认为,贤者治国,当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奉天事鬼,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强国亲民;同时,墨子言义必及利,十分注重做事的工作实绩与效果,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天志下》)。
三是根据岗位职责确定考核内容。墨子提出,不同的官职各有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职责。治国者“蚤朝晏退,听狱治政”,长官者“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治邑者“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各个岗位的任职者都要各精其道,各行其义,各尽其能,当什么官职就应该负责做好什么事务,做到“以官服事”,因此,考核时应以岗位职责的实际完成情况作为考核依据。
6 “上说下教、以行为本”的人才培养思想
墨子生活在一个战乱纷飞,人人皆不相爱,亏他而自利的时代。他认为,教育对于改变这一社会乱象,实现其兴国治乱的治世理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他从维护农与工肆之人的现实利益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精神的人才培养思想。
第一,“上说下教,济世救人”的全民教育思想。墨子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提出全民教育的思想,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接受教育的对象,都是实现政治社会理想的重要力量。“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鲁问》),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国治德修”的理想社会。
第二,“以行为本,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思想。墨子一贯主张亲躬实践,反对妄谈空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耕柱》),他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提出了“以行为本”的实践性原则,“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修身》),只有学识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重视践行,把理论知识变为实际行动,做到志观一致、知行合一,才有实际意义。
第三,因人施教,互动教学的教育创新理念。墨子在教育实践中坚持创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方法,注重教学的实际效果。墨子主张人才培养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施教对象的实际水平和个体差异,“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大取》),因材施教,坚持以人为本,因能分工,量才而用,择务而从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互动式教学,“唱而不和,是不学也;和而不唱,是不教也”(《鲁问》)。墨子认为,只有充分发挥教师“强说于人”的教育主导作用和学生“知其所以然”的治学精神,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方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第四,“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环境育人思想。墨子非常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的习染熏陶作用,“(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所染》),墨子看到洁白的素丝进入染缸后颜色随之改变的时候,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环境对个人修养的重要影响。他认为人性先天并无差别,像纯白的素丝一样,没有好坏之分,人之所以后来形成不同的善恶之心,主要是后天环境造成的,由此他提出了所谓的“人性素丝论”,反复告诫教育者“必择所堪,必谨所堪”,高度重视外部环境对人才培养的熏陶感染作用。
7 结论
综上所述,墨子从人才的慧识善用问题出发,以“贤者政之本”的人才价值思想,“德为先、能为本”的人才选拔思想,“察能授官、量能而用”的人才使用思想,“赏当贤、罚当暴”的人才激励思想,“全面考察、量功分禄”的人才考核思想,“上说下教、以行为本”的人才培养思想,构建了内容丰富而体系完整的人才管理思想体系。尽管墨子的人才管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且“蔽于用而不知文”,但不可否认,墨子突破了时代局限性,打破了传统“任亲用旧”的用人观念,开创了人才标准面前人人平等的先河,坚持彻底的“唯贤是举”用人原则,具有鲜明的人本色彩和以民为本的大人才观,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任继愈.墨子与墨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孙诒让.墨子閒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王裕安.墨子的人才观[J].齐鲁学刊,1995,(10).
[4]池万兴.论《墨子》的人才思想[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