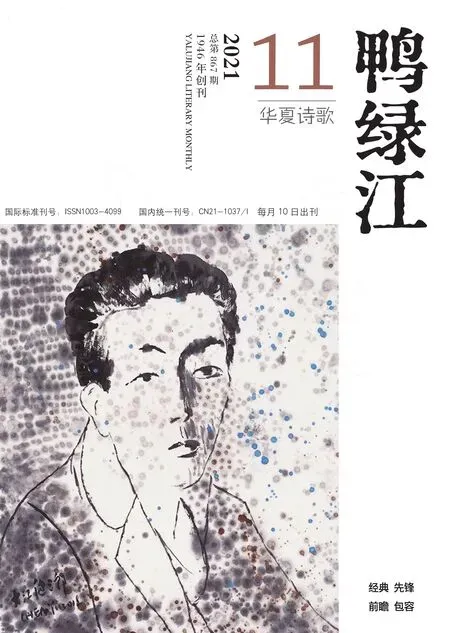虚拟了张惊悚的脸(组章)
苏忠
荷塘语录
夜色荷花,出淤泥又像个头条。
胡同长长,在风里,在月下,顺口溜也有风骨,连让出的悲喜都成了重彩背影。
亲爱的,我说,如果没有淤泥,又如何一路成全你?
你把原罪与七月不动声色地置换,你把人间的抖擞比喻,一一得罪,一一高举。
清香是油画里还醒着的年轻人,那时还乐于给人颜色瞧瞧。
草原石人行
天高,云乱,朝代潦草。
一大群面无表情的石人,走着走着,不知为何掉队了,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全副武装,腰杆笔挺,表情如易燃品。
依然盯紧日出方向,前锋正厮杀,他们要抓紧接应。
草长一茬,马蹄铺天盖地踏矮一季,压不了就秋风扫落叶,就大雪漫天,也不能让青草高过视线的立场。
地球在走,石人正赶路。
许多年轮转远了,许多人在风吹草低中走失。
我在草原上溜达了一阵子,听到导游在催促,心想历代都有逃兵,反正也不差我一个,我还不配有此铁石心肠。
崂山访道
一个人上崂山,且登高,且徐啸,且俯仰。
一个人的快活,满山石头的嗷嗷乱叫,乱石也翻腾,它们都是群居动物,不知何时何地从何处来,都无人认领。
大风满怀热情从远方赶来,它有一百公里的臂膀和一百公里的拥抱,却如同竹篮打水,有吹过来吹过去的两场空。
连云层与山花也连连摇头,在山道左右,不说谜底。
于是乎沿途有落叶在风中鼓掌,眺望里有鸥鸟与浪花与风帆击掌,每一回的重复都是手势一种,都高于尘世的鼓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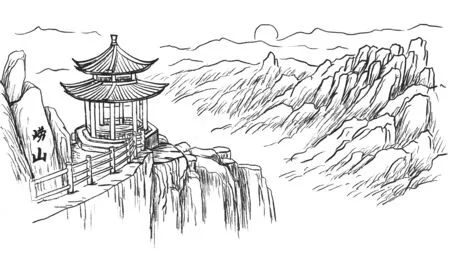
波光漾漾,是大海抽出的上上签,一个站在山顶的人也是。
而黄昏,是落日的一次访道。
青草渡
远山,松果,阳光倾斜,谷是空的,拍几下会响。
风的脚丫是无垠青草,一座小小寺庙扎在堆满鹅卵石的溪边。
我看见神仙的家中空空如也,残缺壁画的情节迷失在灰墙缝隙,某些棒槌走出门槛不知所踪,门前的狮子浑身披满风波。
一列绿皮火车驰过。
蜘蛛网绽放森森冷,生命不过是一道自投罗网的签名,我来了,我看到了,其实慕名而来与到此一游,皆肉身诱惑肉身的理由。
在低吼的青草渡的头几回。
所有合十都是与内心的击掌。
不见不散
稻子挨近篱笆时,风就是金黄的。
人家寥寥,白色炊烟摇着从前的挥别。
山中数日,几个回合下来,有了朝夕相处的亲情,鹅不啄人了只蹒跚温顺,羊在身旁绕来绕去还温暖喊上两声,连田里的螳螂也有了握手的预习,它爬上手背,不动弹。
一连串激烈的鸡鸣声,似乎长长拽住了落日。
而落日晃了晃,终于挣脱,独自落下,溅起了整村的鸡鸣。
稻子才开始起跑,就齐刷刷愣住了。
我只好说些客气话,说即使明天没空,太阳还会来,不见不散哦。
——石界抗疫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