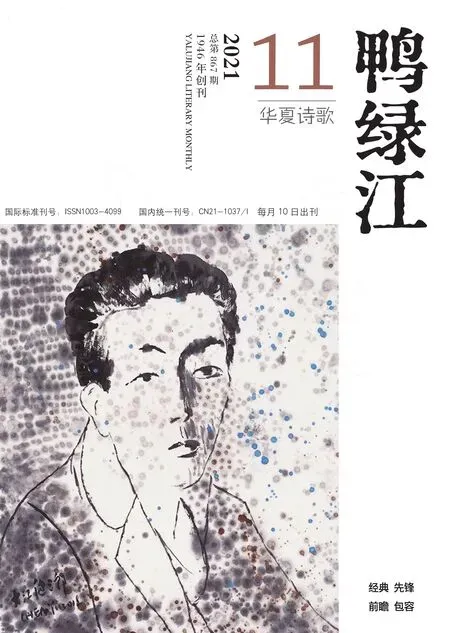一个人到底能飞多高
——漫说“新归来诗人”沙克
邱华栋
《有样东西飞得最高》作为沙克20年的诗歌结集,称得上是一个精华本,里面的矛盾冲突、驳杂气象,既是一种丰富探索的表现,也是走向大气的必然形态。它不仅显示了诗人丰富复杂的创作历程,也给中国当代诗坛提供了实验与创新的好样本。
诗人的声音在今天应该更响亮,对诗人的关注,就是对时代心灵和精神境遇的关注。因此,能参加沙克诗歌作品研讨会,我非常高兴。我还代表《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参会,他特别嘱咐我,沙克是我们杂志的老朋友,祝贺他这次研讨会的召开。第二,我还代表在北京的一些诗人,他们都是沙克的老朋友,听说了沙克召开研讨会的消息,都很高兴,其中有诗人周瑟瑟、祁人,还有商震、树才等等,他们都让我向沙克转达祝贺。
谈到沙克和他的作品。可以说我是比较熟悉的。沙克的诗歌我看了好多年,作为诗歌爱好者、写作者,作为他的同道,我自然要谈谈我对他作品的感受和认知。从写作姿态上来看,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沙克的确算是一个“新归来诗人”,是眼下比较有影响的“新归来者”诗歌写作群落中的重要一员。那么,什么是新归来者诗歌群落?纵观最近30年的当代诗歌史,有一批在“反右”和“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诗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见天日,重新归来,构成了第一拨归来者诗潮,他们以艾青、邵燕祥、郑敏、绿原、牛汉等为代表,再度拿起诗笔,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艾青还出版了诗集《归来的歌》。由此使“归来者”诗歌现象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和文学现象。
而第二拨诗歌的“归来者”,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新时期里,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批写作几年、十几年的青年诗人,在1989年到1999年那一段时间里,暂停诗歌创作,忙着下海、挣钱,去解决生活问题,到了21世纪头10年,他们陆陆续续回到诗歌的队伍里来,重新开始诗歌写作,并且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我本人在这个期间,也有10年时间没怎么写诗,主要去写小说了。后来,也重新写诗了,今年还写了几十首。这些年,我接触了大量的新归来诗人,粗粗统计,全国大约有100多位新归来诗人。说起来,名单会很长。沙克显然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在北京,现在新归来诗人们有许多聚会,经常在“老故事”酒吧里,或其他场所朗诵诗歌。
对于沙克,他的社会学身份,当然应该从“新归来诗人群落”这个角度来看待,尽管他的诗歌写作表现得相当复杂。他在上世纪80年代,20岁左右时,诗就写得很好,90年代中期(1996年)往后的10年,他主要做媒体记者,近5年来重新写诗,作品突飞猛进。研究沙克,必须要注重他的写作历史。他的诗歌写作有30年的心路历程,已经成为我们诗歌时代的一个注脚和象征。
现在的诗歌写作和生产,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状态,既有《诗刊》这样老牌子的枝繁叶茂的大树在开花结果,也有各种各样的民间刊物各表一枝,另外还有许多诗歌网站,以及许多诗歌活动在进行;而写诗的人,全国据说有300万到500万之多,每年出版的诗集有数千种。比如今年5月份上半个月,我已经收到20多种诗集,有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册《千高原诗系》,有杨炼推出的新长诗,那是一首很长的叙事诗。据我所知,有一些诗人,比如欧阳江河、杨炼等在香港将要出版他们的全集,虽然他们离经典化还有些距离。由此可见,当前的诗歌创作之丰盛,诗人之受到重视,已经不是上世纪90年代那种情况了,大量诗人归来了,新的诗人也在加入进来。昨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在北京的艺术社区798工厂参加了一个诗歌活动,那是民间刊物《诗参考》创刊20周年的纪念朗诵会,就在大太阳底下搞朗诵会,来了不少诗人,还给许多诗人发奖,奖杯是像炮弹那样大的水晶杯,上面刻着芒克、树才、沈浩波、周瑟瑟等获奖诗人的名字。其中,周瑟瑟“代表沙克”获得了“新归来诗人奖”,是我给他发的奖,因为我1988年就和他一起写诗了。我是想说,沙克本身就应该得“新归来诗人奖”,主要是他不在北京。不过,他在江苏也很光彩,这次,江苏作家协会特地举办了这个诗歌作品研讨会,范小青主席、汪政先生亲自张罗,可见江苏对他的重视。从北京到南京,两天里我连着参加两个文学聚会,都是诗会,我觉得,现在的诗歌写作状态显得很热闹,特别有意思。
在以上的诗歌写作大背景下,我们认定了沙克“新归来诗人”的身份。下面,我将面对沙克的作品,说说阅读他诗歌的感觉,他的诗歌写作的艺术特点。我与同样是“新归来诗人”的陈义海教授一样,觉得沙克这本新版诗集的名字起得非常有意思。诗集的名字是进入诗集内容的钥匙。沙克非常“虚伪地”请了130来个人,在4个待选的题目中为他的诗集定夺名字,弄了一大堆题内题外的名字后,他竟然都很不满,竟然用抓阄来决定最后的结果,把这个事交给上帝来裁判。后来,诗集的名字就成了《有样东西飞得最高》。他把众多大学教授、评论家倾向最显著的一个名字《唯美的漏洞》(也是诗集中的一首诗的名字)废了,表明他对学院派的不屈服。
既然沙克那么喜欢《有样东西飞得最高》,我想问他,也问他的诗歌作品本身,什么东西飞得最高?到底是想象力呢,还是语言的黄金在天上舞蹈?是《蓑羽鹤飞过喜马拉雅山峰》(诗集中的一首诗)吗?到底什么东西飞得那么高,我觉得挺好奇。什么东西飞得最高?我觉得,那是一种可能性,是对诗歌语言之美、境界之高的最大可能的追求。因此,让沙克披着语言飞翔吧。
读沙克的诗集《有样东西飞得最高》,我感觉到这本诗集确实是气象万千,同时也显得十分驳杂,这是沙克近20年来的写作结晶,显示了宽阔的时空交错所带来的驳杂气象。陈义海教授专门论述了沙克诗歌的背景、特征、多元手法和许多值得表扬的价值所在,也表示了作品难以看懂(晦涩)的问题。除了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以外,我自己对沙克诗歌的感觉是,他的作品,深受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可以说,那是语言至上的诗,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到意象派,到20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西方诗歌流派,以及现代汉诗100年来的流派,对他都有影响。可以说,持续30年的独特写作,使沙克成为中国诗坛的实力派和异数。他能够吸纳和消化大量的现实题材,以忧患意识介入当代生活,这非常可贵,又能像蝴蝶羽化那样,把诗之美以翅膀扑腾的方式,进行灿烂的绽放。

沙克的诗,好多句子非常美,许多诗里都有几句非常漂亮的句子,使我爱不释手。我前些天读四川诗人柏桦的诗集,看到他每首诗里都有一两句诗非常动人,都是时代的警句,也很喜欢。沙克的诗里有很多非常好的句子,我摘选了他的十几首诗,折在书页里面,有机会,我会朗诵的。
我认为,沙克诗集中的信息量很大,包含着文化、艺术、哲学、历史、时代与社会形态种种信息,他的诗的整体风格,让我想到很多大诗人,比如美国诗人史蒂文生,善于从时代里面拎出许多东西来概括。读沙克的诗集,我还想到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后者的诗中有深沉的自我内视,有很多反讽,沙克给我的感觉也是这么好。
沙克诗集里有一首长诗《死蝶》,我特别喜欢,就像我的武大学长、著名诗歌研究专家叶橹教授刚才评价的那样,沙克的这番探索和实验,极具意义和价值,我也这么认为。我精读了这首诗,读到最后,基本上读懂了。这首诗充满了深度的生命体察和哲学思考的大气,可以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相媲美。我收藏着一个小小的玉蝉,那种蝉是汉代的殉葬品,放在亡者嘴里的小东西。玉蝉,意味着复活与再生。《死蝶》给予我特别强大的暗示,使我联想起诗歌史上长诗的力量。虽然《死蝶》只是中型的长诗,却让我联想到艾略特的《荒原》,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那里面都有着许多黑暗与深渊,有着对生命极其深刻的体认,深藏着很多哲学才能回答的东西。在《死蝶》中,我还读到荷尔德林的感觉。因此,这首长诗特别有分量,既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重视的杰作,放在诗集《有样东西飞得最高》的最后,体现了压轴的意义。从这首诗,我们就能看出沙克已经不自觉地写出了经典之作。
说到最后,《有样东西飞得最高》作为沙克20年的诗歌结集,称得上是一个精华本,里面的矛盾冲突、驳杂气象,既是一种丰富探索的表现,也是走向大气的必然形态。它不仅显示了诗人丰富复杂的创作历程,也给中国当代诗坛提供了实验与创新的好样本。
一个人到底能飞多高?我希望沙克披上语言的翅膀,继续飞翔,想飞多高,就飞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