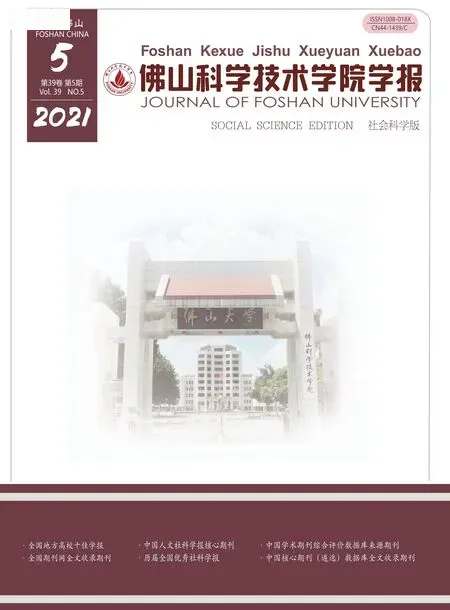南园十二子的结社活动与生命价值
李婵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南园诗社是岭南诗坛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诗社。明初,岭南诗人孙蕡、王佐与十多位诗友在广州南园抗风轩结社,是为“南园诗社”之始。当时,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五人成就最高,被称为“南园五子”,对后代诗坛影响深远。明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等人重开南园诗社,人称“南园后五先生”。明清之际,继“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五先生”之后,以陈子壮为首的一批广东文士再结南园诗社。他们直接传承了南园五先生以来的诗学传统,以复兴南粤诗坛为己任,活跃于明后期崇祯年间的岭南诗坛,后人称之为“南园后劲”,又称“南园十二子”。他们开创雄直新风,使岭南诗风为之一振。“南园十二子”因此成为明清之际岭南诗坛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诗人集群。然而,目前学界对“南园十二子”的关注程度尚远远不够。本文将对岭南的各种地方史志及得以幸存却长期少人问津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佚并整理南园十二子的结社活动,以期彰显曾经成为一时典范却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南园十二子的生命价值及历史意义。
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陈子壮遂与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黎遂球、黎邦瑊、黄圣年、黄季恒、徐棻、僧通岸等十二人重开南园诗社。其后,广东文人曾道唯、高赉明、谢长文、苏兴裔、梁佑逵等人也加入诗社,一时诗学极盛,在岭南影响很大。其时正值天下大乱,清军屡屡进逼,明朝政权岌岌可危,南园诗社的社事活动时行时辍,但诗人们诗酒酬唱,抒发爱国激情,意气慷慨悲壮,岭南诗风为之一振。随着大明政权的覆亡,诗社成员或逝世,或归隐山林,或出家为僧,南园诗社也逐渐消散。
由于明末政局动荡,岭南诗人的社集场地难以固定,诗社活动的参与人员也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即便是同一批诗人,在不同地方进行的诗歌雅集活动,其诗社名称也多有不同,使得岭南诗人的结社活动显得较为随意;加上现存史料缺乏,很难准确地区分每一次的诗人聚会是否属于南园诗社的社集活动。因此,对于岭南十二子的确切的社集活动终止时间,目前难以判定。在对南园十二子的内部交游活动的认真考述中,本文暂以几次比较有影响、参与人数较多的社集活动为重点,以期梳理明末南园诗社的活动轨迹,并通过其雅集时的文学创作来探析南园十二子的文人情怀与生命价值。
一、结社之前的早期集会活动
早在南园诸子正式结社之前,南园诗人们就多有雅集活动。陈子壮、黎遂球一直是南园雅集活动的核心人物,因陈子壮大多时间是在京城任职,故明末南园诗社的许多社集活动都是围绕着黎遂球而展开。特别是黎遂球的几次上京应考,南园诗社成员都有集体的送行之作。现藏于广州市艺术博物院的《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就是由历次岭南诗人的送行诗手迹辑录而成。从诗卷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南园诗人们集会为黎遂球送行的情景。
据考,黎遂球一生前后四次上京参加会试,分别在明崇祯元年(1628 年)、崇祯七年(1634 年)、崇祯十年(1637 年)和崇祯十三年(1640 年)[1]。而黎遂球离开家乡出发赴京的时间则分别为明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六年(1633 年)、崇祯九年(1636 年)及崇祯十二年(1639 年)。黎遂球是当时岭南较有影响的诗人,故历次上京都有诗友为其诗酒送行,这些诗友后来很多都成为南园诗社的主要成员。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送行是在明崇祯六年(1633 年)。是年春,海盗泊广州城下,遂球因次年要上京会试,恐路为盗阻,遂于二月即离开广州。离别前,陈子升、欧主遇等10 位诗友共聚广州东林僧舍为之送行。席上,各人赋诗相赠。[2]从《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来看,当时为黎遂球送行题诗的诗人有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张乔、黄圣年、徐棻、谢长文、李云龙、冯祖辉等。其中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黄圣年、徐棻五位诗人均为后来“南园十二子”的成员,谢长文、李云龙为后期加入南园诗社活动的成员。诗友们在诗中表达了对黎遂球的美好祝愿。如欧主遇《送黎美周会试》诗云:“竹房芝阁数相从,先出长林四百峰。夹道看花金腰袅,群仙分露玉芙蓉。尊开夜月飘霜满,帆带春山点翠重。裁就万言书早上,不虚词赋擅雕龙。”[3]徐棻《送黎遂球公交车北上》诗云:“王春日日送征骖,别思桃花千尺潭。莲社乍违羊石北,杏园遥指凤城南。行边驷马文俱五,握里天人策已三。去住示忘诸有在,试将消息问瞿昙。”[4]479他们希望友人仕途顺利,在动荡时期仍旧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
此处需特别说明的是,当时南园诗社虽没有正式成立,但自明崇祯初年陈子壮因丁忧回归岭南后,曾与南园诗社的主要成员修禊南园,有过诗会活动;且诸人之间在此前即有过密切交往,此次集体送行亦为他们诗酒交往之明证。故此次活动可视为南园诗社的早期活动之一。另外,汪宗衍先生指出,当时陈子壮正在京中任职,不在广东,其送行诗当为后来黎遂球至京中拜访时补作。[5]因当时参与人数较多,且后来诸人诗歌均借《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得以流传下来,故其影响较为深远。
此次活动之前,南园诸子之间已有密切交往。其中几次参与人数相对较多、且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活动有史可考者分述如下。
明天启五年(1625 年),陕西道御史梁元柱因弹劾魏忠贤削籍归,于广州粤秀山麓建“偶然堂”。“每花晨月夕,招邀朋旧饮酒赋诗。”[6]867明天启五年(1625 年),梁元柱与邝露、黎遂球、李云龙、欧必元、黎邦瑊、梁继善等结诃林净社,推陈子壮为社长,常诗酒雅集。梁元柱《偶然堂遗集》卷二有《偶然堂成用韵答陈秋涛亲家》一诗,黎遂球《迦陵集·七言律诗》收有《花朝梁木公招待家大人,同欧子建、赵裕子、戴安仲、邝湛若诸公社集诃林千佛塔赋》《答梁木公入社论诗之作》,均为诃林社集之作。诃林净社的很多诗人后来都成为南园诗社的主要社员。黎邦瑊《诃林社集赋得王园晚斋》一诗亦当作于社集活动之时,此首诗云:“暝色苍茫古化城,同来结夏恰初晴。衣披蕉石云犹润,杖引莲峰气飒清。残照到碑看往迹,曲池流水杂经声。漉巾到处宁辞醉,不觉东林月又生。”[7]从诗中流露出的情绪来看,此时期诗人们生活较为稳定,心态也较为雍容闲适。
明天启六年(1626 年),陈子壮兄陈顺虎在广州城东建东皋别业,子壮与黎遂球、黄圣年、黎邦瑊、徐棻、欧主遇等常饮宴其间,纵论时弊,唱酬甚密。其时参与聚会的还有张萱及何吾驺等。陈子壮《陈文忠公遗集》卷二有《初归饮顺虎家兄东皋别业》《东皋和欧嘉可》等诗,表现了当时诗人间的交往。黎遂球亦曾作《题陈顺虎东皋二首》描绘东皋别业优美的景色。其《浣清堂》诗云:“秋光濯须眉,春翠浮杯酒。况复挥麈谈,玉柄如人手。”[8]99《玉带桥》诗云:“曾眠宝带桥,醉弄太湖月。今日坐长虹,清寒彻毛发。”[8]99另黄圣年亦作《陈顺虎郊园》诗咏道:“结庭人境似蓬莱,兰桂申椒次第裁。看剑深宵龙再会,论文浃日客仍来。乔枝春暖莺簧巧,瘴海风和蜃市开。不用德星占太史,纵横彩笔已昭回。”[6]853赏花论文,依然是文人日常生活的最真实写照。
明崇祯元年(1628 年)四月,袁崇焕重被起用为辽蓟总督,出关督师,陈子壮招集诸文士于广州诃林净社,为袁崇焕饯行送别。诃林寺即广州光孝寺,因院内有诃子树而得名。当时在释通炯的倡议下,陈子壮、黎密(黎遂球之父)等人捐资重修诃林禅堂,落成后复为诃林净社,诸名士多在此吟诗作赋。在当时诃林寺不仅是一处文人雅士聚集唱和之地,还是粤东名士一处议论时政的较为重要的场所。此次聚会诗人们为同乡袁崇焕再次被委以重任而庆贺。陈子壮因与袁崇焕是同榜进士,交情不浅。集会时由赵焞夫作图,陈子壮题引首“肤功雅奏”,诸人题诗于图后,遂成《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卷咏》,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肤功”即肤公,语出《诗经·小雅·六月》“薄伐猃狁,以奏肤公”之句,“肤”大也,“公”乃功也,故“肤功雅奏”可理解为大功告成之意,可见粤东名士对袁崇焕寄予了很大希望。陈子壮诗有云:“此去中兴麟阁待,燕然新勒更何辞。”[9]欧必元亦云:“书从淝水征安石,碑树淮西表晋公。”[4]599当时题诗者十九人,除后来南园十二子中的陈子壮、欧必元、区怀年、释通岸、徐棻等诗人,还有邝露、戴柱、释通炯等人。从诗作来看,岭南文人普遍有着较为积极的入世心态,关注民生,为国家效力,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
同年,崇祯帝重新起用陈子壮,并升左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六月,子壮着戎装赴召,诸友人均作诗以送。欧主遇《送陈秋涛太史还朝》诗云:“载笔中朝第一流,宫衣摇曳返瀛洲。气连牛斗双龙剑,手辟云霄五凤楼。锁闼玉堂官并美,西京东观秘全抽。朝昏茎露千珠重,来往仙槎八月浮。使命光分沧海日,宦情闲对白云秋。偶归径许求羊入,此去书成班马俦。听履早趋鸳鹭序,离筵为典鹔鹴裘。知君黄阁赓歌地,作相还家尚黑头。”[3]区怀年作《送陈集生太史报命还都》,诗云:“烽烟满目连青塞,剑佩生香动紫微。引见预知承顾问,九重渊穆正宵衣。”[10]28从此诗可见区怀年对其充满期待。区怀瑞亦作《送陈集生太史还朝》二首。
明崇祯四年(1631 年),欧必元六十大寿,黎遂球作诗以祝。所作《赠欧子建先生六十初度二首》诗云:“(其一)千秋原在许谁分,岂谓龙头未致云。南阮客来频典褐,北山人去解移文。身长廪量侏儒粟,膝下兰生耳筋。四十万言知已诵,汉门金马倘相闻。(其二)君年三十我生时,三十年来事事知。张耳有金尝结客,孔融当坐可呼儿。儒冠渐腐囊因涩,文价终昂货莫欺。十分百年才过六,且凭欢伯未须疑。”[8]90从诗歌内容看,二人的交往十分密切。是年,陈子升、黎遂球、陈邦彦、欧必元等人诗酒酬唱甚多,其诗文日进,在岭南诗坛影响日益扩大,“以文章声气遥应复社。”[11]34
明崇祯九年(1636 年),黎遂球、欧主遇与诸人社集广州东皋。黎遂球作《东皋修禊诗》,此诗题注云:“丙子三月三日集同社诸公即席赋。”诗云:“黄鸟既鸣,曲池既波。载阴载阳,以景春和。春亦我春,有酒旨多。我友既集,即集逶迤。芳树被席,迁坐凭阿。何以称体,谿谷婆娑。何以称心,嘉言咏歌。既赏清音,亦就舞娥。蹲尊翼斝,交乐且酡。属我不述,来者知何。”[8]99欧主遇亦作《三月三日社集东皋》诗,诗云:“我皇九载,永和期合。蔼蔼时彦,晋人可作。东园之树,秾华未落。于以晤言,曲水为乐。有鸟和鸣,茂林集止。春酒既载,春服以试。薄言采兰,于水之涘。歌以写心,祓禊匪戏。”[6]962从诗歌内容来看,此次宴集,春和景明,诸人诗酒酬唱,气氛非常融洽。此外,黎遂球诗集中《东皋同诸先生上人社集分赋得素馨花灯》一诗,亦作于东皋诗社社集之时。东皋诗社的很多成员同时也都是后来南园诗社的成员。与同道雅集唱和,在共同的诗学理想下相互砥砺,力争在文坛上有所成就,这是当时岭南文人最为突显的生命价值追求。
二、南园十二子的正式结社
明崇祯十年(1637 年),陈子壮以抗疏得罪,除名放归,在广州白云山辟云淙书院自书一联:“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长蓬蒿。”自此闲居山中,寄情诗酒,徜徉于山水之间。友人区怀瑞作《陈集生太史解组辄此相慰》一诗以示安慰:“朝辞蓬阁远天居,犹带炉烟卧草庐。万石归来双彩袖,五云深处一床书。踏花屡引仙人骥,对酒应焚学士鱼。待有行藏随梦卜,喜无磈磊可消除。”陈子壮因一直以来对岭南文化事业的大力扶持及在政坛上的影响力,成为当时岭南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陈子壮的回乡,则为南园诗人的再次聚合提供了契机。
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正月初一日,陈子升至广州访黎遂球。此次见面当是二人相交之始。黎遂球作《新年喜陈乔生见过》诗云:“风雨新年茗气和,瓶花深护待人过。楼随柳色看邻远,坐即桃笙拥袂多。禅案有情凭笔墨,名流何事不江河。长斋拟学黄庭帖,到处临池好赎鹅。”[8]88陈子升亦作《戊寅小岁和黎美周诗》,诗云:“声华街鼓急相闻,烛跋西园至夜分。作赋不曾逢武帝,弹琴犹复看文君。常时歌对吴阊月,奇服香莲楚泽云。何处新知最相乐,颉颃狂燕隔帘纹。”[12]344表达了结识新友人的喜悦之情。同年正月十五日,陈子壮为弟子升诗集作序,序末署有“崇祯戊寅上元日兄子壮撰”[12]271语。自此,在兄长陈子壮的带动下,陈子升也渐渐融入岭南诗坛。
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广东巡抚葛徵奇重修南园三大忠祠,南海知县蒋棻重刻《南园五先生诗》,陈子壮为之作序,黎遂球也为此作《三大忠祠赋》,该文收入《莲须阁集》卷二。早在明崇祯初年,陈子壮丁忧在家时,曾与弟陈子升、欧必元等人修禊南园。明崇祯四年(1631 年),陈子壮进京后社事随即解散,其时影响不大。此次广东巡抚重修南园三大忠祠,并重刻南园五先生诗集,在当时社会影响较大,也成为南园十二子重新结社的直接推动力。
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二月十五日(花朝节),陈子壮与弟子黎遂球、弟子升等十二人复修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十二子”。欧主遇《自耕轩集》中《忆南园八子诗序》对此事有明确记载:“盖自南园五先生结社南园在大忠祠内,风雅攸存久矣。崇祯己卯(1639 年)花期,陈文忠公主盟修复,四美并会,六诗振响。仰挹五先生风流韵事,为十二人,气谊孔洽,唱和代兴,展时彦之盛已。”[3]这是岭南诗坛上一大盛事。其后,吴越江楚闽中等诸名流,亦来入社。对于此事,《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二《欧主遇》传亦记载云:“崇祯己卯(1639年),主遇与陈子壮、子升兄弟及从兄必元、区怀瑞、怀年兄弟、黎遂球、黎邦瑊、黄圣年、黄季恒、徐棻、僧通岸等十二人,修复南园旧社,期不常会,会日有歌妓侑酒。后吴越江楚闽中诸名流亦来入社,遂极时彦之盛。”[11]160由此可知,当时南园十二子的社集影响较大。黎遂球在一次社集时曾作诗《三月三日同诸公社集南园禊祓即席限韵》歌咏当年盛景曰:“如此临文共可传,气清应信永和年。流觞接席凭虚槛,曲水依城系画船。晴散煖香花作雨,节当寒食柳如烟。谁言禊事兰亭胜,得似明妆醉谪仙。”[8]92诗歌描绘了南园周边的优美景色:曲水流觞,画船依城;柳烟轻笼,落花片片。诗人们在美丽的春日宴集,诗兴盎然,其乐融融。
据李健儿《陈子壮年谱》“崇祯十二年”条记载,陈子壮居广州期间,弟子黎遂球师事子壮甚谨,“师弟二人,往往于花朝月夜,杯酒之余,论及时事,则欷歔流涕。”[13]可见师生二人意趣相投,均关注家国政事,拥有一颗赤诚之心。黎遂球《酌云淙邀瀑亭》诗题注云:“同陈秋涛老师作”,当作于二人酬唱之时。该诗云:“斗酒故人趣,牵衣坐岩苔。县泉与云落,写景潆尊罍。万翠忽欲动,态合如始开。山中千岁流,到海生尘埃。仙人太古弦,挥弹听徘徊。餐花痛饮酒,以此名千杯。愚谷当可移,娲石留天隈。翼斝称经营,飞练凭剪裁。”[8]60自此,南园十二子以陈子壮、黎遂球师生二人为核心,交往日益密切,影响也日渐扩大。
此后,南园诗人之间的文学活动更加频繁。明崇祯十二年夏,区怀年请黎遂球为其诗集作序。黎遂球《莲须阁集》卷十八收有《区叔永诗集序》,其文曰:“叔永胸怀澹远,曾再游金陵,入燕市,登眺多感,归乃为园掩关三余自足,花竹禽鱼之与处,丝肉半臂之与调笑,有闲情无杂虑,其为诗乃一变而精洁细腻,得之性者深而出之意者称,亦其才使然也。四言高古典雅,不徒饰也;五言古之冲融澹宕,体物赋象;七言古之艳丽轻逸,百态俱出也。五律之出入王孟,原本太史而工巧神致几过之也。七律之明秀疏落而五七绝句之丰神幽异,冷然而善也……叔永诗前后凡若干卷,于崇祯己卯之夏属予合而定之,既而为序。于时为七月七日。”[8]246可见黎遂球对区怀年的诗歌赞誉有加。另欧必元《九日同社中诸子登粤秀山宴集》《花朝社中赏花》、区怀年《南园社中赠陈集生太史》《秋杪集南园》《元夕曾息庵藩伯招集南园智上人在坐》、黎遂球《三月三日同诸公社集南园禊祓即席限韵》《端溪采砚歌南园社集同陈秋涛、区启图诸公作》、区怀年《春望篇》等均作于南园雅集之时。
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陈子升作《东皋》《云淙》二赋,请区怀瑞为其作序。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卷末附《旧刻〈东皋〉〈云淙〉赋序》对之记载甚详[12]426。
三、黄牡丹和诗推动的社集高潮
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夏,黎遂球北上应举进士,取道扬州。适逢扬州郑元勋在影园举办诗酒会,遂球与之。时影园中黄牡丹盛开,在座者各赋黄牡丹七律诗十首,糊名,送虞山钱谦益评定,遂球被推为第一。元勋镌金罍为赠,并选女乐歌吹迎于红桥,一时传为盛事。遂球当时号称黄牡丹状元,声名大振。清代学者钮琇《觚剩》记载此事云:“崇祯戊辰,扬州郑元勋集四方才士于影园,赋黄牡丹诗,推虞山钱宗伯为骚坛盟主,品题群咏,最者赉以金罍。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还,亦与斯会,即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评置第一,时号‘牡丹状元’。其诗有‘月华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衔落蕊成金屋,凤蚀残钗化宝胎’,皆丽句也。”[14]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十五日,黎遂球归至广州[8]161,受到岭南乡人的热烈欢迎。梁梅《莲须阁黄牡丹诗事歌》云:“声华藉甚江南北,乘兴飘然返乡国。”[15]檀萃《楚庭稗珠录》也记载云:“乡人争艳其事,制锦衣一袭,联画舫数十,郊迎者几千人。”[16]56在众人的簇拥下,黎遂球“被锦袍,坐画舫,选珠娘之丽者,排列两行,如天女之拥神仙。”[17]
在南园诗社的社集活动中,黎遂球以夺状元之黄牡丹诗示诗社诸人。子壮首和之,其后和者日众,各成十首者为陈子壮、曾道唯、高赉明、谢长文、黎邦瑊、区怀年、苏兴裔、梁佑逵八人,合遂球之诗编成《南园花信》一卷,刊印成书。黎遂球为作《南园花信小引》。其序文曰:“南园为国初五先生觞咏处,其后以祀宋大忠三公顷直指葛公来按粤,鸠工饬之。遂球因与吾师宗伯陈公邀诸公复为南园诗社……至扬州憩郑子超宗影园为黄牡丹会,谬辱夜珠明月之赏,所赋十律。归质之同社,于是陈宗伯师忻然为和如数,题曰‘南园花信’。既而,粤诗人和章日盛,爰录诸公之成十首者。宗伯师先成,为首;次则方伯曾先生息庵,侍御高先生见庵,家明府叔洞石广文、谢子伯子、同人区子叔永、苏子裕宗、梁子渐子。为一卷,付之剞劂,且报超宗,以识粤社一时之盛。庶粤东无牡丹而有牡丹,黄牡丹无南园而有南园,影园无粤社诗而有粤社诗,均快事也。”[18]此外,“或未及属和或和而未成十首者不入是卷,其有成十首而不入是卷者,则以和自杀青之后,嗣另汇补入,以识粤社一时之盛”[18]。
此次黄牡丹和诗事件,是南园诗社活动史上的一个高潮,也是联结南园与影园、岭南诗坛与江南诗坛的一个重要契机。其影响正如黎遂球《南园花信小引》所说:“庶粤东无牡丹而有牡丹,黄牡丹无南园而有南园,影园无粤社诗而有粤社诗,均快事也。”[18]香山名士何吾驺也异常兴奋。是年七月初五日,黎遂球生日时,何吾驺特地致书祝贺:“牡丹状元是千百年一状元,非比三年帖括,更以吴越才望同归……庄诵十首真是英敏绝伦,而沉酣痛快、感慨万千。”[18]何吾驺还对黎遂球赠以汉玉觥。黎遂球《莲须阁集》卷十三《谢何相公》题注云:“七月五日贱生惠汉玉觥。”其文曰:“何意重承老师阁下弘推肺腑之恩,忘其蓬历之贱,赐之至宝,赉以手书,颂白圭之诗,俯执唯有加敬。”[8]162对于此事,当代学者朱丽霞教授指出:“作为文化符号的牡丹状元,无意中将江南与岭南的诗坛衔接起来……从此,江南在诗坛上不再无视岭南,黎遂球成为岭南诗坛崛起的奠基者。他们以千里之外的扬州牡丹为媒介遥接岭南前贤——南园诗社。”[19]其观点是较为中肯的。在黄牡丹和诗事件的影响下,岭南诗坛再次崛起,南园诗人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开始在全国诗坛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在《南园花信诗》中收录的诗人除陈子壮、黎邦瑊、区怀年及黎遂球等四位南园诗人之外,还有受南园诗社影响而热心参与诗社活动的诗人,如黎遂球文中所提及的曾道唯、高赉明、谢长文、苏兴裔、梁祐逵五人。他们应是后来加入南园诗社的社友,在诗社后期的社集活动中非常活跃。
四、南园诗社的衰退
“黄牡丹状元”事件的发生及《南园花信诗》的结集是南园诗社活动中的一个高峰,此后诗社成员流动较大,社集活动亦时断时续,南园诗社日渐衰退。
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二月,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消息传到岭南后,南园诗人们在社集时以时事为主题,有感而作诗。黎遂球《莲须阁集》卷三有诗云:“守文列圣德,驱胡高皇功。明运宜无疆,我后承丰隆。过臣亶焦劳,济蹇谁匪躬。金瓯缺辽左,饷额勤输供。遂以困阎闾,焉谋备年凶。适郊逢硕鼠,捍网怜飞鸿。中原多悍寇,懦将愁频攻。驰驱十余载,躏蹂如乘风。荆襄江上流,雒阳天下中。宋辙有覆监,汉都忧其终。近闻亦倾陷,官民泥刀锋。星陨亡上将,藩决哀大宗。狂生识其故,伊昔神凭丛。抚降但养虎,凶服嗟临戎。请剑曷斩佞,伏蒲乌为忠。朝堂难战胜,臧否疑府宫。父书赵括惭,负荆廉颇雄。以此思古人,忾敌将何从。殷忧已叠警,我后惟天聪。河清洗甲兵,酌酒趣群公。”[8]62诗作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心。战事的发生打破了家国的安宁,南园诗社的社集活动笼罩上一层悲伤的色彩,这种气氛,与之前的诗酒风流完全不同。特别是诗人们的创作题材也由之前的文人雅趣和闲适生活的表现一变而为对现实战事的关注及对家国命运的担心与忧虑,充分展现了岭南文人浓郁的家国情怀,并开始呈现出一种慷慨激越的雄直之气。
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九月,区怀瑞离开家乡,北上任北直隶平山知县。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三月禊日(上巳日),黎遂球为陈子升作序。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卷末附《陈乔生制义稿序》有“崇祯壬午禊日年通家社盟弟黎遂球题”语。同年,黎遂球离开家乡,赴京会试。是年欧必元卒。南园社集活动受到一定影响。明崇祯十六年,区怀瑞、区怀年刻成其父区大相之诗集,陈子壮为作《区太史集序》云:“区海目先生以太史名粤也,其诗特盛……余不佞与先生二子游好,以为与于斯文者,得表其墓。今汇先生集而刻之,乃属为之序云。”[20]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黎邦瑊以忧卒。黎邦瑊是一位忠烈的爱国之士,生前一直为家国的动乱而忧心,其《镇海楼同诸子作》诗云:“频年京国思君梦,此日危楼得共登。暑气半消青嶂里,襟期偏洽白云层。海潮飞雨侵瑶席,涧道流霞断古藤。拼醉不愁明月去,松门深夜有禅灯。”[6]695从诗意来看,此诗当作于南园诗人们共登镇海楼之时,且很可能是黎邦瑊临死前不久所作。区怀年亦作《秋夜陪诸公宿镇海楼》诗:“北城轩盖动高秋,万井疏烟暝不收。木落远村微见水,山空凉月正当楼。清砧漫续蛩声溺,丽藻闲舒客思悠。松露满栏沾几席,梦魂容易到沧州。”[10]29诗歌表现了家国动乱的伤痛,当与黎邦瑊诗作于同时。
清顺治三年(1646 年),陈子升离开广州城南故居,于奔走流离中有感而发,作《感秋》四十首,并手录近体诗寄业师欧主遇。其《旧刻城南诗集自序》云:“予自丙戌岁别城南故居,丁亥岁奔走流离,几不自全。伏处江村中犹手录近体诗一通寄业师欧壶公先生。盖忧夫泯泯而托诸皦皦者也。”[12]427对其《感秋》组诗,陈恭尹评价曰:“近所赋《感秋》数十篇,于本色中更加古质,如入崇岳,千岩万壑,分则各具一观,合之乃成博大,不复以字句见奇。夫四时感人,唯秋为甚。先生挟旷世之怀,发弥高之调,对摇落之秋,兴抑郁之感,悠然之韵,触绪纷来,声生情耶?情生声耶?不可得而择矣。”[21]
这段时间,因为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南园诗社的核心成员陈子壮、黎遂球多忧心国事,四方奔走,陈子升亦伏处草野,故诗社活动暂告停歇。从薛始亨《南枝堂稿》所收诗歌可知,1648 年暮春,薛始亨到广州参与南园诗社的社集活动。其《暮春羊城社集(戊子)》诗云:“南园春草遍池塘,客里邀欢一举觞。上巳风流传曲水,建安词赋擅清漳。江云莫辨三株树,驿路难寻五色羊。谁道海滨邹鲁地,咏归还有舞雩狂。”[22]诗中流露出动荡之际长歌当哭的无奈与抑郁难言的酸楚。另薛始亨《南园》诗,亦当作于此时,其诗云:“草深方躅泯,席冷古弦张。谁念沿洄者,睪然叹汪洋。”[22]隐隐流露出动荡之际理想难以实现的慨叹。这是目前所能考证的最后一次南园社集活动。可惜当时参与社集的南园诗人已无法考证。
后来,黎遂球之子黎延祖重游南园,忆及种种往事,有感而发,作《南园故址》诗云:“古祠仍旧在东隅,一读残碑却起予。五典旧闻从舜代,三仁终古见殷墟。鱼须学士悲埋骨,马革忠魂痛绝裾。空有行人知往事,暮云芳草共踌躇。”[6]1141同时,他不无伤心地说:“南园为国初赵御史介、孙典籍蕡、王给事佐、李长史德、黄待制哲五先生结社地,后为祠,祀文、陆、张三大忠,有司岁时祀之。崇祯戊寅,直指介龛葛公捐俸重修,先忠愍公与陈文忠公暨诸名公唱和于此,继五先生风雅。变迁以来,祠属丘墟,人骑箕尾,祀典虽存,望城东而奠祝。偶一过焉,唏嘘怆怀,有感乎五先生之流风余韵,三大忠之日月精忠,陈文忠与先忠愍之文章节义,皆不愧于天地,其庶几有起而继之者乎。因赋之以志其慨。”[6]1141这段话表达了对先人的深重怀念。后清乾隆年间檀萃撰《楚庭稗珠录》,也肯定了南园后劲承继先人之功,并感叹南园的兴衰与明朝的命运紧密相连:“文忠际涉末流,乃纠后进,敷藻继声,虽诸人文采不少概见,而争迪前人光,亦足以作南园之后劲矣。噫,数楹老屋,或兴或废,与有明一代相终始,亦奇矣哉!”[16]51
作为明清之际在岭南诗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个诗人集群,南园十二子在岭南文学史及文化史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结社雅集、酬唱赠答充分展现了明清易代之际岭南文人的高洁襟怀与生命价值,并在诗歌的创作中融入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及浓郁的家国情怀。他们力求恢复“风雅之道”,强调“雄直之气”,对岭南诗派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充分利用地方志资源,在历史的尘封中深入挖掘南园十二子的交游与文学活动,不仅有利于填补岭南文学研究中的缺漏,更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文士的生存状态。而对其家国情怀与生命价值的提炼与彰显,对于促进岭南文化寻根、发掘岭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弘扬岭南人文精神、推动广东文化大省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