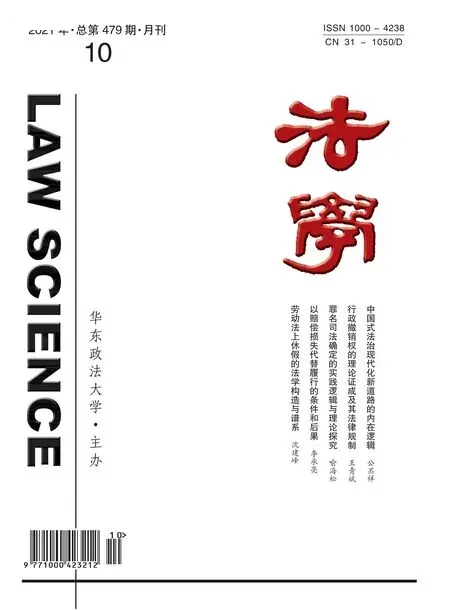WTO法律解释权的错配与重置
●胡加祥
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的“停摆”固然与多边贸易体制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密切相关,但是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导致其瘫痪的一个主要理由便是上诉机构过于“能动”,对于不少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已经超越了其本身含义。〔1〕See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Geneva, February 25, 2019.换言之,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应该放弃“能动主义”倾向,回归“克制主义”的常态。“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本是一对司法的概念,源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官在国内司法审判中的表现。前者意味着司法审判应反映现实变化和社会需求,敢于通过司法方法和现代技术突破既有规则,创造法律;后者意味着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应严格信守法律条文,排斥政治、道德、政策以及个人情感、偏见、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司法能动主义强调面向未来,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维持现实。〔2〕参见姜世波:《国际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政策之嬗变》,载《法律方法》2009年第1期,第203-214页。WTO争端解决机构是WTO总理事会下的一个专门机构,争端解决采用的是类似于法院的二审终审制,通过的裁决报告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与国内司法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实践。从“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的视角来讨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只是一种类比,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殊规定注定了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有其固有之特性。
一、一个谬误的缘起:从“皇冠上的明珠”说起
WTO成立之后,其争端解决机构因作出的裁决具有强制约束力而被一些人誉为“皇冠上的明珠”,〔3〕See Peter Sutherland, Concluding the Uruguay Round—Creating the New Architecture of Trade for the Global Economy,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4, 2000.寓意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设立了一道有效的保护屏障,争端解决机制也因此成为WTO规则中最亮眼的一部分。WTO前总干事鲁杰罗说过:“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价都是不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4〕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贸易走向未来》,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WTO规则以其统一性、强制性以及覆盖面广、参与成员多等特点为全球贸易管制树立了新的范式。《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16、17条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分别在公布后的60天和30天后自动获得通过,〔5〕笔者倾向将专家组(panel)译成“评审团”,参见胡加祥:《从“专家组”一词误译说起——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文简介》,载《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147-152页。考虑到“专家组”一词已被广为使用,本文也选择这一翻译。除非当事方对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或争端解决机构以“反向协商一致”的方式不予通过。〔6〕“反向协商一致”是与“正向协商一致”相反,指在表决时,包括胜诉方和败诉方在内的所有参与表决的成员一致同意不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WTO首任总干事莫尔将这种法治精神比喻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7〕See Mike Moore, The WTO, Looking Ahead,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4, 2000.杰克逊教授则系统阐述了WTO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以规则为导向”,而不是“以权力为导向”。〔8〕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Boston:The MIT Press, p. 109-111.
WTO成员在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后,在享受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的同时,也有恪守自己市场开放承诺的义务。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规则因涉及所有WTO成员,故有些内容规定得比较原则,有些则因谈判分歧较大采取了模糊化处理。基于这些原因,“建设性模糊”内容广泛存在于多边贸易协议规定之中。然而,在具体执行WTO规则时成员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具体的,在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纠纷后,必须对每一个争议点作出法律解释,〔9〕DSU第17.12条规定,上诉机构应依据第17.6条对上诉的每一个议题作出回应。这就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理解和解释WTO规则时拿捏好分寸。争端解决机构的这种“司法解释权”对整个WTO法律体系的存续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相比之下,WTO部长级会议与总理事会的“立法解释权”则显得有点名存实亡,争端解决机构事实上已经成为WTO法律规则扩张与收缩的“阀门”。
长期以来,学者们先是将WTO争端解决机构类比为司法机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官造法”的种种构想。〔10〕在这方面,国外较早、较有影响的作品包括:Ernst-Ulrich Petersmann, How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Contributions by the WTO Appellate Review System, in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ames Cameron and Karen Campbell (eds.), Cameron May Ltd., 1998; Michael K. Young,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Uruguay Round: Lawyers Triumph over Diplomats,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 29, No. 2, 1995.国内较早、较有影响的作品包括:赵维田:《WTO司法机制的主要特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余敏友、左海聪、黄志雄:《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于是,“司法能动”还是“司法克制”成了学界讨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同视角。由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WTO的争端解决作为国际争端解决司法化的代表,对国际法和世贸组织成员的国内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成立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目标追求。分析其法律解释的定位,既要理解“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的要旨,也要了解WTO的制度缺陷与国际社会的现实基础,因为司法虽不等于政治,但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司法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政治主张。〔11〕参见[美]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章:最高法院是一个政治性法院。若无这种超越法律的视角,WTO的争端解决就不可能有效发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的功能,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就会一直纠结于“司法能动”还是“司法克制”,多边贸易体制也会因此变得更加飘忽不定。
二、“司法能动”的勃兴及其成因
司法能动主义在WTO争端解决中的扩张主要表现在“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两个方面,前者指非WTO国际规范在何种程度可以被采纳为争端解决的法律渊源,后者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WTO规则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自由裁量权。对于前者,《WTO协议》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我们可从其他相关协议中找到答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条第3款规定,本协议保护的知识产权源自《巴黎公约》(1967)、《伯尔尼公约》(1971)、《罗马公约》《有关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该条款明确了两层含义:第一,WTO规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非WTO协议只有在明确列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第二,即使是上述明确列举的非WTO协议也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即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明确所指的或当时生效的版本协议。可见,“司法能动”的争议主要聚焦在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上。
在明确了争端解决机构“司法能动”的范围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法律解释的权力来自何处。根据DSU第3.2条的规定,争端解决的目的之一是“依据国际公法习惯解释规则澄清WTO规则”。此处的用词是“clarify(澄清)”,而非“interpret(解释)”。对此,学者莱斯特专门研究过两者的关系。他查阅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经常援引的《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发现“澄清”的定义是“从一个主题、一项申明等中去除其复杂、模棱两可和晦涩的内容”;“解释”的定义是“说明某某的意思”。〔12〕See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larendon Press, 1993, Vol. I, p. 411.莱斯特认为,DSU第3.2条用的“澄清”一词可以等同于“解释”。〔13〕See Simon N. Lester, WTO Panel and the Appellate Bod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TO Agreement in US Law,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35, No. 3, 521-543, 2001, p. 528.笔者亦认同这一观点。
然而,DSU第3.2条只是明确了争端解决的目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权则来自其他条款。DSU第3.9条规定:“本谅解协议不能剥夺WTO成员通过多边贸易协议和诸边贸易协议下的表决机制获得相关条款的权威解释。”DSU第17.6条规定:“上诉(内容)应限于专家组报告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专家组对此所作的法律解释。”这里,DSU明确告诉我们:专家组的工作是“解释法律”。虽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最终需要争端解决机构表决通过后生效,但是倘若没有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解释法律得出的裁决和建议,表决也就无从谈起。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没有一个代表提及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中专家组过分激进或从事造法的事宜,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争端解决仅限于专家组审理。这是一种类似于国际商事仲裁的解决机制,专家组成员都是临时受邀的专家,案件审理完毕后即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今后再次受邀或彼此相遇的几率并不高。专家组的审理就事论事,每一起争端都是一个孤立的案件。专家组成员聚焦的都是本案的事实真相与法律适用,不太会关注此前类似案例的裁决,法律解释也比较中规中矩。“司法造法”的议题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后期讨论成立WTO争端解决机构时被提及的。代表们一致认为,争端解决机构不应该通过对协议创造性的解释,给WTO成员增加WTO协议里未有规定的义务。〔14〕See Summar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oposals for Negoti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Negotiating Group on Dispute Settlement, GATT Doc. MTN. GNG/NG13/W/14/Rev. 2 (June 22, 1988); Meeting of 25 June 1987,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Negotiating Group on Dispute Settlement, GATT Doc. MTN. GNG/NG13/2 (July 15, 1987).但是,何谓“创造性解释”,大家却是莫衷一是。
在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的18个月内,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55个成员代表先后77次提出了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问题,〔15〕See Richard Steinberg, Judicial Lawmaking at the WTO: Discursiv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8, No. 2, 2004, p. 256.争议焦点集中在争端解决机构之前受理的10起案件:DS27、DS44、DS54、DS58、DS62、DS121、DS166、DS177、DS184、DS202。这10起案件占了WTO成立前8年上诉机构受理案件总数的近五分之一。〔16〕截至DS202案,上诉机构共受理了56起上诉案件,其中DS8、DS10、DS11分别由欧盟、加拿大、美国提起申诉,被诉方都是日本。参见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status_e.htm,2020年12月30日访问。有争议的案件比例如此之高归因于WTO上诉机构是一个常设机构,〔17〕参见DSU第17.1条。它不同于一审临时组建的专家组,上诉机构受理的案件是终审案件。由于上诉机构成员是固定的,他们审理时面对的往往就是自己之前审理过的类似案件,即使争端解决机制没有要求(当然也不禁止),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参照之前的裁决。对此,巴哈拉教授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上诉机构报告具有“先例”效力,尽管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事实就是如此。在他著名的“三部曲”作品里,他解释这是上诉机构在审理许多同类争议中形成的“共识”。在多边贸易协议规定不明以及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无法及时作出权威解释之际,上诉机构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充当法律的解释者。他的结论是:通过修改WTO规则来明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这种解释权力。〔18〕See Raj Bhala, The Myth About Stare Decisi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 14, No. 4, 1998; The Precedent Setters: De Facto Stare Decisis in WTO Adjudication,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 Policy, Vol. 9, No.1, 1999; The Power of the Past: Towards De Jure Stare Decisis in WTO Adjudication, The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 33, Issue 3-4, 2001.
WTO争端解决机构司法功能的扩张不仅引起了各成员方政府的关注,也在学界引发热烈讨论。根据斯坦伯格教授的考证,从1982年GATT争端解决开始进入高发期到1994年GATT被WTO取代的这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有代表性的法学期刊发表了110篇有关GATT争端解决的论文,其中只有2篇提到“司法造法”问题。〔19〕这两篇文章分别是: Steve Charnovitz, Environmental Trade Sanctions and the GATT: An Analysis of the Pelly Amendment on Foreign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No. 9, 1994; Daniel A. Farber and Robert E. Hudec, Free Trade and the Regulatory States: A GATT’s Eye View of the Dormant Commerce Clause,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 47, 1994.相比之下,WTO成立不到8年的时间里,相同的刊物发表了有关“司法造法”的论文不下51篇。〔20〕See Richard Steinberg, Judicial Lawmaking at the WTO: Discursiv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8, No. 2, 2004, p. 256-257.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司法造法”对美国的影响,包括涉及国家主权和改变国会批准美国加入WTO的初衷、〔21〕Eg., KalRaustiala, 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ism,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2, 2000.司法能动在程序透明度不够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不民主现象等议题。〔22〕See Lori Wallach, The FP Interview: Loris’s War, Foreign Policy, Spring 2000, p. 37.
WTO争端解决机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构,缺少法院审理中的“发回重审”机制。上诉机构只要接手案件,就必须对上诉的每一个争议点作出法律解释。〔23〕参见DSU第17.6条和第17.12条。对此,穷尽法律解释,甚至创造性解释法律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不容否认的是,在WTO争端解决中,即使依据现有规则作出法律解释,其结果也并不总是唯一的,有时甚至等同于创设新的规则。〔24〕See Armin von Bogdandy and Ingo Venzke, Beyond Disput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es as Lawmakers, German Law Journal, Vol. 12, No. 5, 2011, p. 985-986.在“欧盟诉智利酒精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只要对条约作出正确解释,专家组的结论不可能增加或减损成员方在WTO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25〕See Chile-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DS87, Appellate Body Report, para. 79.然而,DSU第3.2条并没有对何为“正确”的条约解释作出界定。
三、“司法克制”的回归及其合理性分析
能动主义属于现代解释,克制主义属于传统解释。“司法克制”在国内法上的运用最早出现在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其基本含义是要求审判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应“自我约束”,以便政府有更多的行为空间。〔26〕司法能动主义缘何在美国兴起,并与司法克制主义的对立与交织构成了美国司法史的主旋律。对此的详尽论述,可参见郑成良、王一:《关于能动司法的格义与反思》,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4-45页。司法权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官解释法律权力的有限性。按照德沃金的说法,即使法官所宣布的是隐含的法律的意思,那也是法律的意思,而不能是法官个人的意思。为什么要求法官奉行克制主义?那是因为法官也是人,有许多人性的弱点,他可能受社会及个人偏见、情愫因素、社会压力或利益的诱惑。〔27〕转引自陈金钊:《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第29页。美国宪法制定者认识到解释宪法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所以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28〕参见[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2-393页。这说明解释权及解释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权力怎么行使是问题的关键。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争论主要是在宪法层面。在美国,人们对宪法的解释争议很大,而对于一般的判例,只要是明确的,法官们都是遵守的。〔29〕同前注〔27〕,陈金钊文,第29页。
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司法克制”是指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采取诸如限制自身对国际规则的解释权、尊重主权国家的立法、通过恰当方式回避“棘手问题”等自我约束的手法,防止裁决“创造性”地解释规则。这一点在一个成员方数量庞大、需要兼顾各方利益以及裁决对国际贸易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组织显得格外重要。国际法是在国家通过让渡部分主权的前提下形成的,缔约国在关心加入国际组织后能否享受到相应权利的同时,也在乎该组织行使职权时是否僭越了成员方的主权。
GATT成立后,无论是早期缔约方大会指定的工作组,还是后来专门成立的专家组,在审理案件时一直是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摇摆。1951年审理“皮草帽案”的工作组认为,应对被诉方美国的调查结论予以尊重,除非有极不合理的因素存在。工作组并未对何谓“极不合理的因素”作出解释,只是委婉地指出相关部门的调查应基于“诚实”。然而,“诚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原则且内涵丰富的概念。可见,工作组的解释明显带有“司法克制”倾向。〔30〕See Report on the Withdrawal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 Tariff Concession Under Article XIX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CP/106, adopted on 22 October 1951, para.30.1992年审理“挪威诉美国三文鱼反倾销案”的专家组同样认为:“专家组评判对于摆在美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前面的事实应给予何种相应考虑,这是不合适的。”〔31〕United States—Imposi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Fresh and Chilled Atlantic Salmon from Norway, Report of the Panel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 on 27 April 1994, ADP/87, paras. 509-510.而1994年审理“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案”的专家组似乎采取更为克制的态度,他们拒绝接受美国的观点,认为“在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与健康以及保护濒临枯竭自然资源时,GATT第20条给予缔约方如下权力:为实现上述目标,缔约方彼此之间可以实施贸易禁运措施。”〔32〕United States—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 Report of the Panel, DS29/R, unadopted, para. 5. 42.审理上述案件的GATT专家组不仅在行使“解释权”时主动自我约束,在裁决中给出“建议”时也谨小慎微。〔33〕例如,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大会1955年对GATT第23条修正时,增加了“败诉方暂时无法撤销违反规则的措施时,可从别的方面作出补偿”这样的规定。然而在1962年的“乌拉圭诉诸GATT第23条案”、1980年的“智利诉欧共体苹果案”、1987年“加拿大等诉美国石油税案”中,胜诉方都提出败诉方应作出“相应的主张”或“实物复原”的方式补偿其相关损失,这些请求都被专家组驳回。See Uruguayan Recourse to Article XXII, Report of the Panel adopted on 16 November 1962, L/1923-11S/95;EEC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Apples from Chile, Report of the Panel adopted on 10 November 1980, L/5047-27S/98, paras.4.6-4.10; United States—Taxes on Petroleum and Certain Imported Substances, Report of the Panel adopted on 17 June 1987, L/6175-34S/136, para.5.2.10.
乌拉圭回合历时8年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一整套规制各成员政府管制贸易措施的规范体系。为了能如期结束谈判,〔34〕乌拉圭回合定于1994年4月15日之前结束,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从国会争取到的谈判内容审批走“快速通道”(fast-track)机制的截止期快到了。按照这一机制规定,国会只对谈判内容作形式审查。错过了这一截止期,美国国会需要对政府参与谈判的所有内容进行详细审查。谈判各方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采取了模糊化处理,导致部分协议条款的内容不够明确。然而,这些模糊规定是否真的就像有些学者所讲的,使争端解决机构有了一定的空间去发展WTO法?〔35〕参见齐飞:《WTO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47-163页;彭溆:《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的司法造法》,华东政法学院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32页。其实不然,以多边贸易协议为载体的WTO规则是经过GATT的反复实践逐渐形成的,其中《反倾销协议》是在肯尼迪回合达成的第一份非关税贸易协议,然后历经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两次修订。乌拉圭回合达成的12部多边货物贸易协议,其中近一半是在东京回合达成或修订的。〔36〕这些协议包括东京回合首次制定的《反补贴协议》《贸易技术壁垒协议》《海关估价协议》《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及修订的《反倾销协议》。因此,WTO规则体现的是WTO全体创始成员国的共同意志。〔37〕根据《WTO协议》第11条第1款规定,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在世贸组织成立时集体“转会”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WTO成立后,新加入的成员必须签订入世议定书,同意按照其他成员的意愿接受多边贸易协议。议定书的法理基础是因为新成员没有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WTO规则并没有体现该成员的意志。作为加入该组织的“入门费”,议定书等于是新成员接受老成员设立的加入WTO的条件,以体现其尊重多边贸易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争端解决机构具有“造法”功能,代替了WTO成员的意思表示,那么无疑会颠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
要理解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在国际争端解决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必须了解其与国内争端解决之间的关系,因为两者是相互影响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不仅评判各成员贸易管制措施的合法性,而且也影响各成员管制措施的制定。在“美国诉欧盟影响生物产品审批和上市措施案”中,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对WTO规则所作的一系列解释,促成相关成员与其关注转基因产品规制的选民展开对话,帮助他们完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以及减少这些目标对不同选民的影响。〔38〕See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WT/DS291/R,WT/DS292/R,WT/DS293/R,Panel Report, paras.8.2-8.10.正如罗伯特•豪斯所言,SPS协议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此所作的解释能够而且应该被理解为(各成员)不仅没有因为执行较严格的规则而褫夺了选民的合法权利,还提升了风险管控民主决策的质量。〔39〕See Robert Howse, Democracy, Science and Free Trade: Risk Regulation on Trial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98, No. 7, 2000, p. 2329-2357.
“美国诉欧盟影响生物产品审批和上市措施案”凸显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受制于政治和社会文化特定条件的背景下,WTO如何充当敏感问题冲突的调解者。在评估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时,人们应该用反向思维考虑问题:如果WTO不具备有拘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美欧之间的争议结果将会如何?欧盟很有可能在专家组的组成及专家组裁决的执行等问题上面临来自其他成员的巨大压力,就如当年GATT经历的几起农产品争议,美国动辄以单方面报复相威胁,尤其是援引《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40〕美国采取过报复措施的包括“鸡肉战”“油菜籽战”以及其他农产品贸易战。See Robert Hudec,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GATT Legal System, Salem, NH: Butterworth Legal Publishers, 1993, p. 452, 33-37, 246-249.在WTO制度框架下,欧盟无法拒绝执行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裁决,美国也不可以在没有WTO的授权下单方面采取报复措施。若无WTO这样一个平台,美国总统就会面临来自国内农业游说团体和国会议员要求单方面制裁欧盟的压力。WTO争端解决机制成了美国行政当局应对国内压力的一个有效的挡箭牌。不然的话,美国政府和欧盟的行政部门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去化解如此敏感的争议。WTO帮助它们用“去政治化”的方式解决贸易纠纷,从而避免了双方的直接冲突。
四、“司法克制主义”的制度基础与现实选择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无本质区别,两者追求的目标一致,都是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但是,法官采取不同的指导思想,对具体案件则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在一个众多成员组成的国际组织,司法能动主义很可能会造成法制流产,因为不同成员之间的价值趋向差异很大,对于同一条法律的理解自然也会南辕北辙。
能动主义者认为,司法的宗旨是“法官应该审判案子,而不是回避案子……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41〕[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能动主义主张法官在解释法律过程中,不应受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影响,因为现实的重要性优于历史,况且立法者的意图也难以考证。法官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这一格言的最好诠释者。司法能动主义者倾向于减少程序的烦琐,主张超越法律规则的司法救济,表现出对其他决策者更多的怀疑。
司法克制主义则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严格维护法律意志,按照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尊重立法者的愿意,尊重成文法和先例,尽可能地减少法官个人的影响。〔42〕参见李辉:《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的比较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415页。司法克制主义的一个理念是法院不是万能的,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光靠法律知识是难以作出裁决的,还需要借助法律以外的其他专业知识解决。在此意义上,法院应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
WTO成立后,“司法克制”在制度层面得到了进一步落实。《WTO协议》第9条第2款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批准本协议及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具有排他权”,并规定“这种批准决定需得到四分之三以上成员同意才能通过。本条款不得改变第10条有关(多边贸易协议)修改的规定”。这样的规定事实上是把超越法律条文文本意义的解释等同于法律修订,同时明确了法律解释的主体,体现了罗马法“谁制定了法律谁就有权解释”这一古老原则。审理“日本酒税案”的上诉机构认为,这么明确的规定不会引起误解和争议。〔43〕See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p. 5.
从制度层面看,WTO争端解决奉行的是司法克制主义。然而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的现实需求与WTO规则中的解释权配置无法有效对接,导致“有权解释的机构不解释,无权解释的机构必须解释”局面的出现。按照现有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必须将争议所涉及的协议解释先提交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审议批准,然后再由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其作出的裁决和建议,这样就完全按照多边贸易体制设计者的初衷行事,也可以避免目前的纷争与困扰。然而,这种模式因其制度固有的缺陷而根本无法实现。
首先,DSU第14条和第17.10条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都是秘密进行的,尤其是上诉阶段,全程不对外开放,包括上诉方与被上诉方也没有机会参与。〔44〕在专家组审理阶段,申诉方和被诉方与专家组至少有两次见面机会,一次是提交材料,另一次是补充意见。这也是WTO争端解决有别于普通司法程序的地方。如果解释问题提交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决定,这等于争议还没有解决,内容已经公之于众,这样做有违DSU的规定。
其次,与许多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相比,WTO争端解决的高效、快速是在国际贸易纠纷案件居高不下情况下的现实需要。DSU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审理期限分别为6个月和3个月,经申请可适当延长。部长级会议每两年才举行一次。当年关贸总协定将早期的缔约方大会审理争端改为设立专门工作组审理,就是因为两年一次的缔约方大会间隔时间太长。如果部长级会议闭会期间由总理事会行使职权,也有点勉为其难。总理事会事实上是分成若干具体负责的理事会运作的,其中包括争端解决机构,如果让争端解决机构代表总理事会审议和批准解释,它又如何能确保四分之三以上的成员同意?
最后,WTO自成立以来,一直沿用“协商一致”的表决机制,即使在上诉机构遴选成员的问题上,WTO宁愿因达不成协商一致而让其停摆,也不动用表决机制。设想一下,用表决机制来决定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争端解决机构只有在“反向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不通过裁决报告,这就使《WTO协议》第9.2条规定形同虚设,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事实上也没有任何限制。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WTO规则中“法律解释权错配”这一制度缺陷。
在众多的多边贸易协议中,《反倾销协议》与成员国的国内法关系相对清晰,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协议是GATT期间达成的第一份非关税壁垒协议,历经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三次修订,内容相对比较成熟,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适用时的解释空间有限。《反倾销协议》第17.6条明确了反倾销争端解决中的“审查标准”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此基础上也从实践层面逐渐确立了其他争端解决的“审查标准”。〔45〕See Steven P. Croley and John H. Jackson, WTO Dispute Procedures, Standard of Review, and Deference to National Governmen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6, 1996.按照《反倾销协议》第17.6(1)条的规定,对事实问题的审查,WTO争端解决机构应该秉承GATT争端解决实践中保持的“司法克制”,将其权限限定在仅判断成员方政府的事实认定是否公正,不应进行重新调查,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成员国政府事实调查存在错误,否则一般应尊重成员方对事实的调查认定。〔46〕《反倾销协定》第17.6(2)条规定,专家组依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得出几种解释,WTO成员的反倾销措施只要符合其中一种解释,就应该被认定为符合WTO规则。
面对超越一般法律范畴的科技问题,WTO争端解决机构更应该尊重科学家的判断。在这方面,专家组在审理“美国诉欧盟影响生物产品审批和上市措施案”时表现出极大的克制。〔47〕See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WT/DS292/R,WT/DS293/R, Panel Report.专家组有意回避对许多敏感问题的裁决,包括“从总体上讲,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本案涉及的转基因产品是否与其他常规产品相似?”等。专家组赞同申诉方的部分观点,但都是基于程序上的理由,而非实体法上的规定。由此,专家组回避了对欧盟具体管制措施作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裁定。转基因产品能否上市,这在世界各国差别很大,即使是在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的美国和欧盟,其政策导向和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差异。转基因产品的进出口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贸易问题,而是夹杂着政治与科技的世界性难题,这不是专家组或上诉机构通过解释WTO规则能够说清楚的。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使命虽然是“依据国际公法习惯解释规则澄清多边贸易协议条款”,〔48〕参见DSU第3.2条。但是争端解决机构显然无法澄清所有的法律条款。正因为如此,《WTO协议》第10条规定了多边贸易协议条款的修改程序:凡是涉及WTO成员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修订需要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WTO成员同意才能生效,并对其产生约束力,对于不同意修订的成员,WTO可以超过四分之三以上成员的同意表决其是否继续留在该组织或者对其豁免;对于那些不涉及世贸组织成员权利义务的条款,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后对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力。这表明多边贸易协议内容如果不清楚且足以影响WTO成员权利义务的,《WTO协议》 有相应的修改程序,并不需要由争端解决机构加以澄清。换言之,争端解决机构也不能剥夺WTO成员的这一专有权利。
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是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的。立法追求规范的确定,司法追求判决的确定,两者无本质上的区别,差异只在于法律应用的方法上,其根源可追溯至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法学教育理念的差异。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思想向法学教育作了历史性的引渡,进而提出人文教育的理想,这种理念转变既是对中世纪狭隘的宗教教育观的摈弃,又是法学教育由神本主义向人文主义的历史回归。在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中心的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主张人权、理性及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将法学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世俗化的学问,并作为一种独特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来传授。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法系国家的近代法学教育都是以罗马法以及实证法的系统概念和原理为讲授重点,在综合运用注释法学派的教学方法和提供系统的现成教学材料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抽象的逻辑思考及理论体系构筑的能力。〔49〕参见刘侨:《人本法律教育观透视》,载《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72-175页。
相对而言,普通法系国家严格的法学教育起步较晚。尽管早在13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已经设立了法学院,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些法学院只是当地教会的附庸。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英国大学法学院以讲解宗教法规为主,这倒不是说宗教法规在判例法的形成过程中作用不大,〔50〕在英国法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法规的影响和贡献远远大于成文法,因为中世纪初期的英国法官都是学宗教法规出身的,判决也是依据这些法规作出的。参见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而是说明早期英国的法学教育有别于现代意义的法学教育,因为学生毕业以后的主要职业是在地方上担任教区牧师,像律师这种职业资格是经过律师协会等组织培训获得的。这种围绕案例展开的法律职业训练有别于欧洲大陆国家法学院以阐释法条为主的法学教学,孕育了普通法系的抗辩制和法官造法等司法特征。〔51〕14世纪初,伦敦西郊出现了一批小客栈(inn)。当时,一些家不在伦敦的议员和法官在议会开会和法院开庭时就下榻于此。这些客栈多的时候曾达到二十多家,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有Lincoln’s Inn, the Middle Temple, the Inner Temple和Gray’s Inn这四家。这些客栈平时的住客主要是法院的书记员和实习生,因此也被称为Inns of Court(意为“法院客栈”)。到了14世纪中期,法院客栈给住客们定期举办讲座,组织模拟法庭辩论,同时,还各自制定一些内部纪律,这些举措开始凸显现代行业组织的某些特点。经过这些机构培训的人有资格在法院为当事人出庭辩护。目前,法律协会仍然是英国培训出庭辩护律师(barrister)的主要机构,而事务律师(solicitor)的资格则通过事务律师协会(The Law Society)组织的考试获得。直到工业革命鼎盛时期的17—18世纪,英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原先的宗教法规已经无法解释诸多社会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言:“随着立法发展成为一个复杂和广泛的整体,人类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9页。至此,英国法律职业人的培养才逐渐由行业协会让位于大学。
五、温和的“司法”能动与适度的“司法”克制:未来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定位
法律解释权错配的制度缺陷是引发WTO争端解决机构定位争议的原因,但不是其权力扩张的理由。将原因说成理由会固化我们的偏见,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法律只有通过解释才能获得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什么是解释”如同“法律规定是什么”一样令人困惑,这种困惑是理论背景下的困惑,不是现实疑难案件的困惑,〔53〕同前注〔27〕,陈金钊文。其解决之道也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
争端解决中的司法能动主义罔顾WTO体制中原有的权力配置与制衡,不当地行使了“法律解释权”,甚至越权进行“司法造法”,这是导致争端解决机构目前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解决不好也会影响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WTO制度是多边谈判的结果,它融合了各种制度差异和谈判成员的意见分歧,法律条文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立法的“漏洞”并没有为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留有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争端解决机构不像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也不享有“司法解释权”。〔54〕参见李路根:《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及其制度化》,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219-224页。多边贸易协议规则的修改和完善只能依靠参与各方通过谈判完成,而不是靠争端解决机构少数几个裁判者通过扩大“司法解释权”来恣意发挥。否则,争端解决机构对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将与立法者的初衷渐行渐远,最终导致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崩溃。诚如苏力所言:“若不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些问题,能动司法就可能不解决问题,还添乱。”〔55〕苏力:《关于能动司法》,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Z1期,第5-10页。WTO争端解决机构不是一个“药到病除”的神医,也不能包治多边贸易体制的“百病”。
对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趋势,之前也有学者提出过一些协调措施,包括严格审查上诉机构成员候选人、允许第三方对案件表达关切、消极执行争端解决机构报告、通过总理事会及其下属的各种专门委员会表达意见。〔56〕同前注〔35〕,齐飞文,第147-163页。这些方案要么与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不符,要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格审查上诉机构成员候选人是一个很“政治”的思路,如何严格把关、审查标准是什么,这些都可能成为成员之间争议的焦点。但是,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导致上诉机构瘫痪这一现实已经否定了上述方案。〔57〕参见胡加祥:《上诉机构“停摆之后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何去何从》,载《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1期,第90-98页。而且这种做法也与DSU第17.3条要求上诉机构成员“具有法律、国际贸易以及相关领域专业技能”的规定不符。
允许第三方对案件表达关切也与争端解决的程序不符。与一般的司法机构强调公开、透明不同,WTO争端解决机构是一个政治协调场所,专家组审理阶段除了与争议双方有若干次见面交流机会外,其余时间都是秘密进行的。上诉机构审理更是全程不对外公开。专家组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依职权咨询案外专家,上诉机构则完全不接受案卷以外的材料,包括上诉方和被上诉方提供的新材料。〔58〕参见胡加祥:《世贸组织专家聘任机制之研究》,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40-45页。基于这样的制度规定,第三方对案件表达关切也就无从谈起。国内学界曾经热议的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庭之友”问题,〔59〕参见吕航:《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问题》,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4-88页;陈佳婧:《“法庭之友”DSU输入及法理探究》,载《理论观察》2017年第8期,第96-99页。其实是一种背离争端解决机制实质的“妄议”。
至于消极执行争端解决机构报告更是有违多边贸易体制的法治原则。DSU第23条要求WTO各成员通过认真执行争端解决机构裁决来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性和纪律性。WTO成立至今,一直沿用“协商一致”的方式表决,不轻易动用《WTO协议》第10条规定的表决机制;多哈回合谈判因无法“协商一致”通过决议无果而终,没有采用通过数票数的表决方式强行通过改革方案;上诉机构也因成员遴选无法达成“协商一致”而陷于停摆。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WTO的团结,因此,任何不利于WTO成员团结的消极措施都不适合用来改革多边贸易体制。
相比之下,通过总理事会改革争端解决机构法律解释权问题才是正确方向。如前所述,争端解决机构通过DSU相关条款获得法律解释的权力,但是这种解释只有经过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批准才能生效。之前的部分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之所以引起争议,撇开裁决报告内容的是非曲直不说,至少从程序上看也是不够严谨的,因为《WTO协议》 第9.2条规定的“专属排他权”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目前的制度看,这项权力事实上也无法落实,因为即使争端解决机构能够代表总理事会,它也会因“反向一致”的表决机制而使这种批准权力流于形式。故此,重新配置WTO的法律解释权,需要沿着以下路径。
第一,调整争端解决机构的运行模式,使其具有代表总理事会的资格。WTO目前拥有164个成员,总理事会成员是由各成员常驻使团负责人组成的。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不同,WTO是一个“集体治理”的国际组织。总理事会除了代替部长级会议行使职能外,还负责两项具体工作:争端解决和贸易政策审议。因此,从代表性这一点上讲,争端解决机构符合《WTO协议》第9.2条的要求。
第二,将争端解决机构由“反向协商一致”否决裁决报告改为“正向协商一致”通过裁决报告。符合代表性要求,并不意味争端解决机构就一定能够充分行使职权。目前的“反向协商一致”机制事实上剥夺了争端解决机构否决裁决报告的权力,因为这种一致意见实践中几无可能达成。WTO成立至今也未出现过一例通过反向协商一致意见否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先例。如果将“反向协商一致”否决裁决报告改为“正向协商一致”通过裁决报告,即恢复“协商一致”的本意,那么一切都将名正言顺。争端解决机构代表总理事会,名义上是由全体成员组成的,但是在每一次表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决报告的会议上,只有部分WTO成员会参加。根据《WTO协议》 注解1的解释,“协商一致”不考虑不出席表决会议成员的意见,而关注争端解决的成员自然会参与对裁决报告的表决,每一个成员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正向协商一致”能否达成。在“反向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否决裁决报告,有意见的成员无法阻拦裁决报告的通过,因为裁决对其有利的成员不会同意“协商一致”否决裁决报告,但是这会给今后的积怨留下隐患。美国对上诉机构发难就是源于其对之前数起争端解决裁决的不满,但又无法阻止其通过。采用“正向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裁决报告,这不仅给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审理案件施加了压力,当事方若有意见,也有机会及时表达。这样做虽然会影响争端解决的效率,但至少从程序上看是没有瑕疵了,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了给今后留下矛盾的隐患。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反向协商一致”改为“正向协商一致”?这涉及DSU第16.4条和第17.14条的规定。从文本内容看,这是修改幅度最小的选择,可谓“一字之差”。从修改程序看,《WTO协议》第10.8条规定,修改DSU的提议需要得到WTO成员协商一致通过,经部长级会议批准后对全体成员产生效力。这里的关键是“协商一致”,而不是像《WTO协议》第10.3条要求那样按照法定人数通过修改内容。鉴于目前WTO成员对争端解决机构意见较多,修改DSU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以这种对现有体制影响较小的变动换来争端解决方式较大的改变,这个方案对广大WTO成员还是有吸引力的,这也是命运多舛的WTO争端解决机构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选择。
任何法律应用都必须有解释,无解释就无法律适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法律文字的意思就是法律的精神所在”这句西方法谚。〔60〕参见孙笑侠:《西方法谚精选——法、权利和司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解释必须要有边界,解释主体也需要有合法的主体资格。反对解释并不是要求法官成为制定法的奴隶。从孟德斯鸠到布莱克斯通,他们都要求法官只能发现法律,而不能创造性地解释法律,〔61〕参见陈金钊:《法治为什么反对解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7-33页。司法克制主义反对法律解释并非反对所有法条的解释,相反,大多数法条都是需要解释的。但是按照法制的要求,在司法世界居第一位的要素是法律,法官对待法律的姿态是服从。〔62〕同前注〔27〕,陈金钊文。这当然不是在否定法官的作用,而是说在任何一套法律规则体系下,立法者给执法者留下的想象空间是有限的。好的解释如同好的法律一样重要,它除了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外,也要保证解释主体的合格、解释程序的公正。这样的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拥护,也才能真正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在WTO争端解决中提倡实行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因为我们反对能动主义倾向的法律解释主要是反对法官对明确法律规定的解释,并不反对其对那些明显有漏洞和模糊不清的法律规定的解释,因为不解释就无法适用这些规定。我们强调适度的司法克制主义也不是说“死扣”法条,争端解决机构只是充当“自动售货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世贸组织理应担负起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的重任。通过健全争端解决程序,WTO争端解决机构必将进一步发挥推动WTO成员团结与合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