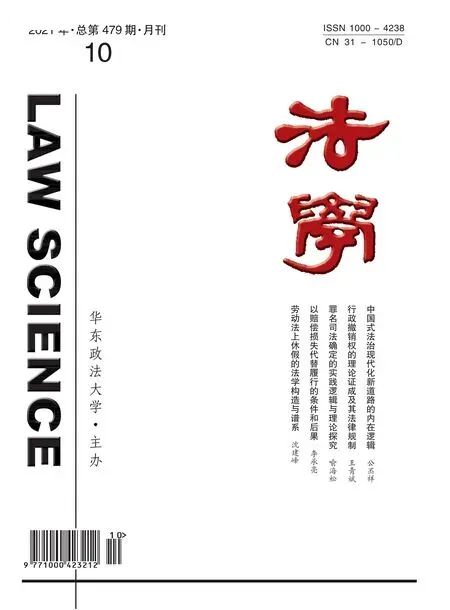身份行为能力论
●田韶华
一、身份行为能力之惑
所谓身份行为,是指以发生身份关系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狭义的身份行为也称纯粹身份行为,在我国立法上主要包括结婚、收养、协议离婚、协议解除收养等行为。广义的身份行为除此之外还包括夫妻财产制协议、离婚协议等行为。本文在狭义层面使用这一概念。所谓身份行为能力,简单而言,即行为人实施有效身份行为所应当具备的能力。如果欠缺此能力,则行为人将被否定实施身份行为的法律资格。由于身份行为之于个人的重要意义,对身份行为能力的规定,不仅关涉自然人对个人事务的自己决定权及个人福祉的实现,而且关涉法律对精神障碍者的平等对待问题,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身份行为能力并未受到我国立法应有的关注,其法律定位不清、认定标准不明给身份行为的登记以及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困惑。
在立法层面,各具体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仅能从《民法典》以及《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收养行为能力。《民法典》第1113条第1款规定,“有本法第一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情形或者违反本编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效”,而总则编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事由之一即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据此,应当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收养行为能力,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实施收养行为则不能从中得出结论。二是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具有协议离婚能力。依《婚姻登记条例》第12条第2项,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离婚登记申请。从中可推知这两类人均不具有协议离婚能力。至于结婚和协议解除收养行为所需之能力,现行立法并未设明文。特别是对于最为重要也最为普遍的结婚行为,《民法典》只要求“双方完全自愿”,〔1〕参见我国《民法典》第1046条。既未对结婚行为能力有所要求,也未将结婚行为能力的欠缺作为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7条第1款更是排除了将此种情形作为婚姻无效事由的可能性。〔2〕该条规定,当事人以《民法典》第1051条规定的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而根据《民法典》第1051条,无效婚姻的情形有三种,即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到法定婚龄。这一问题在《民法典》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彼时对于欠缺民事行为能力者缔结的婚姻,尚可依原《婚姻法》第10条第3项〔3〕根据原《婚姻法》第10条第3项的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的规定将其归于“疾病婚”而认定无效,但《民法典》删除了“疾病婚”这一婚姻无效事由,而其增设的“隐瞒重大疾病”这一可撤销婚姻类型〔4〕参见我国《民法典》第1053条。也不足以涵摄这一现象,这使得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所缔结婚姻的效力如何认定就成为问题。
在身份行为的登记层面,相关问题主要发生于结婚登记领域。虽然《民法典》和《婚姻登记条例》均未对结婚行为能力予以明确规定,但鉴于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能否结婚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些地方即已关注。如《北京市婚姻登记工作规范》(京民婚发〔2016〕177号)第31条第2款规定,能够明确表达结婚意愿、履行登记程序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结婚登记的,监护人应当同意并见证。而《安徽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皖民办字〔2018〕144号)的规定则有所不同,根据其第30条,智力低下、精神病人及精神抑郁的当事人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如能清晰表达个人结婚意愿、履行结婚登记程序,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受理。相较而言,虽然二者均对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能力予以一定的承认,但明显的差异在于后者对行为人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系依当事人在结婚时的精神状况予以判断,与其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关;而且,只要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即能独立实施结婚行为,并不需要监护人的同意。显然,在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问题上,后者的规定较前者更为宽松。
在司法实践层面,有关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始终困扰着法院,这主要发生在有关婚姻效力的民事诉讼或有关婚姻登记的行政诉讼中。从裁判结果来看,法院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结婚行为能力原则上持否定态度,但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结婚则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法院持肯定态度,认为既然相关立法均不存在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的禁止性及限制性规定,故此类当事人缔结的婚姻并非无效。〔5〕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8582号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则持否定态度,至于其中的原因,或者认为法律并未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结婚行为予以肯定,〔6〕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甬行终字第51号行政判决书。或者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所实施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不具有完全的理解和辨识能力。〔7〕参见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2017)冀0984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还有法院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结婚登记应当通过监护制度的辅助〔8〕同前注〔6〕。或“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办理。〔9〕同前注〔7〕。此外,在有关收养的纠纷中,也有法院否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送养子女的能力。〔10〕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2015)横少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以上判决结果虽有差异,但在将民事行为能力作为认定身份行为能力的依据这一点上并无不同。
综上所述,除了协议离婚行为外,包括《民法典》在内的现行立法对其他身份行为的能力问题并未予以明确的规定,由此导致了身份行为登记和司法实践的诸多分歧和困惑。而从实务部门的做法来看,对身份行为能力的理解均未脱离民事行为能力的理论框架或思维定势,其后果是使得那些虽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仍有一定意思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身份行为的自治范围之外。虽然一些地方性规定或个案对此有所突破,但由于身份行为能力的基本理论未能予以厘清,从中难以抽象出统一的规则。在笔者看来,以身份行为能力对标民事行为能力的做法,完全是基于身份行为系法律行为这一定性而进行的逻辑推演,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故有必要对此反思。而鉴于身份行为区别于财产行为的独特性,更有必要构建一套独立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身份行为能力理论,以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作出妥当解释。
二、身份行为能力的定位及其与民事行为能力同质化的反思
(一)身份行为能力的定位
从目前相关研究来看,学界对于“身份行为能力”这一概念着墨不多,相关研究集中在结婚、收养等具体身份行为的能力领域。就结婚行为能力而言,学者多认为其是指法律规定的自然人为婚姻法律行为的资格,是民事行为能力在婚姻法中的具体化,属于行为能力的一种,故应定位于“特殊的行为能力”。〔11〕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姜大伟:《体系化视阈下婚姻家庭编与民法总则制度整合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6页。至于其特殊之处,学界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具有完全意思能力,是结婚行为能力的两个基本条件。〔12〕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有学者则认为,法定婚龄是判断结婚行为能力有无的一般标准,精神健康状况则系例外标准。〔13〕同前注〔11〕,余延满书,第162页。还有学者将结婚能力的“特殊性”进一步扩大,认为除了法定婚龄和精神健康状况之外,该能力还受非精神疾病因素的影响(如原《婚姻法》对“疾病婚”的禁止性规定)。〔14〕同前注〔11〕,姜大伟文,第16页。在这一逻辑之下,有学者更进一步地认为收养法关于收养人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收养资格的规定也系对收养行为能力的规定。〔15〕参见朱涛:《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之法理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6-167页。上述观点一方面将身份行为能力定位于民事行为能力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又在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中加入了法定婚龄甚至法律有关结婚、收养要件的某些规定,这使得身份行为能力的定位极为混沌和模糊,故有必要首先对此问题予以厘清。
要厘清身份行为能力的定位,就要从“能力”一词入手予以分析。一般而言,法律上的能力通常是指“在法的世界中作为主体进行活动,所应具备的地位或资格”。〔16〕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其作为“人自身的一项身份资格”,〔17〕[葡]曼努埃尔•德•安德拉德:《法律关系总论》(第2卷),吴奇琦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页。在民法上主要包括权利能力、实施意思自治行为的能力以及责任能力。就“实施意思自治行为的能力”而言,由于其根植于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因此所具有的自己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18〕参见[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9页。故其核心乃自主决定能力,又由于自主决定能力建立在行为人对行为及其结果能够充分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故在性质上属于精神能力。〔19〕参见[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身份行为作为行为人自主实施的以发生身份关系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其所要求的“能力”亦系行为人可以自己为决定的能力,故在性质上亦属精神能力。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行为人实施各项具体身份行为所需具备的精神能力未予明确规定,但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无论是《民法典》上结婚、协议离婚、收养、协议解除收养中的“自愿”,还是相关主体对收养的“同意”,均包含了对行为人精神能力的要求。〔20〕参见我国《民法典》第1046、1076、1096、1104、1114条。
基于上述认识,应当认为,无论是法律关于结婚要件的规定,还是关于收养要件的规定,均系法律为了维护身份秩序对身份行为的限制,而并非对行为人精神能力的要求,故与身份行为能力无关。至于法定婚龄,虽然其与自然人的生理成熟状况和心智状况有关,但由于其同时还受到一定时期的人口政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因此并非与自然人的精神能力完全对应。特别是我国的法定婚龄之所以偏高,完全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计划生育政策考量的结果,而不是基于精神能力要求的选择,故不应将其纳入身份行为能力的范畴。〔21〕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综上所述,可以对身份行为能力作如下定位,即该能力作为行为人自主参与身份行为的可能性,在内容上是一种自主决定能力,在性质上是一种精神能力。其与缔约能力、遗嘱能力、患者的同意能力等一样,反映了法律对特定类型意思自治行为之精神能力的要求。
(二)身份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同质化的反思
将身份行为能力界定为精神能力,很容易将其与同样为精神能力的民事行为能力联系在一起,并将二者作同质化对待。正如前文所述,这一看法已经得到理论界及实务界的普遍支持。在笔者看来,上述认识获得认同的主要原因,乃是基于身份行为的法律行为定性,认为适用于法律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也应当同样适用于身份行为。这一理由虽然看起来非常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鉴于身份行为的特殊性,仅仅藉由法律行为的定性即导出民事行为能力规范适用于身份行为能力的演绎式推理并非合理。〔22〕关于身份行为的特殊性,参见冉克平:《民法典总则的存废论——以民法典总则与亲属法的关系为视野》,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5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312页。特别是在《民法典》有关身份行为的诸多制度(如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均未完全采用民事法律行为规范的前提下,上述认识就更加值得反思。笔者认为,将身份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同质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民事行为能力标准与身份行为的特质多有不符。虽然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均属法律行为,但其与后者大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由于身份行为形成的是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身份关系,故其意思表示并不像财产行为那样是计算的、功利的和权宜的,而是具有非理性和非功利性的特点。〔23〕参见[日]中川善之助:《身份法总则的课题》,转引自于飞:《公序良俗原则研究——以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这意味着对于财产行为而言正确的制度对于身份行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正如学者所言,虽然是在提取合同、遗嘱、结婚等行为公因式的基础上经过抽象、演绎而形成的,但其规范的典范却是债权合同,故其规则也主要是针对财产行为而设。〔24〕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因此,民法总则中的法律行为制度并非一定能够适用于身份行为。〔25〕同前注〔22〕,冉克平文,第306、319页。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确定的有效实施法律行为的精神能力,其产生原因正如后文所述,主要是为了避免个案审查的麻烦以保障交易便捷和交易秩序,财产行为正是其制度设计的基础。〔26〕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页。正因为如此,学者认为行为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计算能力,〔27〕同前注〔22〕,冉克平文,第294页。行为能力欠缺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精神能力不完全者的财产。〔28〕参见[日] 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Ⅰ民法总则》(第6版补订),渠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这对于不以追求财产利益为目的,更不以效率为其价值取向的身份行为显然不具有可适用性。
其次,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过高,造成一些精神障碍者〔29〕所谓精神障碍,在医学上主要包括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性障碍,以及心境障碍、癔症、神经症、精神发育迟滞等。参见《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3)。参与身份行为的机会被剥夺。目前,法院对于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一般以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为依据,而依司法鉴定技术规范,对于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主要考察以下因素,即能否良好地辨认有关事务的权利和义务;能否完整、正确地作出意思表示;能否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0〕参见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2018年发布的《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指南》附录A:民事行为能力判定标准细则。在笔者看来,这一标准乃是建立在将精神能力完全者预设为“经济理性人”的基础上,这对于交易行为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以非理性和非计算性为特征的身份行为却显然过高。因为即使是一个精神健康之人,对于结婚或离婚行为所导致的权利义务以及个人权益的保护也未必具有良好的认知,更何况是具有精神障碍的人。鉴于法律并未因精神健康者不具有上述认知而否定其身份行为能力,以上述标准作为判断精神障碍者身份行为能力的依据无疑提高了后者实施身份行为能力的门槛,未能体现出法律应有的平等对待。
再次,民事行为能力标准的适用忽略了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在身份行为领域可能存在的自主决定能力。由于精神和思维的复杂性,精神障碍者在特定领域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并不代表其在其他所有领域均无相应的精神能力。临床医学研究即认为精神障碍者并非所有思维均异常,存在离婚行为不受影响且可以正确处理离婚事务的情形。〔31〕参见邱昌建、张伟:《精神障碍患者婚姻能力的评定》,载《华西医学》2004年第1期,第72页。然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重要特征即在于,一旦被认定为行为能力欠缺者,行为人就取得了受法律保护或意思自治受限的法律地位,无需再对其事实上的精神能力作判断。〔32〕同前注〔24〕,维尔纳•弗卢梅书,第215页;同前注〔16〕,梁慧星书,第68页。特别是我国《民法典》第24条第1款所规定的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宣告是一种概括性的宣告,法院并不指出行为人在哪些方面欠缺行为能力,〔33〕参见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1民特28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7民特74号民事判决书等。这种“全有或全无”的范式势必会忽略被宣告人在身份行为领域可能存在的精神能力。虽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存在学者所谓“如缔结婚姻与其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则应当认为其具有缔结婚姻的能力”的可能性,〔34〕李昊、王文娜:《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兼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相关规定》,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0页。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结婚属于“重大”行为为由否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结婚行为能力,〔35〕同前注〔6〕。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身份定位对于其实施身份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
最后,民事行为能力标准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第24条第1款规定了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学界对此的解读是,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任何成年人不得被视作行为能力欠缺之人。〔36〕同前注〔21〕,朱庆育书,第246页。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行为人在办理身份行为登记时,即使未被法院宣告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也可能会因疾病、醉酒等原因存在暂时的意识丧失或精神障碍,于此情形,登记机构应依何种标准认定身份行为能力便成为问题。二是在当事人于诉讼中要求宣告另一方当事人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情形,依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此时应当终止诉讼,经当事人申请依特别程序立案审理。〔3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49条。问题在于此种宣告判决的效力能否溯及至判决作出之前的行为。在实践中,有法院持肯定态度,〔38〕参见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行终字第75号行政判决书。其合理性值得怀疑。〔39〕参见常鹏翱:《意思能力、行为能力与意思自治》,载《法学》2019年第3期,第112页。也有法院持否定态度,但由此面临应依何种标准认定身份行为能力的困惑。〔40〕参见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6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4民特监1号民事判决书。正是由于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带来的上述问题,一些法院在诉讼中依司法鉴定意见或医院的诊断证明直接认定当事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这种做法虽然方便了诉讼,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实有违法裁判之嫌。〔41〕同前注〔39〕,常鹏翱文,第112页。就此而言,现行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实难满足身份行为登记及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身份行为能力认定标准的重构
(一)身份行为能力认定标准的域外法考察1. 大陆法系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
在采潘德克顿体系的大陆法系民法典,其总则编多对行为能力设有明文,然而,从其亲属编的内容来看,有关身份行为能力的规定及学理阐释并未完全按行为能力的逻辑而展开,行为能力也并非认定身份行为能力的绝对标准,这在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中体现得较为明显。〔42〕值得说明的是,在各国及地区的民法典上,不仅行为能力欠缺的类型及范围各有不同,身份行为的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在身份行为能力认定标准这一层面进行比较法考察。
在日本,依其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未成年人、成年被监护人等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中未成年人作出法律行为原则上应取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成年被监护人的行为能力则被全面限制,只能通过其法定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43〕上述内容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3条第1款第10项、第5条、第9条。学理解释参见前注〔28〕,近江幸治书,第42-46页。但依亲属编的相关规定,成年被监护人可以独立实施结婚、收养、协议离婚以及协议解除收养行为,〔44〕参见《日本民法典》第738、764、799、812条。这与总则编有关行为能力的规定完全不同。由此体现出在日本,身份行为并不适用民法总则有关行为能力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身份行为能力就没有要求,在解释上一般认为行为人仍应具有意思能力,而且只要有意思能力,即使是行为能力欠缺之人,也可以单独实施完全有效的身份行为。可以说,身份行为能力以具备意思能力为已足在日本已成为通说。〔45〕同前注〔19〕,我妻荣书,第60页。上述观点亦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所继受。〔46〕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在德国,身份行为领域的意思能力标准通过其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及学理阐释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750条第3款,被收养人本生父母以及收养人配偶对于收养的同意,即使表意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也无需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此外,虽然该法第1304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不得结婚,但在解释上有学者认为,“结婚当事人有可能在其他领域不能形成或控制自己的意思,但可以理解和作出有关结婚的意思表示,此时就不适用第1304条”。〔47〕[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这实际上承认了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具体的理解能力为依据。再有,根据该法第1314条第2款第1项,一方配偶于结婚时处于无意识状态或暂时性精神障碍者,婚姻可以被废止。由于当事人的这种情况并不导致行为能力的丧失,〔48〕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4条,无行为能力人系指不满7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因精神活动之疾病处于长期丧失自由决定意志状态者。暂时处于丧失自由决定意志状态者,并不属于无行为能力人。其所涉及的正是学者所谓的“精神—意思能力”,〔49〕同前注〔24〕,维尔纳•弗卢梅书,第217页。由此体现出“意思能力”之于结婚行为能力认定的意义。
相较日本和德国的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则明确将判断能力(通说认为其与“意思能力”同义)作为某些情形下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根据该法第17条,无判断能力人、未成年人和受总括保佐的人为无行为能力人。鉴于判断能力与行为能力并非完全对应,该法对有判断能力而无行为能力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其中体现出对身份行为能力的特殊对待。如依该法第19条第1款,有判断能力而无行为能力的人,原则上应经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实施法律行为。然而,依该法第19c条第1款,上述自然人可以独立行使与其人格有关的权利,这主要涉及订婚、结婚、订立遗嘱等行为。〔50〕参见[瑞]贝蒂娜•许莉曼-高朴、[瑞]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第2版),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这表明只要行为人具有判断能力,即使其为无行为能力人,也可以独立实施结婚等身份行为。
2. 英美法系身份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
相比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并不存在行为能力这样抽象的概念,其对合同、遗嘱、结婚等行为所需要的精神能力直接采用了与大陆法系中“意思能力”意义等同的“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y)这一标准。〔51〕See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England & Wales); Assisted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Act 2015 (Ireland).对这一能力的认定,早期的英美法曾采用“法律地位(或状态)标准”(status approach),如根据爱尔兰早期的相关法律,如果一个人属于受法院监护的人,那么,其就不具有缔结有效婚姻的能力。〔52〕See Marriage of Lunatics Act 1811 (Repealed).也有法院采取“结果标准”(outcome approach),即以行为人意思决定的结果是否符合一般社会观念判定意思能力的有无。〔53〕See Law Commission, Mental Incapacity, Report No. 231 (1995), HMSO, p. 32.由于上述标准过于限制了精神障碍者的自己决定权,故逐渐被“功能性标准”(functional approach)所替代。所谓功能性标准,即对心智能力的判断系以行为人在具体时间、具体事务中的精神状况为标准,而并非以行为人是否属于受监护人或具有精神障碍为依据予以判断。〔54〕同前注〔53〕,第32页。上述认识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心智能力的专门立法中得到了肯认。〔55〕See Assisted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Act 2015 (Ireland), Sec. 3(1).
功能性标准对于精神障碍者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在此标准之下,一个人不能在某一方面作出决定并不代表其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作出决定。精神障碍者可能没有财产方面的心智能力,但却可能具有对身份行为的决定能力。在司法实践中,该标准被广泛适用于有关结婚、分居、离婚以及收养等行为的心智能力的判断中,体现出对精神障碍者自己决定权的尊重。例如,在英国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肯定了一位智力低下患者的结婚行为能力;〔56〕See Sheffield City Council v. E [2004] EWHC 2808 (Fam).在加拿大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妻子存在精神障碍,但仍然具有同意分居和离婚的能力。〔57〕See Wolfman-Stotland v. Stotland, 2011 BCCA 175; Appeal [2011] SCCA 242.此外,在英国的一起涉及未成年父母决定送养自己子女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对未成年人收养同意能力的判断也应当采取功能性标准,而不应基于其未成年人的身份一概否定其同意能力。〔58〕See Re S [2017] EWHC 2729 (Fam).
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无论是规定了行为能力制度的大陆法系,还是没有此项制度的英美法系,对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基本上采取了建立在个案审查基础上的意思能力标准,使得精神障碍者获得了更多的实施身份行为的机会,这与我国立法及实践仍在民事行为能力的制度框架内规定或阐释身份行为能力的思维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么,何谓意思能力,为何其能在行为能力之外获得独立地位,又能否成为我国法上身份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这些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意思能力标准的理论认知及在我国正当性之证成
1. 意思能力标准的理论认知
所谓意思能力,学说上也称其为辨别事理能力或判断能力,其逻辑起点是法律行为和私法自治。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出发,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果必须建立在行为人能够理解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并能按这一理解为意思决定的基础上,〔59〕同前注〔24〕,维尔纳•弗卢梅书,第214页。而行为人针对上述认识和行为所具有的能力即为意思能力。〔60〕同前注〔19〕,我妻荣书,第55页。由于意思能力是个人所具有的自然的精神能力,对其的认定正如瑞士联邦法院所认为的那样,“其不应当被抽象地确定,而应就特定行为具体地确定,按照行为发生时该行为的性质和意义所要求的能力确定”。〔61〕同前注〔50〕,贝蒂娜•许莉曼-高朴、耶尔格•施密特书,第211页。就此而言,意思能力标准实际上采取的是针对特定人,在特定时间就特定行为是否具有精神能力的个案审查方式。
意思能力的个案审查方式虽然与私法自治的精神高度契合,但与交易的简便性、安全性格格不入,〔62〕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故法律对意思能力的认定采取了行为能力这一定型化的标准,即将不具有正常及健康精神状态的人一律以欠缺行为能力对待并作类型化处理,〔63〕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3条第1款第10项、《瑞士民法典》第17条、《德国民法典》第104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3条等。其意义在于一旦被认定为行为能力欠缺者,就无需对行为人事实上的意思能力再予认定。就此而言,行为能力实为意思能力的抽象化、定型化。由于行为能力只能表明意思能力的大概率情况,在逻辑上不可能完成对意思能力的全面抽象,二者因此未必绝对地一一对应。〔64〕参见孙犀铭:《意思能力的体系定位与规范适用》(上),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1期,第150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认识到这一点,遂在行为能力之外对意思能力予以不同程度的规定和认可,如规定当事人无意思能力时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等,由此形成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并存的格局。《日本民法典》第3条之二、《瑞士民法典》第19条以及《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即为著例。〔65〕有关大陆法系民法典上意思能力规范的比较法考察,参见上注,第149-152页。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虽然意思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基础,但由于行为能力是不考虑行为差异的抽象能力,而意思能力是因人因事而异的具体能力,故二者不一致的情形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正是行为能力制度的局限性催生了独立的意思能力规范和理论的产生,使其得以在行为能力不及之处或不宜适用之处发挥应有的作用,意思能力标准也因此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身份行为领域的选择。
2. 意思能力标准在我国的正当性之证成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民法上民事行为能力的定型化,以及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所导致的身份固化正是前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66〕参见我国《民法典》第19-24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两大法系所提倡的意思能力标准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质言之,在我国法上,对身份行为能力的判断应当突破民事行为能力的思维模式,按照身份行为实施时行为人是否具有依该行为的性质和意义所要求的意思能力予以认定。〔67〕同前注〔22〕,冉克平文,第307页。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即使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也未必就一定不具有身份行为能力;反之,亦然。这一标准在我国法上的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证成。
首先,意思能力标准更符合身份行为的特质,且能在技术层面弥补民事行为能力的不足。一方面,身份行为作为具有高度人身属性的行为,更为重视行为人的自己决定权,该标准以个案审查的方式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身份行为能力,不仅与身份行为的特性高度契合,而且可以依具体身份行为的特质设计相应判断要素,从而能够避免因僵硬适用财产法规则而导致的不妥当结果。另一方面,若适用该标准,即使行为人没有被法院宣告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只要其在实施身份行为时不具有意思能力,即可被认定不具有身份行为能力,而不必诉诸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解决,这在司法实践与身份行为登记中均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虽然这种方式会增加实践的难度,但在“效率”与具有更高价值的个人自由和个人福祉发生冲突时,法律显然应当选择后者。
其次,意思能力标准有利于精神障碍者基本权利及福祉的实现。随着人权保障的发展,包括精神障碍者在内的残疾人的基本人权日益受到重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即要求缔约国确保残疾人拥有与他人平等的法律能力,其中蕴含对残疾人的意愿和选择予以充分尊重的理念。〔68〕参见李霞:《协助决定取代成年监护替代决定——兼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监护与协助的增设》,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5页。而精神障碍者对家庭的形成或解消所享有的自己决定权更应当受到特别的尊重。此项权利一方面因其“自由”的内核关涉基本人权的实现,〔69〕参见林喆:《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另一方面则因为身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的全人格结合”〔70〕同前注〔46〕,史尚宽书,第10页。的性质还关涉个人幸福的实现。因为无论是婚姻还是收养,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人们对爱、温暖以及安全的期待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具有决定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不应被排除在外。如前所述,民事行为能力标准在上述目标的实现上力有不逮,而意思能力标准的个案审查范式则使得精神障碍者的自由意志能够被充分尊重,更有利于个人自由及福祉的实现。
最后,意思能力标准在法律适用层面也具有正当性。有学者认为,在身份行为中使用有别于行为能力的意思能力概念并不准确也不科学,且难以与民法总则上的法律行为形成合理的对接。〔71〕参见张作华:《亲属身份行为基本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6页。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尚值得商榷。应当看到的是,我国《民法典》虽然不存在意思能力这一概念,但一方面,《民法典》第21条和第22条在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中使用了“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表述,其中隐含的“辨认能力”实际上就是意思能力,这意味着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需要以意思能力为基础;〔72〕这已经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参见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20)苏0324民特3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特205号民事判决书等。另一方面,既然民事行为能力无法实现对意思能力的全面抽象,就会存在有行为能力却无意思能力,或有意思能力却无行为能力的可能性,也就不能排除意思能力在民事行为能力之外的独立适用。就此而言,在民事行为能力不及之处,意思能力仍然可以通过解释论获得实证法上的独立地位。〔73〕同前注〔39〕,常鹏翱文,第110-113页;同前注〔64〕,孙犀铭文,第152-153页。而我国《民法典》对各具体身份行为的精神能力均未设明文,这为相关法律解释留下了空间。
四、身份行为能力认定标准的展开与适用
对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采纳意思能力标准,意味着无论行为人是否被法院宣告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均应以行为人在特定时间、针对特定身份行为所具有的意思能力为依据认定身份行为能力的有无,这就需要对意思能力的认定设置相应的标准或判断要素,避免“意思能力”因过度抽象而成为另一个“民事行为能力”。判断要素的嵌入意味着意思能力的认定并非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是融入了价值判断的法律问题,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关系到个人特别是精神障碍者实施身份行为的门槛,应予审慎对待。
(一)意思能力判断中的价值取向
与民法中的其他制度一样,身份行为之意思能力标准的制度设计也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一方面,精神障碍者的自己决定权应当受到尊重;另一方面,精神障碍者作为弱势群体,有因缺乏理性而遭受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可能性,故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由此产生自由与安全的价值冲突,如何选择关系到意思能力的判断标准,对此不可不辨。由于身份行为类型多样,而结婚行为属于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故下文主要以结婚行为为例展开分析。所得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身份行为。
结婚行为之意思能力的判断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不然的问题。因为虽然作出结婚的决定很简单,但结婚的后果却很复杂,不仅涉及人身关系,还涉及夫妻财产制、继承等财产关系,而鉴于婚姻所带来的诸多“福利”,并不能排除以图财为目的的婚姻的存在,由此导致对精神障碍者财产安全或人身安全的担忧。〔74〕See Kimberly Whaley et al., Capacity to Marry and the Estate Plan, Canada Law Book, 2010, p. 70.这使得在结婚行为能力的判断中自由与安全这两种价值的冲突至为明显。对此,各国和地区的选择不尽相同。以英美法系为例,其对结婚行为能力的判断一般采取较低的标准。如英国法院在2004年的一起案例中指出,婚姻契约在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契约,它并不需要较高程度的认知,对结婚能力不应设置过高的标准,否则会剥夺许多精神障碍者对婚姻的体验。〔75〕同前注〔56〕。这一较低的标准固然凸显了“自由”价值,但也为那些仅仅以图财为目的或是具有人身安全隐患的婚姻提供了便利。有鉴于此,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的一些判例遂在传统认定标准之上增加了额外的判断因素,如行为人同时具有管理或保护个人事务及财产方面的能力,〔76〕See Banton v. Banton, 1998, 164 DLR (4th) 176; Feng v. Sung Estate, 2003 CanLII 2420 (ONSC).或行为人具有对婚姻之于结婚对象所产生的广泛后果(包括财产和继承等)的理解能力等。〔77〕See X v. X [2000] NZFLR 1125.与传统标准相比,上述较高的标准体现出对以图财为目的的婚姻的警惕,凸显出对安全价值的特别追求。
笔者认为,于结婚之意思能力的认定,我国应当确立以自由为主导并兼顾安全的价值取向,前述一些国家以安全为名对结婚能力设置较高标准的做法并不可取。首先,结婚以及自己决定权属于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以自由为价值取向体现出对基本人权的尊重,而对结婚能力设置过高的标准有限制基本人权之嫌。其次,正如黑格尔所言,婚姻的本质是伦理关系,其以爱为内在的规定性。〔78〕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1-202页。要求行为人以“保护自我利益”的“经济理性”对待结婚的决定,有违婚姻的本质。最后,婚姻关系不同于财产关系,当事人并非利益的对立者,而是互惠者。无论是法律还是法院均没有权力决定结婚是否有利于当事人的最佳利益,更没有权力以对当事人不利为由否定其结婚的自由。毕竟,“不明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行为人没有作出决定的能力”。〔79〕See Assisted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Act 2015 (Ireland), Sec. 8(4).就此而言,在结婚之意思能力判断要素的设定上,保障个人自由的价值取向应当得到法律更为优先的考虑,以行为人未来有可能遭受损害为由限制结婚自由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但在保障自由的同时,也不应完全忽略对安全价值的考虑,只是该价值的实现应建立在确保行为人的决定系建立在其充分理解婚姻的性质和意义的基础上(因为行为人在根本不了解婚姻为何物时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不能以剥夺行为人的自己决定权为代价。
(二)意思能力判断要素的确定
在确定立法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意思能力判断要素的设定便具有相对明确的思考方向。对于意思能力的判断要素,英美法系比较强调理解能力。例如,爱尔兰2015年《协助决定(能力)法》第3条第1项即规定,心智能力的判断应建立在行为人对其决定的性质和后果所具有的理解能力的基础上。而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和瑞士的民法理论则认为除了理解能力(或辨认能力)之外,还包括行为人所具有的基于其自由意志行动的能力,即意思决定能力。〔80〕同前注〔50〕,贝蒂娜•许莉曼-高朴、耶尔格•施密特书,第210页;同前注〔24〕,维尔纳•弗卢梅书,第218页。在笔者看来,由于意思能力为精神能力,而健康的精神状况不仅包括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也包括能够依其意思自由作出决定。就此而言,将意思决定能力纳入意思能力的判断标准无疑是正确的。法律亦应针对上述两种能力分别设置不同的判断要素。其中,意思决定能力的判断相对简单,其核心是行为人能否排除外部影响而自由形成意思并为决定,故在判断时主要应考量行为人的决定是否受到其无法抗拒的精神状态(如精神疾病、极度紧张、醉酒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排除上述影响的前提下,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意思决定能力。〔81〕参见孙犀铭:《意思能力的体系定位与规范适用》(下),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第123页。相比之下,理解能力的判断则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此尚需作更为细致的探究。
理解能力判断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应当要求行为人对身份行为的何种信息具有理解力(所谓理解力,不仅包括能够理解相关信息的意义,也包括对上述信息作出评价和判断)。对此,笔者认为,在以自由为主导兼顾安全的价值取向之下,该判断要素的选择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身份行为意思表示的特殊性。应当看到的是,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对相关法律后果具有一定的认知,是因为法律行为的后果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而身份行为则不然,其权利义务系由法律规定,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效果意思,故在意思能力的判断要素上不应作与法律行为相同的要求。二是身份行为的伦理属性。身份行为的伦理属性决定了人身关系是其“内核”,财产后果只具有次生意义,故不应要求行为人像缔结财产合同那样,对相关财产权益予以一定的理解和权衡,否则就是要求行为人将精细的利益衡量纳入身份行为的决定过程,降低了身份行为应有的意义和品格。〔82〕同前注〔56〕。这意味着对身份行为意思能力程度的要求低于财产行为。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应当认为对于身份行为之理解能力,仅以行为人对特定身份行为的性质以及基于该性质所产生的后果具有理解能力为已足,而不应要求其对所有的法律后果特别是财产后果均具有理解能力。具体来说,对于结婚行为,行为人应对婚姻的性质以及社会一般观念上婚姻所产生的义务与责任具有理解能力。前者是指婚姻所意味的永久的、一夫一妻的共同生活;后者则指婚姻通常导致的夫妻相互关心、相互照顾以及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等内容。对于离婚行为,当事人应对离婚的意义(即婚姻的永久结束)以及一般意义上离婚所导致的后果(即共同生活的解消)具有理解能力。对于收养行为,当事人应对收养的意义(即解消生父母子女关系,建立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社会一般观念上的收养后果(即被收养人不再与生父母共同生活,而与养父母共同生活等)具有理解能力。对于解除收养的行为,当事人应对解除收养的意义及后果(即解消养父母子女关系)具有理解能力。
(三)意思能力判断规则的适用
如前所述,身份行为能力的判断主要发生在身份行为的登记、司法鉴定以及司法裁判这三大领域,这三个领域均不可避免地关涉意思能力判断规则的适用。但需要指出的是,该规则的适用并不意味着登记机构和法院要对每一个人的意思能力进行评估,也不意味着每一个行为人均要对自己具有意思能力积极证明。在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意思能力推定原则,其是指任何一个成年人,除非有相反的情况(即存在意思能力障碍),均应被推定具有意思能力。该原则体现出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尊重,并有助于避免个案审查中可能产生的公权力恣意,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所承认,也应为我国民法理论所遵循。〔83〕See Assisted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Act 2015 (Ireland), Sec. 8(2);有关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此所作的规定,参见前注〔68〕,李霞文,第109-112页。
意思能力推定原则意味着行为人只有在存在意思能力障碍的情形下,才有可能被认定为不具有意思能力。意思能力障碍在有的情形下较容易判断,如行为人因醉酒、疾病等原因而暂时丧失意识或存在明显的精神错乱。但在有的情形下则不能仅从外部表现得出结论,以行为人存在智力低下、失智以及精神分裂等精神障碍最为常见,于此情形通常需要医学和法学两个方面的专业判断。其中,医学判断系对行为人能否建立临床上的精神障碍诊断作出认定。法律判断则是对精神障碍是否构成对前文所述的理解能力或意思决定能力的妨碍得出结论。显然,无论是意思能力判断的专业性还是其采取的个案审查方式,都使得实务部门特别是登记机构和法院的工作成本大大增加,对此,可以充分发挥司法鉴定部门的作用,利用其专业特长为身份行为的登记及司法审判提供辅助。就此而言,意思能力判断规则在不同部门适用的程度及侧重点便有所不同。
对于身份行为的登记机构而言,意思能力认定的专业性决定了其只能在形式层面适用上述规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能够清晰表达意愿、不具有明显精神障碍的申请人,登记机构应推定其具有意思能力。二是对于严重精神错乱或因醉酒等原因暂时丧失意识,无法表达意愿的申请人,登记机构应认定其不具有意思能力,不予受理登记申请。三是对于存在明显精神障碍而意思能力存疑的申请人,登记机构可要求其提供鉴定部门出具的身份行为能力鉴定意见,以作为是否受理登记申请的依据。在申请人具有身份行为能力但存在行动或表达障碍的情形,应允许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亲友协助完成登记。
对于司法鉴定部门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到意思能力判断所具有的法律属性,并在此基础上规范鉴定工作。一方面,应依意思能力判断规则制定身份行为能力认定的技术性规范,使其更加契合身份行为的特性。另一方面,应在医学诊断的基础上,重视对精神障碍之于被鉴定人理解能力和意思决定能力影响的判断,避免仅依精神障碍诊断否定被鉴定人的意思能力,以使鉴定结果更接近于法律判断,从而为登记机构和法院提供更为专业的鉴定意见。
对于法院而言,应当认识到在意思能力的判断中,医学判断固然是基础,但法律判断才是核心和根本。故应当改变目前过于依赖司法鉴定(虽然司法鉴定意见因其专业性而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但其作为证据之一,仍然需要查证属实才能为法院所采信)的做法,更不宜直接将医院出具的精神障碍诊断证明作为认定意思能力的依据,而应在参照上述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的具体表现(动作、表达、沟通等)、证人证言以及立法精神等对当事人的意思能力作出最终认定。
五、身份行为能力欠缺的法律后果
将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明确为意思能力的主要目的,就是使那些虽然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但仍然具有意思能力的精神障碍者能够实施有效的身份行为。因此,具有身份行为能力之人当然可以独立实施身份行为,对此自无需赘言。但如果行为人因欠缺意思能力而被认定不具备身份行为能力,在现行法上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则是一个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虽然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正如学者所言,由于《民法典》确立了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编纂体例,总则编对于分则各编即具有统辖效力。〔84〕参见孙宪忠:《中国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统辖遵从关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37-38页。故对于《民法典》分则各编未予规定的事项,原则上可以视情形适用总则编的规定。但对于身份行为而言,基于其不同于财产行为的特性,总则编的规定并非均得适用,依情形可以有适用、变通适用或排除适用等结果。〔85〕同前注〔46〕,史尚宽书,第12页。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对行为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后果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行为人如何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规定了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实施(第22条)或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第21、22条)两种救济方式。二是针对行为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定了无效(第144条)和效力待定(第145条)两种后果。对上述规则在身份行为能力欠缺情形下的适用可以概括如下:就身份行为的实施而言,同意实施规则和法定代理制度原则上应排除适用,只在特殊情形下有所例外;就身份行为的效力而言,“效力待定”规则应排除适用,但可依总则编的规定认定身份行为无效。
(一)同意实施规则之排除适用
笔者认为,在行为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欠缺身份行为能力的情形下,不适用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后实施法律行为的规则。法律之所以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法律行为须经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享有完全的私法自治,因此,所谓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实系对前者能力欠缺的补足;〔86〕同前注〔24〕,维尔纳•弗卢梅书,第1061页。另一方面,法定代理人有义务照顾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和财产,赋予其同意权也可以弥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智力、经验方面的不足。然而,身份行为意思能力的认定采取个案审查方式,其结果是行为人或者具有身份行为能力,或者不具有身份行为能力,并不存在身份行为能力“不完全”而需要补足的情况。而且,身份行为所具有的情感因素和人身属性决定了“其并非一个需要专业咨询或协助的领域”,〔87〕同前注〔56〕。最终的决定权更不宜置于他人之手,故不存在由他人同意后实施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实施身份行为应区别对待。在行为人具有意思能力时,应允许其独立实施身份行为,而无需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这一点在前述日本、德国以及瑞士等国家的民法典中均有体现,也应为我国民法理论所接受。其结果正如学者所言:“结婚、离婚、收养和子女认领等身份行为的能力,应持续永久受法律承认,可以单独实施而无须经过特定监护人同意。”〔88〕同前注〔68〕,李霞文,第115页。而在行为人不具有身份行为能力时,则不能实施身份行为,不存在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后实施的余地。
(二)法定代理之禁止及例外
身份行为能力欠缺的情形原则上也不适用法定代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身份行为具有高度的人身属性,行为人对此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允许他人替代作出决定不仅不符合行为人的真实意愿,也与身份行为的性质相悖。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如《法国民法典》第458条、《瑞士民法典》第19c条以及英国《心智能力法》第27条第1款等都对身份行为之禁止代理予以了明确规定。在我国,依《民法典》第161条第2款,依照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学界通说认为,结婚、离婚、收养等身份行为即属于该条所谓依其性质不得代理的行为。〔89〕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6页。此项认识值得肯定。
然而,上述结论固然有利于尊重行为人的自己决定权,但在有的情形下一概禁止代理也可能发生不利于精神障碍者的后果。例如,在法国第一民事庭以及最高院判决的一起案件中,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女孩处于其父亲的监护之下,其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希望收养她,但法院认为女孩不具有同意能力(此种情形下的收养依法须经被收养人本人同意),而这种行为依法也不得代理,故判决其不能被收养。〔90〕参见[法]斯泰法尼•莫拉齐尼•才登伯格:《特殊弱势群体的人身性行为》,载李贝编译:《法国家事法研究文集——婚姻家庭、夫妻财产制与继承》,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09页。有学者认为上述判决并不利于对女孩利益的保护,因为作为受法律保护的特殊弱势群体,其自身利益要求人们作出决定,而不是选择不作为,故基于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代理。〔91〕同上注,第209页。
上述情况在我国也可能存在。例如,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04条,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应当双方自愿。收养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在解释上,应当认为已满8周岁的被收养人自主享有对收养事项的同意权,其同意构成收养成立并生效的必要条件。〔92〕参见薛宁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婚姻家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42页。而在年满8周岁的被收养人因精神障碍不具有同意能力时,如果不允许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同意的话,收养行为就不能实施,这使得为保护未成年人而设的收养制度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故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需要,应当允许法定代理人代为同意。那么,在行为人不具有结婚行为能力时,能否以为其提供保护或照顾为由,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作出结婚的决定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虽然婚姻能够为精神障碍者提供一种自然保护,〔93〕同前注〔90〕,斯泰法尼•莫拉齐尼•才登伯格文,第220页。但其本身并非作为保护性制度而存在,如果以保护为名允许法定代理人代理行为人作出结婚决定,则不仅有违婚姻的本质,与结婚自由原则也多有不符。
(三)身份行为的无效及补正
如前所述,除收养行为外,我国《民法典》对于身份行为能力欠缺者所为身份行为的效力未设明文。就这种情况下所缔结婚姻的效力而言,学者之间存在无效说〔94〕同前注〔34〕,李昊、王文娜文,第110页。和可撤销说〔95〕参见马忆南:《民法典视野下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兼论结婚要件》,载《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3期,第28页。两种不同的观点,而各国和地区对此的规定也不尽一致,有可废止〔96〕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第1款、第2款第1项。、无效〔97〕参见《瑞士民法典》第105条第2项、第107条第1项。以及可撤销〔98〕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96条。等不同效力。对此,笔者认为,将此类行为的效力认定为可撤销能够体现出对身份行为能力欠缺者的个人意愿以及既成身份关系的尊重,可以作为今后立法完善的方向,但就目前而言却很难在现行立法上找到依据。相比之下,无效说可以藉由《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规定解决现实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因而更具有可操作性。
以《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认定身份行为能力欠缺情形下的身份行为无效,其法律适用问题可通过以下路径解决。在身份行为能力欠缺者同时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可直接适用总则编第144条认定此种行为无效。在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由于总则编第145条规定的“效力待定”这一后果有违身份行为的终局性、确定性和自主性,故不适用于身份行为。于此情形应对该条变通适用,认定此种行为无效。至于在身份行为能力欠缺者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由于总则编对此无相关规定,故应认为存在法律漏洞,鉴于意思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在本质上的同源性,可以类推适用第144条,认定此种行为无效。上述结论对于收养、协议离婚、协议解除收养等身份行为的适用固无疑问,但对于结婚行为则由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7条第1款对婚姻无效事由的限制性规定而存在障碍。对此,应当认为上述解释对《民法典》第1051条作了过于严苛的解读,完全排除了《民法典》总则编相关规定的适用,未尽妥当,实有必要通过限缩解释予以修正。即应将其理解为“除《民法典》第1051条规定的三种无效情形外,以违反婚姻家庭编的其他规定为由主张婚姻无效的,不予支持”,从而为结婚行为能力欠缺情形下婚姻无效的认定留下余地。
将欠缺身份行为能力者所实施的身份行为认定为无效也面临一个问题,即如果行为人恢复了意思能力应作何处理。应当看到的是,从谋求身份关系的安定性出发,各国及地区的立法均承认瑕疵身份行为可因补正转为有效。〔99〕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315条,《日本民法典》第745条第2款、第747条第2款等。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0条对此也予以了承认,即规定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婚姻不再被认定为无效。上述规定可以适用或类推适用于因欠缺身份行为能力而致身份行为无效的情形。至于如何适用,有学者认为,于当事人恢复行为能力之后,即应认为无效情形消失,婚姻即为有效。〔100〕同前注〔34〕,李昊、王文娜文,第111页。对此,笔者认为,由于在欠缺意思能力情形下实施的身份行为并不能反映行为人的自由意愿,故意思能力恢复本身并不能当然导致无效情形的消失,只有当行为人恢复意思能力后明确表示维持身份行为效力的,才能认为无效情形消失,效力瑕疵才能得以补正。这一点也有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可资参考。〔101〕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315条第1款第2项、第3项。
六、结论
身份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是实现婚姻家庭法上意思自治的工具。从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身份行为的实施应当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精神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可以当然适用于身份行为。在我国,长期以来将身份行为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同质化的观点只是建立在单纯逻辑推演的基础上,忽视了身份行为及其能力要求的特殊性,特别是剥夺了具有意思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实施身份行为的可能性,对其正当性应予反思。
鉴于身份行为区别于财产行为的特性及其对个人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在民事行为能力之外构建独立的身份行为能力理论体系。身份行为能力制度应当以充分尊重个人意思自治特别是精神障碍者的自己决定权为核心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由与安全之间的适度平衡。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应摒弃以抽象化、定型化为特征的民事行为能力标准,而采取以个案审查为基本范式的意思能力标准。意思能力包括意思决定能力与理解能力,其中对理解能力的判断应当以行为人对特定身份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一般观念所认为的后果予以理解为已足,而不应当要求对所有的法律后果特别是财产法律后果均具有理解能力。行为人在具有身份行为能力时,应当被允许独立实施身份行为。而其在欠缺身份行为能力时,则不能实施有效身份行为,原则上也不适用同意实施规则以及法定代理制度。欠缺身份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身份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但从尊重既成身份关系的角度出发,可经由补正而转为有效。在意思能力标准及其相关规则设计之下,个人在身份行为领域的意思自治,特别是作为特殊弱势群体的精神障碍者的自己决定权有望得到法律更加充分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