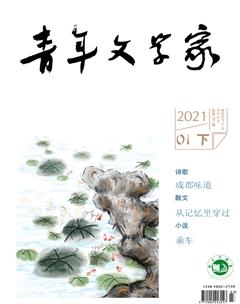《今昔物语集》中“狗头丝”故事研究
摘 要:成书于12世纪中叶的《今昔物语集》是日本文学史上最大的说话集,全书分天竺部、震旦部、本朝部3部分,各部分又分为佛教故事和世俗故事。本稿试图对出自《今昔物语集》本朝部世俗故事部分的一则有关“狗头丝”的故事,从标题结构、语言特色、叙事手法以及故事构思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明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分析故事的文学性与说教性。
关键词:今昔物语集;狗头丝;说教性;文学性
作者简介:马可英(1980-),女,汉族,山西晋中人,硕士,湖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3--02
《今昔物语集》(以下简称《今昔》)是日本文学史上最大的说话集,大体成书于12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全书共31卷(其中第8、18、21卷缺失),按照佛教传播的时空分为天竺部、震旦部、本朝部3部分,各部分又分为佛教故事和世俗故事。书中收录故事1200余则,大多讲述宣扬佛法的佛教故事,也描绘了上达天皇贵胄英豪,下至庶民乞丐强盗的种种人物,记录了民间广泛流传的神佛、动物、鬼怪故事[1]。它对我们了解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参考与研究价值。同时,《今昔》参考了中国宋元以前的大量资料,尤其是震旦(中国)部分大多出自于中国的文学典籍,故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对这部说话集的成书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讲,这部作品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今昔》本朝部卷二十六第11话《参河国始犬头丝语》(参河国“狗头丝”的由来)是一则有关“狗头丝”的故事。译文如下:
从前,参河国(又称三河国,现爱知县境内)某郡的郡司娶了两房妻室,让她们在家养蚕。有一年不知何故,原配夫人养的蚕全部死去,郡司因此极感不快,从此对她冷淡起来。仆从们见状也都对她不予理睬。因此,原配夫人家境日趋冷落,心中也是十分凄凉。
有一天,她发现桑叶上附着一条蚕在吃桑叶,便将它取下来饲养。这条蚕长势喜人,夫人心中甚是欢喜。这天,当夫人观看大蚕吃桑叶時,家中养的白狗竟然跑过来一口吞下了大蚕。夫人伤心又无奈地想,我竟然这么命薄,连一条蚕都养不活,想着想着便对着白狗流下了眼泪。这时,白狗打了个喷嚏,然后从它的鼻孔里吐出了两根长约一寸的白丝。夫人不胜惊讶,便揪住丝头往外拉,越拉越长,最后拉出足足有四五千两后才露出丝头,这时白狗便倒地身亡了。夫人心想这狗必是神佛化身来帮助自己,就把狗埋葬在房后园里的一棵桑树底下。
当夫人正发愁这么多生丝无法纺织时,郡司丈夫恰巧因事路过家门。当他看到这罕见的白丝时就询问夫人原因。夫人便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他。郡司闻听深悔自己不该怠慢神佛保佑的人,于是,立即留在了夫人这里。
后来那棵埋葬白狗的桑树上,结满了蚕茧,他们便取下缫丝,仍然是绮丽无比。郡司把此事上报国守,国守转奏了朝廷,从此便由三河国向朝廷进贡“狗头丝”。这“狗头丝”还用来纺织天皇的御衣。也有人说郡司原配夫人的蚕是由二夫人蓄意害死的,至于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
由此看来,他们夫妇由于“狗头丝”的出现才破镜重圆,这都是前世的因果。故事就是这样的。[2]
“狗头丝”作为平安时代进贡朝廷并为天皇做衣服的生丝,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白丝。《延喜式》卷二十四“主计上”中记载:“凡贡夏调丝者。伊贺、三百絇。伊势八百八十絇。白丝。参河二千絇。犬头丝。”[3] 这说明“狗头丝”是参河国的特产。因此,当地人民为强调其珍贵性,完全有理由编造美丽的传说故事。而从《今昔》性质看,原创故事的可能性也不大,编者很有可能是在民间“狗头丝”故事雏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故事进行了一定的改动。但正因此,才使“狗头丝”的故事得以广泛流传。在日本,以《今昔》为出处的“狗头丝”故事不少,还有被作为神社起源说,甚至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看闻御记》(1416-1448)中有相同的故事便是佐证。
接下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故事进行分析。
1、标题结构
这则故事标题为“参河国始犬头丝语” (参河国“狗头丝”的由来),其中包括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参河国、事件——出现“狗头丝”。这种主谓结构的标题,通俗易懂,使人读过之后便对故事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同样结构的标题也出现在该卷其它几个故事中。比如:卷二十六12话“能登国凤至孙得带语”(能登国的凤至孙获得宝带),13话“兵卫佐上倭王于西八条见得银语”(长缨兵卫佐于西八条发现白银),14话“付陆奥守人见付金得富语”(陆奥国守的家臣发现黄金致富),15话“能登国堀铁者行佐渡国堀金语”(能登国采铁人往佐渡国挖金)等,都是主谓结构,并以“语”结句。
《今昔》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晚期,当时正是日本社会向中世过渡的阶段。封建律令制逐步瓦解,农民阶层势力增强,武士阶层开始抬头,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转型期。与此同时,私渡僧、民间寺院兴起,寺院庄园领主化,使得佛教逐渐普及并趋于世俗化[4]。人们突破旧的等级认同和价值观,更多地关注社会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昔》的编纂者为达到向普通民众宣传佛教、弘扬佛法的目的,采取了比直接宣传佛法更为有效的途径,即讲民众身边发生的事或一些奇异之事,来吸引民众的眼球,并借此来弘扬佛法。体现在故事标题上,就是叙述尽量详细易懂,让民众好接受并有兴趣阅读。可见,故事标题如此命名,意在吸引读者注意力,从而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
2、语言特色
《今昔》是一部佛教说话集,因此,在世俗部中也不乏佛教用语,渗透了佛教意识。故事中,原配夫人在看到白狗吃了大蚕时,伤心地想,自己竟然这么命薄,连一条蚕都养不活;当看到白狗鼻子吐丝时又想:“这狗必是神佛化身来帮助自己”;郡司听了夫人讲述白丝的来历后,“深悔自己不该怠慢神佛保佑的人”;话末评语:“由此看来,他们夫妇由于‘狗头丝的出现才破镜重圆,这都是前世的因果。”上述3处心理描写与话末评语明显使用了佛教用语,包含了佛教思想。
对于故事中无法用常理理解的现象,编撰者煞费苦心地用“神佛庇护”“宿报”等佛教用语来进行解释。然而,从故事脉络来看,这样的解释很是牵强。尤其是结尾处说夫妻能破镜重圆都是前世的因果,但是故事中明显缺少前世的相关情节,既没有解释原配夫人为什么能得到神佛庇护,也没有讲夫妻二人前世的因缘。因此,特意用“宿报”来解释不可思议之事,正反映了编者极力渗透佛教理念,对民众进行说教的明确意图。
3、叙事手法
3.1脉络繁杂、一波三折
该故事出场人物较多,事件脉络繁杂交错,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出场人物除了主人公原配妻子外,还有郡司、二夫人、白狗、国司、“狗头丝”等。事件则在“狗头丝”由来的主线之外,穿插了平安时代租庸调制下百姓向朝廷进贡的事实,描绘了当时参河国一带农村养蚕的情景。在叙事中,通过对郡司原配妻子境遇在恶化与改善间不断反复的栩栩如生的刻画,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简单概括如下:
蚕死,不能养蚕(恶化) → 发现一只蚕,养(改善) → 白狗吃了蚕(恶化) → 白狗鼻子吐丝(改善)→ 白狗死(恶化)→ 白狗埋身之处的树上生出蚕,作茧吐丝,丈夫回到身边(改善)
另外,前面提及的3处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也为故事增添了文学性和趣味性,最终加强了编撰者的宗旨——说教性。
3.2有意渲染故事的真实性
故事中清楚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出现了平安时代的官职名称,行文中还有“也有人说是现在的妻子杀了原配妻子的蚕”等证明有“旁观者”存在的字眼,这些都给人一种毫无疑问的真实感。故事越真实,就越具有可信性。毋庸諱言,以一种讲述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口吻来叙述其实并非完全可信的事实,这正反映了《今昔》编撰者竭尽全力地想达到故事真实性效果的强烈意图,其最终目的自然是为更好地宣传佛教,弘扬佛法。
4、故事构思
从白狗埋身之处的树上生出蚕茧这一构思,我们可以看到死体化生故事的影子。日本不少神话故事,尤其是创世神话中有大量的死体化生故事,如《古事记》中讲到,五谷是从女神尸体中化生而来的——“大気都比売神”死后,头生蚕,目生稻,耳生栗,鼻生小豆,阴部生麦,屁股生大豆[5]。“狗头丝”的故事中,白狗死后,被埋在树下,之后树上结出蚕茧,即白狗死后化为了蚕。这说明“狗头丝”的故事是以创世神话的死体化生故事为母体而构思的。进一步分析,日本的死体化生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神话故事的影响而产生的。上述女神尸体化生五谷的故事与盘古的故事极为相似便是佐证。“盘古开天辟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狗头丝”这则故事以死体化生为母体,构思上富有一定的文学性。
另外,从卷二十六第11话到18话整体来看,编纂者有明确的分类意识,即把同一主题的故事放到一起,构成一个“故事群”。11话“参河国始犬头丝语”,12话“能登国凤至孙得带语”,13话“兵卫佐上倭王于西八条见得银语”,14话“付陆奥守人见付金得富语”,15话“能登国堀铁者行佐渡国堀金语”,16话“镇西贞重从者于淀买得玉语”,17话“利仁将军若时从京敦贺将军行五位语”,18话“观硕圣人在俗时值盗人语”,无一例外都是“意外致富”的主题。这样的编排方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故事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结论:
通过以上四个角度对“狗头丝”故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今昔》的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使用佛教用语,渗透佛教意识,并且有意渲染故事的真实性,加大故事的可信度。同时,使用主谓结构的标题,采取一波三折的叙事手法,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有意对同类故事进行编排,并借助日本创世神话中死体化生的思想来编写故事,以此来实现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加强故事的说教性,达到宣传佛教、弘扬佛法的目的。作为日本文学史上最大的说话集,《今昔》时空跨度大,出场人物多,故事种类杂,兼具说教性与文学性,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论《今昔物语集》中的中国物语[J].王晓平.中国比较文学,1984(1):85.
[2]今昔物语集[M].北京编译社译,张龙妹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925-928.
[3]新订增补国史大系 延喜式中篇[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2:600.
[4]平安时代的信仰和生活[M].山中裕,铃木一雄编.东京:至文堂,1994:11-16
[5]日本创世神话中的两性崇拜现象[J].方倩.青年文学家,2019(1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