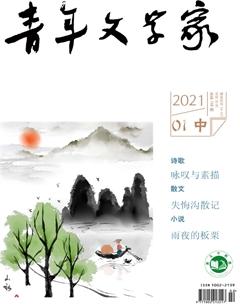《煤河》的丛林精神解读
摘 要:《煤河》是澳大利亚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丛林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丛林小镇的故事。本文从丛林意象入手,分析了作品中關于动植物及丛林自然景观的描述,指出丛林生活对丛林精神形成的重要影响,并从独立精神,伙伴情谊和反抗精神三个方面解析故事中人物的丛林精神。
关键词:《煤河》;丛林精神;反抗精神
作者简介:陈丽娟(1994.5-),女,汉,山西晋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2--02
引言:
《煤河》是澳大利亚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昆士兰遥远的农村”[1]1,“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丛林小镇。”[1]2米勒创作了多部“反映昆士兰中部地区社会生活的小说,且多以农村而非城市为背景”[1]1,这与他早年在昆士兰中部丛林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
“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丛林上的一个国家。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丛林不仅指早年到处是桉树的自然风貌,它还代表着一种具有澳大利亚乡村气息、远离城市、贴近自然的勇敢坚毅、豪爽不羁以及艰苦抗争的人文精神,丛林生活蕴涵了具有澳大利亚民族特色的丛林精神。”[2]64“丛林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是真正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3]1本论文拟从小说中的丛林意象着手,通过文本分析,对《煤河》的丛林精神进行较为细致的解读。
一、丛林意象
“在土著人心中,一切生命体、动植物以及这片大陆上的风俗、文化、仪式都与丛林地貌有关,他们认为丛林地貌是先民们去世后用遗留的生命体创造的,丛林地貌是先辈们的超灵存在。”[4]52小说中有关植物、动物和丛林独一无二的景观的描写随处可见。
小说开篇,主人公鲍比·布鲁和他的父亲被告知母亲死讯时,“那是下午晚些时候。微风徐徐,从西边的荒漠吹来大块大块灰色的云朵。那云朵仿佛刚在什么地方下过雨,现在突然投下黑影笼罩了牲畜围栏。围栏里的牛都不安地躁动着,大声吼叫起来。”[5]6这一段景物和动物的描写预示着噩耗的到来。“灌木林里,伴随他们(年纪大的人们)的只有穿行在树木间的牲畜踩踏大地的声音。被分开的母牛和小牛犊在你的马前面互相叫唤着寻找对方。”[5]7丛林里一片和谐,这是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幸福美满的家庭的印证。文中还多次提到老鹰、蚁蛉幼虫、黄知更鸟、乌鸦、黑风头鹦鹉、袋鼠、白蚁、蛇等动物,以及金合欢树、粉绿相思树、桉树、无花果泉、红墙等自然景物,这些丛林独一无二的景观,孕育着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丛林精神。
二、独立精神
独立精神体现在小说中许多人物身上,尤其是主人公鲍比·布鲁。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鲍比努力谋生:“我的父亲死了,本的父亲也死了。对于我们俩。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为谋生计,我不得不环顾四周,找一条新路。”[5]13找到新工作的鲍比,兢兢业业,充分发挥自己在丛林里练就的本领,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鲍比的独立精神还体现在他对知识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上。半文盲的鲍比有幸遇到从海岸来的新警察丹尼尔·柯林斯的大女儿艾瑞·柯林斯,跟着她读书写字,故事最后描述在监狱里的生活时,鲍比提到:“就是在斯图尔特监狱,我变成一个读书、写作的人。我一直在艾瑞·柯林斯教给我的那些知识的基础上,积累文化。”[5]427鲍比的朋友本·托宾身上也充分体现了独立精神。本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一直以强壮、坚韧而闻名,“我从来没见过本做事半途而废。加倍努力才是他的习惯。”[5]50“除了爸爸,本·托宾是我知道的最出色的丛林人……本·托宾从一开始就干大人的活儿,熟知那块岩石裸露的干旱之地。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他找不到的清冽甘甜的山泉水了。”[5]54鲍比和本都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丛林人,而这与他们在丛林里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三、伙伴情谊
艰苦的丛林生活造就了丛林人之间深厚的伙伴情谊,这在鲍比和本的关系中充分得以体现。鲍比和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和父辈一起走遍这块蛮荒山野的每一寸土地。”[5]53他们在丛林中患难与共,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本总是把我当作他的小兄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我这边。”[5]54他们的父亲去世后,鲍比和本便不像从前那样经常到灌木林干活儿,即便这样,他们的友谊也丝毫未减。本向鲍比分享快要做父亲的喜悦,并且希望鲍比早日成家。鲍比和本被判处绞刑时,“我看了本一眼。他面带微笑。我很高兴能和他一起上路,而不是孤零零地被他留在身后……能和本一起赴死是那一刻我最大的心愿。”[5]409-410“‘他们要绞死我了,鲍比!我笑不出来,但大声喊道:‘我爱你,本!‘我也爱你,鲍比·布鲁!他大声喊着。”[5]418这是他们最后的对话。
伙伴情谊还体现在人与动物的相处中。小说中“老娘”和迪普是除本之外,鲍比最好的伙伴。“老娘”是一匹母马,因纪念鲍比的母亲而得名“老娘”,“这匹母马还是小马驹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5]36“老娘”总是能知道鲍比心中所想,鲍比也十分信任它,爱惜它。“我知道这匹母马绝对不会拒绝我的指令。它勇敢,而且判断能力极强,抵得过本·托宾十匹公马……这匹母马对我言听计从。”[5]213迪普是埃斯米养的狗,它似乎知晓一切,能看到人不曾看到的东西。它也同样是鲍比的好伙伴,“我关上围栏的时候,迪普就像一把椅子似的,直挺挺地站在‘老娘身边,看着我,舌头耷拉得老长,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我告诉它,我认为它非常棒。它高兴得简直要瘫倒在地上,绕着我转来转去,舔我的靴子,讨我的好。”[5]288-289故事中鲍比被丹尼尔夫妇押着去找艾瑞和米里亚姆的场景中,“迪普在围栏前面停下,呜呜呜地叫了几声……仿佛知道再也不会见到我们,但又太害怕,不敢和我们一起走……我看见它(老娘)脑袋朝后仰着,因为害怕,翻着白眼。”[5]330-331“老娘”和迪普的反应一方面表现出它们同鲍比的情谊之重,另一方面暗示了故事的走向。
四、反抗精神
丛林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丛林人乐于抗争的精神,《煤河》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便是本·托宾,小说中描述了他与丛林的抗争,与父亲的抗争,与警察的抗争,以及最后与命运的抗争。年少就辍学的本在环境恶劣的丛林中艰苦生存,与丛林进行抗争,练就了超乎常人的丛林本领。“在丛林里,在马背上,他如鱼得水,是一个非常可靠,可以信赖的人。”[5]59
本与他父亲的抗争要追溯到他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儿学会随随便便就提上帝的名字,父亲听到之后用马鞭柄打他,差点儿把他打死。”[5]60 “本长大之后,他的父亲还经常打他,而且打得非常凶狠,好像他还是个小孩子。”[5]51本从未还过手,总是默默忍受着,唯有用大笑进行抗争,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十分可怕的笑声。
本与警察的冲突完全是一场误会,其根源便是丛林与城市的文化冲突。小说中着重描述了丛林与城市之间文化及行为方式的差异,为故事结局进行了铺垫。首先是两任警察行为方式的不同。乔治·威尔逊是干草山人,他在这里干了三十年的警察,“任职期间,倘若遇到麻烦,他总是在亲自介入之前,先让矛盾自行化解,分清是非。”[5]15而丹尼尔·柯林斯“是个照章办事的人”[5]17。乔治·威尔逊在山里长大,对干草山的风土人情很熟悉,他知道如何跟大家相处。丹尼尔和柯林斯急于改进干草山,却不肯花时间慢慢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如果你不愿意打搅他们平静的生活,如果你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理解到位——就像乔治·威尔逊那样——我得说,干草山不是个难管理的地方。”[5]22其次是丹尼尔夫妻与干草山人行为方式的差异。山里人不会刨根问底,“没必要知道的事情我们从来不问,即使想知道的事情,也把疑问留给自己,等待时机弄个水落石出。”[5]29可是丹尼尔却总在提问。山里人若是在丛林里看到小动物或是蜂房,都会沉默不语,等原路返回去的时候便把他们带走。丹尼尔如果在丛林里看到了什么,他会立刻指给你看,似乎在炫耀是他先看见的。干草山的人从来不多问,更不会干涉别人的工作。埃斯米却不同,她不仅限制女儿们的自由,还过度干涉丈夫的工作,这为后来的悲剧也埋下了隐患。
悲剧发生之后,本和鲍比被指控犯了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但事实并非如此。唯一能作证的艾瑞没有出面作证,真相被埃斯米扭曲,加之媒体的失真报道,没有人相信本和鲍比的话,真相随着本的死被永远埋葬。“报纸上刊登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都被描绘成没有良心,对自己的同胞没有丝毫怜悯之情且无恶不作的坏蛋。”[5]393“报纸上一直没有提到的是,那天上午,‘枪战之后,是本·托宾负责处理‘后事,把我们一起送回到干草山警务站。”[5]398“这是新闻媒体在未探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进行的武断报道,是一种不负责任、不计后果、职业操守缺失的表现。伪装成道德批判者,给纯善的人扣上邪恶的帽子,没有比这更卑劣的行为了。”[6]72本被判绞刑,他与命运的抗争宣告失败,但他不遗憾,因为迪兹走进了他的生活,爱他,永远纪念他。
结语:
丛林生活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丛林精神,《煤河》中所展现出来的丛林人物的独立精神,反抗精神和伙伴情谊是他们生活的真实体验。作者在颂扬坚韧、不屈的丛林精神的同时,揭露了以埃斯米为代表的海岸人的虚伪,批判了人性之恶。
参考文献:
[1]【澳】狄克逊·罗伯特.亚历克斯·米勒《煤河》:关于清白无辜、残酷制度的寓言[N].李尧,译.文艺报,2017(004):1-2.
[2]张加生.劳森短篇小说的丛林意象[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64-69.
[3]Schaffer,Kay. The Bush,Gend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stralian History[M].侯書芸,刘宗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张加生.澳大利亚“丛林神话”与“劳森神话”论析[J].国外文学,2017(02):51-58.
[5]亚历克斯·米勒 (Alex Miller). 煤河[M]. 李尧,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07(步客口袋书).
[6]颜丽蕊.奇幻的疗伤与追寻之旅——《微笑的狼》创伤叙事研究[J]. 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6):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