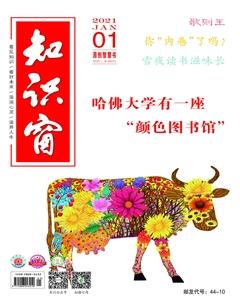彩色的葡萄
欧阳晨煜

我家附近有个古怪的字画城,之所以说它古怪,是因为它常年紧闭大门,似乎在保护和凝集着一种氛围,不肯外泄。它庞大而臃肿,漆着古色的红漆,格格不入地站在繁华的闹市,比邻时尚的商厦。
我多次路过这个拘谨的字画城,没有任何的吆喝声和流动的音乐,没有开放的态度和欢迎的趋势,它只是自顾自地维护着一种朱红色的典雅,好像小心翼翼地巩固着一种自尊。终于某天,我扣开了它的大门。牛皮色的光线充盈着整个字画市场,我像一张照片瞬间被冲洗进去,安静却饱满、典雅却茂盛是这张照片的背景。在目光从巨幅的牡丹、长卷的山水和黑白的书法丛中掠過时,一幅藏在角落里流光溢彩的葡萄彩墨画,载着几分魔幻的色彩牢牢地抓住了我。
准确地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彩色的葡萄,它们超越了生物属性自身的颜色,却无比真实。把想象之物变幻为亲眼看到之物,让人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这些彩色且大胆的葡萄,惊艳并光耀了这个古老的市场,它们截取了写意画最边缘的题材,却意外地改换了这种水果日常的颜色,在常识之外产生了奇异又抽象的感觉。
每一株葡萄的颜色都是异常丰富的,每一颗上都有细碎的光点,淋着奇妙的颜料。所有葡萄的色彩都是复合的,渐变的,有黄色向紫色的渐变,青色向橙色的推移,蓝色向紫色的转接,黄色向红色的过渡。这些颇具想象力的色彩相撞,溶解在大同小异的葡萄上,反而给了这一架葡萄明艳通透、波光粼粼的视觉效果。更惊人的是,由于近百颗葡萄的色彩均有差异,从状态来看,所有葡萄都似乎告别了静物的形式,转而都是动态的存在。
惊讶之余,我开始疑惑画家为何会将葡萄描绘为非常规的彩色,也不禁猜测如此大胆着墨用色的画家一定是位先锋前卫的年轻人。因此,我走进了这位画家的画室,去靠近那些在我眼里完全虚构的葡萄。在这问画室里,满墙都长满了这样奇幻的葡萄画,葡萄原始的张力在极其丰裕的色彩中一层层被逼开。可令我意外的是,这些葡萄的主人是一位70岁的老画家,而且在他眼里,葡萄彩墨画完完全全是带有回忆色彩的真实产物。
老画家出生在新疆,对于葡萄的描摹已有几十年的经验。他不仅对这种水果的形状、纹路等细节了如指掌,更将收集经验的重点放在了葡萄的颜色上,并选取了动态的、身临其境的观察角度和方法。长期观察后他发现,纯粹的紫色只是葡萄最广为人知的一瞬间,且葡萄与紫色对应的这种认知是凝练却不准确的,因此,依照陈旧经验所描摹出的葡萄便也是失真的、单一的。其实,许多童话般的斑斓色彩并不是出于想象,而是生物本身所呈现的自然色彩。
老画家告诉我,彩色才是葡萄最真实的颜色。他所画的葡萄都经历了非常细微的生长阶段,它们都处在成长之期,因此不会呈现出完全成熟后的浓郁紫色。多年的观察中,他记录着每个成长阶段的葡萄的色彩,这些成长阶段并非科学的严格划分,或者说,画中的葡萄成熟过程甚至比科学规定里的更细腻、更完整、更诗意。或许是青涩的葡萄第一次沐浴阳光,第二次糖分涌动,第三次历经雨季……在这些条件不同的阶段中,葡萄的情绪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记录这些不为人知的时刻和场合,是因为比起成熟期,众多葡萄成长阶段的色彩更生动、新鲜,值得观看。
小朋友问我:“我总是不能填满那四百字的稿纸,不是太长就是太短,怎么办?”“这样吧,”我回答,“不如把那四百字分为四个部分,一个部分一百字。”“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小朋友恼了。“不,不,我是正经的。”我说,“文章结构,总有起、承、转、合,刚好是四段。”“那不是太过刻板吗?”小朋友不服气道。“基本训练,总是刻板,所有基础,没有一样是有趣的。等到你成熟时,就会起变化。”我说。“怎样的变化?”小朋友问。“起、承、转、合,”我说,“可以变成合、转、承、起。或者任何一个秩序都行,只要言之有物。”
小朋友说:“我明白了。如果将‘转放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意外结局。”“你真聪明,一点就会。”我赞许。“那么每一段不必是一百字也行?”小朋友还想确定一下。“那是打个比喻。”我说,“先解决你写得太长或太短的疑问。”“但是,有时还患这个毛病呀!”小朋友说。“那么,你宁愿写长一点。修改时,左删右删,文字更是简洁。”我说。“有时不知道要写些什么才好。”小朋友说。“我也是一样呀。”我说,“所以要不停地观察人生,不断地把主题储藏起来。”“有了主题有时也写不出来呀!”小朋友说。“那么你先要坐下来,坐到你写得出来为止。这也是一种基本功,最枯燥了。写呀写呀,神来之笔就会出现。”我说。
小朋友不太相信,露出像我开始写的时候,不太相信前辈所讲的话时一样的表情,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