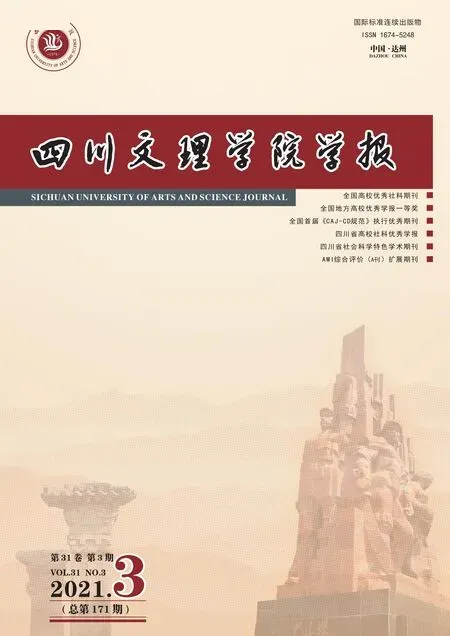“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建构与清王朝前期政治合法性塑造
——以《明史·流贼列传》为中心
刘欣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眉山分院,四川 眉山620010)
1633年-1644年,张献忠率军先后五次入川,与清军、明朝残军和地方武装势力交战,对四川造成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目前,关于“张献忠屠蜀”历史事件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①这有助于我们认清该事件的真相,但对其历史记忆②形成的分析却付之阙如。③官修史书对于“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启《明史》编纂工作。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明史》全书刊成,有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记载了张献忠屠蜀事件。然而,《明史》的记载却未必是真实的历史记忆,正如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所说,“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于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在清朝前期,④清政权面临政权认同等危机,急需利用各种手段塑造自身政治合法性,⑤而通过编修《明史》建构出特定的历史记忆,以影响时人的认知便是其中之一。《明史》如何建构“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清王朝塑造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如何影响这种建构?民间私修史书建构的“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如何与《明史》配合或竞争?这些问题值得探索。本文通过对《明史.流贼列传》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以期回答上述问题,并以此认识当时的政治、文化特点。
一、《明史.流贼列传》对“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的建构
(一)张献忠屠杀民众
《明史.流贼列传》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议兵并起,故献忠诛杀益毒。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2]3318如今已有学者对该数字的正确性提出质疑,⑥但无论如何,《明史》以此为后人留下了张献忠凶残的历史记忆。
张献忠对其下属也极其残暴。如“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2]3318
四川遭张献忠之乱后,“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2]3318
有学者指出,“儒学社会对王朝合法性现实层次上的需求,简单说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王朝是否能够建立或维护‘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的君主秩序;二是王朝是否能够做到敬德保民、从民所欲”。[3]在清朝前期,清廷采取了减免赋税、建立社仓制度等多种措施保障民生,恢复经济发展。如康熙终身注重蠲免钱粮,减轻民众负担,蠲免总数约达“一亿五千万两之多”。[4]46其以儒家民本思想作为施政关键,甚至将“爱民”总结为清王朝的“祖宗家法”。[4]47这些措施体现了清王朝的儒家民本思想,彰显了其在儒学社会中的合法性。而《明史.流贼列传》所书写的张献忠行为则与之相反,表明大西政权既不存在一个正常稳定的君臣关系,也不能“敬德保民、从民所欲”,从而否定其合法性。
(二)张献忠屠戮地方士人
《明史.流贼列传》描述了张献忠屠杀四川读书人的残忍行径:(张献忠)“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2]3318对于不肯合作的地方士人,“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而屈从于张献忠者也难逃一劫,“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以致编纂者感慨“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2]3318
这一叙事与清王朝缓和满汉矛盾,消解农民军抗清政治合法性,以争取汉族士人支持的现实需求有着密切关系。
清王朝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其在有着“夷夏之辨”观念的汉族士人前面临着民族和政权认同问题。明亡后,有部分汉族士人依附农民军抗清,在他们看来,“在与满清异族的夷夏之防面前,朝与贼的界限就不再是那么不可逾越的”。[5]此外,1647年1月张献忠阵亡后,大西军转战重庆继续抗清,同时全国各地不少农民武装力量也举起抗清大旗。⑦上述情形都迫使清王朝考虑如何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以稳固其统治。
尽管存在“夷夏之辨”,但“夷”与“夏”的区别并非绝对,“夷”可通过认同汉文化认同实现身份转变,正如大儒韩愈在《原道》中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据此,清王朝以开科举、修拜文庙、经筵日讲等多种形式表达其对汉族读书人和儒家的尊重,其中更是以敬拜文庙和经筵日讲等手段实现了集“治统”与儒家“道统”于统治者一身。
清王朝早在入关前便已开科举取士: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年)举行科举考试,录取二百多人,此后又于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1641年)开科取士,将大量汉族士人吸纳到政权中。这样既吸收了大量人才为国家所用,同时也能获得汉族读书人的支持。清军入关后,清廷掌权者多尔衮继续推行科举,以“笼络和收买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消除其反抗情绪”。[6]四川贡院毁于明末战乱,康熙四年(1665年),冀应熊请于四川布政使朗廷相、按察使李翀霄,向四川巡抚张德地申请改明蜀王府为贡院。“具题建修,倡捐有差,堂署号舍颇备前建,明远楼及贡院坊焕然一新,制称宏敞”。[7]贡院早日建成便可保证士子科考。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更是吸引了一大批汉族读书人。
由于文庙是孔子和儒学的一个象征,修建、敬拜文庙便成为统治者表达尊儒尊孔态度的一种方式,因而受到清统治者重视。早在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已在盛京建成文庙,祭祀孔子。入关后,顺治帝曾两次册封孔子;康熙帝多次亲诣山东文庙,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8]89雍正帝在其即位第一年即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作为“夷狄”的清统治者修建、敬拜文庙是向汉族士人昭示其对汉文化的认同,进而表明自己已成为华夏族一员以消解民族矛盾,甚至使原本由士人掌握的“道统”归入了统治者。[8]93
经筵日讲也是清帝尊儒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其掌握儒家“道统”的另一种方式。顺治十二年(1655年)四月,顺治帝开始举行经筵,但在顺治朝经筵日讲只流于形式。到了康熙时期,经筵日讲才真正成为帝王学习儒家经典一种方式,而康熙帝也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康熙帝逐步改造了讲课的形式,使经筵日讲不再是只由讲官进讲,而逐渐变为帝王与讲官互讲,最后成了帝王先讲、讲官后讲,结果使经筵讲官沦为帝王附庸,儒家“道统”从士人转移到了帝王手中,使清帝集“治统”与“道统”于一身。⑧
清王朝的上述措施伴随了《明史》编纂至刊发的全过程。《明史》建构了张献忠残酷屠戮四川科考士子的历史记忆,以此向天下读书人表明:与尊重读书人、儒家,掌握儒家“道统”的清王朝相比,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为无道,从而否认其合法性,同时也彰显了清军剿杀张献忠及入主中原的合法性。
(三)张献忠不得“天命”
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是中国传统王朝证明其政治合法性的方式之一,《明史.流贼列传》亦对此加以利用。
《明史.流贼列传》首先否定张献忠起兵的正当性。“破重庆,瑞王常浩遇害。是日,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献忠怒,发巨砲与天角”。[2]3318古人认为有雷而无云,预兆着臣下叛乱,国将易主。⑨史书将天无云而雷与张献忠杀瑞王朱常浩之事相联系,意指张献忠于明王朝而言是叛贼,从而否定其起兵合法性。此外,史书叙述张献忠以炮轰天的行为则表明其对天不敬,更不会受到天命眷顾。
《明史.流贼列传》也暗示张献忠被清军擒杀是天意。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率军出川北,“欲尽杀川兵”,川军统将刘进忠听闻后带兵而逃,投奔入川清军,为其引路。张献忠军“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2]3318若无大雾,张献忠或许能提前发觉清军,不至于“猝遇”。大雾似乎有意出现配合清军击杀张献忠,这暗示着天助清军,也就意味着“天命”眷顾清王朝而非张献忠,从而否定后者政权合法性。
二、私史与《明史》的配合与竞争
在清朝前期,读书人也通过修史以表达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对清王朝的态度。这些著作在“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方面,或与官修《明史》配合,或与之对抗。而清王朝为维护其政治合法性,对与《明史》不同的历史记忆加以压制。对此,笔者以《蜀碧》《罪惟录》为代表进行分析。⑩
(一)《蜀碧》——对《明史》的正面呼应
在私史中,从正面呼应《明史》的主要有彭遵泗的《蜀碧》等。私史与官史共同为时人建构起“张献忠屠蜀”的残酷历史记忆,塑造了清政权的合法性。
彭遵泗《蜀碧》著于其早年进入京城之时。彭端淑在后序中指出,该书意在将张献忠屠蜀之事“笔之于书,使后之君子得以考之,则死者可以无憾”。[9]该著初刻于乾隆十年(1745年),所引之书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五种,“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有史料”。[10]有学者认为该书真实性受人质疑,[11]笔者从话语分析角度看,无论内容是否失真,《蜀碧》在内容和叙述方式上与《明史.流贼列传》相似,否定了张献忠政权的正当性,肯定了清王朝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
《蜀碧》主要从两个方面叙述张献忠屠蜀的暴行:一是屠杀四川读书人。“贼诡云选举,用军令严催上道,不至者孥戮,并坐比邻。既集,令之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斩之”。[12]24二是以剖腹、矛刺等残忍方式屠杀普通百姓,连妇幼老弱亦不放过。如“一老人自扶杖出,见贼,絮语生平穷苦状,谓不能具主人礼。贼笑曰:‘若苦如此,何必更住世间?’杀之。”“贼杀所获妇女小儿。贼以妇女累人心,系令杀之。有孕者剖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火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12]27正因张献忠军残暴,不仅残明地方官员不肯降之,其亦不为四川百姓所接受。如大西军欲假扮官军袭击通江城,路上遇见一童子,便告诫之不要透露他们身份,“童子佯应之且走将及城门大呼曰:贼至矣!贼杀之”。“时邑人王廷辅妻阎氏闻贼入,遁深林中,被贼搜执,触树未死,骂贼,贼怒杀之”。[12]19这段记载颇为可疑,若张献忠部性情残暴,则很可能杀害童子以防其泄露他们的踪迹,而不会将他带至城下。尽管《蜀碧》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存疑,但该书通过对大西军暴行的大量细节描写,从而否定张献忠政权的合法性,这与《明史.流贼列传》相同。此外,书中也暗指张献忠等人不懂儒家之道,如张献忠部捉住士民祝丕传及其母,“欲杀其母,求以己代,不许;遂大骂,母子罹害”,[12]14杀害孝子体现着其对孝道的蔑视。
《蜀碧》在叙述清军入川诛杀张献忠经过时亦暗示清军得“天命”和人心。“王命导师疾行,至西充之凤凰山,会大雾,王潜勒军登山……王诇得之,挥铁骑促贼营。时方辰食,献衣飞蟒半臂,含饭,率牙将数十人仓皇出视。进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兰射之,一矢中其喉”。[12]30这段叙述可能是来源于《明史》,但比其有更多的细节描写,更好地体现了清军神勇,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大西军,而“大雾”似乎有意帮助之。此外,书中还记载:“献在成都,忽谓:‘今入厄运,三年中莫可支吾。独有遁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数载,可免耳。过此仍横行天下。’初欲入武当为道士,不果。伏诛时年四十一”。[12]31再次强调张献忠阵亡是天意。此外,书中也表现了四川民众对张献忠恨之入骨。清军捉住张献忠后,肃亲王豪格“乃按佩刀仰而祝天曰:‘献忠罪恶滔天,毒流万姓,予受天子命,奉行天诛,谨敢为百姓复仇。’祝讫,亲加刃于献,磔杀之”。[12]30-31说明清军入川目的在于奉天意诛杀祸乱四川的张献忠,为被其杀害的百姓复仇,实为“王者之师”。清军将张献忠尸体挂在军营大门,“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烂殆尽”,表明四川民众对张献忠的憎恨,从而说明清军入川正当性。而张献忠被擒后,部下投降,“四养子兵溃东走”,[12]31从侧面体现出清军对农民军的强大威慑力。
(二)《罪惟录》——不同于《明史》的历史记忆
持不同立场的史书对“张献忠屠蜀”的书写存在差异。王海洲认为,“社会记忆通过剔除意欲忘却的过去,以及加入并不存在或者故意歪曲的内容,以重建历史的现实意义,最终使得传统在一个社会的框架中得以延续并不断变迁。政治权力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有利于其统治的操作,但社会其他权力系统也能使用这种方式来实施抵抗”。[13]在《明史》成书之前,已有史家撰写“张献忠屠蜀”历史,其建构的历史记忆与《明史》大相径庭。反清的查继佐的《罪惟录》便是其中典型,其以此表达自己不认可清王朝的立场。
查继佐(1601-1676),浙江海宁人,字伊璜。清军南下时,其奔赴浙东参加抗清战争,在鲁王监国时又参加过保卫钱塘江的战斗。抗清失败后隐居在海宁,致力于明代史实的整理、书写。查继佐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写成《罪惟录》,并将自己的褒贬观点寓于其中。他在《罪惟录》中持反清立场,对“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的塑造也与《明史》《蜀碧》不同。其记载张献忠之死:“进忠导蓝旗固山反攻献忠,直抵西充县。献忠方巾被一枝梅直掇,猝骑,遇敌凤凰山,举弓睨北师左部,北师右部将亦睨射献忠,则献忠与左部将并倒”。作者以“北师”指称清军,不同于《明史》称“我兵”或《蜀碧》称“王”,表明了自己对清政权的态度。“献忠与左部将并倒”这个细节暗示了清军并非神勇无敌,其为击杀张献忠也付出了代价。这段描述也未体现清军击杀张献忠的是为百姓复仇的意义,也没有提大雾的影响,从而否定了《明史》叙述中所隐藏的清军得天命之意。此外,该书只写了张献忠杀戮官员和士人行径,而未提其杀害普通百姓。“围重庆四日,城破,瑞王阖宫被难,旧抚臣陈士奇死之。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陷成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悬榜试士,士争趋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挟策以死”。[14]该书写成后,“涉及大量为清廷所忌讳的史实,所以书成后无人敢付梓刊印发行”,[15]只能私下流传,直至193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结 语
明末清初时期,张献忠入川并建立大西政权,与残明军队、地方武装和清军作战,使四川饱受战火摧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为官修或私修史书所记载,成为影响后人认知的历史记忆。然而,历史记忆并非完全真实,其往往受现实需要影响。保罗·康纳顿指出:“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16]
清军入主中原之初,面临农民不断起义和汉族士人不认可等问题,遭遇政权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清朝开启了《明史》编纂工程,意图通过历史书写建构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方式之一就是通过阐述张献忠等人屠杀普通民众和读书人的残暴行径及其不得“天命”情形,在天下士人心中建构出张献忠残暴、清军乃王者之师的历史记忆。
学者指出,《明史》颁布之后,“有关明代的史事和定论已出,即使继续私家修史的工作,也仅仅是表示对官修《明史》的附和与赞同而已”。[17]私家修史对《明史》的附和与赞同,是部分士人主动将自己精神融入清王朝意识形态,认同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一种表现。如彭遵泗《蜀碧》虽意在讲述历史以供后人查考,与清廷编修《明史》目的不同,但内容则与之相近,与清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契合,代表了乾隆时期部分读书人对清王朝的认同态度。这部分私史与官史相呼应,共同建构起“张献忠屠蜀”的历史记忆,影响时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知——抗清的张献忠大西军残暴而清军仁义,从而塑造出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
另一方面,与《明史》内容不符的私史则长期受到压制。如在官修《明史》颁布前便已成书的《罪惟录》,由于持反清立场而不敢公开刊行。其所建构的与《明史》叙述不同的“张献忠屠蜀”便成为了历史记忆长河中一股暗流,这也使得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得到维护。
注释:
① 明末至民国时期,史家对张献忠多持否定态度,视之为“流寇”。新中国成立后,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下,史学界对张献忠的评价有所改变:肯定其农民起义领袖地位,同时贬抑他与李自成分裂及其曾被明王朝招降的行为,讳言其“屠蜀”之事。1980年代后,一些权威研究者又为张献忠“屠蜀”翻案。如今,不少学者对张献忠及其屠蜀认识趋于客观,如李映发在《张献忠其人与杀人》(《寻根》2010年03期)指出《明史》等史料对张献忠屠蜀有所夸张。与之同名的学者张献忠亦在《“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指出,明末清初时期造成四川人口减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张献忠屠杀外,还有明军、清军、地方武装、农民军以及降清后复叛的吴三桂在四川的烧杀及瘟疫,而清廷为了打造自身合法性,极力将屠蜀责任归在张献忠身上。此外,一些学者对张献忠屠蜀人数也提出质疑,如冯广宏《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文史杂志》2009年06期)等。
② 关于“历史记忆”的概念,本文参照赵世瑜教授的定义。赵世瑜教授认为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 or memory for the past)“指个人或集体对过去的记忆”,参见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 20 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76页。
③ 苏循波《清修〈明史〉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求索》2013年第3期)分析了清王朝在《明史》中通过四种方式塑造自身合法性:以“天命观”诠释清王朝合法性,言宦官之恶揭示出明清易代的必然性,隐匿某些史实以美化清王朝,诋毁农民起义。但未具体分析《明史》如何“诋毁农民起义”。
④ 本文所提的“清朝前期”参考冯尔康教授的划分标准,即“入关以前是开国时期,顺、康、雍以及乾隆前二十三年为前期,乾隆十四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为中期,下余的时期为后期”。参见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55页。
⑤ 本文所提“政治合法性”概念,参考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就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
⑥ 参见冯广宏《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文史杂志》2009年06期)等。
⑦ 如1647年春广东陈邦彦等人举兵;1647倪安东,韶州瑶族人民抗清;1648年春浙江东部四明山大岚山寨起义,浙江农民的抗清斗争,到1655年还有金华地区的东阳县农民数千人等;1648年,山东榆园农民起义,坚持到1651年,鲁东农民军坚持到1662年。具体可参见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⑧ 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异变》(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⑨ 如《太平御览》:“《汉书》曰:武帝征和四年,天清晏无云,有雷,声闻四百里。至后年,侍中莽何罗反”。
⑩ 清代记载“张献忠屠蜀”事件的私人史学著作主要有: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蜀龟鉴》,冯甦《见闻随笔》,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欧阳直《蜀警录》,沈荀蔚《蜀难叙略》,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及孙錤《蜀破镜》等。笔者选择《蜀碧》为代表,原因有二:一是该书是在《明史》颁布后公开刊刻,在内容上呼应官方《明史》;二是作者生长在雍乾盛世且仕清,这一背景更能体现彭遵泗等读书人通过怎样的历史书写表达其对清王朝的认同。选择《罪惟录》为代表的原因是:其一,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将褒贬寓于其中,尤能反映查继佐等反清士人的政治态度;其二,该书是查继佐经历“明史案”后所著,能反映清代前期,在朝廷严厉的文化政策之下,反清士人的历史著作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