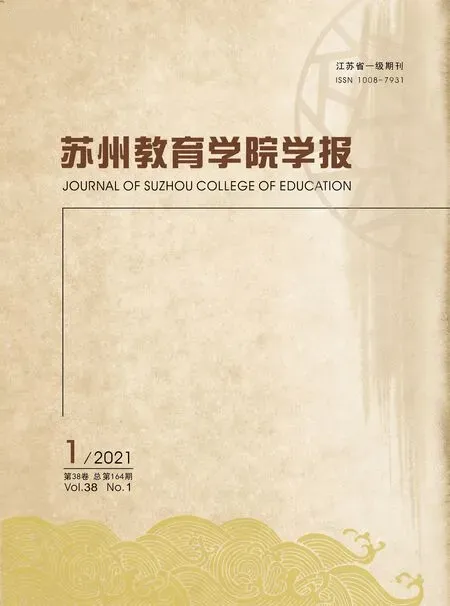中国青春电影的新路径—评《少年的你》
邢玉茹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中逐渐明晰的类型电影,青春电影主要“以青年人、青年心理、青年问题等为题材,反映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关注每个人由少年走向成年之间的过渡时期独有的生命体验,以青年文化性为鲜明特点”[1]。青春电影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在经历了革命与激情、集体主义、反思与伤痕、成长与困惑的青春话语表达后,21世纪以来,开始向迎合大众审美的怀旧、狂欢话语转变。
2013年,赵薇执导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后票房高达7.26亿,在电影市场掀起一股怀旧热潮。自此,青春电影势如破竹:《青春派》(2013)、《前任攻略》(2014)、《同桌的你》(2014)、《匆匆那年》(2014)、《左耳》(2015)、《栀子花开》(2015)、《睡在我上铺的兄弟》(2016)、《我们的十年》(2016)、《乘风破浪》(2017)、《后来的我们》(2018)……火爆的IP、类似的故事,使青春电影蒙上了一层俗套的怀旧面纱,限制了观众对青春的想象。仅仅五年时间,怀旧青春电影就从爆发式增长陷入口碑转向、票房锐减的局面。在中国电影事业产业化升级的重要时刻,青春电影如何走出审美疲软期,构建全新的青春电影话语体系,迫在眉睫。
《七月与安生》(2016)、《悲伤逆流成河》(2018)、《狗十三》(2018)、《过春天》(2019)已经在尝试打破青春电影的固有审美:七月和安生代表个体成长中的两种精神撕扯;易遥成为校园霸凌受害者的银幕代表形象;少女与狗表现了青少年被迫成长的冷峻;单亲家庭女孩佩佩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可以看出,电影从业者已经开始探寻新的青春电影创作路径,但因电影本身的完成度、传播度、票房、口碑等原因,还未找到成熟的方向。直到2019年,曾国祥执导的《少年的你》一经上映,口碑爆棚,最终票房15.58亿,并登陆北美院线,成为现象级影片。《少年的你》颠覆了青春电影的怀旧印象,自觉回归现实主义土壤,以平等、尊重的眼光观察青少年,在青少年群体参与的社会实践中洞悉其真实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于社会议题中展开青春、成长叙事,与充斥怀旧意味的过往的青春片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质,为中国青春电影新路径的探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一、打破怀旧滤镜,直面社会问题
2010年以后,青春电影逐步趋同,多“以青少年的青春成长经历,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春校园为故事背景,以80后一代成长的共同经历为故事基础,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与生活经历,唤起一代人集体的青春记忆”[2]。《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电影开头的迎新横幅、社团招新活动一下子就将观众带入了校园的青春氛围中;《同桌的你》中,林一为保护同桌周小栀而打架、两人在课堂上偷偷递糖等情节,细腻地完成了观众“对号入座”式的观影;《匆匆那年》中,方茴面对感情的变质,一句“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赚足了观众的眼泪。怀旧本没有错,它是缅怀青春的重要方式,但内容雷同、情节俗套的怀旧影片扎堆上映,直接消耗了观众的青春记忆,在获得短暂共鸣后,影片就只剩下故事的躯壳了。
《少年的你》不再执著于以当下的视角去追溯过去的青春,表现挽歌式、追忆式的美感,而是坚定地打破了怀旧滤镜,在反怀旧的叙述中讲述社会热点问题,在拟真化场景中表达青少年的现实焦虑。近年来,校园霸凌事件不断曝光:2012年广州清远县某学校4名女学生群殴插班生;2013年昆明女大学生徐婷婷被11名男生虐待;2013年浙江一小学男生被4名同学囚禁;2017年15岁学生张超凡被同学殴打致死……透过“群殴”“虐待”等字眼,我们足以窥见校园霸凌的残暴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基于此,社会各界应当行动起来,全力解决校园霸凌问题。2018年,落落执导的《悲伤逆流成河》率先在电影领域触及校园霸凌话题,主角易遥被霸凌的遭遇令观众痛惜。但影片将校园霸凌和三角恋糅合,电影虽然“好看”了,但霸凌主题的纵深感被明显削弱了。而《少年的你》则更加严肃,它采取跨类型的呈现方式,将尖锐的社会现实题材与青少年校园成长叙事结合起来,客观叙述了校园霸凌的普遍性、残暴性和无逻辑性。首先,女主角陈念被欺凌的场所并不局限于教室,还有楼梯、排球场、厕所甚至是校外,魏莱肆无忌惮霸凌的背后,站着一个个冷漠、恐惧的人,椅子上的脏水、迎头砸来的排球、故意推搡的魔掌……这些行为总是在嬉笑或漠视中毫无阻碍地完成,陈念的隐忍不止是自身性格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周围人冰冷的态度。可以说,旁观者的冷漠加剧了校园霸凌的普遍性。其次,虽然电影尽可能地规避了血腥场面,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其中多种霸凌形式的呈现窥见其残暴性,看到陈念所经历的言语、肉体、社交和网络霸凌。电影始终没有正面交代魏莱等人欺凌胡小蝶、陈念的原因,胡小蝶跳楼自杀后,陈念心疼地将自己的校服盖在她身上,自此,陈念就变成了下一个胡小蝶,各种打着恶作剧的幌子,实则有意图的攻击行为接连不断,这种无逻辑的恶,增加了青少年校园霸凌研究的社会学意义,霸凌动机、霸凌对象选择背后的逻辑,值得社会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的你》中几乎没有出现关于陈念被霸凌的新闻报道,而仅将之作为社会现象去展现,电影尽可能地降低了校园霸凌的新闻性和奇观性,凸显其社会性和恒久性,这是电影在直面社会命题时应有的姿态。
二、跳出成长怪圈,聚焦精神成长
青春电影的“核心母题一定是成长,是人从孩童过渡到成人的整个阶段中对自我的认知、认同,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第一次交锋而引发的叛逆、冲突、调整、妥协与融合,以及对爱与生命的裂变式思考和体验”[3]。
“成长”是一个动态命题,根据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青春电影对“成长”的表达也会不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桃花泣血记》(1931)、《歌女红牡丹》(1931)、《青年进行曲》(1937)等影片中的青春男女,是中国电影史上较早出现的青年形象,在当时社会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影片主要传播进步思想,是彷徨、苦闷青年的一剂良药,这一时期电影中的青年形象代表的是群体,而非个人,青年人的成长就是抵抗侵略、冲破封建礼教束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春电影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在政治的框架下叙述青年人由个体走向集体、坚定革命理想的过程,是表现“成长”的主要方式,如《小兵张嘎》(1963)、《英雄儿女》(1964)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青春电影的转折期。20世纪70年代,中国时局尚不稳定,关于青春的叙述仍旧表现为政治青春,但自20世纪80年代始,文艺工作走向了正轨,电影得到了多元发展,以青年人的视角窥探历史创痛、讲述校园故事,成为这一时期电影的主流表达,如《庐山恋》(1980)、《豆蔻年华》(1989)等。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正式进入转型期,这时候的青春电影中出现了一批充满个性的青年人,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坚守自我、追求价值,是这一时期电影表现“成长”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青春电影的个性化表达更加明显,多真切地以青年人为中心,表现其叛逆、困惑,探索他们与自我、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头发乱了》(1994)、《周末情人》(1995)、《小武》(1998)等,都昭示了青春电影的成长叙述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集体化、个性统一化已成为历史,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认同成为新的方向。
21世纪后,伴随着商业发展,青春电影追求市场、迎合经济,逐渐由叛逆青春走向了一条以怀旧为主,掺杂暴力、狂欢的“青春”的道路,且愈演愈烈,使得“成长”的表达落空,“‘成长’已被彻底抹除了仪式及终极价值”[4]。近年来的青春电影,对于成长的理解和表述都过于狭隘,成长主题被限制在青春的爱情体悟中,一般以精练的对话或旁白作为成长的标志。如《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说:“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后来的我们》中,分开多年后再相遇的林见清和方小晓,面对错过的青春,以一句“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来告别青春。同时,也有部分电影借主人公的过激行为来表现成长,《前任攻略》中孟云和林佳分手后,一个在最繁华的广场上扮演至尊宝直至被警察带走,一个狂吃芒果导致过敏被送往医院,影片以充满狂欢性质的青春告别仪式狭隘地定义了“成长”。除此之外,有的电影甚至忽视、抗拒成长,《左耳》始终聚焦几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通过车祸、打架、偷情等情节传输“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的信息,而影片对成长的观照却几乎没有;《重返二十岁》(2015)、《二十八岁未成年》(2016)等影片则以主人公穿越回青春时期的情节,来彰显青春无敌的主题,但实际上,从侧面表现了年轻人对当下生活的无力感,本质上是对成长的抗拒与不满。
《少年的你》则跳出了近年来青春片设置的成长怪圈,没有形式化、瞬时性的成长,真正关注了青少年的精神成长。影片中,高考和成年并不是少年长大成人的标志,理解责任的终极意义、善意地回馈社会等精神层面的裂变式升华,才是少年成长的真正标志和价值。这一成长叙事的变奏,弥补了怀旧青春电影所造成的成长母题的断裂。
首先,饱受欺凌的陈念和孤身一人的小北互相取暖,在陈念失手导致魏莱死亡后,小北毅然决定顶罪,牺牲自我去拯救对方,这是两人情感的顶点,但也充分暴露了青少年对法律和责任的浅薄认知。顶罪入狱和负罪前行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其结果也是小北和陈念无法承受的—前者直面死亡,后者将永远堕入愧疚的黑暗中。警察郑易是他们精神救赎的助力,郑易谎称小北被判死刑,击破了陈念最后的心理防线,真相昭然若揭,两人也从畸形的顶罪、救赎圈套中解脱出来。此时电影如果停留在这里,少年则有被动成长的嫌疑,并没有完成自我认知的救赎。实际上,影片最后运用光影技术,将两人在看守所四目相对时的面部特写重合,陈念和小北从最初的错愕、痛哭,再到坦然相惜,哭戏层层递进,情感步步贴合,预示着两人将共同承担法律的制裁,正如最后在警车上超越时空的灵魂对话—“你怕吗?”“以前有点,现在不那么怕了。”“你呢?”“以前不怕,现在有点。”陈念从畏惧、愧疚到勇敢面对,小北从冲动、莽撞到开始思考,不同的心理变化昭示着相同的精神成长。
其次,陈念和小北出狱后的镜头处理,也暗示了电影对青少年成长问题的认知。在电影结尾,小北一如既往地保护陈念,而陈念则保护着独自回家的小女孩。陈念从学生时代的漠视、恐惧,到反抗、憎恨,再到成年之后的释怀,可以说,她完成了与自我的真正和解。
《少年的你》点燃了“成长”在青春叙事中的光亮,将落空的“成长”复原到原有的位置,直面了社会议题和青少年的精神困境,以其当下性和经典性,实现了成长主题的逆风飞翔。值得注意的是,《少年的你》的成功,是整个文化语境和电影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之前,《嘉年华》(2017)、《过春天》(2019)、《阳台上》(2019)等已经开始指引出中国青春电影的新方向—将“青春”放在社会问题的语境下检验。但这些电影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官方话语的影响,叛逆边缘的少男少女最终都回归到主流认可的轨道,带有社会规训和教育的意味。《少年的你》吸取经验,努力避免主流话语的干涉,虽然在陈念和小北的成长道路上不乏引路人,但影片极力呈现的是青少年与自我的精神和解,进而达到与社会的和解,规训意味大大减少,这是《少年的你》的突破和独特之处。
三、解构群像模式,塑造典型人物
“每个青春电影里都有一个女神一个傻白甜和一个胖子。”[5]这句话精准概括了21世纪以来,青春电影中人物设定趋同化的特点。在怀旧氛围下,描摹出校园集体生活中的人物群像—围绕在男女主人公周围的同学—他们性格相仿,人物设定类似,扮演着“助攻”或“情敌”的角色,常常成为电影中的第二条情感副线,这几乎是青春电影默认的叙事结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助攻”角色老张,“情敌”角色许开阳,情感副线阮莞和赵世永;《匆匆那年》中的“情敌”角色乔燃,情感副线林嘉茉和赵烨。不同电影中定位相同的人物具有互通性,固化的人物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观众审美的疲劳和电影艺术水准的下降。
作为一部多元素的青春电影,《少年的你》大胆解构了青春电影惯用的群像模式,影片中的人物具有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是情节发展的叙述动力,更是电影主题的表现载体。影片对于校园霸凌主题的理解,渗透到了每一个人物的身上。
首先,电影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外,还刻意突出了两个人物—李想和徐渺。李想善良并能保护自己,是电影中的边界性人物,既不是欺负陈念的霸凌一方,也不是保护陈念的正义一方;徐渺本性不坏,但胆小懦弱,没有能力对抗霸凌,因而站到了施暴者一方。这客观揭露了“施暴者—受害者”之间的矛盾转换关系。可以说,李想和徐渺是旁观者和隐形受害者的典型代表,是校园霸凌中不可忽略的人群。
其次,《少年的你》也将视点横向化,通过父母、警察和班主任几个人物,触及了家庭伤痕、社会伤痕。电影中关于父母的镜头并不丰富,但足以构成一幅病态家庭的浮世绘,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其家庭都是扭曲、残缺的。校园欺凌的带头者魏莱,是胡小蝶自杀的元凶,但她毫无悔改之意。电影通过警察的调查,将魏莱的家庭情况展现给观众,在知道魏莱的所作所为后,其母亲对警察说:“我们家孩子不会暴力对待别人的……那个自杀的孩子或许是因为家庭教育不行,玻璃心,同学和她开几句玩笑,就受不了跳楼自杀了。”面对鲜活生命的消失,魏莱妈妈仍在一味护短,连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同理心都没有,她的冷漠自私在短短两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魏莱家庭的扭曲远不止母亲,父亲因为魏莱复读的事情,一年没和她说话,在这种溺爱、高压、自私的家庭环境下,魏莱形成了表面乖巧、实则乖张的性格。施暴者罗婷的家庭同样如此,其父母在电影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他们来学校为罗婷求情,父亲对她拳打脚踢,母亲跪地哭泣;第二次是罗婷背着醉酒的父亲。简短但充满张力的画面将其父母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罗婷生活在充斥着懦弱、暴力、酗酒的家庭中,父母虽没有缺失,但父爱、母爱却实实在在地缺失了。再反观受害者陈念的家庭,一方面,父亲缺位,母亲因欠债东躲西藏,更谈不上对她的关心,增加了陈念被霸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残缺的家庭使陈念比同龄人更加懂事,她行事孤僻,遇事隐忍,面对困难,她始终坚信只要熬过高考就能仰望星空,但以“熬”制暴的被动策略反而进一步助长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班主任和警察的角色,则精准抓住了现实中治理校园霸凌的一体两面,即担负惩治、管理责任的校园层面、社会层面。电影中的班主任没有明确的姓名,无名状态象征了学校在处理校园霸凌事件时的温和、模糊态度。当警察介入调查时,校方对陈念施加压力,企图将霸凌淡化为普通冲突。当陈念勇敢坦白后,学校开除了班主任,并尽可能地在学校内部处理问题。班主任离职时对陈念意味深长的凝望,显影了校方在校园霸凌事件中的尴尬境地,面对家长和社会的考核、问责,温和、模糊的处理方式对校方来说是“稳妥”的,但绝不是恰当的。警察郑易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社会对校园霸凌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他年轻热血,希望拯救跌进泥潭的陈念;但另一方面,郑易这一形象也揭露了霸凌事件中“无法可依”的现象,霸凌者多是未成年人,因而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在陈念向郑易坦露被霸凌的经历后,魏莱等人仅仅只受到了停课警告的处罚。
《少年的你》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一步步揭开校园伤痕、家庭伤痕和社会伤痕,使观众在沉浸式观影中无限接近真实的校园霸凌,对陈念生产生同理心,并通过小北的形象完成了情感的共鸣和期许。小北是在情感与法律的悖论语境中被塑造出的有所指涉的人物形象,包含着底层人物的悲剧性、英雄主义和侠义心肠;但同时,他的顶罪行为又与法律的权威性相悖。在情与法之中,小北选择了“情”,甘愿坐牢也要让陈念走出逼仄的阴沟,这使得观众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悖论中,对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小北—产生了共情和拯救欲望,形成对解决校园霸凌现象的集体观照,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交互机制,以推动社会命题的解决。
对比相同题材的《悲伤逆流成河》,《少年的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具有现实性和经典性,它的每一个人物都倾注了导演对校园霸凌的深刻思考,不仅塑造了施暴者和受虐者,也考虑到了隐形受害者、学校责任人和社会救助者等相关人物,这对现实事件的处理具有重大参考意义。而《悲伤逆流成河》则将重点放在了情感纠葛上。可以说,《悲伤逆流成河》敲开了关注校园霸凌的窗口,而《少年的你》则推开了这扇门,它以不同层面的人物,多维度展现了校园霸凌形成的社会生态,在探索其频发原因的同时,也大胆、客观地直面校园霸凌治理的挑战,影片中的警察郑易的名字谐音“正义”,他以坚决的执著和勇气,帮助陈念和小北完成了自我救赎,显示了社会和国家对于校园霸凌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坚定的治理决心。
四、结语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称:“去年一部关于校园霸凌的电影《少年的你》,将校园霸凌问题再次拉入大众视野。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校园霸凌话题依然是代表委员关心的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建议,“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单独立法……制定校园霸凌专项法律法规要更加细化惩治‘量’的标准”。[6]《少年的你》兼顾审美愉悦和社会效应,充分发挥了电影的文化传播力,为中国青春电影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青春电影不应一味逃避现实,只关注怀旧和狂欢,而应从促进青年发展、社会进步的角度积极探索全新的青春话语体系,探讨社会变迁中青年人的社会学意义,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青年、塑造青年,追问青春成长的本质和价值,助力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