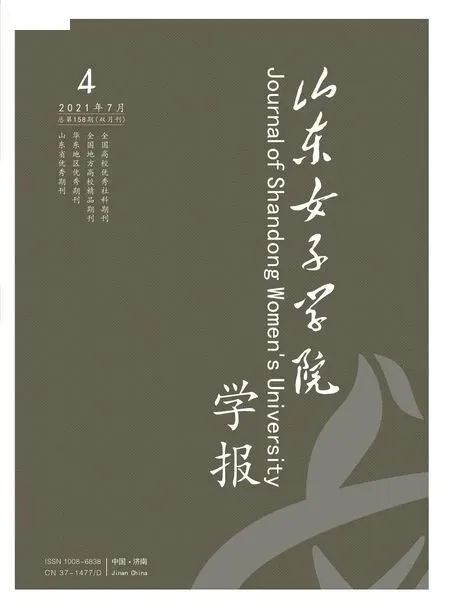从《妇女共鸣》看民国女性对1931年国民会议代表权的争取
刘人锋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410004)
1931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国民会议。按照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妇女团体没有单独获得代表名额,因此女界掀起了一场争取代表权的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以后女子参政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妇女共鸣》不仅积极为妇女团体争取参加国民会议的权利,而且作为当时主要的妇女刊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女界的争权运动,但是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对这次女性争取国民会议代表权的运动关注较少,较重要的是汪澎澜[1]考察了当时运动的概况。本文在仔细研读《妇女共鸣》的基础上,研究了当时女性争取国民会议代表权的言论及行动,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
一、《妇女共鸣》概况
《妇女共鸣》由妇女团体妇女共鸣社创办。1929年1月由陈逸云、李峙山、傅岩、王孝英、谈社英、徐元璞、舒蕙桢等发起的妇女共鸣社成立于上海,是一个以促进妇女文化为主旨的团体,“以出版刊物,提高妇女知识,纠正妇女思想为宗旨”[2]。
1929年3月25日,《妇女共鸣》创刊,该刊物“不取社长制委员制等名目,惟以实际负责人主持其事,设经理及总编辑,负责一切行政及编辑事务,社员人人以社务为己任”[2],刊物的经理与总编辑,多由社员担任,其中以李峙山、谈社英二人负责的时间较长。随着1930年冬妇女共鸣社迁往南京,《妇女共鸣》从1931年1月第39期起也迁往南京出版。
为什么刊物取名“共鸣”?对此,《妇女共鸣》特意多次解释:“就是希望觉悟的姊妹们共同起来为我二万万妇女鸣不平的意思”[3]。“一方面代表妇女界之痛苦压迫而鸣,一方面予受压迫而痛苦之妇女自鸣之机会。”[4]其不仅要积极为破除对妇女的不平而发出呼声,也要让妇女自己发出呼唤公平的声音。
在创刊号上,《妇女共鸣》刊登了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倡导者郑毓秀写的《发刊词》,阐述了《妇女共鸣》创办的原因,“自女权勃兴,乍言解放,自由平等,误解殊多。甚或矫枉过正,逾越范围,未获新知,已失故步;且于应享权利,反多忽视,兴言及此,能不慨然”[5]。先知先觉的妇女运动倡导者们认为,改变这种状况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且认识到女性欲求平等,知识尤其重要,因而创办《妇女共鸣》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增加女性的知识储备。
妇女共鸣的社员多为从事妇女运动的中坚分子,该社在推进文化、出版刊物以外,对于一切妇女运动都积极参加,如国民会议、救济水灾、提倡国货、废娼运动、法律平等运动等,《妇女共鸣》都予以大声疾呼,以期唤起妇女界及国人的注意,而且还联合各团体发起实际的妇女运动。《妇女共鸣》获得了良好的办刊效果,当时许多青年读者来函,感谢《妇女共鸣》给他们精神的鼓励和指导。如1931年春,临时国民代表大会妇女要求增加妇女名额;1933年春,妇女界要求立法院修改刑法运动;1935年冬,妇女界争取代表名额,发起妇女国民代表竞选会;1938年,妇女要求有国民参政会的名额;抗日战争时期宣传妇女服务工作等,都是由于《妇女共鸣》的提倡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与其他妇女刊物相比,《妇女共鸣》刊物创办的时间相对较长,直到1944年,“说者谓自有妇女运动而后,所有各种妇女自立经营而能延续至数年悠久之刊物,殆以《妇女共鸣》为第一”[2],其不仅为社会所称许,当时国民政府宣传部立案时,也将《妇女共鸣》作为为妇女界唯一的刊物,可见民间和政府都重视该刊,《妇女共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妇女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积极争取国民会议参与权
1930年11月,国民党四中全会确定于1931年5月举行国民会议,立即引起女界的关注,谈社英表示,“吾人所应注意者,即将来代表之产生法,以及代表之人数”[6]。根据司法院长王宠惠的解释“国民会议乃为解决目前建设中国之重大问题”[6],谈社英告诫“女界欲求贯澈男女地位平等主张,固不能不以全神注之,全力赴之,一方面争应享之权利,一方面以尽应尽之义务”[6],不要疏忽,不要放弃,要未雨绸缪,尽早准备。同时,谈社英对国民政府寄予希望,认为“当此一切不分性别时代,逆料国民会议之代表,必可尽量容纳女子,绝不至仍有以男子为中心之误,顾名思义,正不能专以男子为国民也”[6]。
但是,鉴于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只有两三个女代表,谈社英提示,如果“未能真正公平分配男女代表,则女界亟应起而奋争,万不可静默退让,或熟视无睹,以为不干己事,放弃国民之权利与责任”[6],如果放弃,那么不仅是女界的羞耻,也是女子作为国民的罪行,因为女子作为半数国民放弃责任,那么国民会议就不是全体国民的会议,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钱燕书也认为,“若女界噤若寒蝉,不加纠正,是放弃职责”[6],因为国民党的党纲规定男女平等的原则,女子从职责上讲有争取代表权的义务。
关于女子要求参加国民会议的目的,莫祥之认为,“妇女解放问题,非单纯的嘉惠妇女问题,其直接间接实促进社会及民族之进化”[7],原因在于女子占总人数的一半,“妇女问题如不得适当的解决,即社会问题不得适当的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得适当的解决,社会即不能作健全的发展,民族亦不能为健全的进化”[7],所以女子争取国民会议代表权从表面看是妇女解放的要求,从长远看并非单纯的妇女解放运动,而是促进社会的进步。
除了在《妇女共鸣》发表言论,莫祥之还写信给胡汉民,强调国民会议是全体国民的会议,女子居国民之半,可是“代表选举法中既无妇女团体选举代表之明文,而就过去会议选举之经验,绝无女子参加之地位”,假使在整个国民会议中,并无女代表参加或者仅有几个女代表,“不将成为畸形的国民会议乎。如此现象,殊非本党高唱助进女权之发展政策所应有也”[8]。
钱燕书从女子自身利益出发阐明女界为什么要求国民会议代表权,她指出,“妇女本身之利害,惟妇女本身知之最切,认之较真”[9],约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有关女子的利益若不定诸约法难以确定,而国民会议将讨论约法,所以女子必须参加讨论。而且,“各省妇女团体对于女界痛苦,既素有研究,本共同之目的,以改善妇女之生活,发展社会之事业”[9],这是目前女界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女界争取参加国民会议的原因。
虽然女界积极争取选举权,要求规定女子参加国民会议的人数,但是根据情势,专门规定女子参加的人数难以做到,可以“舍弃团体运动而为各个运动”[10]。既然国民会议规定参加的团体没有性别的限制,那么只要这些团体内有女子,女子就有参加国民会议的希望,而这些团体中最有希望的就是国民党、教育会及国立立案大学,因为这些团体中易有女性成员,女界在“国民党及教育会国立立案大学选举代表时,注意运动,庶可得若干名额”[10],但是,如果不重视在这些团体内争取代表名额,女界参加国民会议的希望就很小。
与谈社英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女子在其他团体中被选为代表不同,金石音坚决认为选举法应该把妇女团体加进去,原因是“妇女在各界里,正当萌芽的时代,势力微弱岂有地位可言?岂有被选之希望?”[11]如果不把妇女团体加进去,那么名义上各界代表能包括男女两者,实际上却不能包括,而“国民会议乃国民自决其命运的会议,不是请人来包办的会议,国民会议又系实事求是的会议,而非徒有其表的具文”[11],既然是国民自决其命运的实事求是的会议,就应着重实际,把妇女团体也加进去。另外,由于妇女长期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正在谋求解放,因此在与男子有同样的需要之外,尚有其特殊的需要,所以,“第一男子不应代表妇女之需要,第二男子不能代表妇女之需要”[11],为了充分表现全体国民的需要,唯有于一般规定之外,特别列入妇女团体。
与金石音的观点类似,青萍指出,“中华民国的主权,不是属于任何一人或某部分人的,而是属于全体国民的”[12],只要一个人在国民的资格上没有缺陷,便是中华民国的主人,这是不分性别的,可是《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所规定的有选举权的团体中唯独没有妇女团体。虽然在孙中山的遗教中,对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没有明文规定,然而正如胡汉民所说:“因为时迁事异,有些团体根本没有存在了,于是不能不有小小的出入,可是实际上并不与总理的遗志相背”[12]。照此说来,“加上妇女团体也仅是小小的出入,实际上一样不与总理遗志相背了”[12]。
虽然女界积极努力,但是国民会议“五百余人中,寥寥十余女子,不及百分之三,且此十余女子中,又有大半列席无表决权”[13]。尽管如此,女界仍未放弃,在国民会议即将召开之际,谈社英希望,“全场代表能具平等观念,远大眼光,以女界问题为整个国民问题,毋存不足重轻或儿戏视之之观念,至女界所提之议案,自皆有切身利害或与社会有关系者,固希望能完全通过也”[14]。如果占人口半数的女子的地位权利不能健全,也就是全体国民的地位权利不能健全,国民会议是解决国家大事国民痛苦的会议,如果不能解决女子的痛苦,国民会议也就不是为全体国民谋幸福的会议。
为了在国民会议上能够发出女子的呼声,《妇女共鸣》组织女界提了很多提案,例如严禁缠足、修正民法亲属编,修正刑法及娶妾以重婚罪论等,谈社英特意撰文提出希望国民政府重视女界的提案,“设此次提案视为无足轻重,随意置之,不予执行,则不特有乖中央召集国议之旨,亦无以副总理主张开国民会议以适应国民需要之遗训”[15]。女界之所以争取规定妇女出席代表名额,固然是为了表明国民身份,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要解决女子问题,当然,政府执行提案是尽义务,女界也负督促执行的责任,不能交了提案就了事。
三、质疑选举法及相关言论
1931年元旦,《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公布,其中规定各地方代表按照定额由下列团体选出,“甲、农会,乙、工会,丙、商会及实业团体,丁、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之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戊、中国国民党所谓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以依法设立者为限,其实业团体与自由职业团体之资格另定之”[16]。该法公布后,妇女团体如京市妇女救济会、中华女子参政会,要求政府明令规定妇女团体参加代表选举权与定额,以符合国民党男女在政治上平等地位的主张。
但是胡汉民在立法院发表演讲《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表示“总理之规定,不能更易,以倘有变更,必多纠葛”[17]。那么孙中山有什么规定呢?“参加国民会议之代表,应由现代一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选出”[17]。谈社英认为,“总理主张开国民会议时,尚为军阀时代,彼时妇女运动,销沈已极,初无几许妇女团体存在,当时,总理以就现状而言,故无妇女团体而有‘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之规定。现今情势既异,所有‘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一条,已不适用于此次,而有所变更,则未列规定之妇女团体,又何尝不能加入”[17]。胡汉民在讲演中说:“总理要开的,乃至我们想召集的国民会议,是在各地方脱了军阀的淫威和压迫,使人民真正能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时的国民会议,过去会议之艰于召集,总因是由于军阀的迭起叛乱,如果贸然召集,那我们所召集的一定是军阀政客以及流氓的分赃会议,而决不是国民会议,这样我们到战乱敉平国势大定的今年,才实行召集,实在是适合总理(尤须于最短期间内促其实现)的遗教。”[17]谈社英认为这段话正可作为增加妇女团体的反证,因为国民会议本来就是为采纳国民的意见来解决国家的问题,需要适合时代的情势,便于人民的要求,既然代表资格的第八条“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因为不适于当时的情况而更改,那么现在也可以根据形势加上妇女团体,“当时实况,各地鲜有可以参加之妇女团体,是以总理未加规定,断不能昔日未加规定,今日即不能参加,倘竟拘牵文字,不重意思,试问‘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之资格,现今究竟能承认之否?”[17]因此国民会议选举中加入妇女团体,不是违反孙中山的遗教,而是遵守,如果孙中山不重视解决妇女问题,又怎么会有种种男女平等的规定呢?
谭汉侠则直接质疑《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她认为此次采取的选举方法以职业为原则,表面看来很公平,没有对女性的歧视,“然不知社会的实况,妇女能够参加各种职业团体的人,究有几个?假使偶有一二能够参加各职业的团体,而有此被选举希望的人,又究有几个?”[18]这是有名无实的男女平等,既不能与男女平等的原则相符,也不能体现“国民”二字。
从法律上讲,1930年7月17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第一节《人民团体之分类》规定:“本案所称之人民团体,除地方自治团体另有规定外,分为职业团体,及社会团体两种:一、职业团体:如农会,商会,工会,工商同业公会等。二、社会团体:如学生团体,妇女团体”[18]。由此可见,国民党完全承认妇女团体是一种合法的正式人民团体,既然承认为合法的正式团体,那么妇女团体应当取得法律上的权利地位,也允许选出代表。至于说妇女团体并非一种职业团体,不能享有代表的权利,那么“选举法中第五条第四项(如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大学)及第五项(中国国民党)所规定的,又是否均为职业团体?如果此种团体可解为一种职业团体,那末我们妇女团体,又何尝不可解为一种职业团体?如果此种团体不能解为一种职业团体,何以彼能取得代表的权利,而我们妇女团体则不得有呢?”[18]
莫祥之从多方面质疑《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的合理合法性,阐述女子有权参加国民会议。首先,根据是1924年孙中山在北上的宣言中,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的原则:“一为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人民之需要;一为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7]。现在虽然时势不同,但是原则未变,妇女占国民的半数,如果要实现召开国民会议的这两个原则,那么就要充分表现妇女的意志和要求。选举法名义上没有男女的限制,事实上女子无当选的可能,因此女子可以要求为实现这两个原则对女子的选举权作特别的规定。其次,国民党的政策既然标为“无性别,无阶级之全民政治”,就应考虑到女子以其在社会上地位微弱的原因,不易与男子获得同等的地位,而且国民党的对内政纲中特别规定“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7],那么对在社会上势力微弱的女子就应特别加以扶持。再次,国民党四中全会宣称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是“将一切根本问题,恳切开陈于全国国民,以期齐一全国国民之心志,集中全国国民之力量,以立民有政治民享之基”[7],根据这个宣言,如果承认女子有参加共同努力的必要,就不能不在国民会议中给予女子相当的地位,让女子明白她们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所应负的义务。最后,从事实来讲,女子从事家事者即为从事职业者,女子所负的责任,所尽的义务非常重要,妇女团体虽然不是以职业来命名,但是实际上是由职业者组成的团体,现在的情势与孙中山时期主张有变化,“立法既以适合现代情势为原则,则不适者可易,需要者当亦可增”[7],因此选举法依据现在的情势对妇女团体作特别的规定很有必要。
四、与反对派的论争
对于女界争取参加国民会议的权利,社会上有不少反对之声。
第一个与反对派论争的女性是莫祥之。有人说:“在政府公布之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中,并无禁止女代表参加之明文,何以知将来无女代表参加之可能或居绝对的少数乎?”[19]对此,莫祥之辩驳道,“此就过去会议之经验及代表选举法之本身而察知之,在我国过去最近举行之种种会议中,凡在本党覆育之下者,均无禁止女子参加之明文,而考其结果,则全为男子所包办,女子则几乎绝迹”[19],况且,“在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中,所定有选举权者为‘一农会,二工会,三商会,及实业团体,四大学及职业团体,五本党’,就上述的范围中女子之加入农会商会及实业团体者,可谓绝无仅有,女子之加入二,四,五,三项者,虽尚有最少数之份子,而以最少数与最多数较,谓女子有选举之可能,不亦难乎?”[19]由此可以预测女子无参加国民会议的可能。
有人说,“女子既不参加各种事业,即对社会无贡献,对于社会无贡献之人,其无被选举为国民会议代表之可能,固属当然”[19]。莫祥之说,社会的进步不是仅凭男子就可以的,必须男女合作,“而欲使女子在社会上负促进社会进化之责任,则必须提高其地位使有参加的可能与兴趣,然后始能表现其充分之能力:是以在现代世界的潮流中女子之地位,莫不随其社会进化之程度而为逐步的进展”[19],而且女子“在社会上所负之责任在家族制度下之中国,则为綦重。盖竭其毕生之精力负家庭整个之责任,与男子之从事农工商等等之职业工作者又何以异?”[19]女子对于家庭的牺牲精神和责任观念非常强,不是一般从事任何职业的男子所可比拟的,因此认为女子没有参加社会职业,对社会没有贡献而不能参加国民会议的观点,其实是不明白女子责任的重要,莫祥之的这番辩驳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是承认女子家务劳动的价值,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观念。
有人说:“召集国民会议系根据总理遗教,在总理遗教中,关于国民会议之宣讲,未有妇女团体参加之明文,今若加入妇女团体,是非总理之遗教也。”[19]莫祥之认为这是不了解当时与现在社会情形的不同。立法贵在合乎社会的需要,既然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遵依孙中山遗教开国民会议的演讲中说,现在规定国民会议的代表与过去不同,是由于“时迁事异,有些团体根本没有存在了,于是不能不有小小的出入,可是实际上并不与总理的遗志相背”[19]。那么,“有小小的出入”恰恰体现了适合社会需要的立法精神,只是在孙中山发起召集国民会议时各地均尚无妇女团体,因此没有妇女团体选举国民会议代表的规定,而现在有许多妇女团体,“所以依据现代之时势而加入妇女团体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之规定,不得谓为违背总理的遗志”[19]。
有人说,“政府法令中不特别提出女子,正为尊重女子之人格,根据男女平等之原则,使一切均享受与男子平等之待遇”[19],莫祥之认为这个说法“若就女权已发达之国家言之则可,若就中国之社会,女权运动方在萌芽时代,则不可。”[19]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需要政府特别培植,尤其需要政府特定法律来扶植。莫祥之建议在《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第五条五项后加入第六项妇女团体,使妇女团体与其他五项均有参加的可能,“并不与男女平等之原则相抵触,且更适合现代立法之精神”[19]。
第二个与反对派论争的是李毅韬。有人说:“工,商,实业教育,大学,自由职业,国民党等选派代表各团体中,并未限制妇女参加,何以妇女不在各团体内努力竞选,而独争妇女团体之选派代表权?”[20]李毅韬认为就表面观之,这种论调似乎有理由,但是按之实际则大谬不然。女子参加团体的本来就不多,何况在知识、能力、经验、活动力和竞争心等方面,都较男子弱些,因此在任何团体内与男子竞选都没有优势,她举例召开三全大会时,也说选举男女平等,可是女代表仅有二三人。这说明“妇女在各男女混合团体中,不能当选为代表,正如农人或工人若使之混合于教育会、商会,大学校等知识分子团体选举不能当选同一情形。”[20]
第三和第四个与反对派论争的是青萍和陈逸云。1931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国民会议与妇女代表问题》,批判女界斤斤计较于代表权。该社论的第一点反对意见是:“关于此项问题,本可不成问题,因中央日前已有解释,谓此次国民会议代表之选举,系以职业团体区分,无分性别,妇女似可于职业团体中发挥其选举权。不必仍以‘女界’自居,仍以妇女为特殊阶级,以自示差等于男子;惟现在妇女团体似仍不肯放弃此项权利者,至不惜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以争之。”[21]
这是很多反对者所持的观点,青萍反驳道,“职业团体中,有没有多量的妇女在内?每个职业团体中,纵有一二妇女在内,此一二妇女分子,是否有于该职业团体中发挥其选举权的可能?”[21]陈逸云则指出:“全国职业团体尽操男性掌握,若责令女子于各职业团体与男子竞争,谈何容易,以一方参加职业团体者多属男性,事实上男性已占绝对优势,一方则男女平权虽法有明文,而社会习惯重男轻女,牢不可破,纵令职业团体中之女子,才华卓越,学识超人,然因社会积习过深,断难得予女子发挥权利之机会。”[22]这不是由于女子自卑,而是由于在数千年男权制度下,男子占据了优势资源。
社论第二点反对意见是:“国民会议如有妇女代表参加,是否有益于妇运前途?妇运前途是否可遵循此种类似之途径以求发展,或须另寻其他途径?”[21]同时加以引申,认为国民会议如有妇女代表参加,莫说可以改进人民幸福,即使妇运前途亦不可乐观。因为“一般已受教育与未受教育之妇女,均竞慕虚荣,爱装饰,嗜娱乐,一切应有之权利与义务,不知享用和履行;故吾人常谓妇女对于权利二字,在家庭中,只知‘争’利,不知‘用’利;在政治上只知‘争’权,不知‘用’权;此次请愿,国民会议必须有妇女代表参加,便是明证。”[21]此外还举例说上海妇女知识幼稚,游手好闲,已甘为衣饰化妆之奴隶。
对此,青萍指出,“妇女的成功与否,既是政运成功与否的表现;可知妇运便是政运中的一个肢部。况国民会议又为采纳全国民众之意见,用以解决国家大计的组织。妇女自愿应有代表参加,如此方能决定妇运前途,并其发展的计划。具体的来说: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与否,便是决定妇女取得妇运工具与否的关键”[21]。也就是说,政权是妇运的工具,要想妇运发展,便非有妇女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不可。至于竞慕虚荣,爱装饰,嗜娱乐,对一切应有之权利与义务,不知享用和履行等,青萍认为“这种病态,并不是妇女所特有的病态,而是现代男女青年共有的一种病态。同时这种病态期中的妇女,仅是女界中的一部分,并代表不了全女界”[21]。女界中固然有许多只知争权不知用权的女子,可是既知争权也知用权的女子并非没有,这次请愿国民会议必须有妇女代表参加就是证明。谈到上海妇女知识贫乏,无所事事,沉迷装容,青萍说一般男子不也是这样吗?为什么这样的男子“毫无疑问的承认他一定能应用政权?”[21]
社论第三点反对意见是:“各国妇女运动之逐渐成功,实由一般妇女经过长期之奋斗而来。妇女从长期之奋斗中,已获得充分之知识与能力,其知识与能力,在实际上已与男子跻于平等之地位,故对于既得之权利,均能充分行使;而在我国,妇女各种主要权利之获得,均不曾经过奋斗,即由本党自动的赋予,故对于所得之权利,均不加重视,且大多数妇女,缺乏教育机会,缺乏政治能力,以致不知行使既得权力之方法,遂使中国妇运呈此黯淡之现象。”[21]
青萍辩道:“我国妇女各种权利之获得,虽由本党自动之赋予,但这并不是因为妇女缺乏知识与能力,而予以特殊的优待。”[21]女子占国民的二分之一,国民党自然要赋予女子各种权利,如果说女子因为缺乏知识能力就不能赋予权利,是否无知无识的男子也不应赋予权利?至于说因为缺乏教育,缺乏政治能力,不知行使权利的不只有女子,“目前充满着男性色彩的:工人团体,农人团体,以及商人团体,又何曾不与妇运同样的呈露着黯淡现象?”[21]况且大多数女子缺乏教育机会,缺乏政治能力,并不是这些女子甘心不长进,而是宗法社会必然的现象,正因为种种缺乏,“妇女界才更应当行使政权。不然,这种缺乏,将永远缺乏着,更得不着满足之一日了”[21]。
社论第四点反对意见是:“妇女当先改造个人之精神生活,并应充足个人之知识与能力,用其知识与能力,一面提高全国农工社会妇女的地位,一面从事于职业团体之活动,以增进其精神上物质上之能力,不在用会议之方式‘争权’,乃在从实际生活上以‘用权’,则得矣!”[21]
青萍认为,国民党“虽承认男女教育机会的平等,但社会的势力,经济的势力,是否应许每个妇女,去充足个人的知识与能力,这却又成为问题了”[21]。因此女子还是非争权不可,争得权利以后,方可借权利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而用会议的方式争权胜过暴力的抗争,所以女子要取得国民会议代表权。
五、女子应该如何做?
《妇女共鸣》不是单方面要求国民政府给予女子参与国民会议的权利,同时还从近期怎样参与国民会议,从长远妇女运动的发展方面提示女子应该怎么做。
从近期而言,第一,要争取代表权。在国民会议召开前,谈社英告诫“女界同志应引前事为戒,早作预备,注意其代表产生法,俾使依法产生代表”[6]。李毅韬提出要组织请愿团体,主要目的是请求“规定妇女团体选派代表,而其副带目的在使党政当局,及社会人士,明瞭妇女之要求,此后对于妇女之权利不至于忽略或漠视”[20]。同时还可以促进女子自身觉悟,为行使权利而奋斗。为了争取代表权,还要组织竞选团体,“预先物色堪为代表之人选,合各地有选举权之妇女,集中力量推选之。”[20]
第二,要重视提案。李毅韬认为要组织提案研究委员会,“准备有关妇女福利之提案,及关于国民会议之参考材料,以供女代表之参考”[20]。谈社英说女子的切身问题未必即与男子同其利害,也不是男子所能代表其意志的,所以“无论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人数之多寡,提案之工作俱不可不早日预备,而此等提案关系整个女界之休戚,务须审慎周详,共同研究,并集多数女界讨论之”[23]。
谈社英非常重视提案工作,她强调“此次女界之提案,关系至大,于其范围性质,亟宜审慎,否则非当时不能通过,即将来反受影响,甚或贻人口实,谓妇女一再要求代表权提案权,未见于女界有何等利益也,且各地预备提案之代表,既不远千里而来,若不审慎周详,择其问题大而有益于女界者研究而讨论之,以谋永久之幸福,则不亦虚此行乎?”[24]具体而言,她认为提案的范围应该在以下几方面:法律方面,如民法“亲属编中之妻冠夫姓,及夫妻财产制之夫对于妻之财产有使用收益之权”[24],不符合男女平等的原则,可以提出修改。教育方面,“应要求当局厉行平等教育,使一般社会对于子女务须授以平等教育,养成女子知识能力与男子相等之机会”[24],社会方面,“解除女子痛苦之社会团体,应使当地政府充分加以援助,以便女子有救济之所”[24],这一点是很有远见的,类似于今天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女子提供的庇护所。对于媒体,谈社英提出,“严令禁止报章书籍提倡有伤风化及青年自杀等等,以免一般社会易于默化而受其影响”[24],据当时的报道,青年男女堕落及自杀的较多,一旦有这类事件发生,女子更为痛苦。这点意见也很有远见,媒体对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起到示范、诱导的作用。
第三,要重视宣传。青萍提出,要“作速实行宣传运动,以期多数同胞澈底认识世界潮流所趋,以及女权维系人类社会之密切关系,而至心悦诚服,情愿安分守己,不至攫取他人应有之权利,以为己有”[12]。
第四,在国民会议即将召开时,《妇女共鸣》对参会的女代表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指出女界争取代表权是为了争取国民的地位,不是专为对抗男界谋女子之幸福,“当随在以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前提,尽我一份国民之责任”[25],告诫代表们要“先事团结,俾意见一致,不至自相矛盾也”[26],“女界的意见第一要一致,绝不可彼此歧异,授人口实。”[27]总之,一是要明白做代表的职责,二是女界内部要团结。
代表们还要“充分表现今日妇女之才能,使全国人士认识妇女在政治上之力量,以建设妇女在政治上之稳固基础,及一般人对于妇女之良好观念。”[28]在会议时发言虽不可多,但是遇到重大问题,要代表妇女酷爱和平与真理的美德简要申述意见,“以调剂男子强暴偏私的心理,以图有益于国家民族”[28]。妇女代表当然也不要因为有才就表现出优越感,“发表言论,宜乎简短详明,不可有碍秩序也”[26],“要人人负责,不能视为交际场所,随意出席,随意退席”[27],要知道“国民会议是谋解决国家大事,不是给个人出风头的”[27],如果这样做会妨碍妇女参政。
此外,代表们要善于学习,对各方报告与提案内容加以深切的注意,因为这些内容“皆与今日中国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实际材料,足以增进个人政治经验与学识。勿仅认此次出席为对妇女问题有关的提案表示意见而已”[28]。
从长远着想,《妇女共鸣》反思选举法将妇女团体排除在外的原因。李毅韬认为“妇女运动过于消沉,妇女团体对于社会国家亦无新建树”[20],因此妇女团体被人淡忘。莫祥之也认为女子“缺乏团结之精神,各地妇女运动之呼声,散漫片段,未能有相当之步骤,作整个的一致之进展”[8],这次参加国议运动的初期也是如此,所幸最后少数觉悟的女子一致努力,才获得几个代表权。唐国桢认为原因是“对于妇女教育和训练之不足而已”[29],希望当局者注重妇女教育。
今后妇女如何努力?对女界自身而言,李毅韬认为,女子“在个人方面应如何努力求知识能力之猛进;在团体方面,应如何协助国家推进社会事业之发展”[20]都是应该思考的。莫祥之指出,“妇女运动之本身,当然应建筑在全体各阶级妇女之上,欲其有相当之成效,必赖全国妇女之共同努力”[8],也就是说要团结全体妇女。陈逸云比较全面地提出今后妇女运动努力的方面,要“提倡女子教育”,“注意扶助农工妇女”,“提倡妇女职业”,“矫正妇女思想”,“提高妇女人格”,“团结妇女团体”[30]。
对全体民众而言,妇女团体的代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今后应集中力量解决妇女问题,发扬妇女特性,促成男女平均发展之社会”,要“以妇女问题实为社会问题之重要部分”,因为妇女运动不是以男性为斗争对象,更不是以解除女子本身的痛苦为唯一努力的目标,而是“整个民族之病症治疗”,因此妇女运动的目标,是“发扬妇女之天才与特性,转移一般社会谬误之心理,俾可共同解决整个民族问题”[31]。
六、争取的行动
民国女性除了在《妇女共鸣》发表文章,展开辩论,积极争取参加国民会议的权利外,还采取了具体的争权行动。
一是妇女团体召开会议。1931年1月16日,南京市妇女救济会第六次常会第四项议程,就国民政府公布之国民大会代表产生法未规定妇女团体有选举代表权,“议决呈请党部,转呈中央明令规定,全国妇女团体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定额”。1931年1月24日,中华女子参政会开会专门“讨论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公决:“(一)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女界同胞响应,向国府建议。(二)向国民会议建议,将来国民会议出席代表人数,应有女子三分之一参加。(三)讨论于二月开始征求会员大会,以扩大团结”[32]。
1931年4月1日,南京市妇女救济会、女青年会、妇女共鸣社三个团体召集10多个妇女团体代表开会,讨论提案之事,成立南京市妇女对国民会议提案讨论委员会,推定成立提案审查科、征集科、文书科,通过提案原则案[33]。
二是发通电。在全国妇女争取代表席位的声浪中,尤以广东省妇女界呼吁最疾。广东妇女多次发起力争国议代表权的活动,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对各妇女协会、妇女团体发出通电,指出,“我国妇女,现在各团体中,虽略占地位,然以其数衡之,究不及男子之半数,似此将来结果必难获选”,号召女界“务须一致努力,各在自己所在属之团体内尽力活动,以求达到被选举为代表之权利”[34]。
三是请愿。1931年2月24日,广东女界成立妇女参加的国民会议协进会,各校女性师生一律请假参加。女界3000余人集聚省党部,并列队环游全市,要求参加国民会议。推举伍智梅、邓蕙芳等12人赴省市党部请愿,要求转请中央,准予选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而该省党部已根据此项要求,转恳中央,特别规定名额,准其选派代表参加[35]。
1930年12月,天津妇女文化促进会成立,呈请天津市党部转呈中央力争妇女团体代表,而且发快邮代电,要求各界予以援助,认为对于妇女代表不明文予以规定,是将女子与男子同等对待,但是“女子教育尚在幼稚时代,论社会地位,既不能与男子抗衡,论活动能力,尤不能与男子角争,在此情形之下,若使妇女与男子混合选举,将见国民会议席上,无一女子,即有之,亦居极少数”[36]。
1931年3月8日,南京妇女议决公推代表向国民党党部及国府请愿,被推选的代表11日向国民党党部及国府请愿,请愿书中说,“妇女固已一切享不分性别平等之待遇,惟以实际上女子参加于各种团体者,人数既少,势力又微,而选举习惯,竞争运动,势所难免,以妇女之势孤力弱,不宜当选,自在意中,倘任其自然,希望于农工商学等团体中竞争代表名额,稍有常识者皆当知其不可恃也,然则妇女代表,不易取得,正意中事,而所谓国民会议之国民,将尽为男子,岂非若天坛宪法所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民国全体男子组织之同一畸形怪剧,岂我提倡女权之三民主义旗帜下之国民会议所应有之现像”[37]。“若万一因产生代表之团体,已经规定,不便再定妇女团体产生代表额数,则恳予迅速另筹变通办法,以便遵循,总期妇女能于国民会议中,占有相当地位,稍尽国民之职责,不贻党国男女歧视之羞,则于愿已足,固不敢专门要求规定妇女团体之名额也”[37]。但是,这个请愿书没有得到批示,妇女代表于3月19日、3月26日两次请求,中央秘书长陈立夫接见,表示已转达中央,会设法补救。后来得知仍以案已规定不便变更为辞,代表们得此消息异常惶惑[38]。
各地妇女团体代表于1931年4月9日向国民党党部请愿,于右任、孔祥熙、丁维汾、陈立夫接见,允决在事实方面设法补救。15日第二次请愿,“一,请速予决定妇女参加国民会议名额,二,请中央多介绍各省市妇女候选人,三,请规定妇女团体推派代表列席”[39]。陈立夫接见请愿代表,答复对于第一项因中央法令已定,不能有所变更,第二项已准予照办,至第三项列席问题,须待国民会议主席团允许,当可照办。
四是提出提案。女界提出的提案有《严厉禁娼案》《修正民法亲属编案》《增设女子中学及乡村女子师范学校案》《请国府通令各省市社会局于有工厂处普设工儿寄托所案》《禁革蓄婢养媳之陋俗以重人道案》《严禁女子缠足违者以法律制裁案》《修正刑法案》《请决议纳妾者以重婚论为人妾者以妨害家庭论案》《普及农村妇女教育以利训政案》《各省推广女子中等教育案》《请于首都设立全国妇女职业指导机关案》等[40]。
国民会议结束后,女界代表以各地妇女团体代表名义提交呈文,呈请国民政府执行女界的提案,说明“所提各案固不仅有关妇女一方面之利益,并藉以促进训政之完成”[41]。
七、结果及影响
1931年5月7日,“请愿团得国民会议秘书处公函,主席团批准十人列席,其余旁听……以四月二十五日虽经推定十人,而各地继续来京参加者又有若干人,为求公允起见,乃由前所选之十人及候补五人总辞职,重行改选,以地方为标准,当推出莫祥之(豫)、谈社英(沪)、唐国桢(京)、李应莹(川)、喻维华(津)、舒德进(皖)、龚增纬(鄂)、宋鉴秋(鲁)、喻筠(赣)、王素意(平)等十人为列席代表”[42]。另外还有陈逸云、谢纬鹏等十七人特别旁听。此外,通过正常选举而出席国民会议的女代表有陕西省代表刘纯一、河北省代表李峙山、浙江省代表史志英、广州市代表唐允恭,还有广东省代表邓蕙芳、伍智梅、杨道仪选出而未出席[43]。至此,女子争取代表权的运动基本结束。
虽然女界对这次争取国民会议代表权的成绩不满意,认为女性参加的人数太少并且多半列席无表决权,但是运动本身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是有十名妇女团体代表得以列席会议;二是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国民党代表候选人中有女性并且当选,其中广东的邓蕙芳、伍智梅、杨道仪,河北的李峙山均为国民党中央提名并当选,刘纯一、史志英、唐允恭能够当选应该与本次运动也有关系。同时,此次运动对后来女性参加南京政府举行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南京政府举行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就不再有性别限制,在1946年公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中规定增加妇女团体选出代表二十名,台湾、重庆、新疆及东北十二省新增加之代表中应各有妇女代表一名,总计应该选出妇女代表三十五名[44]。1947年举行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时,先在《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规定“妇女团体选出者共一百六十八名”[45],“后经立法院会议,妇女立委们的热烈争取结果,便增加了一百二十三名。在区域方面增加三十名,……职业方面增加了七十二名,在边疆增加了十名,在海外侨胞方面增加了十一名。现在共有妇女代表名额二百九十一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