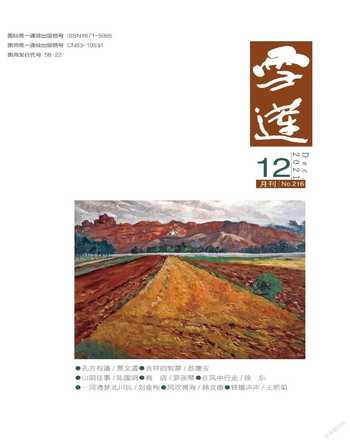在风中行走
1
似乎不可以说,我厌倦了什么……
还没有彻底衰老,还对将来怀着希望,而绝望感隐隐令我疼痛。
一种深入思考的感受,一种默然爱的纯粹,一种不被理解的真实,一种存在的不确定——仿佛只能保持着克制、平静。
似乎不可以说,我还能自由地爱着什么……
我已不再年轻,已不再相信曾经相信过的爱情,而孤独感又时常令我有着疼痛。
一种可以自我调控的感情,一种在芸芸众生中将心比心的态度,一种被文明教化的温良,一种平平淡淡活着的决定——仿佛只能活着,并不再渴求奇迹发生。
似乎不可以说,我如何如何……
我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我已经意识到对自我的背叛,我已经活在现实中我的阴影。
有种爱是以不爱为借口,有种妥协是以理解与包容之名,有种活法是随波逐流的轻松……
有时我喜欢行走在风里,一言不发地迈动著匆匆的脚步,仿佛远方有着另一个我,期待着与我邂逅。
2
独自一人时我想,最好什么都不写,只凭着意识到的存在感,往生命的深处畅想就好了。
有一种虚空的爱无中生有,它无色无味又渐渐转为香甜或涩苦——我感到自己身体里有遥远旷野里的一朵小花在绽放,有凭空而在的蝴蝶蹁跹着庄子与上千个我的冥想。我的时间与空间里有孤独的火熊熊燃烧着此在的局限,我幻想不被写出的诗行被无声地朗读。不确定的一切无需重新命名,已存在与命名的被设想存在的思想与意志取消,被想象与情感纷飞的雪花轻轻覆盖。
一个纯粹世界的假象,一种不被探究的真实,上千个我中最初的那个我,或者难以描述的那个我呼吸着过去的那个我的感受与想象,无意却在否定所有的我与世界——这是种爱的流露,这种爱的溢出令我羞愧,甚至令我莫明想要大哭一场。或许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在空无的深处是没有诗,甚至也没有存在这种被创造与意识的事物的。
活着,只是朝着无限与爱的虚空活着。
3
如果有些资本,又选择了投资的方向,你相当于是在做一项事业,只是你请的是无形的员工为你工作。关健是,你要选对方向,管理好资金,才能持续发展壮大你的事业。如果你的这项事业是炒股,这很简单,但也相当考验人。
很多人不用工作便可以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加,最终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过上了优越的生活。他的成功,除了因为有一定的资本,重要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资本运用得好,可以让钱生钱。钱是可以生钱,但所有的买卖都不是稳赚不赔,所以投资又是有风险的。能够控制风险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靠运气支撑的,这种能力是学习与思考沉淀升华出来的,这种能力源于经验和思想的不断结合更新。
在股市上,有常赚钱的,也有经常亏钱的,通常是赚钱的少,亏钱的多。谁都不想赔,谁都想赚,但无论如何还是赔的人多赚的人少。你想要成为少数,说来也是件容易的事。赔钱的人不见得不爱学习,可天天学习也一样会亏,因为学习只是一方面,重为最重的是——你明白,你更要做到。简单说,你要守纪律。
看好一支股票,可以适当做T,但卖出去多少还要在适当的价位买进来多少,要对那只股票持之以恒,如果一味追涨杀跌,最终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亏的是自己。能在股市上获得成功的人,往往是可以为自己制定纪律并严格遵守的人。
任何人想要在某个方面获得成就,都要对自己进行有效的管理——制定并遵守纪律。而这本身,并非是平常人能做得到,执行好的。
4
每天夜深人静时我就想对未知的存在说点什么,我要说的未必是给某个具体的人,我想说的更偏向于自言自语,可以说,我是想说给未知的存在的。
对于已知的,我能感受到自己不想再说,拒绝再说,而每一次言说都是一种不理性,不自控,甚至是不自爱,然而对于未知的,未来的,我又有着隐约的期待与热爱。
当世俗的观念与情感升起来时,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写,不必写。当纯粹的思想与情感升起来时,我又会觉得,不必想太多,想写便写。写,也未必全然敞开,敞开也未必真能放得开,放得开也未必真正写得到位,写得到位也未必真正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与理解。
现实生活对每一个人提种种要求又有着种种限制,这种存在也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认为是正常与合理的,却不见得是正常的,合理的。
真正的作品,一定是以作家与艺术家的天性也可以说是灵魂为底色的,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总体倾向于妥协,其结果必然是被弱化或被异化。即便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了非凡的卓越的成就,他也是尤其被弱化和异化的——他终将承受比平常人更多的虚空,因为有些成就的获得终要失去,也可说,有些人拥有越多,成就越大,危害也便越大。
真正的好作品源于生活的说法,不如表述为源于作家艺术家的心灵。一切艺术创作关乎心灵,是为着人性的,人类的灵魂纯粹、共存和谐而存在的。正如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但社会生活未必是人存在的本质。
人是恒久活在矛盾中的,文学和艺术能让人趋向于矛盾的消解,让人回归,让人在有生之年,而非以死的方式回归,让人在趋向于向自然回归——人是自然环境的动物,但人的存在又是趋向于反自然的,反自然,也可以视为反自我——尽管人各有各的背叛自我的理由和无奈。
没有自我的爱与奉献可以称之为是无知的,对他在的冒犯——尽管那种存在又被称之为高尚甚至是伟大。人以各种方式建构人类的生活,人也将以出奇不意的方式摧毁人类所建构的一切。正如人类反对战争,喜欢和平,然而战争的发生并不以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文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必然是与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存在是相悖的,应当允许甚至是提倡这种相悖,不然人类便是某种意义上的对自身的背叛。
不必急功近利地去确定或确立什么,人类当对未知的、不确定的保持着足够的敬畏之心。而文学的,艺术的,是不确定的,趋向于对未知的一种存在。
5
母亲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不信有鬼神,也从来不曾对鬼神有敬的言行,上了岁数时却改观了。然而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人到中年,我有些信了命运之说,也有些相信了世间有鬼神,但骨子里也仍是个自我的人。我的自我又是随和包容的,和朋友聊天时,说到一个我并不赞同的见解,为了不破坏聊天氛围,也会嗯嗯啊啊,点头表示,是这样,也许是这样。
也有坚持自我的时候,那时我会反对某个人的某个观点,却又不愿意去争论。我早些年是会的,那时与朋友争起来,常会面红耳赤,甚至是不欢而散。我喜欢那时的自己,又觉得此时的我之变化也是正常。此时我所认识到的自己,大约是这样的——我终于活在地面上了,认同了要工作,要赚钱,要扎扎实实生活,但我内心里却又觉得,这并不是人生或生命的实质。我的实质又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无尽的虚空。我对无尽的虚空有着潜在的向往。这说明我对“灵”有着无比的渴望。我的骨子里相信万物有灵。灵,是虚空的,又是存在的。那种在难以言说,难以捉住,更别说细细打量研究了。灵之存在需要感知,也需要表达。写作是对灵的表达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创作,也是对灵的表达的一种方式。
积极向上的人生,或积极进取的人类,当是有着对“灵”的向往的,简单说,要相信人有灵魂,万物有灵的。梵高可以通过一双旧皮鞋或几朵向阳花达传生命之力,安徒生可以让小锡兵变得有生命有故事,如果我们从庄稼地里摘取一根稻草,独自凝视它,思考它,它也可以千变万化,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写一组诗——但你总会觉得意犹未尽,没有写好。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种说法是对的。我们都认为,人是最为复杂的动物,这大约也是对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之不断的进化,其初衷未必是想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凡俗的人的格局未必太高远,也未必会想太多问题并让那些问题有确定的答案——而这正是文学和艺术要继续发扬光大,持续存在的理由。
文学的,或者艺术的创作,是要提出问题,决解问题,是要为着发动和提升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類去了月球,又把机器人送上火星,这些努力可以看成是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但这些探索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认识自身,认识物与物的关系。认识的过程,也是“灵”参与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只是我们人类现在还认识不到我们坐着的沙发是有生命的,喝的水是有生命的,沙发或水,与人类是一个整体。不管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是个整体。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你不认为万物是有灵的,便是潜在的反人类——尽管你意识不到,不知可不被怪罪。
我在这世界上生活了四十余年,热爱并实践于写作也有三十余年,在我的感受中,万物是有灵的,人人都应当认识并确认这一点。这有利于世界变得美好,也有利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充盈与纯粹。每当我怀疑这一点的时候,便感觉到,我的生命是那样的有限,我的人生是那样的无趣。当我确信万物有灵的时候,能渐渐感受到自己在那颗因思想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心变得喜悦起来。那喜悦从空漠遥远的地方如一束特别的光与我结合在一起,而我与宇宙万物结合在一起。
因为这样的认识和感受,我觉得自己并非只是活着的一副空皮囊。对照我以前写下的,不管是《欧珠的远方》,还是《诗人街》,我觉得生活中的我,活成了我的反面。但不管我多么想生活得好一些,我骨子里是渴望着脱离所谓现实生活的。因为,追求现实生活的人,终究只活着他有限的一生。而人要想活得更多,更广,更久,是应该活得有些不切实际,活得有些特立独行的。
好在,人的一生可以上千次审视自己,改变自己的活法。
好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只要你想要创造奇迹,奇迹便有可能发生。
人真正的好运气,好状态,是基于他相信万物有灵才可发生的。
6
今夜有雨,也没说非得跑到阳台或走到窗外看一看。
我在收拾书房。我把收藏的佛像、石狮子、石头等摆到它们该呆着的地方。它们该呆在什么样的地方,或者说,我明天该干点什么,大致是可以确定的。那大致确定的,也是可以打破的,只要一个念头产生,只要行动起来。就像写作,今天可以不写,也可以写。一个念头产生,写,坐在电脑前便可以写了。
人生的种种不确定,也可改变,只需要有了想法,行动起来。只是人到中年,想法少了,行动力也不如从前,基本上凡事都本着顺其自然,依心而活。尽管事实上未必如此,可心境与状态,还算得上是恬淡自如。如果没有干扰的话,绝大多数时候喜欢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呆着,什么都不太想做,只是漫无边际地想着事情,也不知想了什么事情。仿佛那样的存在,有利于自己进一步成为一名作家,一位诗人。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内在的那个自己会与我交谈。那无声的言语,静默的时光,令我感到美好。回想过去那样的自己,再想想自己之外的人类世界,我觉得一个新的世界,如果能从那样的自己开始就好了。想一想,不由得一笑。再想一想,实际上,喧嚣的世界也在安静的一面,只是人们很多时间并没有深入其中罢了。
此时,雨变大了,隐隐还听到了雷声。
雷声如诗,让我想到,是天空在大声朗读着什么。
7
长篇小说开了头,还是没能写下去。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别的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上去了。时光是浪费了吗?孩子在成长,工作在做,生活在继续。只是,在写作上没有继续。也不是没有继续,只不过没有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没有体现出创作的价值。
其实,每一天,都有机会,都有变化。每一天,都需要选择,都是新的。一天天的累加起来,便是一个个月,一个个年,便是人在时光里的变化,那变化的过程形成了人的一生一世。人在时光里渐渐成长、成熟、老去,这个过程,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首长诗或一部长篇巨著,每一个人都需要再认识,再发现。但通常,多数人的存在并不会有太多的人去关注。
一个人老了便老了,没了便没了。老并不可怕,有点儿可怕的是一个人一生一事无成。人还是要追求活得如何值得的问题。但一般人不会想这样的问题。一般人要么忙得没工夫想这样的问题,要么是闲得发慌,想方设法逃避这样的问题。当然,只是想一想这样的问题是无益的,重要的还是要行动起来,去寻求一些人生的意义。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追求。哪怕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也有着他的追求。追求未必高远,很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对生活质量的提升的追求,对身边朋友亲人的关心照顾——这两者都需要经济条件或能力。有人生活得艰难,通常是缺少一定的经济条件或相应的能力。或者说,我为了获得这种所谓的经济条件或能力,把本该用于写作的时间与精力,消耗进去了。细想来,这是错的,但这错也未必没有价值。
人活着有为小家为大家之分。为大家的写作也算是一种,但小家管顾不好去为大家,这种“高尚”在当下这经济社会里,似乎是有些不切实际。进行艺术创作的人,一般人不太了解,也不太理解。进行艺术创作的人,追求的是超越,对现实生活,对平凡人生的超越,这种自我的超越,通过作品或成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事实上,人有权力选择他认为适合自己的路去走。为小家也好,为大家也好,总的来说,人活着还是为着别人的。每个人都免不了要生活在俗世之中,哪怕再成功的人也无法成为神仙,但人与人之间相比较还是大有不同。与众不同的人,确实有着值得敬重的一面。人,大约都想着受人敬重的,因为那样地活着,活得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
只是,那样的价值与意义的实现,往往让人倾其一生,呕心沥血。像路遥那样去写,值得吗? 会有不少人说,值得,也会有更多的人说,不值得。
8
中午睡了一会儿,下午带孩子去爬凤凰山,回来后吃过晚饭与朋友聚聊到晚上十一点钟,回家洗漱过后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这失眠的情况并不多见,今晚却结结实实地失眠了。失眠之前想过股票,想过小说,想过明天的工作,想过要不要写一篇随笔。先是放弃了写随笔的想法,现在又要再写一写。写一写,大有不写不能交差之嫌。
虽说这段时间没有正儿八经写过什么作品,但写长篇的想法像“暗物质”时时刻刻作用于我,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为什么一定要写长篇,为什么不能把中短篇进行下去呢?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仿佛这写长篇的想法长在了我的头脑中,内心里,挥之不去,清除不了。我似乎是在等一个时机,那个时机到了的话,不写将不可能,什么也阻止不了。那样的一个时机是需要积累与感受的结合达到一个瓜熟蒂落的程度吗?我不知道。
昨日晚上与一写作的朋友喝酒聊天,感受到写作者各有自己的局限,而打破这个局限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要太清楚地看问题,想问题,那或许是错的——最好的办法便是继续写下去,依着自己的内心写下去。内心,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确确实实可以构成他所在的世界的一面镜子,而且,可以是一面魔镜,让读者通过那面魔镜,看到现实世界中有的和没有的,存在的和不存在的。
再次想到卡夫卡,想到他所说的,一切皆是虚构。我相信,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认知,是一个真正写作者的坚定智见。确确实实,在卡夫卡面前,许多写作称得上是无意义的,但我从来不愿意否定那所谓无意义的写作是无意义的。也并非是说,存在的便是合理的,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写作,是一个由个人到众人,由具体琐碎的生活到庞杂抽象的社会,由现实到精神的创作和承续。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了写作的人,都有他的价值和意义。
9
晚上十二点过后是我的时间,这时间也只能有个把钟头,熬得太晚了对身体不好。这时候孩子睡了,房间里安静下来,都市的喧嚣缓和减弱下来,窗外的夜色正好,如果有一轮明月,便更是诗情画意。这时我抽一根烟,沉静下来,想写点什么。有时写了,记日记一般,有时凑成一篇短文,好像也算是对生活在过去的一天的交代。不管写不写诗歌和小说,只要在写,便使我感觉到,我仍然是个写作者。
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写作者,在这个有了大变化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上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定位?思来想去,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写作也只不过是使我的人生多了一抹亮色。炒股票能赚钱的,做生意做得风声水起的,会点儿音乐的,大约他们的人生也会因此多一抹亮色。写作者的我与他们有何不同呢?有,又或者说没有,似乎刻意去区分也无多大意义。我清楚的是,我打心里是认可写作的意义的,也是认可自己写作者这一身份的,只是不知何时,不再把这意义与这一身份看得那么重要了。
作为写作者的前辈们,那曾写出过优秀作品的,不管是逝去的,还是依然活着的,他们曾经的或现在的对写作的执着终究给他们换来了什么?物质的,名誉的,或者是他们把写作这项事业,当成了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的意义所在——这是重要的,别的都不是那么重要。这是重要的,因此我依然不能够想着放弃写作,以便获得多一些的轻松。所以我会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写下一些文字。
我希望孩子越来越大一些以后,生活得越来越没有负担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扮演好写作者这个角色,最好扮演得有声有色,生龙活虎。有时我想,我放下了写中短篇小说,有时只不过是偶尔写一写小小说,大约是为了要写一部我想要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小说呢?我说不好,但我希望这是一部特别的,带着我的灵魂气息的长篇。我不知何时才能开始这长篇的写作,仿佛开始的那天,便是要把我这个写作者的身份进一步加强似的。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对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说说心里话,或者去通过文字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是种幸运,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的存在,几乎是沉默着的,无声无息的,一味生活在现实的沉重里的。
这个人类的世界要变得越来越好,大约是需要那许许多多的、平凡的或卓越的写作者的。也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区间,读者和写作者相互成就的结果令世界更加美好。
【作者简介】徐东,出生于山东郓城,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出版小说集有《欧珠的远方》《藏·世界》《大地上通过的火车》《新生活》 《想象的西藏》 《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诗人街》,长篇小说《变虎记》《我们》《旧爱与回忆》《欢乐颂》,诗集《万物有核》等。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奖等,部分作品被译介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