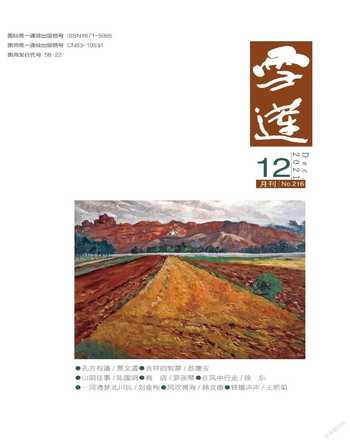商 店
日子倏然而逝,转眼又是年关。
回乡高速上,车子明显比往年少。沿途树木,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些枯涩枝桠。寒风吹彻,枝桠瑟瑟作响,远远近近,仿佛生出无数双瘦削之手。后疫情时代,一年细碎收成,大体是经不起盘点的。枝桠垂向地面,心生羞愧。
野溪河畔,那块被村民平整好,用以年节停车的空地,再不复往日拥挤。一队蚂蚁从几片残叶爬过。许是车子发动机启闭间的余震使然,几粒莹白米饭很快从它们的触角滚落。
沾染泥浆的饭粒,粘稠,滞胀。蚁群纷乱,轰然蚕食,之后,作鸟兽散。几副小小的木制桌椅,散乱无序地支楞在门口,桌面被数本寒假作业潦草覆盖,孩子们却不知道去了哪。我随手一翻,瞥见了儿子还未完成的看图写话:乡村过年。一点也不热闹,到处空荡荡的……心中不免一阵忧怅。
公公关了电视从里屋出来。素喜热闹的公公居然能一个人守看越来越寡淡无趣的电视?要知,往年这个时候,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公公他人基本上是扎在商店的。扎在商店做什么呢,有时是与打工返乡的年轻人斗地主,有时是与日日相见的老辈人推牌九。当然,公公年岁毕竟也大了,老眼昏花的,玩不了太久,他会随时停下,再随便找个人将他的好坏手气悉数接去,然后转转脖子,捶捶腰,站在桌边当个很得体的观众。所谓得体,当然是说读过旧日高中的公公深谙观棋不语真君子的古理啦。还别说,公公观战时背手而立的缄静,能让闹腾的商店,多出那么點久远的况味,看着看着,传统的年也似乎多出层厚重的古朴。站一会儿,商店主人家一招呼,公公便悠悠接过递到跟前来的小竹椅子,围着商店的火盆子烤起火来。去喊公公吃饭的我,也时常会在火盆子边坐一会儿,听听乡亲们闲聊趣事,更多时候,我会选择长久注视一只猫。那是一只成了精的猫,它的眼是洞悉世事的眼,人间万象都藏在它的一双棕色瞳孔里。与之对视,仿佛可以看见时光的纷纭、世代的更迭。那一刻,猫在我心里,仿佛是隐于现世的旧朝遗老。
凭票购物的年代,村子里的商店不叫商店,叫代销点,隶属于供销社,后来,因村子是大村,人多,又扩改成了门市部;也不开在礼堂,而是开在礼堂对面那一排屋子所在的地方。据公公回忆,规模大得很,五六间房屋面积,坐北朝南,东西两个大门,油漆的蓝色门窗,从东边的门进,右侧是衣服布料鞋帽的柜台,各式布料卷成轴整齐竖放在柜面上,墙上挂着大小成衣,柜子里摆着好看而实用的鞋子;正对面从东往西,依次是文具专柜、生活用品专柜、烟酒零食专柜和农业生产专柜,铅笔、钢笔、墨水、纸张,头绳、衣扣、针线、松紧带,饼干糖茶,油盐酱醋,锅碗瓢盆,酒缸锡壶,菜种化肥,犁耙铁锨,应有尽有。
公公回忆的时候,还特意站到商店门口,用手划拉了一下,指给我看,意思是我们村,老牛了。公公还说,听诊器,方向盘,杀猪刀子,那时候,物资有限,营业员是很吃香的一类人,但和他基本都是好朋友,有什么物资到了,总在第一时间知会他,连最常用的火柴,哪一批好,哪一批次,他心里都是有谱的。那时候,香烟可以拆盒,散着支卖,干一天农活,不是先回家,而是串到门市部,花上一两分钱买支零烟,狠狠吸上几口,一身疲惫困顿,很快烟消云散……我默默听着,能感觉到有老人家独有的傲骄心态在里头,便忍住没告诉他,其实,在我的老家白沙乡,曾有过比这大出近一倍的供销门面,都不叫门市部,直接就叫百货商店,光营业员就有好几十个。穿戴整齐的他们,知书达理,童叟无欺,对谁都是一脸真诚的笑。
他们个个手上有绝活:卖布料的,布动尺走,尺寸一量,用剪子剪一小口,“刺啦”一声,没有丝毫犹疑与反复,料子就完美扯折到了顾客手中,绝不多出一根出轨的线头;卖饼干,放两张草纸,分两摞码好,草纸对折一卷,两头一包,头顶上的纸绳左右一个十字结一扣,再将纸绳一扯断,漂漂亮亮就给包好了,知道顾客是家有喜事的,还会从柜台里抽张小红纸,麻利剪个小方块嵌在十字结下头;一毛钱的水果糖,随手一抓往柜台上一甩,不多不少正九块;还有,小孩子最喜欢的打酱油,要半斤,酱油提子舀出来的绝对不会超过六两。
我喜欢看营业员亮绝活的样子,仿佛只要肯努力,人人皆是如来,无论“世界”这个多变的孙猴子怎么折腾,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也喜欢看琳琅满目的商品,它们多像是生活恩赐给每一位普通人一个微缩的万花筒,只要打开,惊喜就能扑面而来。
上小学时,我几乎每天一有空就往那钻,麦乳精的瓶子,桔子、雪梨罐头不知吃空多少个。那个最和蔼的营业员李阿姨,每回在街上看到我,必扯住我的脚步,反复提我与商店的一段小过往:“小丫头,那会儿,你三四岁吧,跟你姑婆来逛商店,对一双粉色的、有蝴蝶结的凉鞋喜欢的不得了。哭着喊着要买,你姑婆不肯,说你脚上穿的是新鞋,是你爸爸不久前去上海出差才买回的小新鞋啊。偏你鬼灵精一个,眼睛儿溜溜一转,将一只脚使劲一抬,再一晃,脚上那只鞋就不知飞哪去了,商店人特多,挨挨挤挤得,大家帮着,左右没找着,你可不就得逞了。”

上中学后,那座建在乌江边的乡粮管所取代了百货商店在我心中的地位,成了我的新“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偌大的仓库,美观大气的砖房,洋溢力学之美的机械,亲如一家的工人,乌黑的传输带,轰鸣的车间及米与糠的混香……粮管所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深深着迷。当听到一个堂姐要与粮管所的一位正式职工结婚的消息时,我着实高兴地在厅堂里翻了一个很不女孩气的大筋斗。
高一寒假,从县城回家,大巴停在廖家村的地盘上。过去的零落田畴被大块整合,依着省道建起了一处比粮管所不知大多少倍的农贸市场。超市,菜市场,早点店,夜宵摊,一家接一家的零售店面,还有卡拉OK和酒店。穿过农贸市场,我有一种错觉,仿佛穿行在大河之上,而每一个人都在时代的江河中热气腾腾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硕大的农贸市场,让廖家村成了白沙新的中心,而曾经是中心的我们村被笼统唤作“老街”。老街路面,不如新中心平整,许多地方早已出现坑洼,一个不留意,“坑洼”崴痛了我的脚。脚趾连心,潮湿的雾气很快蒙涌我的眼睛,似乎连带晒在沿街老房子的太阳都有些恓惶……衰朽的门窗,褪皮的外墙,斑驳的瓦砾,潦倒的杂草,我却是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百货商店的消失的。姑婆仿佛懂我,轻声说了句,关了好几年了。
公公喜欢久待的这家商店,开了有近四十年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放开市场,多种经营主体“忽如一夜春风来”,那间让公公至今说起仍引以为豪的门市部没能迎来“病树前头万木春”,和身边并排连着的数幢老房子一起,湮灭在历史铁蹄深处。
有敢吃螃蟹的第一个村民租用老房子,在废墟对面,村礼堂的部分空间,开起了这阆田村第一家私营商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求学或打工谋生,这家店似乎成了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儿童最喜欢的去处。至我嫁作钟家妇,我的公公、婆婆每天早晚,至少两趟必去商店,买东西是次要的,主要是要听信息、听八卦:某某崽俚(儿子)打工打出了老板样,办了厂,发了财;某某崽俚娈(靠甜言蜜语哄骗)到一个外省的好看媳妇,酒还没做呢(没结婚呢),女方就挺起一个大肚子来(怀孕);某某闺女,涂脂抹粉,穿露出奶沟里(乳沟)的衣裳回村,肯定在外没学好;某某崽俚读博士,听说要把爹娘接去美国,咯就问神罪(这就受罪了),外国话叽哩呱啦的,一句话也听不懂,不会把嘴憋臭……与其说商店经营着一村人的柴米油盐,不如说成为全村信息集散地的商店填补了一村人的情感黑洞和精神空白。我每回回村,婆婆都会一个劲儿地鼓动我去商店坐。等我从商店回来,婆婆便开始滔滔不绝跟我分享她一段时间以来搜集到的信息。这些人事我知不知道不打紧,关键婆婆觉得去过商店的我,已然接受了乡村最深层次的熏陶,跟乡村同呼吸共命运,是可以跟她站在统一战线的盟友。
“怎么没去商店玩?”我问公公。
“生意不好,商店倒闭了!”公公神色有些黯然。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记不得这是哪位作家写过的一句话。汹然而至又盘桓不走的新冠病毒,何尝不是压在每个人头上的一座大山。
数十年来光阴,几万里地山河。村里的商店就这样消失了,天地,田野,江河,浩荡有序,收容人世大小变迁,我们又将在不可逆的时光里迎来新生的什么?
【作者简介】罗张琴,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在《中国作家》 《上海文学》《天涯》《散文·海外版》等刊发表作品,有作品选入《21世纪散文年选》《中国随笔精选》《中国年度散文》《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民生散文选》等选本,出版有散文集《鄱湖生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