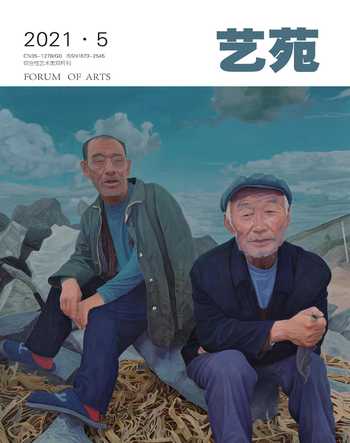形式·媒介·证据
张执中
摘 要: “意向性情感”是马利坦美学思想中的“枢纽”,其内涵复杂多变,向来令论者难窥堂奥。概言之,“意向性情感”主要呈现出三大面向:首先,它是“诗性直觉”对艺术质料进行赋义的形式;其次,是“诗性直觉”进行认识和创造活动的同构性媒介;最后,是确认“诗性直觉”存在的证据。三者在逻辑上相互支撑:形式是媒介的存在模式,而媒介是证据的显现条件。然而,在马利坦的体系内部亦有诸多张力,正是这些疑难造成了“意向性情感”在概念上的暧昧不清:第一,“意向性情感”与“诗性直觉”的因果关系遭遇了误置,其同构异质的事实没有得到重视;第二,马利坦在论证上力图摆脱作为前提的纯粹信仰,但最终却寄托于类信仰的主观体验,这与他“新托马斯主义者”的调和立场密切相关。
关键词:雅克·马利坦;意向性情感;诗性直觉;新托马斯主义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是雅克·马利坦最具代表性的美学著作。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该作的讨论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各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诗性直觉”“创造”等关键概念的澄清,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诗与美之关系”“诗与艺术之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对马利坦的艺术本体论进行重构。约翰·汉克、周丹、克冰等学者都是此一阐释路径的代表。然而,“诗性直觉”并非马利坦论述的根本起点,其运作奠基于更为原初的情感机制。以往的研究以“诗性直觉”为圆心向外、“向上”探究,而本文则意图为“诗性直觉”完成向下“奠基”,重点围绕马利坦艺术理论的基石“意向性情感”进行分析,如此,方可更為清晰地擘画其思想图景。
何为“意向性情感”?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马利坦对艺术创作中两种情感的区分:其一,是作为“质料”的动物性或纯主观情感;其二,是作为“形式”的意向性或创造性情感。在马利坦看来,前者并非艺术创作中的重点,甚至基本与艺术无涉,后者才是诗性认识特有的媒介,换言之,它是“诗性直觉”(1)得以运作以及优秀艺术作品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马利坦这一观点的提出,既是其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然,也是他突破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的结果。下文将从马利坦对艾略特的批判出发,分析“意向性情感”的概念内涵及其在“诗性直觉”体系中的枢纽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对关键的理论疑难进行阐发。
一、作为形式的情感:“意向性情感”的基本内涵
马利坦之所以提出“意向性情感”或“创造性情感”这一概念,是为了将其置于“动物性情感”的补充层面。以“动物性情感”为论述中心的创作论在他看来仅是“感伤主义者”的诗学,远非理想状态。马利坦将“动物性情感”定义为一种纯主观的情感(作为单纯心理学状态的情感)[1]27,他在《艺术与经院哲学》曾指出:“我愿意接受艺术家构想好并且放在我眼前的对象的支配地位;我愿意毫无保留地放弃自己,并进入与艺术家共同享有的一种情感状态——这种情感状态来源于我们借以交流的同一种美、同一种超验之物。但我拒绝那种通过刻意谋划的导向性手段来诱发我的潜意识的艺术处于支配地位,我抵制那种某个人意图强加于我的情感。”[2]前者就是所谓的“意向性情感”,后者就是他意图批驳的“动物性情感”。前者是双向、沟通、交流式的;而后者则是粗暴、独断、强加式的。
但这样的表述更倾向于艺术鉴赏层面,而非艺术创造层面,因此仍不完备。所以,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中,马利坦着重论述了创作过程中两种情感的区别,并从否定和肯定两方面对“意向性情感”做出了定义。在否定层面,他通过批驳对立的“动物性情感”为该概念划定了大致的范围。这主要体现在他对T·S·艾略特的批判中:“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讲到的情感和感受,也只是动物的或纯主观的情感和感受。”[1]133艾略特的确指出应该避免某种情感:“诗不是情感的释放,而是避开情感”“诗不是感情,也不是回忆,也不是宁静”。[3]8艾略特显然意在批判华兹华斯“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论断。马利坦则认为,艾略特虽然指出了人们应该避开纯主观或作为质料的“动物性情感”,却没有对作为构词要素的情感、作为通向实在的媒介情感——即“意向性情感”的本质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动物性情感”的变形(即被赋予艺术形式),并不能仅依赖于所谓的“自我克制”,而必须凭借“意向性情感”的作用。因此,“意向性情感”不是由诗人表达或描述的情感,不是作为在创作中作为材料或题材的那种东西的情感,也不是诗人那种能使诗篇对读者“感动至深”的情感。[1]132马利坦通过以上的批驳,展示出“意向性情感”的否定层面。为使其概念边界更为清晰,我们还需对其进行肯定性的定义。
按照马利坦的论述,“意向性情感”是作为形式的情感。它与创造性直觉(即“诗性直觉”)融为一体,给予诗篇以形式,它有如意识活动一般,呈现出意向性。或者说,它“自身内蕴含着无限多于自身的东西”。[1]132若要厘清这一论断,有若干问题需要得到阐明:第一,“形式”在马利坦的使用语境中意味着什么?作为“形式”的情感如何可能?第二,马利坦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意向性”?它与“形式”有何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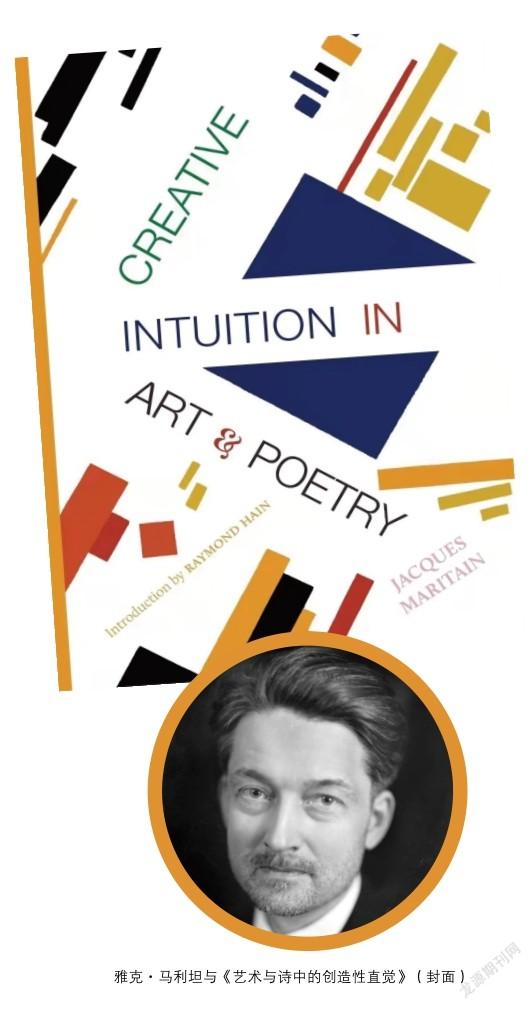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得知,“动物性情感”被马利坦视作质料般的存在,这与他“新托马斯主义者”的立场密切相关(尽管马利坦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称号,在他看来,托马斯哲学是永恒的,具有真理的价值,因而不存在新与旧的分别[4]37)。在通常的理解中,新托马斯主义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形质二分的模型:原始质料作为绝对潜能,并不具备现实性,而形式使质料得以现实化并拥有确定结构。质料本身是混沌的,未切分的,形式使之成为有清晰身份的实体,从而能够“与其他事物相分离”。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方能理解情感如何作为构词要素而存在。而在马利坦的语境中,形式并不是事物的抽象原则或根据,亦不是远在彼岸的理念。在他看来,当某件事物能以若干种可能的方式存在或发生时,我们便可以用形式一词指涉它存在或发生的某种特定的方式。换言之,形式并不隔绝于事物,它通过与质料发生关系而显现自身,这意味着形式具有复多性。这正是“新托马斯主义者”力图调和超验之物与感性之物的理论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马利坦为何将“意向性情感”定位为一种“媒介”,因为它一旦离开质料便会失去功能性存在,无法维系自身。
与此同时,在一般的艺术理论中,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文论中,常将情感视作等待表达的内容,“形式”则意指情感所借助的表达手段,形式与情感(内容)在此似乎是对立的。那么,“意向性情感”如何实现从“内容情感”到“形式情感”的转变?如果以黑格尔美学为参照系,则形式本身便是情感性的。艺术的形式或客观性,在他看来不是外在自然的客观性,而是内心的客观性。换言之,形式即情感规律。[5]354黑格尔实质上是将形式归结为内容,但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困惑,即内容如何完成形式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架构下,这的确不构成问题)。在马利坦的体系中,情感是作为概念和观念(notion)的对应物存在的,而后两者在前反思阶段是无法被构型的抽象物,不能赋予诗歌以结构,只能作为物质要素而存在。因此,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反向推论:情感作为概念的对立面理应被赋予具体的形式,成为意义的承担者。[6]78但是,仅用反证法显然不能服众,因为它仍是概念系统内部的自我设定。面对这一疑难和困境,马利坦决定引入“意向性”概念进行解决。
马利坦是在托马斯主义的语境下使用“意向性”一词,意指纯倾向式的存在,它是朝向对象的纯粹非物质。“意向性”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经验,都与某个对象相关联,后世受托马斯主义影响的布伦塔诺等人就是借由此概念摆脱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因而,“意向性情感”是一种指向自身之外的情感,它“自身蕴含无限多于自身的东西”。[1]132正因如此,“意向性情感”能够使“动物性情感”也指向自身之外,而这个外部即形式化的情感,它剥离了动物性情感中的无节制发泄的成分。动物性情感在形式化之后,仍是内心状态,要转化为世界中的艺术作品,情感还需要现实化、物质化,而这一外化的过程同样离不开“意向性情感”。由于意向性情感“无限地多于自身”,它能够否定情感的内部性,使之转化为具体的语词符号。于是,“意向性情感”便成為了沟通内外的表达手段——或作为“构词要素”——它脱离了内容或质料的层面,成为了形式化的存在。由此,通过“意向性情感”不断否定自身、超出自身的特质,内容的形式化以及形式的外在化问题便获得了解释。
当然,也有论者指出马利坦的体系的不完备之处:一方面,马利坦认为“形式”不具备脱离质料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意向性”又是“纯倾向性”的、“非物质”的。作为“形式”的“意向性情感”,两者在基本概念上无法完全契合。但问题在于,作为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利坦并不将“质料”看作是某种物质。在阿奎那哲学中,质料是三分的。其中,原始质料并不具备任何现实性,只能在思想中存在,而具有现实性的“特指质料”(designated matter)显然不是马利坦的问题域。因此,马利坦的叙述主线与理论意图仍是清晰不谬的:“意向性情感”是一种作为形式的情感,它不仅赋予“动物性情感”以形式,且自己本身也是艺术创作和表达中的重要手段。但“意向性情感”不仅作为形式与表达手段而存在,它同时也是马利坦“创造性直觉”(诗性直觉)理论体系中的枢纽概念,因此,我们还需将其放在更为宏观的脉络之下进行考察,方能不致偏废。
二、作为媒介的情感:“意向性情感”与“诗性直觉”的同构性
“诗性直觉”或“创造性直觉”是马利坦的艺术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通过“诗性直觉”,艺术家进行着不同于逻辑或推理状况下的认识与创造。但初次见到“诗性直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一概念是可疑的——因为其修辞似乎预设了某种“非诗性直觉”或“理性直觉”。但从克罗齐等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直觉知识可离开理性知识而独立,是与逻辑知识相对立的:“直觉知识并不需要主子,也不要依赖任何人;她无需从旁人借眼睛,她自己就有很好的眼睛。”[7]7“直觉”与“诗性”一词在概念上多有重合,维柯也用这一词汇描绘原始人“非概念式”的思维方式。[8]221这样看来,马利坦提出的“诗性直觉”岂不是同义反复?其实不然:由于“诗人”在古希腊文语中意味着“创造者”,所以我们可以将“诗性直觉”理解为“创造性直觉”,这也是马利坦书名中的应有之义。但是,创造性仅仅是“诗性直觉”的一个侧面,其认识功能(即“诗性”的认识)的证成,不能仅通过“诗”与“创造”的词源学论证而获得解决。于是,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马利坦对“诗”的定义,通过不同维度的审视,才能较全面地理解马利坦以“诗性”修饰“直觉”的特殊用意。
在马利坦看来,“诗”并不是某种文学体裁,而是“更普遍、更原始”的过程,即“事物的内在存在与人的内在存在之间的联系,它是一种预言”。[1]9在这个意义上,“诗性”具备了某种认识功能,虽然这种认识功能更多具有某种“预言”的神秘性质。因此,在“诗性直觉”中,客观真实与主观性、世界与灵魂整体不可分割地共存着。[1]134
那么,“意向性情感”在“诗性直觉”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马利坦认为,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诗性直觉”与“意向性情感”是融为一体的,它们给予诗篇以形式。[1]132而“诗性直觉”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某种同质性手段,这种手段(即诗性认识)——在马利坦看来——是一种通过“倾向”或感情同质性的特殊认识,更精炼地说,这是一种“体验性”的认识,它与精神创造性本质上相一致。[1]130这里的“倾向”与“意向性情感”中的“意向”是同一种存在。它们是沟通自身与他者的重要媒介,如若失去“意向性/倾向性”,主体与外部的交流就不可能实现。马利坦自己也承认,这种同质性的特殊认识,“凭借情感而发生”,而这种情感在其语境中指的便是“意向性情感”。[1]131
“诗性直觉”的内容既是世界事物的真实性,又是诗人的主观性,而二者都是通过“意向性”或精神化的情感被朦胧地传达的。[1]137然而,“诗性认识”本身是“不认识自身的认识”,它是前反思的。按照马利坦的说法:“灵魂在对世界的经验中被认识,世界在灵魂的体验中被认识。”[1]137这种认识不是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理性认识。而是为了生产而认识,是创造性的认识。然而,“诗性直觉”的认识与表达成型必须要通过清晰化的“反思”阶段。如何从这种“前反思”过渡到“反思”便成为了马利坦理论体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此之时,马利坦再次引入了“意向性情感”。“意向性情感”的诞生,便是从以外物为对象的“前反思”到以自身为把握之物的“反思”阶段,其联系物我的“意向性”使得解决这一“由外转内”的理论难题成为可能。马利坦表示:“对于人的灵魂来说,在认识自身之前认识事物这是自然的;但是,对于自我的经验是最主要的——因为当主观性对自身认识之时,在智性自由生命的半透明之夜中获得的情感便成了意向性和直觉的。”从这一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利坦看来,自反性与意向性是同时产生的。除此之外,马利坦将“意向性”与“直觉”两词并置,充分说明了两者的交融关系(如上文所说,“融为一体”)。这意味着,“意向性情感”不但在“诗性直觉”的认识功能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并且在“诗性直觉”的创造功能(即清晰表达)中也起到了中介作用,由此我们能够理解,“意向性情感”为何与精神创造性在本质上一致。实际上,“诗性直觉”应该属于马利坦“直觉”体系中的“非哲学直觉”:马利坦的“直觉理论”有两大层次,即哲学与非哲学直觉,两者各有三个面向。前者能够展现感性的知觉世界、个人行动中的“自身”,以及范围广阔的抽象知识。后者则展现为行动中的谨慎,艺术中的创造性,以及个人精神生命中对上帝的依靠。[9]这种“非哲学直觉”是能够被日常语言所反思,并且能够被普遍智慧所承认的。而使其能够进入语言反思阶段的关键“媒介”便是“意向性情感”,它让我们以“非概念”的方式打开通往实在之路。[10]8由此可知,作为“媒介”的“意向性情感”在马利坦艺术理论中的枢纽地位。
然而,在马利坦的宏大构想之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意向性情感”与“诗性直觉”不仅仅具备同构性,并且是“融为一体”的。但在随后的表述中,马利坦便认为“诗性直觉”是“前反思”的,而“意向性情感”诞生于“反思”的开始。这意味着,两者在结构层次上处于不同的异质地位,在逻辑上有先后关系,并非能够天然地融于一体,换言之,两者融于一体的状态是有限制条件的,同构而异质的两种存在如何融合是马利坦未曾说明的环节。另外,虽然马利坦引入“意向性情感”是为了使艺术创作的具备可表达性,也就是使“诗性直觉”能够完成由内到外的“物象化”,但这里存在逻辑先后的混淆:在马利坦的逻辑顺序中,是认识的自反性使得“意向性情感”得以产生,因为“诗性”本身就是“事物的内在存在与人的内在存在之间的联系”,所以能制造“意向性情感”。但诗性直觉的两大功能——“认识”与“创造”都需要“意向性情感”作为中介式的介入,而“诗性直觉”的存在又是由其功能确立的。离开了“意向性情感”,“诗性直觉”便无法成为完整的概念,换言之,“意向性情感”是构成“诗性直觉”的要素,它亦是后者的决定者。因此,两者是互相决定、在逻辑上同时产生的,“诗性直觉”不可能在逻辑上处于优先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意向性情感”不仅是与“诗性直觉”同构异质的存在,而且能够从“媒介”成为决定性的“枢纽”,是“诗性直觉”两大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意向性情感”同时具备了“媒介”的消极性和“枢纽”的积极性,这是由其特殊性质,即沟通物我的“意向性”决定的。马利坦试图利用“诗性直觉”和“意向性情感”的同构性来生成后者,却遗忘了前者的确立本身就预设了后者的存在,因而陷入了逻辑的悖反。
三、作为证据的“意向性情感”:超验之物的经验性存在
在马利坦的理论体系中,“诗性直觉”产生自灵魂自然的、最高自发的运动。[1]137而灵魂本身是难以描摹的,“审美情感”“内在之意”这些在心中成型之物,如今也渐渐难以应对语言哲学的拷问。此外,马利坦本人拒斥系统分析,偏好灵光一闪式的洞见,使得他对事物的认识与表述多借助于类比与隐喻,这更加剧了概念含义的晦暗不明。[7]79这样一来,“诗性直觉”的存在亦会陷入可有可无的尴尬局面。但是,马利坦坚持认为:在认识中,我们与关于事物原因的知识相关联,与表明灵魂的某种高贵知识本身相关联。[10]8因此,灵魂在认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是出于信仰的预设,而是可以验证的事实。
就具体的运作过程而言,灵魂能凭借其能力(即“诗性直觉”)与事物交流来探求自身,也通过“诗性直觉”证明自身存在的事实。[1]137马利坦表示:“因为诗性直觉产生在这幽深处……所有灵魂力量通过意向性情感共同经验到某种使它们苏醒的存在真实……诗人在这里经验尘世的事物,经验它们直到他能言说它们、言说自己。”[1]154因此,“诗性直觉”在其自身的实现中也保留了“经验性”(即与事物的接触能力)的层面,这就为其被经验性地讨论或间接性地证明提供了可能性。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证明“诗性直觉”存在?马利坦认为:“不论是画还是诗篇,这种作品都是被制成的对象——只是在作品中诗性直觉才达成对象化。而且它必须永远保持作为对象的稳定性和价值。”[1]141也就是说,作为超验之物的“诗性直觉”乃至灵魂的存在与运动,其凝固性的存在证明留存于作品之中,因此,我们对“诗性直觉”的确认需要借助于它停驻在艺术作品之上的痕迹。
那么,这样的一种“痕迹”究竟是什么?换言之,这种显现或“对象化”除了诉诸“相信”的层面之外,能否有其他的证明?或者说,这种“痕迹”能否经由更为具体的感性方式被观察者发现?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这种“痕迹”便是艺术作品对观看者的情感唤醒。而这种情感唤醒,其主要的实践手段仍是“意向性情感”。马利坦认为:凭借诗性认识和“意向性情感”的效力能够脱离自我中心的我(ego),并将其转化为一種创造性自我(self)。在此意义上,艾略特所提出的“非人格性”——“艺术家的进展是不断自我牺牲、不断人格消亡的过程”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消亡的是自我中心的我,但创造性自我得到了更好的维护。[1]158这种创造性自我是艺术家作为精神交往行动中的人,是作为人的个人(human person as person),而非作为个体的个人(human person as individual)。由于作为人的个人都具有相通精神本质,所以我们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在认识和爱的状态下与另一个和另一些交往。[1]156因而,艺术家留存在作品中“创造性自我”经由能够沟通物我的“意向性情感”而获得存在的确认。这样的存在呼唤沟通与交往,这一沟通不仅仅体现在创作中,也同样体现在鉴赏和审美体验的过程中。[2]38简而言之,那些能够令欣赏者产生沟通欲望的作品,能够引起个人情感共鸣的作品,以及通过该类作品所达到的交互性的“意向性情感”效应便是“诗性直觉”确实存在的证明。
但是,这样的“痕迹”或“证据”仍不是肉眼可清晰分辨的,它虽然确实存在,但却并非实体。这是由“意向性情感”的形式性与纯倾向性导致的。前文提到,“意向性情感”并非独立、抽象的实体,而是仅作为功能性的形式而存在。这便意味着它没有具象化的“肉身”。这与索绪尔对“语言”的论述十分一致。语言作为形式而非实质的存在,虽然纯然是心理层面的,但并非是抽象的。[11]23原因何在?在其语境中,“抽象”并不与“具象”相对,而与实在(real)相对。“抽象”更多地诉诸某种观念性质的东西,而这种观念性的产物未必是实在或真实的,它们可能仅仅来源于人的预设。譬如数学中的角度,便是人为抽象的结果。索绪尔认为,语言的非抽象性就奠基于构成语言的那种“联结”——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同意——是实在的。[12]23“意向性情感”亦然,虽然我们无法通过肉眼亲见其存在,但眼见未必为实,眼不见未必为虚,更何况“虚在”也是一种“在”。“意向性情感”作为形式,其本身并不能自证价值或存在,而只能在与他者的区别关系中获得存在。换言之,它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它同语言一样,通过主(欣赏者)客(艺术品)间的“联结”获得了不可磨灭的实在性,同时,这种“联结”还建立于艺术家及欣赏者之间,从而获得了集体性的同意。因此,“意向性情感”虽然不是实体,但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与其融为一体的“诗性直觉”的存在也是真实而非虚假的。通过由实在到“虚在”的转化,看似不可捉摸的“诗性直觉”就依靠“意向性情感”在作品中获得了一席经验之地。
然而,“意向性情感”对作为物质个体或自我中心的“我”的转化,以及对“创造性自我”的生成带来了一个理论盲点:“意向性的情感”还能够算是情感吗?它虽然拥有了意向性,并且能够作为形式而获得真实存在。但是,“情感”又在何处?它帮助人们脱离中心自我,但没有了自我,还有情感可言吗?人们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马利坦本人在修辞上的不彻底性或悖论性。作为“动物性情感”对立面的“意向性情感”,依然与前者共享“情感”这一内核,而作为自我中心的“我”对立面的“创造性自我”,也与前者一起面临“我”的检验,作者在否定之中却又无意识地肯定前者,看似对立的概念之间藕断丝连,这无疑会给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两组术语所面临的状况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自我”的悖论更多地来自于翻译的出入(2),而“情感”的悖论才值得讨论。
超越“自我”(ego)的情感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被转化为“意向性情感”如何可能?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自然很难理解这一悖论:如若“我”都不在了,那么情感又属于何人,来自于何处?然而,“意向性情感”本身就是超个人的,它并非个别人的一时冲动,它从“我”出发,并最终离弃了“自我”:凭借沟通主客的效力能够使创作者摆脱自我中心的“我”。这种情感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上帝之爱”,它具有普遍性,非限于一己且通向自身之外。马利坦认为:“诗之我”更接近于“圣人之我”,虽然目标不同,却都是献身的主体。[1]157这正与其“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立场相吻合。正如柯勒律治所说,主体是经由将自己客观地建构为自己而成为主体的,这意味着将自己视为他者。[13]181“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不仅意味着存在 “全然的他者”,还隐含着“自身的他者化”(self-othering),这导致马利坦在艺术创造领域以相互的、双重的“参与性”模式取代了单向的主体模型。[13]5在马利坦看来,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并不是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人格性(personality)不同于个体性(individuality),后者是对存在的限制,要从个人身上排除他人之所是,从而限定自我。而前者则意味着自身的内在性,同时需要认识的交往,需要爱。[1]156这种超越自我,面对其他个体的“爱”,便是“意向性情感”得以可能的条件,因为“爱”不但指向个体,也同时指向他者。马利坦的理论体系看似诉诸“智性”,并不追求神秘,但在其实际构想的核心部位,“信仰至上”的立场仍是不变的。只不过,他将“上帝之爱”推而广之,扩充为个体超越“自我”对他者的“爱”,这种类比是将人的灵魂结构看作上帝本身的分有,而其存在的确证最终只能诉诸体验。
结 语
在马利坦的艺术理论中,“诗性直觉”概念无疑获得了最多关注。但“意向性情感”才是使“诗性直觉”得以可能的根本要件。马利坦引入“意向性情感”,使之与纯质料的“动物性情感”相区分,突破了感伤浪漫诗学的窠臼。艺术作品的诞生,离不开“意向性情感”对艺术质料的赋形。作为非物质、纯倾向性的“意向性情感”,它能够使“动物性情感”指向自身之外,即从混沌的非形式走向形式。其次,“诗性直觉”存在属性与运作上的困境:在属性上,诗性直觉是“前反思”的,但在其运作过程中,艺术作品的表达与成形必须进入反思阶段。“意向性情感”是使“诗性直觉”完成这一过渡的重要媒介。因为在马利坦看来,反思性与意向性是同时诞生的,而“意向性情感”与“诗性直觉”又是同构异质的联结体。最后,“意向性情感”是“诗性直觉”存在的证据。“诗性直觉”虽然虚无缥缈,但在艺术创作与鉴赏中的共通感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情感唤醒的“痕迹”正是“意向性情感”纯倾向性存在的结果,离开了“意向性情感”,我们便失去了为“诗性直觉”奠基的可能。
注释:
(1)“直觉”一词在马利坦的用法中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哲学”的意义,意指无需中介的直接知识与即刻洞察,这意味着在理解问题之前没有其他先被知晓的对象作为使理解成为可能的条件。其二是“非哲学”的意义,它指的是一种“预言”(divination),这里强调的是认知活动在产生过程中的自发性(spontaneity)而非“哲学”意义上的直接性(immediacy),在这种状态中正确的观念(right idea)会自然地涌现在眼前。“诗性”在马利坦看来即某种预言性,它能够联系事物与人的内在存在。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中,马利坦的“诗性直觉”更多地使用“非哲學”层面上的含义。
(2)中译本将ego译成“我”,将self译成“自我”,便会造成上述疑难。应将self译作“自身”,因为在马利坦的术语使用中,self并不具备意识的自反性,这也与“诗性直觉”的前反思特征相吻合。
参考文献:
[1]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克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Jacques Maritain.Art and Scholasticism[M].(trans. Joseph W.Evan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4.
[3] 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4]让·多雅.马利丹[M].许崇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John Hanke.Maritain’s Ontology of The Work of Art[M]. Hague:Martinus Nijhoff, 1973.
[7]贝内德托·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焦万尼·维柯.新科学·上[M].朱光潜,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9]James G. Hanink.“Poetry, Beauty, and Contemplation: The Complete Aesthetics of Jacques Maritain by John G. Trapani”[J].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65, 2011(1).
[10]雅克·马利坦.科学与智慧[M].尹今黎,王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2]周丹.艺术:美的诗性生存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3]David Haney.The Challenge of Coleridge:Eth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Romanticism and Modern Philosophy[M].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