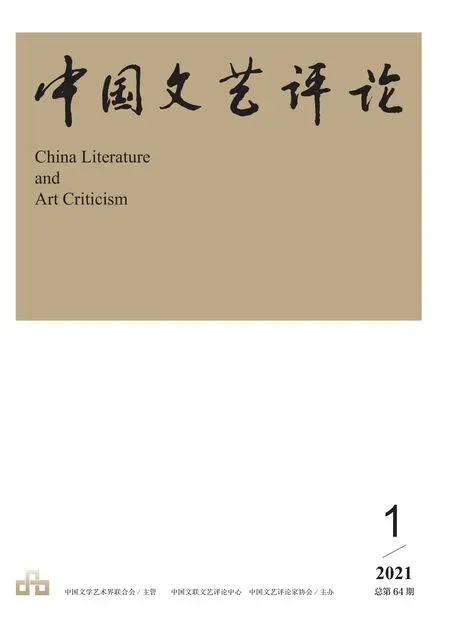脱俗 去杂 免酸
——访舞蹈理论评论家张苛
采访人:唐坤
书生意气 往昔峥嵘
唐坤(以下简称“唐”):
72年前,您作为华北大学三部的学生开启了艺术生涯,当时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在华北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您之后的艺术发展道路产生了哪些影响?张苛(以下简称“张”):
1949年,我还是一名教会学校的高中生,即将从武汉文华书院毕业,一心想着要投身革命,和几位意气相投的同学一商量便决定结伴去解放区报考“鲁艺”。这一路上颠沛流离,在国统区时还被当场拦下,书被撕得稀烂,最后跌跌撞撞到了解放区。当时我姐夫在清华任教,他建议我不妨试试报考华北大学,没想到竟然考上了。华北大学当时下设四部两院,校长是吴玉章。其中,“一部”就是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我所在的“三部”有文艺学院性质,下设工学团、文工团、美术工厂及乐器工厂,也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三部”实际上集中了不少原“鲁艺”的师资,前半年主要是政治学习,听取各种报告和讲座,强调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思想改造,宣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后半年则是专业学习,强调在生活中学习,再利用艺术改造生活,创作方法多选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我当时腰鼓打得不错,也会扭些秧歌,在建党节还去先农坛表演过腰鼓,但并没有想过要往舞蹈方面发展。那时,学校里已经开始忙着排练由胡沙和戴爱莲任导演的《人民胜利万岁》大歌舞,演出队伍由华北大学三部文艺演出队及当时文艺界的精英组成,之后在中南海怀仁堂成功上演。学生们的能力和各自擅长的领域也在这次大歌舞里得以充分展现,直接影响各自毕业后的去向,善舞的彭松、徐淑媖、隆荫培等人被分到舞蹈团。1950年年底我毕业了,被分配至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工作。也正是在这一年,党中央为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因素导致的民族隔阂,决定派团到各民族地区访问,于是从北京各文艺单位抽调人员。我有幸加入了由刘格平、费孝通带队的西南民族访问团的文艺队,兵分三路去西康、四川、云南、贵州,宣传民族政策、寻找素材,同时还举行慰问演出,为时近一年。我所在的二分团去的是云南,这期间我一直是跟胡松华搭档,后来胡松华调走了,郭淑珍就女扮男装跟我配合。文艺队少不了慰问演出,但队里大多都是学音乐出身的,演出时缺少舞蹈节目,于是我主动请缨,边干边学,阴差阳错地开启了自己的舞蹈生涯。
唐:
您参与创作的经典藏族民间舞蹈《草原上的热巴》、彝族舞剧《阿诗玛》已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这些作品背后真实的生成轨迹是什么?可以谈谈您当时和欧米加参老师等人合作的创作经历吗?张:
中央民族歌舞团在建团之初,就提出“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到生活中去建团”的口号。歌舞团里的年轻人背起行李卷儿,奔赴大西南,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道路,尤其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找文艺创作的源泉,在当地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养分。西南工作队的基本班底就是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工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前身),1953年,工作队在云南省迪庆州中甸县搜集歌舞素材,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期间正巧赶上端午节,当地的藏族同胞们在山上安营扎寨庆祝节日,欧米加参和妻子以及他的弟弟正好卖艺流浪到此。欧米加参的妻子个儿不高,身形灵活,她当时跳的那段铃鼓舞令人叫绝,譬如“送鼓平转”“猫跳翻身”“缠头拧身”等翻鼓动作后来成为我创作《草原上的热巴》里开场的素材。工作队的演员们当下就跟着反复学习揣摩,我们走时,索性就带上他们,将其吸纳进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受情境感染,我写了两首诗,《东方升起了金黄色的太阳》和《藏族青年骑马回家乡》,刊登于1953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稿费,那叫一个兴奋,赶紧给夫人做了身衣服。可以说,这一年的积累,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甚至是当地的风物传说,都成为我创作的一把钥匙,没准儿哪一天就在心中交汇奔涌。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我正在北京西北的南口长城劳动,当时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边军特意把我接回来,希望我能尽快编创一个藏族舞蹈。采风的素材正好大有作为,于是我以“热巴”为基础,运用不同藏区的舞蹈素材,譬如民间流传的“巴塘弦子”“踢踏舞”、寺庙宗教舞蹈中的“鹿舞”元素以及藏戏中的舞蹈技巧,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创作出《草原上的热巴》,并让戴爱莲先生过目,当时的领舞张曼茹,以及苗族舞蹈家金欧,均因这部作品而崭露头角。作品完成后,我又被送回劳动地继续改造。这部作品后来成为团里的代表剧目之一,并在国际上获奖。由于历史原因,“文革”结束后,我关于《草原上的热巴》的署名权方得以恢复。
图1 1983年,张苛在湖北恩施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指导排练
我有一个观点:艺术是最好的沟通合作桥梁。在创作彝族舞剧《阿诗玛》时,我们在保持鲜明民族特点的基础上运用了交响编舞和意识流手段,在那个年代不啻于一种颠覆观念的大胆尝试,也招致一些非议,譬如阶级性弱化,但随着演出的成功,这类质疑声渐渐消隐。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歌舞团的舞剧《阿诗玛》赴中国台湾交流,这是第一部在台湾演出的大陆舞剧,而当地的演出单位颇有些疑虑,生怕全剧充满阶级斗争意识,待演出结束后,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宝岛观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台湾同行问我《阿诗玛》是什么结构,我告诉他是“色块”。颜色是敏感的,不同的色块不仅是物理场,也是心理场,实际上《阿诗玛》的结构形式就是颜色流和心理场,追求的不是视觉真实,而是感觉上、情感上的真实。这种真实,让海峡两岸的舞蹈家心意相通、情意相投。
云彩南端的舞蹈
唐:
对于民间舞蹈研究者与创作者来说,田野采风都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入云南山区采风,据说还带着枪。还有一种说法是您曾三十余次深入云南采风,几乎已经成了半个云南人。您在采风时所秉持的立场、视角、态度乃至方法是什么?对现在的舞蹈采风,您有什么建议?张: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第一次随团去云南,大伙下了车一起朝城里走,第一个见到的便是聂耳的母亲,紧接着在昆明正义路遇到一个“红领巾”,我们领导就打趣地问:“小朋友,你长大后做什么?”“舞蹈!”这个“红领巾”就是周培武(知名舞蹈编导,舞剧《阿诗玛》编导之一)。
图2 20世纪90年代,张苛为创作舞剧《云海丰碑》在西双版纳采风
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南地区还未完全解放,工作队里的一位长笛手就在访问至四川甘孜州理塘县时不幸被叛匪杀害,年仅24岁。云南森林密布,多溶洞,持有枪械的叛匪非常猖獗,工作队中的女同志去采风有时不得不乔装打扮为男性。当时从北京去云南还没有通火车,更别说是飞机,我们坐着汽车一路颠簸,经成都、重庆,再至贵阳,还记得就在从贵州驶往云南的路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云南这边远远望去是一片耀眼的红土地,与贵州境内的土地颜色完全不同,泾渭分明,从此我就记住了这片红土地。我去过云南的各个地区,尤其是下面的县市乡镇,仅某些州的采风就不下30次。采风是创作的一种具体形式,对于创作人员来说,步子应扎实,而思维要活跃。构思始于观察——无论是创作前如采风时的观察,还是孩提时视觉感受的印象——总不能凭空想出个构思吧!那么创作呢?有人说“到舞蹈内部去寻找”,这话也对也不对。对是因为舞蹈终归是舞蹈,创作者应掌握舞蹈特征,谙熟结构之法、编舞之法的规律。不对是在于舞蹈是社会、自然环境、历史渊源、民族性格等通过舞蹈家实践的产物。我们常说“一个民族的舞蹈能透视一个民族”的道理就在于此。舞蹈其“内部”与“外部”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即使到“内部”去寻求,也必须联系“外部”的探索。我还是深信“生命之树常青”这句名言,要到生活中去,云南的舞蹈之树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紧紧抓住了红土地的根须。
唐:
您和云南舞蹈界可谓渊源颇深,也成为许多云南籍少数民族舞蹈家的挚友和长期合作者,譬如您曾多次担任杨丽萍舞剧的总顾问。您如何看待当下少数民族舞蹈人才培养的模式,这其中,成才是否有规律可言?张:
一想起云南,便想起云彩南端千姿百态的舞蹈翻涌似海的意象。而当我一想到这舞的山、舞的海,却又叠印出许多朋友的面容,如老一辈的毛相、刀美兰、刘金吾、朱兰芳……也有相对年轻一代的杨丽萍、陶春、苏自红……这一拨儿。这些人都是独特的,易感的,爱思考的,又都对自己的家乡和民族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他们的舞蹈艺术有着独特的构思和独特的形式。陶春比较能放得开,人很机敏,当演员时就琢磨着编舞,当编导时也从未忘记演,他现在不仅蜚声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而杨丽萍就是从红土地上长出来的,十二三岁就跟着大人在那儿跳,她常跟我聊起自己对于家乡最初的印象和记忆:小时候吃水果糖,糖纸是各种颜色的玻璃纸,把它蒙在眼睛上,这世界完全变样了。她所要追寻的正是这个,也许可以理解为艺术的“陌生化”——将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回归到新奇的状态,她对生活的感知不仅仅是细腻,而是通透。让她正规地跳一段成品舞蹈,她不会,模仿力极差,但如果把创作意图讲清楚,她能给你一个惊喜,甚至是奇迹,充分发挥出演员的再创造能力。她动作的韵味是熏出来的,“土”,却带着“土风”升华。我跟小杨(杨丽萍)合作过很多次,不仅仅是参加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的《雀之灵》,还包括许多其他大小作品,其中有个节目叫《雨丝》。当时她刚从云南回来,说云南总下雨,想用滑跪来表现,我一看,她的腿都滑破了,我说不行,演完你的腿也没了。我们俩坐在排练场里苦思冥想,试图推翻原来的设计,既要出新又要到位,想了好几个点,但始终不是很满意。近半夜12点,她突然将手举至面庞前,微微颤动着手指——这不就是准确的艺术形象吗?我一想,这雨丝不就似老天撒下的带着情感的网,而云南农村女性通常遇雨不躲,她好像是被这雨所融化了,不是拒绝,而是全情投入和满心喜悦。有了形象和创作意图,节目很快就定了下来。倘若说舞蹈成才真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必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珍贵天赋,无论是捕捉细节的能力,还是思维的密度、广度和频率,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图3 20世纪80年代,张苛和杨丽萍一起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排练厅编排《火塘》
民族民间舞不是“小摆设”
唐:
有人称您是“民族民间舞的百科全书”,但可能许多人并不知道是您直接促成了1980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举办,可否详细说下这其中的故事?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后续又举办了四次,您如何评价这种“国家在场”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图4 20世纪90年代,张苛为创作舞蹈诗《啊,傈僳》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采风
张:
1979 年,为拨乱反正,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小型调查团,我作为国家民委的代表与调查团一起调研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的文艺界情况。回来后,我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组织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来振兴民族民间舞蹈。国家民委负责人把我的信转给了中央,中央非常认可这个建议,批准了这一活动,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国家民委。但当年举办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从1980年开始第一次正式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首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不仅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和节目参加,而且当时尚未确定民族识别的苦聪人、夏尔巴人、僜人,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两千多名优秀演员荟萃北京,四百多个节目中有140个舞蹈,想想这是怎样的盛况?当时活动包下了整个西苑饭店,所有演员都住在那儿,他们观摩其他代表队的演出,互相交流,每一场演出都要研讨,大家提意见,好在哪儿,不好又是哪儿,相关报道几乎每天都见诸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与此同时,由于人员众多,各种花费开销不菲,最终决定五年举办一届,后来自2001年起又陆续举办了几届,但已经达不到首届的规模。就我担任过评委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会演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审美为导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一直很重视少数民族艺术的发展,当时的舞蹈界能涌现出一大批少数民族舞蹈人才与国家的文艺政策、民族政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国家层面上的鼓励和支持,尊重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逻辑,将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置于与社会文化更为良性的互动关系之上,不仅仅是在展现少数民族舞蹈五彩斑斓的形象,更是在演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也有利于我们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的视野更加开阔,格局更加合理,善莫大焉。唐:
现在舞台上的某些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常被诟病趋于雷同,且无鲜明特色,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张:
其实不仅仅是民族民间舞作品之间存在雷同。一次,有位知名的编导朋友邀我去某舞蹈学院给他新创作的古典舞提意见,我坐在那儿看了半天,经人提醒才意识到自己竟进错了朝鲜舞排练课教室,而我居然并未发现,因为相似到已经辨认不清舞种的属性。我们很早以前就强调向“民族民间”学习,要求学会、学像、学好,其中“学像”在当时的语境下被认为是主要的。但实际上,往往学着学着就走了样。朝哪儿变呢?靠什么变呢?民间靠古典、古典靠芭蕾、芭蕾靠现代、台下靠台上……靠来靠去,原来的舞姿动作散了架,原来的风格韵味消失了;又因为你靠我,我靠你,大家互相靠成了一个样。早在20世纪80年代,保护舞蹈“原生态”的问题就是舞蹈界的热点,引发了众人的讨论乃至关注,为此还举办过针对原生态舞蹈传承的“艺人传习所”,这就涉及到继承与借鉴、保护与发展、学习与运用、意味与形式、“原生态”与现代技法思维的撞击。在杨丽萍自编自演的群舞《女儿国》里,合作者就是来自于云南安宁“艺人传习所”的民间艺人,民间舞跳得非常娴熟,但上了台就分不清方位。两个月的磨合后,民间艺人变了,杨丽萍也变了,没变的是民间艺人身上的“原生态”和杨丽萍一贯的奇思怪想。这证实了一个问题:要抓“原生态”,这是根,是源;而借鉴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要的。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物理的,不能是生搬硬套的,不能是加法,而应该是化合的、融合的,是保护特色风格又发扬特色风格的。
唐: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舞蹈的发展,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对于中国舞蹈尤其是民族民间舞蹈的未来,您又有怎样的展望和期待?张:
舞蹈的特征在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中呈现得异常鲜明,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优秀舞蹈作品中就得到了证实。如同深与宽的辩证关系,少数民族舞蹈在舞蹈特征上的探索,也正是在拓展与探掘的关系中进行的。如果从题材上看,包罗自古到今、自然界万物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像任何艺术品种一样,有自身的擅长和局限,少数民族舞蹈更多属于表现民俗风情的范畴,对现实题材的开掘不够宽广,也不够深入。但是少数民族舞蹈没有固定的模式、程式,与生活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在题材的开掘上还有宽广的领域。而就创作方法而言,这数十年来的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因编导而异,呈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但尚未形成有影响的艺术流派。未来,更大的灵活性表现在原始状态和多属自娱性的舞蹈走上舞台时,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以民族的习惯为依据,做大量的吸收、借鉴,却不离民族艺术发展的轨迹。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努力是努力的,重视也是重视的,可是它不是“小摆设”。这其中有创作者的问题,也有舆论提倡的问题,当然,创作者自身的提高尤为重要,不要永远站在一个坝子中间,要有高原,更要有高峰。民族舞蹈有自己的风格特色,随时间变迁而变化,让风格特色透出时代精神,融两者为一体,这是今后少数民族舞蹈艺术发展的重要课题。
鱼与“渔”
唐:
作为一名有建树的舞蹈编导,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您后期转向理论评论?这与20世纪8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的“民舞消亡”论是否有直接关联?张:
确实曾有过一段时间大家对民族舞蹈颇有争议,认为民族舞蹈过时了,不吃香了;认为不是如何继承民族舞蹈传统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继承的问题;认为只有现代舞才能表现现实题材等。但最让我困扰的还不是众人对民族舞蹈的看法,而是去各地辅导经常会遇到“究竟怎么编?”这一问题,也就是具体如何去创作一个节目,至于理论,则往往被大家选择性地漠然置之,即使有几位勉强来听,也是心不在焉,好不容易听完,也只对具体的编创层面感兴趣,也就是对“鱼”有兴趣,对“渔”却无感。理论的价值在有些人的天平上几乎接近于零,莫非理论真是灰色的?这让我苦思不解,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脑子里这个“理论到底有多大作用”的疙瘩,竟在事实面前冰释了。“文革”结束后,舞蹈界在欣喜若狂的情绪里有一种饥渴感。譬如“解放思想”,知易行难,具体来说,创作、表演、教学该如何打破旧程式,如何适应新形势,如何满足观众的需求?……我们犹豫、徘徊、停滞。演员、编导、教员,当然也有理论工作者,都急切于求知解惑,都有如饥似渴的同感。也几乎是自发的,在那时,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舞蹈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北京的大冷天,很多年近半百的同行们顶风冒雪骑车去北京师范大学听美学讲座。另一现象是我们爱“吵”——争论,私下“吵”,会上“吵”,写文章也“吵”,争个不停。但事隔不久,《玉卿嫂》《黄土地》出来了,《鸣凤之死》出来了,《铜雀伎》《金舞银饰》出来了,我认为我们舞蹈艺术有所前进和发展,都与“吵”、与舞蹈理论评论工作的开展分不开。问题是,我们理论评论工作者的作用鲜为人知,我们的价值少有人评说,我们往往被忽视、遗忘,甚至习惯了连自己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但这又像理论的特征。如果解决的只是个别的问题,如像扑灭眼前的火那样急需的,那当然显眼,也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那是不是理论呢?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解决个别的问题,而是寻求规律性;它的价值也不仅仅闪光在一些现象上,而是能照亮本质。它有无用之大用。

图5 20世纪90年代,张苛在内蒙舞蹈编导训练班授课
唐:
对于舞蹈编创,您现在还关心什么样的问题?张:
缺少好作品,当然这也跟我现在年纪大了有关——看得少,也就显得孤陋寡闻,所以这样的说法也许有失公允。近几年去剧院看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演出,但都几乎等不到剧终就想撤离……还是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好作品,有品位,更有品格,即做到“脱俗、去杂、免酸”。此话怎讲?“脱俗”指的是要避免人云亦云,一个舞蹈作品选材的角度、立意的深浅、构思的巧拙、手段的新旧、风格的浓淡……高下立现,它实际上是创造性的、闪烁着智慧火花的劳动,也就是“出新”。要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的条条框框出发;要为表现内容去创新求异,而不是为新而新;不排斥向外来艺术学习借鉴,但要坚持在“我”的基础上出新。所谓“去杂”就是去除芜杂,我们常说“繁花似锦”,但庞杂的繁花未必能成锦绣。从如此多的素材中挑选哪些动作作为元素,如何有机穿插组织,同时又避免把规律性搞成了“模具”,这些都是学问,因此从创作心态到艺术实践都要盘活素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这“去杂”也可以是一种心态,对艺术不能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多些纯粹,如果为了某种非创作动机去生编硬造,终归会成为伤仲永的故事。“免酸”是指创作不要有酸腐气,气韵要辽阔高远,不负天地。“活在当下、悟在心中,便是吴哥永恒的微笑”。这是我当时编导班的学生陶春在柬埔寨所编创的舞剧《吴哥的微笑》中的解说词。它讲述的不是中国故事,但却是中国的创意、中国的理念、中国的手法以及中国的管理。我看过现场演出,感慨其佛不能大笑又不能不笑的微妙处可谓拿捏得当,而观演完毕,信步走出,却见剧院前正好有一汪塘水,而这演出不正好似其文化的倒影,千年的微笑便是其中真意。生活是浩瀚的,我们的思维愈活跃,手段愈多,路子就会愈走愈宽。访后跋语:
冬日正午过后的阳光里,木地板上摇曳着斑斑点点的光影,客厅被书架环绕着,90岁的张苛老师戴着棉帽坐在沙发上微笑着倾身向我伸出手。握手的瞬间,对视的刹那,我脑海里无端地冒出小时候所看动画片里大力水手的形象——突出的额头和大鼻子,还有那顶不可或缺的帽子……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耿直、无畏、善良,还有些小俏皮,才是两人的共通之处。即便是这般年纪,即便是身体欠安,说起舞蹈,张苛老师依旧会兴奋地击掌而笑,或干脆停下来沉浸在昔日的情绪中,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太多风霜。而张苛老师的夫人——同为习舞出身的金立勤老师则一直静静地端坐在我们对面,偶尔提醒或纠正一下张苛老师忘却的内容。
张苛老师是湖北人,18岁便到了北京,说话却带着颇为浓重的云南口音,这大概与他长年与云南有密切交集相关。采访伊始,张苛老师也坚持从云南编导和舞者谈起,因为双方相互成就,像是一场共同完成的修行。张苛老师自我调侃是“半路出家”,从舞蹈演员转编导,继而又转理论评论乃至舞蹈教育,由于历史原因还曾尝试过填词作诗、打追光、换幻灯片、到工厂里使钢锉……在人生的每一处拐角随着境遇辗转,体验着不同的社会生活和世间人情,慢慢濡化,乃至一点一点地贯穿和左右着他如何创作舞蹈、如何评判舞蹈。而张苛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末慨叹的那句“可能有天生的舞蹈家,却没有天生的舞蹈理论家”,大概也道出了他大半生在舞蹈界摸爬滚打后的一种“体悟”。区分舞蹈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从其擅长的舞种加以区分;也可以从其涉足的领域背景进行划分;还可以通过世代来加以分隔,但张苛老师似乎都可以纳入这些不同的序列,一直持续地、默默地为舞蹈付出着,用舞蹈搭起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多元而充满生机,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脱俗、去杂、免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