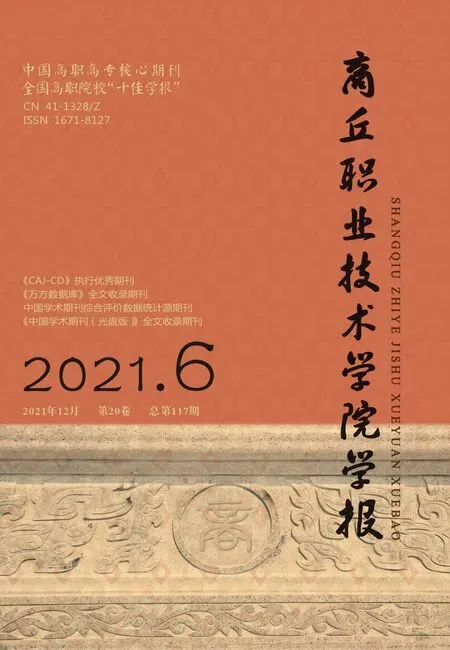《果园城记》的故乡书写
毛康丽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果园城记》是师陀的代表作之一。《果园城记》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家1938年至1946年间与果园城相关的18篇小说。师陀在《果园城记》中描绘出一个立体的中原小城——果园城。果园城一改河南往日贫瘠、落后的面貌,呈现出一派温馨安逸的乡村景象。师陀以其独特的视角切入果园城的社会结构,为河南的文学地图增添上重要的一笔。
一、《果园城记》的文学景观
在作者的笔下,果园城的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师陀在《果园城记》中为果园城奠定了明亮的底色:“这正是阳光照耀着的下午,越过无际的苍黄色平野,远处宛如水彩画的墨影,应着车声在慢慢移动。”[1]1这一画面安静、辽阔,充满古典美。随着文章的展开,作者重点描述了河岸、田野、古城下的城坡、果园城外的天空以及果园等景象。
作者的描述是由城外向城内展开的,通往果园城的是一条阳光照耀的大路,路两边的郊野上是新犁的田地、硕果累累的果园以及成片的林场。田野上是明净的秋日晴空和天边慢慢长起的云。随着与果园城距离的缩短,城郊附近的景物陆续进入读者的视野。河岸上种着柳树,河岸下长着鸭跖草、蒺藜和蒿蓟等各种杂草。视线向下可以看见深绿的水面、水面上远去的白帆和漫天的霞光。河流蜿蜒流向远方,进入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走过河流后是长满青草的城坡和古老的城墙。师陀通过马叔敖的视角从远郊的田野到近郊的河流再到城郊的草地和古老的城墙,由远及近,为读者介绍了北方小城具体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布局。果园城见证了师陀的青春和故事,师陀对果园城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果园城的一幕幕景色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难以忘记。师陀在《果园城记》中这样写道:“我缓缓向前,这里的一切全对我怀着情意。久违了呵!曾经走过无数人的这河岸上的泥土,曾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踩过,在我的脚下叹息似的沙沙的发出响声,一草一木全现出笑容向我点头。”[1]4因此,师陀的果园城多是晴天,没有萧瑟和凄凉,处处透露出宁静和谐,俨然一副桃花源的样子,奏响了一曲美妙的田园牧歌。师陀对于果园城的景观描写蕴含了深厚的思乡之情以及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写出了返乡游子眼中的故乡景象。
“一个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景观,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属性,还有人文属性。”[2]因此,人文景观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相对于果园城自然景观的优美宁静,果园城人文景观的呈现则更加复杂。一方面,其以一种衰败、压抑的景象表现社会的黑暗和绝望;另一方面,其则通过生机勃勃的城隍庙和充满烟火气息的街道展现着生活的安逸舒适。师陀用文字为我们绘制出果园城的城市地图。他在《果园城记》的开始就介绍了果园城的布局:“此外这里还有一家中学,两家小学,一个诗社,三个善堂,两个也许四个豆腐作坊,一家糟房。”[1]8-9随着叙述的推进,果园城的结构愈加明晰,依据作者其中蕴含的不同感情可将文中勾勒的人文景观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果园城的城墙、塔、布政第、进士第和公馆等建筑。这类建筑往日辉煌,今日已然衰败。左家悬挂着“传胪”匾额的大门,胡家的布政第以及马家的高墙,这些建筑既“显示了乡土中国权力格局的差异地理学”[3],又表现出它们主人往日的权势。如今,在师陀的描述中,这些庭院和门楼却十分破旧。朱魁武的公馆又大又深、毫无生气,像巨大坟墓。刘爷的房屋寥落,马家的高墙已被夷为平地,胡家的布政第挂满了蛛网、灰穗。唯有塔依旧屹立在果园城中“隐喻着时间的强大无情与人世的无常脆弱”[4]。二是繁华热闹的城隍庙以及温馨闲适的街道。城隍庙及其周边是与说书人、卖油翁和邮差先生以及卖货郎相关的地方,这里熙熙攘攘,充满烟火气和勃勃生机,展现了一种与传统建筑完全不同的面貌。相比城隍庙的嘈杂,宁静和闲适是街道的主调。街道上时常卧着打鼾的狗,摇着尾巴过马路的猪和坐在门口同邻人悄声聊天的女人们,呈现出一种家长里短的脉脉温情。三是庭院和庭院上空明净的天空。果园城的女人们被困在封闭的庭院中。素姑的院子是寂静的,只有凋零的丝瓜棚和寥寥的花草,处处透露出衰败的气息。庭院其实是她们的牢房,她们在庭院中消耗生命。庭院的衰落破败正是她们生活状态的体现。除了庭院外,天空也常出现在作者笔下,但与庭院不同的是天空代表着希望与期盼。素姑眼中的天空是高的,蓝的,清澈的。在《颜料盒》中,作者以天空作为文章的结尾:“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地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不变的、痛苦的,沉重地响着,好像在钉一个棺盖。”[1]104远处的天空和树林的锤声相互对应,更显出天空的美好与遥远。在师陀笔下,公馆虽然高大,但萧条破败,但果园城的街道却总是充满生机,庭院的天空也是清澈干净的。这一对照蕴含了师陀对于底层民众的同情,对于压迫者的憎恶。
二、果园城景观呈现的原因
在师陀笔下,果园城之所以被如此清晰且生动地描写,是因为它是作者以故乡为原型创作出来的。果园城的成功塑造与师陀对故乡的了解密不可分。师陀曾说过:“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个活的人。”[5]268若要写出这样一个小城,师陀需要对中国的小城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1910年,师陀出生于河南杞县,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1925年至1931年,师陀在河南开封读书。1931年,师陀离开家乡,奔赴北京。1936年,师陀从北京迁往上海。纵观师陀写作《果园城记》前的人生经历,师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杞县度过,其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了解大多数也源于家乡杞县。在河南郾城度过的20余天虽然激发了师陀写作《果园城记》的想法,但并不足以支撑他写出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师陀曾说:“那么他假使有机会看见这本小书——果园城的一角,可能认为跟他的果园城大有出入。这是我的果园城。其中的人物是我习知的人物,事件是我习知的事件,可又不尽是某人的写照或某事的拓本。”[5]268-269由此可见,果园城是师陀在故乡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是属于他自己的,并不是友人的郾城。
在地域文化上,果园城熔铸了河南的文化特征。一方面,开封作为八朝古都,对于封建的传统势力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敬。开封气候宜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有很大的优势,农耕文明十分发达,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在这里汇集、发展。果园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正是道家顺从自然规律的体现,而对于布政第和朱魁武这些旧势力的崇拜和迷信则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河南作为中原腹地,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久经战乱之苦。河南临近黄河,经常决口,多次发生洪水灾害。各种灾难磨炼出河南人民坚韧、勤奋、吃苦耐劳的品格。在果园城中,人们对于苦难都有一个宽容、豁达的态度。
在结构布局中,果园城的建筑在杞县都可以找到。1985年,师陀返乡,曾带领刘增杰先生游览杞县县城。据刘先生回忆,城隍庙、小西门以及书中提及的公馆在杞县都是真实存在的。在文中不止一次被提起的塔也有原型,即大云寺塔。大云寺塔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城南25公里瓦岗村大云寺旧址上,是一座八角七级楼阁式的砖塔。师陀将大云寺塔和杞县城楼融合在一起,使塔的意蕴更加丰富,塔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权力的象征。城隍庙也是真实存在的,根据史料记载,杞县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与县衙、文庙并称县城三大建筑。
不仅是建筑,《果园城记》中的人、事、物很多也源于师陀的回忆。师陀童年时期曾在城隍庙听过书,说书人一章就是师陀根据自己的童年记忆加工而成的。《期待》中为革命牺牲的年轻人则是依据共产党员马培义创作出来的。杞县一直有“马孟侯,边赵刘”的说法,这六大家族是《果园城记》中胡、左、马、刘四大家族的原型。
《果园城记》不仅是作者故乡的艺术化呈现,也可看作是作者个人经历和情感在作品中的投影。1925年,师陀前往开封求学,在求学过程中接触到进步思想,“并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过一个小刊物《金柝》”[6]。1931年,师陀假借读大学为名北上。北京是新文化的发源地,各种文化思潮在这里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师陀得以接收到了不同的思想。师陀在北京参加反帝大同盟,和汪金丁等人创办刊物,结识多个左联作家。同时,北京作为封建势力的根据地,是明清两朝的故都,权力和等级观念已经深深刻在人们心中。收录在刘增杰先生编校的《师陀全集》中的师陀的回忆漫笔《两次去北平》,讲述了师陀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师陀眼中的北京是破败的、萧条的,封建王朝的权力制度被渐渐瓦解,新的国家悄悄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与旧的权力规则的激烈交锋使师陀对于权力的变更也更加敏感。同时,北京也是新旧文化角斗的战场,师陀在北京感受到了新旧文化的冲突。在新文化和权力视角的熏染下,师陀以现代性的视野看待果园城,果园城的腐朽落后便一览无遗。《里门拾记》是师陀原乡志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师陀在《里门拾记》中所描述的故乡是黑暗的、罪恶的,所描写的重点在病态的社会和畸形的生活方式上,常被看作是有意识地反田园叙事。宗法制社会的落后与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导致社会矛盾尤为激烈,作者对故乡也尤为排斥,认为“倒以为能在那里住一天的人,世间的事,便再没有不能忍受得了”[7],所以,《里门拾记》中的分裂性降低了,代之的是强烈的讽刺和批判。在《果园城记》中,师陀沿用了现代性的眼光回望故乡,揭示了故乡的社会结构和由来已久的弊病,也显示走向没落的命运以及原著居民落后、颓废的精神状态。与《里门拾记》不同的是,虽然《果园城记》中的人文景观底色黯淡,但仍存在一抹亮色。钱理群先生认为:“在这里,仍然显示了作家对生命本体的一种乐观的信任与期待。”[8]这与师陀在上海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1936年,师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上海的经济领先于全国,是现代化都市的代表。1937年,我国开始全面抗战,上海沦为文化上的孤岛。师陀被强制放弃写作,失去经济来源,加之当时全国都处于一个物资贫乏的境地,他的经济更是拮据,最后只能搬到一个花园别墅的亭子间里。师陀将这个八尺大的阁楼叫作饿夫墓,足以看出他对自己生活状况是很不满意的。师陀在上海生活期间,除创作了《果园城记》外,还写了一部分与上海有关的作品,如散文集《上海手札》、长篇小说《结婚》等。在《上海手札》的后记中,师陀曾说:“这些所谓‘手札’的一至十三写成于二十八年六月中旬到九月初,十六至十八写成于二十九年六月下旬,中间两篇写成的时日目前已不记得,想来大约是在二十八年年底。”[9]由此可见,《果园城记》与《上海手札》的写作时间相近,然而两部作品中蕴含的感情却截然不同。师陀笔下的上海是虚伪的、冷漠的,这里的人与人之间都隔着厚厚的膜,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享乐,他人的痛苦和民族的危难似乎与他们全不相干。师陀在上海看到了商品经济下人的异化,现代都市人情感上的缺失和性格上的缺陷。上海腐朽的一面让师陀对现代文化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师陀一直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审视上海,他眼中的上海无疑是片面的。在上海,师陀无法得到情感上的归属感。思想上的迷茫、经济上的窘迫、情感上无处寄托,让师陀重新将目光投向故乡。师陀开始怀念农村温情、纯净的人际关系和优美、辽阔的乡间景象。因此,作者对于果园城的描述相对平和,不再进行一味地批判。此时,《果园城记》中呈现的故乡与《里门拾记》中呈现的故乡相比少了些苍凉,多了些温暖。
三、师陀故乡书写的意义
在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作家描绘出许多不同的地理风光和乡土人情,萧红的呼兰河,废名的黄梅乡村,沈从文的湘西。然而在师陀书写果园城之前,河南似乎被人遗忘了。随着唐宋以来的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北上,河南渐渐没落,不再有往日的繁华与辉煌,只剩下苦难与战争。贫穷、愚昧、落后似乎成为河南的代名词。但是,河南在中国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河南则居于中原的中心位置。中原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河南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河南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的发展史。因此,河南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被磨灭的。师陀所写的自己眼中的河南,为中国文学版图补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师陀身上既有现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当一部分作家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些作家接受了先进的教育,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他们在作品中回望故乡时,或批判,或认同,抑或两者兼有。如:废名的作品既有对人性美的赞颂,也有对乡土困境的叩问;沙汀的作品中刻画了贫苦农民、土豪劣绅的形象,表达了对于四川广大农民的同情和农村腐朽势力的揭露和讽刺。师陀和这些作家有相同的人生经历,在其作品中表露出与这些作家相似的情感,但是,师陀作品的独特性更加突出。首先,《果园城记》不局限于某个侧面的展现,力图从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典型的中原小城。其次,相较于同类型的作品,师陀在《果园城记》中宣泄的感情更加复杂,对于故乡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社会的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悲伤也有期望,更有思念。最后,《果园城记》并不是师陀首次书写故乡,在《里门拾记》《落日光》中就有过尝试,但《果园城记》中呈现的故乡是他对于故乡的最终印象。这一印象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结合师陀的人生经历和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心路历程。
历史上的河南似乎总与郑人买履、揠苗助长这些贬义词联系在一起,杞县则以“杞人忧天”一词为世人所知。在当代文学史上,无论是阎连科的《丁庄梦》还是刘震云的《温故1942》,展现的都是河南的困窘和落魄。相较于这些作家,师陀眼中的河南是不同的。他将自己作为中原大地的一分子,从内部讲述其所见所闻,展现河南大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象。师陀生于中原,长于中原,对这一片土地不仅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更有极强的认同感。师陀笔下的河南有着蔓延至天际的麦田,清澈的小河,闪着金星的泥土,奔跑的孩子,赶着耕牛回家的农人,夕阳映照下的古城墙和屹立数年的塔。这里土地富饶、人民淳朴善良,没有连年的战争、遍地的饿殍。师陀为我们揭开了那个困窘、衰败的河南的另一面,让读者对于河南、对于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师陀的《果园城记》反映了当时中国乡土小城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时代浪潮中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果园城是由实际控制者、依附控制者的无赖、地主以及被控制者三部分组成。实际控制者由朱魁武以及与之相关的胡、左、马、刘四大家族组成。他们有着显赫的家族历史,在果园城盘踞多年,有深厚的势力,依靠地主、无赖、控制果园城的方方面面。无赖、地主则是朱魁武等人统治果园城的爪牙,他们分布在果园城的各种机关、各个地方,如北门街的好汉爷依仗朱魁武的权势在城门口向过往的小贩收“税”,挨家挨户收礼。果园城的女人、农民、手艺人生活在他们的统治下,女人们更是被作为物品困于庭院。然而,作为权力象征的公馆、城楼此时只剩下断壁残垣,这显示着以朱魁武为代表的绅士集团的衰败且无法挽回。朱魁武、刘爷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胡家兄妹二人无力维护家族荣耀。年长的一辈无力支持现状,新的血液又难以为继,旧势力的权力衔接已出现断层。以徐立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又不被果园城的原著居民理解,也没有人认同他们的做法。果园城旧有的统治者已无法维护自身的权力,新社会制度的代表力量又受到排斥,师陀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处于时代浪潮中的北方小城的尴尬境地,从内部观察并表现了小城的社会结构。果园城是师陀虚构出来的小城,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果园城又是师陀在故乡杞县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是众多中原小城的缩影。师陀在《果园城记》中表现了乡土农村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缺陷和走向衰落的趋势是河南乃至整个中国当时面临的真实困境,其中蕴含的感情也是旅居在外的知识分子对于故乡情感的全面展现。
师陀与故乡的关系经历了认同、反叛、再审视三种不同的态度。这三种不同的态度与师陀个人的地理经验关系密切,以开封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北京为代表的新文化,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商业文化,以及开封、北京、上海三地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对故乡的态度。师陀对于故乡的刻画经历了《里门拾记》《落日光》到《果园城记》的转变,体现了师陀在三种文化影响下对故乡态度的变化。脉脉温情是难以淡化的底色,故乡的衰败和社会结构的弊病正是现代性视角给他的启示,故乡纯净的人际关系和质朴的人性的开掘是上海给师陀带来的影响。从师陀对故乡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当时处于时代浪潮中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抉择与挣扎。不止师陀,许多乡土作家的作品中都表现出这种分裂性。这是当时时代风潮和文化角斗在个人身上的显现,师陀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动荡、各类文化交织的年代里,离乡背井的乡村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思想困境。因此,师陀与故乡关系的演变过程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参考,也为我们阅读现代作家作品、了解作家心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果园城记》是师陀以故乡为原型,杂取河南郾城等地区塑造出的中原小城。师陀描绘了小城的自然风光、地理环境、空间布局和风物人事,为河南的文学版图增添了新的坐标,丰富了文学版图的内涵。同时,师陀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果园城记》中如此复杂矛盾的情感正是他对故乡情感的集中体现。此种情感既是多方文化博弈产生的结果,也是作家的人生经历在作品中的显现,这为我们了解那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变迁提供了途径。
——师陀小说《争斗》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