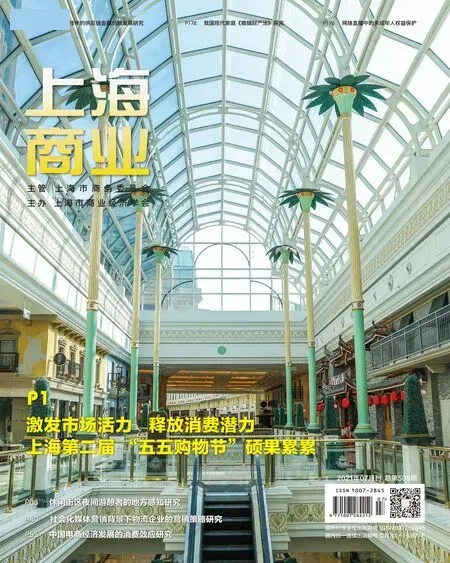网络直播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廖崯淇 阳相翼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前言
网络直播,由于受制于即时性,增加了直播内容的管理难度,导致直播内容参差不齐,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产生了诸如未成年人高额打赏、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违规信息传播以及未成年人权益遭受不法侵害,权利救济无果等法律问题。为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不受侵害,本文通过建议国家制定相关法规,建设行业自律规范,促进网络直播平台完善履行监管义务,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 网络直播中未成年人权益受损现状分析
(一) 未成年人作为主播的权益受损现状分析
《2016年直播行业洞察报告》统计数据表明,在网络主播总数中,作为未成年人的网络主播数量占总人数比例为12%,而这仅仅调查了11岁到16岁的网络主播的数据信息,由此可见现今未成年主播数量的惊人程度。由于未成年人主播大多心智不够成熟,导致违反公序良俗的直播内容发生;同时还存在一些未成年人主播,在“粉丝”的诱惑下,做出不端行为;此外还出现一些未成年主播中途辍学等情况。因此,《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明确约定,“不向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开通主播注册途径”,禁止未成年人进行直播行为。湖北武汉市发布的《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48条第4 款作为地方性法律法规首次将网络直播行为通过民法中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分别对待相关规章制度都对未成年主播与直播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只是地方性条例和行业公约尚不具备全国约束力。
但是由于网络主播与其所属的公会(经济公司)、直播平台之间关系非常杂乱,而作为未成年人的主播与其签约的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因为目前未成年主播与网络直播平台的雇佣劳动合同关系问题,其实并不符合劳社部对未成年人特殊用工的限定条件,由此,网络主播与平台之间的签订的雇佣关系合同更类似于是合同性质的非典型合同关系,暂时由民法进行规制。根据我国《民法典》十七条 、第十八条 以及第十九条的规定,未成年人主播与直播平台签订合约显然是并不符合未成年人的智力水平、阅历的,可能构成雇佣童工,侵犯了未成年主播的权益。
此外,未成年人辍学直播的现状,也明显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规定。
(二) 未成年人作为受众的权益受损分析
2017年11月,16岁男孩因为网络直播打赏花掉了母亲赚来的四十万;2018年10月,9岁女童为了打赏喜欢的网络主播一个月就花掉三万;相似的是,在2019年4月,位于河南一名9岁男孩因为打赏主播两月花光了父母10万存款。在网络直播领域,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发展尚不成熟,分辨事物的能力较弱,难经主播的循循诱导,再加上大部分未成年人阅历浅薄,对金钱敏感度不高,对新事物的好奇,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和快捷支付,致使一些未成年人经常做出高额打赏的行为。
而依据我国《民法典》有关规定 ,在网络直播领域中,网络直播受众打赏相应主播的行为可以视作其对主播一种赠与行为,未成年人打赏与主播应当视为二者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关系,可以通过《民法典》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的规定,依照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通过法定监护人的追认来确定打赏行为的效力或者依法予以解除。当前我国未成年人高额打赏退回困难,明显侵犯了有关赠与合同的撤销权。
(三) 未成年人作为主播或受众共同受损权益现状分析
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事权利,使得其权利主体有权自我地决定对他人渗入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的范围,拥有对是否向他人公开自己的私密的自由和决择权,也就是拥有对公开的程度进行限制的自由。现如今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隐私不遭受他人的侵犯,然而在网络直播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一个被摄像头包围的年代,个人隐私权的维护显得异常的艰难。在网络直播盛行的形势下,网络主播为了获得网友的喜爱,带来收益,经常会展示其私生活的一面景象,这也成为了备受当下关注网络直播的形式。与此同时,网络主播为了大量圈粉,由于受众的窥私欲,致使其公然侵犯他人隐私权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而由于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自保能力较弱,在直播过程中个人的隐私权非常易于遭受他人的侵害,作为未成年主播在进行直播过程中存在被诱使或不小心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可能性,导致其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的对象,此外未成年人也存在被他人暴露在直播镜头下的可能,从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暴露出隐私。未成年人隐私的泄漏极易于使他们产生潜在的危害,例如使得这些未成年人遭受诱骗,成为不法分子的施加伤害对象等等事件发生风险提高。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怎样保障未成年人主播的隐私权,何以认定主播侵犯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公共空间下的直播行为民众是否有隐私权保护,网络直播过程中未成年人误闯入直播画面是否属于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这一系列问题尚待深究。与此同时,对于网络直播侵犯他人隐私权,其责任应当落在何处,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的责任又如何划分,尚未明了。
二、 我国网络直播未成年人权益受损的法律原因分析
在网络直播迅速壮大的同时,其拥有的问题也日渐暴露和显现出来。为了改进直播环境,营造良好的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网络直播氛围,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有关规定。但通过对我国法律的分析,发现我国在网络直播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法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这也就是目前网络直播领域中未成年人的权益屡屡遭受侵犯的原因所在。具体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一) 现有规定位阶较低
目前针对网络直播领域的相关规定,大多属于部门规章或地方性管理条例,如文化部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武汉市发布的《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以及规范性管理文件或行业公约,如闻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北京地区的部分直播平台共同约定发布的《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都只是在各部门行政监管的角度各自发布相关规章制度,就立法层次而言,现有的规定位阶较低,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监管层次,法律约束力较小,而一些值得学习的管理规定甚至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没有法律强制力保障其实施。
(二) 监管部门职权划分模糊
网络直播领域中的监管部门较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的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可以对违法违规网站依法查处;文化和旅游部对文化市场中存在的网络直播违法行为可以依法进行管控;国家新闻广电总局有权依法监管在网络直播平台内发布的音乐、影视作品;公安部和全国扫黄打非小组又有权对网络直播领域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涉黄涉暴现象进行依法打击;工信部对于在网络直播领域中的直播网络游戏的内容又有依法管理的职权;对于网络直播领域的广告又由工商部管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公安部和全国扫黄打非小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等监管网络直播平台的部门至少有十个,但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彼此沟通和协作,使得其职权划分模糊,执法主体责任不明确,管理内容容易重复的现象出现。
(三) 惩罚制度缺乏
尽管,我国在网络直播领域针对网络直播做出许多政策文件,但多以建议、鼓励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管理为主,针对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惩罚制度缺乏或惩罚力度较小,缺乏威慑力。对于大部分违反规定行为发生往往采取以“约谈”、“要求加强监管”等举措,并没有对网络直播平台或网络主播的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详细规定。这样对于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困难,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容易产生处罚过轻,违法成本较小,不具有威慑力的情况。或者由于“整治运动”的原因,造成处罚过重,这样既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又不好把握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三、保障网络直播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建议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具体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下建议:
(一)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各国及地区针对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中的权益保护都做出相应完善的法律体系,相较于我国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文件,更具有强制力;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借助政府行政权力对相关人员进行限制或进行权利救济,更加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应当在立法中做到透视网络直播平台、网络主播、受众以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四方主体的法律关系,明确各主体责任,确定权利救济途径,从而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促使网络直播平台履行其监管义务,网络主播禁止发布违法内容并明确处罚标准,保护直播受众尤其是未成年受众的合法权益,其次对于未成年受众的监护人也应当做出相应要求,尤其是关于未成年人注册必须经过监护人同意这一点应当从地方法规升级到法律要求,更利于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不受侵犯。
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立法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尽管目前我国已经鼓励直播平台建立的分级浏览机制,但仍然不够规范,缺乏统一的标准,一些平台仅在手机端设置青少年模式,而忽视了电脑端,部分平台甚至“一刀切”取消了青少年模式下的网络直播版块。因此可以借鉴MPAA电影分级制度 通过法律明确分级机制的统一标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全面成长。
(二) 建立全行业的自律规范体系
吸取他国优秀经验,不难发现,各国都在鼓励行业自我管理,建立全行业的自律规范体系,制度行业自律公约,相互协作,共同维护网络秩序,对于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减轻国家负担。而目前我国仅有《北京市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相较于他国,尤其是美国、日本而言具有明显的地域限制性和能力限制性,该公约只针对于北京市内的二十几家网络直播企业,而这二十几家直播企业中,受限于地理因素,缺乏目前热门直播网站的影子,其生效空间不大。
而在学习现有行业公约的先进经验上制定面对全国的行业规范会更为容易,更有利于建造起全行业的自律规范体系,尤其是《北京市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的网络主播黑名单制度,在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将更加具有约束力和威慑力。
(三) 推进网络直播平台自我监管,构建从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监管模式。
目前我国已经要求进行网络实名认证。但还需要网络直播平台加以配合实名制度的落实,从源头掌握未成年人的身份。同时建立起网络直播平台事先审核和自我监督制度,从而使网络直播平台发挥出对直播内容的监管作用,及时中止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直播,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减少甚至杜绝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直播内容出现。网络直播平台还应当建立事后审查追责机制,通过探讨网络直播平台、网络主播与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同时,平台也应当及时清除在平台上的违法乱纪,淫秽色情等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直播内容以及相关的言论。并且为了加强平台清查的力度与效率,平台内部应建立与完善举报制度。平台内的任何成员都有向直播平台举报的权利,平台接到举报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给予举报者回复。如若举报有效,则平台方应在24小时内删除不当的直播内容并将其公示,情节严重多次违反或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平台方会对其进行追责,采取封号或是罚款的方式进行惩处。从而构建源头、过程、末端实施平台全过程监管的模式,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总的来说,在网络直播领域下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中国外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方式,尤其是在网络直播平台管理方面我国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的有待解决。但在借鉴过程应当立足于我国国情,综合考量,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未来的网络直播,将吸引更多的未成年人的参与。面对新形势,结合网络直播的行业特色,保护网络直播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急需网络直播平台发挥作用。同时,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将会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