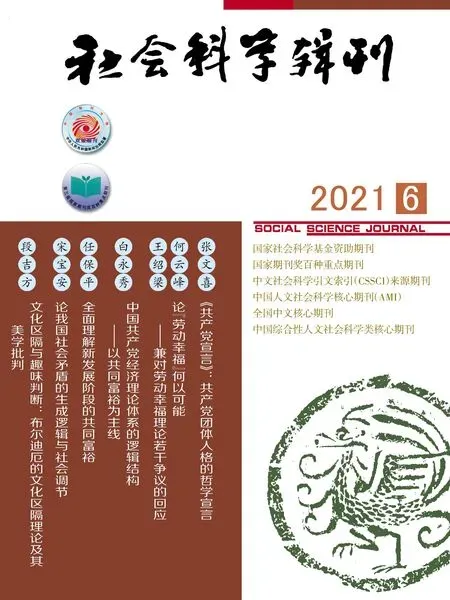著作权立法与司法的产业利益之维
孔祥俊
著作权制度涉及作者、传播者和消费者(社会公众)三方主体的利益及平衡。作者是作品和著作权的源泉,传播者的利益可能构成在著作权以外的延展(如传播者的邻接权),而传播者和消费者更多地构成对著作权的限制(如“避风港”、合理使用等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者及其所代表的产业利益越发成为著作权制度发展的核心推手。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利益平衡的法律表达。但是,著作权立法通常并未打破各方利益的平衡。随着著作权法立法的完成,利益平衡必然再进入法律适用的过程。鉴于产业利益在当今著作权法适用和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就此加以探讨。①鉴于大陆法和英美法分别使用“著作权”(“作者权”)和“版权”的不同用语,本文因语境的不同而使用相应的用语。
一、著作权法产业推动的一以贯之
著作权法发展史始终伴随着产业推动的历史。如有的国外学者所说:“传统观点将版权视为作家和艺术家的法律,然而事实却是版权源于出版商且长期以来为企业家而非创作者的利益服务。”〔1〕“事实上,被视为作者权利的版权其实有利于出版商,尽管这样命名,版权继续起着出版商权利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倒是从版权产生就一贯如此。”〔2〕
(一)产业利益始终是塑造著作权制度的核心动力
众所周知,英国早期版权法是由出版商推动发展和变革的。前版权法时代,“谁创作了作品无关紧要,因为作者并非是行业工会的成员,在出版商版权中没有一席之地”,“版权最初与书籍的生产和销售有关,而非作者的创作”〔3〕。1710年英国《安妮法》是版权法的里程碑,版权开始被视为作者的权利,开创了现代版权法的初步框架。该法出台的背景是,出版商以言论控制和图书审查为理由垄断图书出版版权的局面无法继续维持,转而以作者为表达中心,以确立作者权利的方式,依赖作者对出版商的仰赖,通过将版权控制权赋予作者的间接安排,继续限制出版竞争自由和维持图书贸易秩序,但又通过规定一定期限的权利,回应书商工会内外对原来的印刷专利和出版商终身版权的反对,在作者、出版商和公众之间达成了初步的共和局面。版权期限的规定限制了出版商的垄断利润,书商则将永久版权视为生存的基础,不愿意仅因为法律意图剥夺其财产而甘愿沦为公共利益的牺牲品,在试图通过议会立法挽救败局之后,又转向司法,试图通过司法赋予作者永久性普通法版权的方式,作为出版商版权的替代物,即事实上可以通过转让再获取作者的权利。这场努力导致了40年的司法战斗。大出版商通过诸如Millar v.Taylor案、Donaldson v.Beckett案之类的案件,开始对版权期限制度发起了被称为“书商之战”的挑战。①这很可能是英美法上持续时间最长、最引人注目的知识产权战斗。参见〔美〕莱曼·雷·帕特森、斯坦利·W.林德伯格:《版权的本质:保护使用者权利的法律》,郑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7-28页。这些挑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后,书商转而推动版权期限的延长,导致19世纪和20世纪版权期限的一再延长。〔4〕可见,在近现代版权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版商推动的身影自始活跃着,其中书商为保护版权(出版权)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争斗。
美国版权法奉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作者或者作品存在与否,而是要问著作权是否为确保信息和娱乐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所必需。”〔5〕美国版权法发展变革无处不有产业的身影,更是产业利益直接作用的结果。“在美国著作权的政治圈内,通过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共识而完成立法,已经成为主导性方法。”〔6〕例如,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制度、侵权判断的“红旗标准”等适应网络著作权保护利益格局的制度框架,并为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提供了范本。这些制度架构不是法律推理和逻辑建构的产物,而是著作权人、互联网产业及社会公众利益博弈、妥协的结果。互联网产业发挥了尤其关键的作用。最后形成的法律条款,如“避风港”等特殊制度设计,不过是以法律语言对所达成的利益格局进行的精准表达。
(二)产业需求始终推动著作权的不断扩张
著作权法的历史总体上是一部权利扩张史,同时也是作品市场扩张史。比如,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欧洲开始以作者权为战斗口号,以自然权利为理论基础,扩张著作权的范围。美国则是以功利主义为指引,不断扩张著作权。尤其是,每当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市场扩大,著作权也就扩大到新兴市场。〔7〕
在美国版权法发展中,著作权始终是随着技术发展而通过立法进行的扩张。如,“随着像录音机、收音机和电视机之类的新技术为那些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开拓出新的市场,国会通常——即便姗姗来迟——提议扩张法律范围,将新的使用方式纳入其中”〔8〕。这些扩张与代表版权人的产业推动直接相关,而合理使用等制度的发展同样与使用作品的相关产业的推动相关。
产业发展推动了著作权客体由封闭式保护到开放式保护的转变。以美国版权法为例,1790年版将保护的对象限定为图书、地图和海洋图;1831年修正案扩展了保护对象并将蚀刻版画和雕刻归入其中;1912年版则是将音乐作为保护对象,并赋予作者录制权加以保护。1912年赋予电影版权保护,电影成为作品,电影公司成为作者。1976年版权法时代,电视机和计算机成为通讯产业的突出代表,其产品受到版权保护。电视现场直播(播放时进行录制)、机器可读的计算机芯片及软盘上的“软件”,均成为版权作品,各种企业所有者随之被视为作者。〔9〕1976年版权法对于版权进行概括性保护,即“固定在任何有形表达载体上的作者的独创性作品”,均属于保护范围。这使得版权保护进入开放性规定时期。只要符合法定作品条件,即可纳入版权保护。这使得版权范围得到高度扩张。其中,产业利益得到充分贯彻。例如,“1976年,信息和娱乐产业的胜利尽管不是完全的,却是巨大的。例如,版权保护被专门延伸至电视现场直播(即便任何被广播的‘作品’,版权都应该提供充分保护)。……如今版权不仅保护著作,而且保护图片、哑剧、舞蹈、雕刻、电影、录音制品、计算机程序和电视现场直播——它们都可以被(作为雇主的)企业‘创作’”〔10〕。
著作权保护权限不断延长。美国1790年版权法初始保护期为14年。后来在这个一百年期间,保护期仅延长了14年。“表面上看似版权保护期延长主要是为了作者的利益,但被证明是一个借口。受益最多的用户是促成法律通过的人——拥有公司版权的行业成员。”〔11〕1998年联邦国会通过了《版权保护期延长法》,将未来版权和现有版权的保护期统一延长了20年,从而使得作品的保护截止期限达到作者去世后的70年。①参见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Pub.L.No.105-298,112 Stat.2827(1998)。经修订之后分散规定于《美国法典》第17篇各条。
著作权的权利范围不断扩张。例如,美国早期版权制定法(包括《1909年版权法》)结构非常简单,条文非常抽象,仅赋予版权人非常基础性的权利,主要依赖法院在制定法的框架下发展版权普通法。以后每次微小的修改都仅添加一两项新的受版权保护的客体,主要是为反映新技术带来的新表达形式,保护范围的扩展程度非常小。但是,有学者指出美国1976年《版权法》在篇幅和给予作者权利方面都呈现急剧的增长与提升;同时,“过去几十年间版权不断扩张,其中最成问题的方面包括更长的版权保护期,宽泛的复制权和演绎作品权,以及《数字千禧年版权法》规定的数字权利,后者阻碍先前被认为不侵权的使用行为”〔12〕。
(三)产业发展和经济利益决定了著作权标准的不断改变
在美国,“版权法的形成在历史上曾经而且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版权企业家的诉求。这些产业成员构成了不同寻常的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控制了媒体)并且继续同立法者协商获得法定利益——常常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整个版权历史显示了这些企业家的影响力,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76年版权法的制定”〔13〕。如美国最高法院所说,“1976年法案……是二十年间创作者与版权使用产业代表之间协商的产物,受版权局监督,在较小程度上受国会监督”②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 v.Reid,109 S.Ct.2166,2174(1989).。创作者与版权使用企业的利益经常一致,如后者常常受让版权而成为版权人,且后者也常常成为前者的代言人。如美国学者所言,“令人不安的是,如今版权诉讼中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艺术家、作者或者作曲家的身影了。主要的利益持有人是出版商、电影或音乐制作者以及其他媒体公司——而他们的动机几乎无一例外是为了获得金钱回报”〔14〕。
以作者权文化为标志的欧陆国家,在高度强调作者权的同时,也自降标准,为产业发展留出空间。例如,作者权理论有两项原则:其一,只有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作者,而不是像电影公司或者唱片公司这样的法人,才具有著作权保护的资格;其二,某一作品欲获得某种保护,必须真正是创造性的,显示出“作者人格的印记”。它们对于创造性采取高门槛。因此,诸如广播、录音等形式的成果可能会因缺乏一定的独创性而难以构成作品。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国家都需要通过构造某种知识产权来为其本土市场唱片业和广播业的发展提供保护,故而所谓的“邻接权”制度便应运而生。“邻接权观念的演变过程是缓慢形成的,最初提出这项原理是为了填补由严苛的作者权理论所造成的空隙,到后来却成为保护主义故意编织的一个谎言。它肇始于照相术,这是对作者权文化提出挑战的第一项技术。欧洲人最终巧妙地解决了关于这些以技术手段所产生的图片是否属于‘作品’的问题,方法就是称摄影师为作者,认定在照片上存在着他人的人格印记。电影也被归入作者权的范围,只是证明起来稍费劲一些。录音制品最终把欧洲的立法者逼到了问题的墙角边上。表演者和录音棚内的音乐师可能属于所谓作者的这一撮人。但是,录音制作者权和录音技师又是什么呢?实时直播的电台电视台广播,尽管它们编辑制作过程中需要创造性,但也似乎被安置在作者权的殿堂之外了。解决的办法是宣布,在录音制品和广播节目上所存在的权利,根本就不是作者权,而是邻接权。”①之所以称为邻接权,“是因为这些保护水平较低的权利就只是倚靠着高高在上的作者权这座殿堂而已”。参见〔美〕保罗·戈斯汀:《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158-159页。
总之,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始终是产业利益的推动史,产业在塑造和变革著作权制度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产业力量推动著作权法发展的新态势
当今时代,著作权保护与商业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既承载着智力成果保护与推动经济发展的使命,又肩负着维系社会创新激励和防止过度干预的平衡任务。因此,著作权制度不但早已不只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而且被应用于科技创新领域。著作权的保护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而与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版权法的商业化和产业推动,尤其以美国最为典型,其立法和司法也最具世界影响力,也更具有启发价值。这里主要以美国版权法为例加以说明。
(一)产业利益集团游说影响愈演愈烈
按照监管俘获理论,版权法是最适宜实现监管俘获的领域之一,具有特殊利益集团进行立法交易的全部特征。该理论认为,如果特殊利益集团规模较小、同质化程度较高并且成员拥有较大个体利益,这些小集团在影响政府决策者方面比更加多元化和拥有较小个体利益的大集团更加有效。最有可能因知识产权过度保护而获益的人是知识产权人,他们在大多数知识产权法相关问题上是一个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特殊利益集团。相对应的一方是各类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创新成果的消费者。消费者利益与促进最优创新通常高度一致,但知识产权人在国会明显拥有更强大的话语权。如美国学者所说,版权法具有特殊利益集团立法的所有标志性特征,包括:(1)法定利益由小集团集中享有,而法定成本由众多人分散承担;(2)最优监管的框架不清晰;(3)具体而极其详尽的制定法结构(反映着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而非允许更多司法自由裁量空间的概括式制定法结构。〔15〕
由于版权已成为权利人越来越有价值的资产,代表这些人的特殊利益集团拥有组织和游说扩大版权保护的激励。②利益集团游说已使美国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发生改变。“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维持了垄断所造成的高昂成本与创新激励所产生的动态收益之间的平衡。但近年来,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因为企业的游说团成功改变了知识产权制度,使其化为增强企业市场势力的工具。以至于到了现在,我们甚至难以判断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究竟是在鼓励还是扼杀创新。”参见〔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刘斌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76页。《1976年版权法》及其后续几个修正案具有复杂的结构,非常不同于之前几部《版权法》,这本身就表明立法俘获程度不断提高。美国版权登记官芭芭拉·润格尔(Barbara Ringer)在《1976年版权法》通过之际说,该法“极大地偏离了1790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版权法”,给“美国版权制度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其中一些变革的程度非常之大,可能标志着版权的基础理念本身已经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③Barbara Ringer,First Thoughts on the Copyright Act of 1976,22 N.Y.L.SCIL.L.REV.477,479(1977).。《1976年版权法》是特殊利益集团立法的典范,它“充斥着具体的、经过激烈讨价还价的妥协”④Jessica D.Litman,Copyright,Compromise,and Legislative History,72 CORNELL L.REV.857,857-59(1987).。特殊利益集团将它们之间达成的交易详细地落实在立法文本之中,以免把自己暴露于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之下。这与版权法的传统做法截然不同。在过去,调整新技术的规则通常需要以普通法方式进行试验,之后才会被吸收到制定法之中。⑤Frank H.Easterbrook,The Court and the Economic System,98 HARV.L.REV.4,16-18(1984).指出“法律规定越详细越表明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法官拥有的自由度也就越小”,并主张法官在面对所有类型的立法时都必须考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经济客体(如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参见Robert P.Merges,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citude: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1900—2000,88 CAL.L.REV.2187,2190(2000)。过去一个世纪里,在国会制定“宽泛的授权性修正案”的领域,《版权法》都能够非常高效地适应新技术,因为这种立法方式“为法院塑造规则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为不可避免地将准普通法变革整合进主要修法过程争取时间”;相反,“反映一时性关切的面向具体技术的、详细的法律条文……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发展知识产权法的准普通法过程”并且“事实证明难以适应新技术”。转引自〔美〕克里斯蒂娜·博翰楠、赫伯特·霍温坎普:《创造无羁限——促进创新中的自由和竞争》,兰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
美国当今著作权法的发展,尤其充斥了利益集团的身影。美国1998年《版权保护期延长法》对于未来版权和现有版权的保护期的统一延长,是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版权法》最明显的例子。①该法又被称为“米老鼠条款”,因为它得到迪士尼的大力支持,迪士尼依靠该法继续控制了米老鼠的版权。“除此之外,这一条款没有为社会带来任何效益,反而限制了知识的自由流动。”参见〔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刘斌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76页。《千禧年版权法》则是在出版、唱片、计算机和通信行业的众多特殊利益集团支持下制定的。根据目前法院对它的解释,《千禧年版权法》出现了保护过度的局面,因为它并没有为如下行为留下合法存在的余地,即出于个人或对社会有益的目的从事的对版权人没有造成损害或仅造成很小损害的接触作品行为。它不但对数字化作品的盗版行为规定了额外的惩罚(在传统版权法保护以外新增加的惩罚),而且还惩罚出于传统版权法从来不加禁止的(事实上还加以鼓励的)使用目的而接触作品的行为。〔16〕争论不休的私人复制行为是否侵权问题,背后是强大利益集团的角力。电影和唱片公司希望禁止私人复制,而录像机生产商等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则持反对态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二)版权标准更趋于迎合产业发展需求
传统的著作权保护理论和法律标准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突破。例如,为了保护数据库、软件等成果,美国等国甚至通过降低著作权保护门槛的方式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以期使得版权的保护强度和商业的现实需求相匹配。具言之,如在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等著作权保护中,对作品的独创性(原创性)或者可版权性标准或许有新解读,计算机软件被作为文字作品保护(如美国、欧盟)②美国为适应计算机软件保护的需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计算机软件的可版权性等问题进行探讨,最后通过适当调整版权标准,将版权作为计算机软件保护的重要渠道,视其为文字作品。参见〔美〕罗伯特·P.墨杰斯等:《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1页。欧盟为了允许对计算机软件提供版权保护,变通其对作品原创性的原有解释。参见〔英〕埃斯特尔·德克雷主编:《欧盟版权法之未来》,徐红菊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380页。欧盟以同样的变通解释方式,对于香水气味基于著作权保护。参见Cases Civ.13 June 2006,Nejla Bsiri-Barbir。,而未必符合传统原创标准的数据库或者被作为作品进行保护,或者比照保护著作权的方式进行保护(如欧盟)。③“数据库指令规定了比版权低的保护水平,将数据库作为数据的汇编,而非原创智力创作进行保护。”参见〔英〕埃斯特尔·德克雷主编:《欧盟版权法之未来》,徐红菊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如美国最高法院在甲骨文诉谷歌案的判决中所述,计算机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与许多其他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有所不同,因为计算机程序总是出于功能目的。④GOOGLE LLC v.ORACLE AMERICA,INC.,593 U.S.(2021),Decided April 5,2021.
比如,原本在立法意图和制度设计上泾渭分明的著作权与专利权等其他知识产权,在其相互界限和立法政策等方面有了新的交叉和模糊。⑤一些著作权裁判将促进科技创新这种原本属于专利权的固有元素,纳入了新型著作权保护中的利益衡量,一些专利法原则被用于著作权领域(如通用产品原则等)。而与传统著作权保护给人留下的“阳春白雪”和“温文尔雅”之气相比,著作权在这些商业领域中充当的利益平衡角色则充分体现了其功利性色彩和实用主义精神,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塑造了著作权法的新规则标准。当然,有人甚至更为深刻地指出:“(美国)一直热衷于将著作权扩张至那些具有经济价值的作品用途上。”〔17〕“商业主义是著作权信条 (commercialism is copyright’s credo)。”〔18〕在当今技术和经济背景下更是如此。
(三)利益平衡突出强化科技创新等新元素
著作权保护中的科技创新与商业调整始终处于交集状态。如戈斯汀教授所说:“著作权从一开始就是技术之子。在印刷机之前,并无任何著作权保护的必要。但是,随着活字印刷使得人人都能接触文字,并且随着一些王室、贵族或者富人的赞助偏好被大众消费者越来越集中的需求所取代,就有必要采用一套法律机制,对作者、出版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作出商业性调整。答案就是著作权。几个世纪之后,照片、录音制品、电影、录像机、CD、DVD与计算机已经极大地拓展了对娱乐产品与信息进行机械复制的市场,并且增强了著作权在调整这些市场时的作用。但是在今天,这些非常相似的技术,挟互联网之力,正在考验着著作权调整信息与娱乐产品市场的能力。”〔19〕在著作权法发展中,技术是动因和推手,市场调整是灵魂。产业将技术与市场相结合,不断推动著作权制度的变革发展。
当今时代,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并维持二者间的关系已然成为利益平衡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例如,“版权原本意在保护诸如图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类的文化创作物。但是,过去二十余年来,在录制娱乐(音乐、电影、电视)、图像游戏和软件行业,版权已经具有像最经常用的保护创新的手段那样的商业重要性。商业活动日益增强的全球化,伴随着数字化日益广泛的影响,对于版权产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提供了新的机会”〔20〕。
网络著作权保护即是在此种新机制理念下利益平衡的重要体现,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Sony案和Grokster案则进一步诠释了利益平衡的新转向特征。
美国最高法院在索尼案中率先将对技术问题的考量纳入版权保护领域,为技术发展开辟“避风港”,所确立的规则被广泛地称为技术时代的“大宪章”①索尼案规则是一项使革新者豁免非其控制事项的责任的大承诺。参见Lital Helman,“Pull Too Hard and the Rope May Break:on the Secondary Liability of Technology Providers Copyright Infringement,”Tex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nal(Summer 2010),pp.111-166.。在索尼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借用专利法上的“通用产品规则”,解决了涉科技创新领域的版权保护利益平衡。②该案判决认为,“通用产品原则”适用于版权法时,“必须在版权所有人有效而非仅为象征性的法定垄断权保护的合法需求与其他人在实质性非相关领域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之间达成平衡”。参见Sony Corp.of America v.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464 U.S.417(1984).这就是近年来在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领域中耳熟能详的技术中立规则。该规则为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开辟了更大的空间和余地。
Grokster案则是对索尼案规则的再次诠释,并构建了新的利益平衡机制。美国最高法院在Grokster案中首先指出:“通过版权保护支持创造与通过限制侵权责任促进技术革新,这两种相互竞争的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本案的主题。”③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v.GROKSTER,LTD.545 U.S.913(2005).“对版权材料的数字传播从未像今天这样威胁着版权人,因为每一份复制件都与原件一模一样,复制很容易,而且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使用文件分享软件下载版权作品。对此类软件使用的程度可能使公众直接进入对版权政策的辩论。有迹象表明使用诸如Grokster的软件复制音乐和电影的便捷性助长了对版权保护的蔑视。当本案呈送到我们面前时,有人认为这些担忧被其他不同的疑虑所抵消了,即不仅对侵权者,而且基于软件的非法用途潜能对软件的散发者施加责任会限制有益技术的进一步发展。”④该案判决在此处的注释指出:“但这些价值相互之间的排斥性不应被夸大。一方面技术创新者,包括那些编写文件分享计算机程序的人,可能希望(获得)对其作品的有效版权保护。另一方面创造性作品通过改进后技术的广泛传播也可能产生新作品或为刚刚起步的艺术家带来观众。”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v.GROKSTER,LTD.545 U.S.913(2005).
在Grokster案中,Breyer大法官在其撰写的意见中对于Sony案规则进行了如下阐述:“索尼案的规则……允许那些能够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新产品开发者事先知道,提供他们的产品将不会导致巨额经济责任。”⑤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v.GROKSTER,LTD.545 U.S.913(2005).“索尼规则强烈地保护着新技术。这一规则有意使法院难以在涉及新技术的情形中认定间接责任。它确定法律将不会对提供具有双重用途技术的人施加版权(侵权)责任(他们本身并没有从事未经许可的复制),除非所涉产品将几乎只能被用于侵犯版权(或除非他们积极地引诱侵权行为)。索尼案因此承认版权法并不意图压制或者控制新技术的产生,包括(也许特别是)那些有助于更有效地和更广范围地传播信息和思想的人。”①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v.GROKSTER,LTD.545 U.S.913(2005).“索尼案规则注意到了在面对涉及的技术问题时,法官(的能力)是有局限的。法官没有特定的技术能力去回答有关目前或未来技术可能性或商业前景的问题,而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和风险投资者自己之间可能存在极端严重的分歧,不同的答案还可能取决于关注的对象是开发阶段的产品还是销售阶段的产品。例如,考虑是否可以在Grokster软件中附加一种可以过滤掉侵权文件的设备的问题。米高梅公司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容易做的事,几家制造和销售过滤技术(的公司)提交的法庭之友也是这么说。Grokster公司说这样做根本不是容易的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几名明显没有利益关系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也同意。法官应该相信哪一种观点。索尼案说法官无需进行判断。”②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v.GROKSTER,LTD.545 U.S.913(2005).
(四)司法裁判具有更为广泛的行业影响力
立法经常具有滞后性,在回应新技术对于著作权新客体等的容纳时,经常显得有些迟缓。即便予以回应,因受制于种种情形,通常都是有限的。司法却可以与时俱进,能够及时回应著作权保护的新需求。如戈斯汀教授所说:“随着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国会根据技术变化而调整著作权法的能力,看起来却变得越来越小。国会自通过美国首部著作权法以来的两个世纪中,一直扮演着追逐新技术……的角色,通常落后于新技术大约二十年。……著作权所有人通常期望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来保护他们免受新技术所带来的威胁。如果说国会得花上20年时间,才能将一种由新技术所带来的作品使用方式纳入其中,也许能够更快些。”〔21〕司法具有适时调适法律标准和适应新发展的功能,在经济和技术更趋复杂的当今社会中,司法在满足著作权调整需求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突出作用。
例如,在历时十年拉锯战的甲骨文诉谷歌案中,其主要涉及甲骨文的Java API是否可以获得版权保护以及谷歌的行为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责任豁免。③谷歌在开发Android操作系统时使用了超过1.15万行甲骨文的软件代码,被认为属于“合理使用”,并不违反版权法。美国最高法院称,计算机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与许多其他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有所不同,因为计算机程序总是出于功能目的。由于存在这些差异,因此合理使用对计算机程序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提供基于背景的检查,以使计算机程序享有的著作权垄断处于其合法范围之内。④GOOGLE LLC v.ORACLE AMERICA,INC.,593 U.S.(2021),Decided April 5,2021.最高法院认定,谷歌对Java SE API的复制行为,仅包括使程序员能够将积累的才能用于新的、转换性的程序中所需要的那些代码行,这在法律上是对材料的合理使用。“这里有争议的复制仍然是一种合理使用,因此谷歌的复制并没有违反版权法。”⑤GOOGLE LLC v.ORACLE AMERICA,INC.,593 U.S.(2021),Decided April 5,2021.该案审理的背后其实直接牵扯到上万亿的美国软件市场,因而也获得了业界广泛的关注。
综上,总体而言传统的著作权保护领域相对稳定,新科技新产业则川流不息和变动不居,对于著作权保护不断提出新要求,涉及这些领域的著作权创新异常活跃。上述标杆性判例充分说明了当今版权法前沿领域,产业博弈异常激烈,版权标准的确定直接影响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因而成为产业博弈的重要战场。产业发展的需求重塑了一些法律标准,融合了一些法律原则,强化了科技创新的利益考量,不断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法官们经常在促进产业发展与维持利益平衡中殚精竭虑,但又屡屡在解决由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带来的著作权难题中贡献和展现司法智慧,创造了一系列裁判的路标和丰碑,不断推动著作权保护理念创新、法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产业利益元素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著作权法立法中,产业和利益集团的博弈更直接、显性和激烈。这与我国的立法过程和制度背景存在巨大差异。当然,我国著作权立法会以特定的方式听取产业意见,反映产业呼声和体现产业利益。研究我国著作权法发展中的产业作用,既要看到与欧美国家的巨大差异,不能盲从跟风,又要看到共同的规律和趋势,必要时可以参考借鉴。
以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利益,同样是我国著作权制度架构和法律适用中的重要元素。特别是从软件保护开始,著作权法在商业成果保护上不断扩展,如引进类似于专利的商业成果保护规则;有时需要模糊处理思想与表达的界限,甚至以表达为名将保护触角实质性地延伸到内容(如网络游戏的玩法和规则等);将科技创新作为著作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衡量的考量因素。著作权保护与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有更加紧密的关联度,成为后者的强烈支撑,商业成果保护已成为著作权保护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总之,产业发展需求对于著作权法的因应提出特别的需求,强化了一些新动向。
(一)著作权的人格性淡化而财产性和商业性强化
世界范围内的著作权法虽然有作者权体系与版权体系的基本分野和历史传统,但作者权体系与版权体系的区分更多停留在一般性说法和哲学层面,其实际差别并没有这么大。特别是在实际问题的具体处理中,功利和效用考虑经常占上风,两大法系的法院即便采取不同的具体说理,但结果却经常殊途同归。〔22〕因此,作者权和版权两大体系的实际标准越来越接近,并且著作权的财产性和商业性越来越突出,法哲学和法律制度正在向财产化和商业化方面进行深度转化。
我国著作权立法的总体体系更多受作者权体系的影响,但实际采纳的法律标准更接近于版权体系。尤其是司法实践受美国版权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较大。比如,实践中对于构成著作权的独创性标准采纳的基本上是版权法体系中的低标准,而不是作者权体系中的高标准。前一时期曾经在著作权裁判中发生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区别是独创性高低而不是有无的分歧和争议,但最终的主流观点仍然坚持独创性有无而不是高低,即只有“独创性的有无”,而无“独创性的高低”①在“央视国际诉暴风”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与作者是否从事了创作,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判断角度,而创作是一种事实行为,对于是否存在创作这一事实行为,只能定性,而无法定量。因此,电影类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划分标准应为有无独创性,而非独创性程度的高低。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7号民事判决书。。这说明独创性门槛标准本来是低的,再以高低区分著作权与邻接权已不具实际意义。再如,我国著作权法对于正当使用(“权利的限制”)采取了作者权体系的法定列举主义,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借鉴美国判例法中的合理使用法理,实质性扩张合理使用的范围。
随着著作权保护中产业利益衡量的增加,有必要更加淡化著作权的人格性而强化其财产性,使著作权制度更利于作品的传播、利用和流转,更好地发挥其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保护客体的开放性调整
在著作权保护中,在遇到是否保护新出现的商业利益或者客体时,往往涉及个人权利与公有领域之间的界限如何分割的问题。这始终是一个矛盾体。这既要适当保持著作权保护的开放性,又不能过于开放而损及公有领域。是否给予开放性保护,要有正当性支撑,甚至有时靠直觉。诚如戈斯汀教授所说:“支撑所有这些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是这样一种直觉:人们应当能够获取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即‘谁播种谁收获(to reap where they have sown)’。当某一项知识产权规则从其传统的表面内容看,无法与这种直觉认识相适应时,法院就会扩张该规则的外延,给予创作者以其所应当获得的东西。”〔23〕我国修订前的《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规定有较强的封闭性,但法院通过扩张适用的方式进行开放性适用。修订以后的《著作权法》开放了作品范围,只是在把握未列举作品的法律构成时,仍需要进行正当性分析,包括发挥直觉的功能。作品的开放性显然尤其顺应了科技创新和商业活动变动不居的保护需求。归根结底,“所有这些规则的核心,当然也就是著作权的核心,是一张由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错综交织的网。要分清哪儿跟哪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24〕。“知识产权法在私人产权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是一种法律上的人设(legal artifact),而非自然存在的现象。这条界限的移动,不仅因特定法官而异,也随着各个国家以及文化上的态度而变。”〔25〕
相比于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而言,之前的《著作权法》对保护客体采取的是“列举+兜底”的封闭立场。但是,产业创新和科技发展不断催生新的作品类型,司法实践不得不积极应对。例如,前些年对于新出现的作品类型,先是尽可能通过扩张其他列举性规定的方式变通解决,最后仍不敷使用,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在司法政策中对于“其他作品”进行开放性解读,即“对于确有保护必要、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客体或者客体使用方式”,“运用著作权权利的兜底性规定和独创性裁量标准”,“根据最相类似的作品类型或者运用兜底性权利”对游戏提供保护。①在“央视国际诉聚力”案中,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指出:著作权所保护的权利内容是相对开放的,法院完全可以运用著作权权利的兜底性规定和独创性裁量标准,对于确有保护必要和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客体或者客体使用方式,运用兜底性权利给予保护。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88829号民事判决书。这些做法符合司法特点和规律。因为,法律适用从来都是动态的和因应式的,在法律既定的背景下,司法只能通过与时俱进的客观解释和漏洞填补,使法律适用跟上和符合实践发展的时代需求。
刚刚修订的著作权法对于作品采取了开放性规定,即规定了“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的兜底性条款。该规定符合科技和经济发展不断催生新作品的保护需要,有利于促进科技和产业发展。即便如此,随着科技和产业发展,新商业成果仍然层出不穷,这些规定在具体适用中仍难免需要进行创新性解释,甚至在必要时需要填补法律漏洞。这永远是法律和司法的宿命。
(三)法律标准的变通性、灵活性和弹力性
在著作权保护中,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经常成为推动法律标准进行适应性改变的动因,并使法理认识随之转化和深化,同时对著作权标准的变通性、灵活性和弹力性提出更高要求。产业发达和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也经常成为著作权保护中最活跃的前沿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法律标准的认识和把握经常具有尝试性和变动性,甚至前后相互矛盾,也允许前后矛盾。诚如韦伯斯特所说,“由于环境变化致使意见前后矛盾,常常情有可原”〔26〕。此种情况非但情有可原,更是必不可少。
例如,前几年热议的体育赛事节目(画面)保护,在其可版权性定性和保护路径上曾经一波三折,经历了由不保护,到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试探性的保护,再到著作权与反不正当竞争的交错性保护,最后汇入著作权保护的主流。过路的旅馆终究不是行程的目的地。期间阶段性采取的保护态度、认识和标准,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显然与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息息相关。
据笔者回忆,早期学界和实务界公认体育赛事节目不构成作品,不给予著作权的保护。这一阶段的国内体育产业并不发达,国内尚未形成强大的产业利益和保护需求,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体育产业不断呼吁中国国内对于体育赛事节目进行著作权保护。后来国内体育产业有所发展,随之出现了保护需求,并推动了法律保护的逐渐破冰。2010年前后,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尝试以反不正当竞争进行保护。②当年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体育赛事节目的判决被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后因这种做法虽然有新意,但是共识性不强和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未获刊载。笔者亲历过这一过程,但目前找不到该案判决书。再后来随着国内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保护呼声日益提高,遂出现了以反不正当竞争还是著作权保护的争议和分歧,但总的背景和逐渐形成的共识是应当给予保护,只是对于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作品尚有疑虑,于是有的采取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孵化性”保护,有的直接以著作权进行保护。近年来,随着以著作权保护逐渐得到认同,遂以北京高院再审改判“央视诉暴风”案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7号民事判决书。为标志,形成了纳入著作权保护的共识。新修订著作权法采用“视听作品”的上位概念,使得体育赛事节目保护问题有望得到正面的根本性解决。
再如,20世纪末开始的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早期,网络游戏曾按照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近年来游戏产业发展迅猛,涉及游戏的保护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并成为业内热点。法律争议的焦点集中于是以反不正当竞争还是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其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事实上又发挥了过渡性保护的“孵化”作用,最终归到游戏作品和著作权的保护主流。而且,在著作权保护中,开始由于对能否将网络游戏整体上作为作品尚无共识,先是将网络游戏元素分拆为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等进行保护,后来按照整体进行保护逐渐得到较多的认可,开始以整体的视角(如之前纳入类电影作品的情形)进行网络游戏作品的保护。
在纳入作品保护之前,法院对于游戏的玩法规则、数值体系、技能体系、操作界面等元素是否构成作品中的表达持谨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主要的维权路径。例如,在“炉石传说”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案①暴雪娱乐有限公司、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游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装潢纠纷、虚假宣传纠纷、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判决被告整体抄袭原告游戏(所谓“换皮游戏”)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相关规定。判决之所以未将被抄袭的游戏纳入作品范围,是因为此时法院仍囿于通常的思想与表达的观念认识,即游戏玩法规则、数值体系、技能体系、操作界面等元素属于思想,而不是表达。
随着我国游戏产业的不断发展,仅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兜底保护显然不足以支持和促进这一新兴产业。法院逐渐开始尝试使用著作权法规定的兜底性权利以及独创性标准,在参照同类型作品的基础上为游戏提供保护。
如在《太极熊猫》案中,法院认为,游戏玩法规则具体到了一定程度,足以产生感知特定作品来源的特有玩赏体验,足以到达思想与表达的临界点之下,可作为表达。②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在《奇迹MU》诉《奇迹神话》网游著作权案中,法院认定角色扮演类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影作品。该案是全国首例将网络游戏整体画面作为类电影作品进行保护的案例。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190号民事判决书。而在“《王者荣耀》游戏”案中,广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王者荣耀》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作品”,被告传播《王者荣耀》游戏短视频的行为构成对腾讯公司的侵权。④本案为国内认定MOBA类游戏(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连续画面构成类电作品的首例判决。详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19)粤0192民初1092—1102、1121—1125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事例说明,像独创性、思想与表达之类的法律标准本来都是弹性的,虽然可以在抽象概念和学理上进行清晰的区分,但在复杂事实的具体适用场景中,经常没有绝对客观的清晰界限,即形成了形而上清晰、形而下可能会模糊的强烈反差。因此,对这些法律标准的解读有时并非一成不变,完全可以应时而变,以服务于保护需求。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法律调整的需要适时拓展法律标准,乃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法律适用不能僵化机械,不能被固有的认识和理论简单束缚。比如,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本来就不是不可逾越的法理障碍,只可能是特定时期和条件下作茧自缚的理由。
网络游戏保护中的玩法规则、数值策划、技能体系等构成要素,属于思想还是表达,可以基于网络游戏的特殊场景进行分析判定,在不属于有限表达和公有领域(如有的基础规则)时,可以基于玩法等在内容与表达上的紧密结合度,将其归入表达的范畴。思想与表达的界分本来不可能有一把精准的尺子对其进行丈量,其灵活性恰恰可以适应、适合并易于满足不同的保护场景和保护需求。
总之,司法与学术有不尽相同的逻辑和旨趣,司法总归要顺应实践的变化和需求。实践和需求才是根本的推进力量。同样的法律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变换法律解读,使其更为契合实际和符合保护需求。况且,法律适用允许尝试甚至试错⑤具体观点详见孔祥俊:《司法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94-96页。,最终再形成共识。
(四)著作权与其他知识产权的兼容交叉
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奉行“各行其道”的规则(channeling doctrines),即各类知识产权各具独特的理念、理论、标准和方法,相互并不重叠交叉。而且,知识产权涉及权利与公有领域的界限和平衡,知识产权之间的交叉保护易于扩张权利,而不利于维护利益平衡。但是,随着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渐趋于向权利人倾斜,知识产权不断扩张,各类知识产权法律之间的交叉重叠保护(overlap-ping protection)现象时有发生。〔27〕①当今知识产权法律“呈现多层保护间的重叠,诸如外观设计保护(同时涵盖版权、设计专利和商业外观)”。计算机软件保护涉及商业秘密、专利和著作权等多领域。“从知识产权的实践看出,传统的理论界限已经模糊。现在,影响高科技企业的重大交易和案件特别涉及复杂的技术、知识产权法的多项领域及反垄断问题。在计算机和信息科技领域内,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突出。”参见〔美〕罗伯特·P.墨杰斯等:《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05页。但是,由此导致的法律冲突和利益平衡更为复杂,更需要审慎考量。
例如,工业品外观设计与计算机软件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有更多的重叠。如在甲骨文诉谷歌案②GOOGLE LLC v.ORACLE AMERICA,INC.,593 U.S.(2021),Decided April 5,2021.中美国最高法院所称,计算机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与许多其他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有所不同,因为计算机程序总是出于功能目的。这种特性使计算机软件易于成为著作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重合保护的对象。具有功能性的形状可以受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同时若具有可以与功能性分离的艺术性,可以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但美学与功能性特征真正能够分离的很少。〔28〕2017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若某实用物品符合下述两个条件则可以获得版权保护:(1)该特征在脱离原先所依附的物件后仍可被视为构成一个二维或三维的艺术作品(分离性);(2)无论是其本身或是其依附于其他的有形载体作为表达,均需符合受到著作权保护的绘画、图形或雕塑作品的定义(独创性)。③Star Athletica,LLC v.Varsity Brands,Inc.,580 U.S.(2017).分离性测试应聚焦于被提取出的特征究竟为何,而不是想象在把设计提取完成后还存留了多少的实用物件。④Star Athletica,LLC v.Varsity Brands,Inc.,580 U.S.(2017).2019年9月12日,欧盟法院在Cofemel案中也对服装设计的独创性进行解读,即服装设计若欲获得著作权保护,需要满足两个要件:(1)依据作者个人的智力原创 (original subject matter,in the sense of being the author’s own intellectual creation);(2)对于该创作的表达属于应受保护的作品类型要素(classification as a work is reserved to the elements that are the expression of such creation)。⑤Case C-683/17,Cofemel— Sociedade de Vestuário SA v.G-Star Raw CV,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Third Chamber)of 12 September 2019.法院特别表示,“美学效果”(aesthetic effect)或“艺术价值”(artisticvalue)完全不是也不应成为著作权保护所需要考量的因素。⑥Case C-683/17,Cofemel— Sociedade de Vestuário SA v.G-Star Raw CV,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Third Chamber)of 12 September 2019.这些司法态度使得版权与外观设计的保护界限更为模糊,但显然使版权保护空间扩大,更利于版权法在相关产业的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再如,就数据而言,欧盟版权保护涉及内容的选择和安排,特别权利则保护不被抽取和再利用的内容本身,但在实践中仍有重叠。〔29〕
我国著作权与专利、商标、反不正当竞争等保护的交叉现象日益突出。例如,著作权与专利权保护本来各行其道,但近年来相互交叉的现象不断出现。主要体现为,商业性元素对于著作权领域的不断介入,使得著作权法发挥了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功能,如著作权和专利权在激励创新的目标上形成一致;在保护功能上的殊途同归(实用艺术作品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技术中立)等原则借鉴自专利法。当然,交叉重叠保护也会带来保护上的相互冲突,如实用艺术作品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专利到期后能否继续受著作权保护,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不同观点。诸如,有的主张不再给予著作权保护;有的主张不再受著作权保护,对专利权未保护的部分给予著作权保护;还有主张专利权失效后,不影响其受著作权保护。第三种观点为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30〕不同观点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平衡,重合保护的态度显然有利于权利人。
例如,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法保护一直极具争议。从原理上讲,实用艺术作品兼具实用性与美学性,司法的保护既需要对其艺术性贡献予以认定,又不能使其功能性特征被个人所垄断。因此,我国司法实践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主要是参照了美术作品的保护方式,具言之,看其具有艺术性美感的部分能否从观念上被分离出来,从而决定是否对该部分实施单独的保护。当然,观念上如此取分是清晰的,但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功能与形式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就此点而言,这并不会使版权对所谓‘功能设计’的保护受到威胁。”〔31〕而且,这种区分是为了给著作权法介入实用品的保护寻求依据。在客观效果上,这种保护使得著作权保护介入相关产业领域。
在实践中还存在著作权法与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交叉兼容与界限划定,不断地为著作权保护提出新课题。例如,商标授权确权程序中经常涉及援引著作权作为在先权,此时著作权的保护标准是否需要特别把握,以及商标权与著作权之间的冲突是否需要特别的平衡,均值得进一步考量。〔32〕例如,侵犯在先著作权的注册商标,在特定情形下,可以阻却在先著作权的充分救济。如侵犯在先著作权的注册商标超过法定争议期的,不能再请求宣告无效①《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且在民事救济上也受到限制。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法释〔2009〕23号)规定,超过争议期间的,“人民法院不再判决承担停止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民事责任”。这是两种权利之间以及权利保护与秩序维护之间利益平衡的结果。近年来,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保护著作权的案件有所增多,且出现诸多保护新动向,如作品名称、角色名称等作品元素的保护范围、条件和限度等问题,涉及不同法律保护之间的立法政策的冲突和协调。这些问题经常需要深层次的利益考量。
总之,著作权与其他知识产权的界限不是牢不可破的,交叉重叠就是著作权保护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动向,值得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
(五)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法律技术频繁深度结合
立法和司法截然不同。诸如,“立法者与法官必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法律问题。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法官裁判的却是特定个体之间的纠纷”〔33〕。通常而言,立法更多是进行宏观判断和总体性利益平衡,而司法则是基于个案和就案论案,使一般性法律得到个别化适用。但是,这并不意味司法裁判只关注个案和微观。法律适用有时不仅要进行微观考量,还要进行宏观考量;不仅关注法律的技术性适用,有时也关注政策性考量。此时就涉及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和互动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带有方向性、涉及重大界限性或者理念性的法律适用,宏观的和政策性的考量往往不可或缺且异常必要。比如,对于涉及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或者行业性行为标准等问题的新类型案件,涉及重大法律标准创设或者改变的案件,需要加强宏观考量,注重把握科技和经济发展大势,在宏观把握的指导下取得更好的微观适用效果,避免过度限于法律适用的技术主义、流于简单的法条主义和法律的技术性思维。如果在裁判时一时还看不清发展的方向和问题的实质,宁可在裁判中留有余地和不一步到位,采取司法渐进主义进路。
总体而言,与传统著作权保护相比,涉及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著作权法在不断拓展新领域,在法律适用中更加需要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法律的多重考量和适度结合,尤其要防止机械的法条主义和简单的法律技术主义进路。
例如,在“三网融合”政策下,原本独立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业务领域和功能上出现交叉重合。IPTV就是“三网融合”的典型代表,不仅提供传统的电视直播服务,还在节目直播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提供回看服务,允许用户对已播出的节目进行点播。IPTV同时具备传统电视机和计算机等移动设备的技术特征,融合了典型的线性传播模式和网络下交互式的传播模式。IPTV回看模糊了广播电视网与互联网的边界,引起了定性和处理的争议,即IPTV回看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同的定性直接涉及IPTV运营的授权模式,以及回看服务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当前对于以IPTV等进行的“广播电视回放”是否侵权及如何认定侵权,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裁判。此类案件的处理直接体现如何处理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对此,法院存在截然不同的裁判态度。有的法院判决认为提供“广播电视回放”的行为应定性为对电视剧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近年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等法院的判决倾向于认为IPTV回看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如在《花千骨》“IPTV限时回看”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在三网融合的IPTV平台当中,针对某一时间段中的涉案影视剧作品,用户可以在相应时间段内按照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点击“回看”获取涉案内容,故被诉行为落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3696号民事判决书。
有的法院判决则认为,“提供广播电视回放”的行为不应定性为对电视剧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如在“杭州IPTV”案中,杭州互联网法院判决从产业政策、法律、技术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认定“杭州IPTV”中的“IPTV回看”模式不侵犯乐视网对《芈月传》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②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初4603号民事判决书。
“广播电视回放”与信息网络传播在技术特征和功能等事实特性上既近似又不同。“广播电视回放”与信息网络传播的确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实现了“交互式传播”③“广播电视回放”功能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下要素和环节:1.提供“广播电视回放”的主体。提供“广播电视回放”的主体通常不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本身,而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旗下的新媒体机构,或者是数字化有线电视运营商,抑或IPTV内容运营商。2.提供“广播电视回放”的渠道。目前能够回放广播电视节目的渠道主要有互联网网页(如央广网、央视网)、手机APP(如“央视频”“云听”)、DVB数字电视机顶盒(如歌华有线机顶盒)、IPTV等。3.提供“广播电视回放”的主要环节。上述“主体”通过设定好的程序,把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信号固定下来并临时存储在服务器上,然后分别通过上述“渠道”向用户提供短期(通常是五天或七天)的回放服务,使用户可以在错过广播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回放短期内曾经播出过的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回放”使得用户和受众无需等在收音机、电视机前收听收看节目,传播不再完全是单向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交互性”,用户在不同程度上可以选择收听收看的时间和内容。但是,二者在功能、技术、传播客体等方面又有重要差异。这种异同是认定“广播电视回放”法律属性的重要基础。如果取向于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可以将其归入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如果取向于相异点,则可以区别对待。这正是引发认识分歧的原因,也是准确把握其属性的基础和关键。技术特征是法律认定的事实基础,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运用既有事实,使其服务于法律调整的目的。对于新技术新产业引发的新法律问题,法律认定既要注重在法条之中对号入座,更要注重宏观政策和发展方向的把握。换言之,处理此类问题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以纯规则取向的技术主义进路,即立足于技术事实和法条细节,寻求微观上的法条对号;另一种是宏观考量性的政策进路,即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宏观的政策取向和发展方向的判断考量,再决定具体的法律适用。不同的进路不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新技术新事物的出现会为塑造新的法律标准提供新的可能性和机会,至少提供了一个重新进行利益衡量和法律界限取舍的机会。经利益衡量认为没有必要在原有的法律渠道上改弦易辙的,将新事物纳入原轨道;如果需要改变的,则以新事物的新特性为理由,另起炉灶地选择新的法律路径。鉴于“广播电视回放”与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在传播技术和功能上不尽相同,而又有交叉重叠,且系传播技术新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涉及如何对待产业发展和公众利益。因此,此类情形比较适合以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法律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定性。如果仅仅拘泥于法律技术性分析进路,可以基于回放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存储和提供行为,且有一定的交互性,而认定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如果着重考虑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有利于公众享受便利,且考虑回放通常都是本应观看者的延时观看,并未给权利人造成太大的额外损失,即综合考虑权利人、产业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则以不认定为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范围为宜。如果采取后一种选项,则需要以另外一种法律路径加以实现。例如,可以将回放服务者视为回放设备和技术的提供者,不视为广播电视节目的提供者,不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根据技术中立原则不让其承担提供作品的责任。而且,公众是回放广播电视节目的受众,可以纳入“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公众的行为不侵权,回放服务提供者也就不涉及间接侵权问题。
可见,无论认定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均是以“广播电视回放”与原有的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存在技术和功能上的差异,该差异支撑截然相反的认定,但截然相反的认定体现了价值取向和法律方法的差异。肯定其构成侵权的,更多是基于微观的和逻辑的法律方法,是法律适用的技术主义进路;否定的认定体现了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法律技术的结合,即以宏观的政策性考量是决定性的,回放在技术和功能上的独特性使得宏观考量具有立足点,能够实现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法律的链接。否则,宏观和政策的考量即成为无本之木。
总之,从“广播电视回放”的法理和裁判之争中,可以看到两者裁判思路的划分和选择。北京法院的上述裁判更倾向于法律技术主义进路,而杭州法院的裁判更立足于宏观与微观及政策与法律的结合。对于诸如此类的新事物,两种进路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者就是精准适用法律而后者不是。经过利益衡量后选择路径,更为稳妥。选择的过程可能需要超越纯粹的法理,将政策纳入考量范围,但选择之后必须落实到具体条文。笔者更倾向于杭州法院的方法和结果。
四、结语
历史总能照亮现实和指引未来,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现实。历史和现实表明,产业利益是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推动力量。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塑造当今著作权制度的生力军。著作权保护需要处理好与产业发展的关系。首先,必须高度重视著作权法的产业促进功能。在产业利益更多融入著作权法的时代,著作权制度呈现商业化趋势,正在进行商业化的改造。推进产业发展是著作权法的重要目标。著作权保护的目标、价值和定位必须与时俱进,反映和适应这些新的趋势。其次,在著作权保护中,必须重视产业利益的元素。尤其是,需要在新的视野之下进行利益平衡,既不能盲从又不能无视产业发展需求,而应当根据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进行恰当的利益考量和平衡,防止片面化。再次,借鉴国外经验时需要加强对其产业背景的研究分析。我国著作权法发展中,始终存在参考借鉴西方国家的著作权法问题。国外著作权法与产业利益互动具有复杂的关系,我们既要看到其促进产业发展的积极方面,又要看到其独具特色的利益集团游说和监管俘获的一面,充分认识其著作权制度的复杂性,善于甄别分辨,防止盲从。
--评《版权法之困境与出路:以文化多样性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