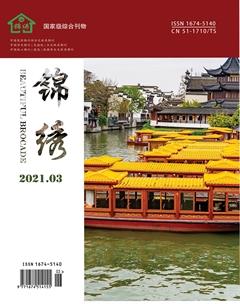浅谈气质型乐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吴玉双
摘要:自20世纪初积极心理学兴起,气质性乐观成为该领域中的研究焦点之一。气质性乐观由Carver与Scheier基于自我调节模型提出,是指个体对未来积极结果的泛化预期。乐观能使个体产生多种积极的生理、心理效应,如提高自身免疫能力、增强主观幸福感、提高成就动机,促进自尊与自信建立等等。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证明,气质性乐观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因素,与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有着密切联系。本文通过文献法,在中国知网、谷歌学术等搜索引擎中以“气质性乐观”、“心理健康”、“Dispositional Optimism”“Mental Health”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整理,简要介绍气质性乐观、心理健康以及二者间的联系,并对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心理健康;气质性乐观;乐观主义
1.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
1.1气质性乐观
“气质性乐观”或“乐观主义”指对事件积极结果的泛化预期,而那些总是对事件积极结果抱有期待的个体被称为“乐观主义者”。有研究表明,乐观主义者在工作中能够更好地进行资源分配,能够根据任务优先级进行良好的选择与判断,且在解决问题时往往能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郝亚楠等人关于气质性乐观神经生理学研究中发现,气质性乐观之所以能够提高幸福感、促进成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乐观者存在一定正性偏向,这一偏向主要体现在注意、知觉、应对策略选择等方面,乐观者脑部前扣带回、前额叶皮质区域具有更高的激活水平;此外,还有研究表明气质性乐观有可能与遗传有关,一些双生子研究结果证明,遗传在气质性乐观形成中所起到的效果大约能够达到30%。
1981年,Carver与Scheier基于自我调节模型,提出了“气质性乐观”(dispositional optimism)概念,并且认为气质性乐观是一个单维结构,其中一极是乐观,另一极为悲观。二人据此于1985年编制了气质性乐观测量量表——LOT生活定向测验,并指出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此后30多年中,有关气质性乐观研究日益丰富,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些理论。
1.2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素质(Mental health quality)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某些内在、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或身体特点,这些心理品质和身体特点影响或决定着个体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并进而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状态。
心理健康的标准有很多,目前尚未形成公认的评定标准。我国关于心理健康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35年,学者徐春霖认为提升心理健康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1) “有能够为止努力的一个或多个目标,并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获得他人夸奖,得到他人的承认”;(2)“感觉到自己正在往积极的方向进步”;(3)“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这与传统的心理健康衡量标准中积极状态的评价类似,将自尊、自信、成就感(或成就动机)等变量,或是如Seligman等人所认为的“幸福感”这类心理状态作为心理健康的积极状态的评价。传统心理健康衡量标准中消极状态的评价多以抑郁、焦虑、压力等心理量为主,较早的研究中,Parkes(1992)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作为测量工具,比较了在岸石油工人与离岸石油工人的心理健康情况。这类测量工具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也常有出现,例如,AA.Mohammadi(2016)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抑郁量表、焦虑量表以及压力量表(DASS)作为心理健康的评价标准,研究了益酸菌酸奶对生化工人心理健康的影响;B.Pakula(2018)在一项关于同性恋、双性恋个体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同样也是选用了焦虑量表、情绪量表等测量工具作用心理健康的评定标准。
1.3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Lemola等人(2011)的关于儿童睡眠质量的研究显示,乐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一方面,研究遗传因素可能对儿童形成气质性乐观具有较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较乐观的父母会在儿童早期通过积极的培养与指导,使得儿童的乐观逐渐得到发展。
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抑郁水平等心理健康指標显著相关。侯爱和(2010)研究表明,气质性乐观在应对方式与应激事件中起到调节作用,在面对巨大压力或生活事件刺激时,乐观者能够采用更积极的应对方式,使个体能有效应对压力、适应环境,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袁莉敏,张日昇(2007)通过归因方式问卷、气质性乐观调查问卷、贝克抑郁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对35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气质性乐观调节归因方式与抑郁、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在归因方式与抑郁、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张姝玥、许燕等(2008)通过发放症状自评量表、气质性乐观量表与简易适应能力问卷对473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气质性乐观、适应能力均能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并且二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气质性乐观在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
2.讨论与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认为有如下几处值得进一步研究。
首先,目前关于气质性乐观研究中,大部分国内研究都关注气质性乐观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以及气质性乐观的神经生理机制。而气质性乐观的究竟起自何方源于何处,是因为某个特定的基因?还是更多地源于生命早期父母的教育与指导,父母不同的认知风格、所教授的面对应激事件的应对方式,会如何影响个体气质性乐观的发展?如何分离出遗传与环境之间的作用。这些问题的探讨较为少见。
其次,气质性乐观概念源于国外,国外相比于国内对其的研究范围较大且深,受中西方文化差异,乐观这一概念可能在西方属于褒义,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可能被认为是“玩世不恭”。如何开展本土化的研究,如何将乐观放在东方文化的视角上来对个体进行研究,也值得深思。
最后,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着力于如何通过发展个体的气质性乐观,从而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改善,即气质性乐观的应用。早期国外研究提及,两周的每日5分钟自我肯定练习有助于气质性乐观的发展。近年也有研究者将中国传统的茶道文化融入气质性乐观发展的研究中,这也是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
(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