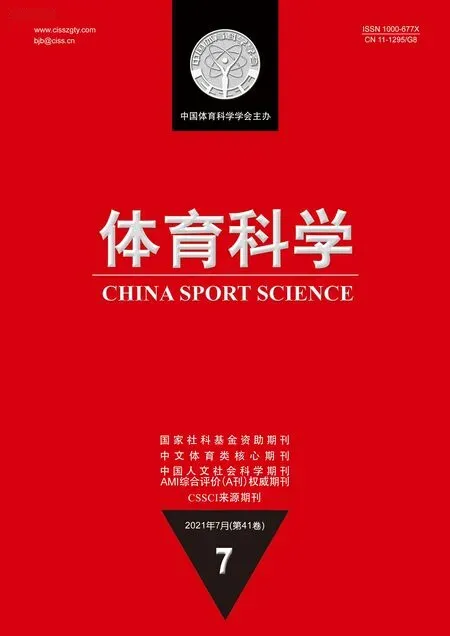新中国妇女体育70年发展的社会动力与历史经验
熊 欢
新中国妇女体育70年发展的社会动力与历史经验
熊 欢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妇女体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制度、体育制度以及性别制度是如何交互作用推动了新中国妇女体育的发展,揭示了我国妇女体育成就与变革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政治任务、社会需求以及文化符号,总结了新中国妇女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道路的选择。研究认为从“身体的解放”到“国家建设”,从“工厂田野”到“国际赛场”,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投入”,我国妇女体育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影响下,走出了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从政策激励到内生需求,激发出女性力量。妇女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折射出我国平等、多元、包容社会的形成。我国妇女体育的继续前行需要从赋权女性到赋能女性转变,汇聚女性集体力量、尊重差异、均衡发展,在开发妇女体育市场价值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其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
妇女体育;社会动力;性别秩序;社会制度;体育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毛泽东同志提出“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时间,中国女性开始介入到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中,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也从边缘逐渐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成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妇女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一步一步走上了国际体育的领奖台。新中国妇女在体育领域的成就,不仅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和光耀,也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更折射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坚韧的女性力量。
我国妇女体育的发展与国家命运以及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虽然70年的历程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只是一小步,但是这70年在中国大地所发生的变化,给人们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社会快速转型与高速发展的大潮中,妇女体育也迎来了特殊的社会动力,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既是中国社会性别秩序重构的折射,也反映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内生需求和道路的选择。
“妇女”一词是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下对女性政治身份的修辞(汤尼·白露,2012),“妇女体育”因此也具有一定政治色彩,更强调了女性作为国家主体身份参与的体育活动。从参与的形式来看,妇女体育包括了以竞技运动为主的活动,也包括了以运动锻炼和体育教育为主的身体活动。在新中国体育制度的特定背景下,学者们通常按照其参加人群专业性的特点分为女子竞技体育与女性群众体育。虽然在不同时期,妇女体育的侧重点和语义内涵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体育体制的改革,它们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边界逐渐重合。本文将从妇女体育整体发展的视角出发,以妇女体育在不同阶段的社会动力为切入点,回顾其走过的70年历程及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
1 从“身体解放”到“国家建设”:新中国初期妇女体育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民当家作主”政治身份的转变使社会成员满腔热血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新中国建国伊始,就制定了男女平等的国策,明确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地位,赋予了中国女性前所未有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妇女生产力被解放出来,积极地投入到了社会生产与国家建设中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极为重视人民的体质,倡导发挥体育运动的价值。作为妇女解放事业和体育事业的会合领域,妇女体育也正是在“身体解放”“社会平等”与“国家建设”等多重任务的推动下,开始起航。
1.1 新中国初期国家建设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成为首要任务。新中国体育建设的方针与思路也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建设祖国、巩固国防(冯文彬,1950a)开展起来的。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在1950年7月20日的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指出,“我们需要以体育来锻炼大家的体格,以体育来发扬人体劳动的能力,培养敏锐的智慧、高度的创造性、坚韧的意志和勇敢坚强的革命品质......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祖国和捍卫祖国的任务”(熊晓正等,2010)。与此同时,妇女运动也与国家政治经济任务紧密相连。与西方妇女自我救赎的解放路径不同,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Johnson,1983)。受到马克思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新中国建国初期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想主要包括3个关键内容:1)无产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2)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物质基础;3)全面发展是妇女解放的目标(Croll,1995)。因此,在实践层面,新中国重视妇女在革命运动中的参与,明确妇女合法的政治地位;主张并推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从家庭劳动(包括生育、抚育)的模式中走出来,同男性共同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明确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同时加强妇女文化教育实践,提升自身素质和自觉意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人力资源(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1988)。
当妇女成了重要的社会生产力时,妇女体育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我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以“身体的解放”为起点的(Hong, 1997)。体育教育和运动锻炼在妇女身体解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塑造女性健全的体格打下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女子体育的开展大部分是通过教会学校体育的方式开展的,而能受到教育的往往是精英女性,对于广大的劳苦大众和基层妇女来说,体育运动离她们还很远。也因此,“旧体育”被一批专家学者批判为“脱离人民的体育”(徐英超,1950),为少数人垄断的工具(冯文彬,1950b)。如何使体育运动普及到劳动人民中去,成为普通妇女强健身体的途径,从而使她们能担任起国家建设的重任,更充分地释放社会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时代重任。
1.2 新中国妇女政策与体育政策的保障
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服务是建国初期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也是各项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我国妇女政策和体育政策的制定也是基于这一方针。除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内在需求以外,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也是各项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社会不平等是社会主义主要政治目标和价值倾向,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包括妇女政策和体育政策。性别不平等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障碍,因此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1952年2月11日,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2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条规定:“不分性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法律形式保证了男女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土地分配问题要求“按人口统一分配”,确保了妇女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工厂,同工同酬制度的贯彻实施,赋予了妇女平等的劳动权利,也促进了妇女劳动的积极性;1950年新中国正式实施的《婚姻法》废除了封建包办婚姻、一夫多妻制,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前提下,规定了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妇女在家庭婚姻中的平等地位。除了在法律条文和政策文本上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以外,在社会实践中,妇女工作也从中央到基层开展起来。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成立为妇女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基层妇女组织、妇女干部的培养为妇女政策在地方的宣传和贯彻实施提供了保证。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扩展了女性的社会空间、丰富了妇女生活的维度,为妇女体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新中国体育政策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指示下,明确了体育事业的任务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反对资本主义体育为少数人服务的思路,提出“不但是学生,而且工人、农民、市民、军队机关和团体都要搞体育”(朱德,1950)。普及化和经常化的体育发展方针为在广大妇女群众中开展体育活动创造了机会。首先明确了妇女作为劳动者应该成为体育运动普及化的对象,消除人们对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歧视;其次,使体育运动成为妇女社会生活的常态,以促进妇女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在妇女政策与体育政策的双重引导下,妇女参与体育的合理、合法性获得了保障。
1.3 社会结构的支持
国家政策是推进妇女体育工作开展至上而下的动力,然而其具体的操作和落实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协调运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国家-单位两位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刘金伟,2013)。在“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建设依附在国家政权体系下,以政府为主体,依靠政治动员的力量,服务于政治目标。在这种社会建设模式下,集中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了社会整合的目标。
体育活动之所以能在薄弱的群众基础和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在广大妇女中开展起来,无疑与计划体制和高度统一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所组成的社会: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单位组织。单位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李汉林,2008)。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单位社会的生活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常态,而私人空间和个人活动随之被单位生活覆盖。妇女的体育活动也多通过行政手段由单位组织起来。城市妇女体育活动在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得到有效组织;农村妇女则在生产合作社中,由青年团、妇联和民兵组织推进,建立了各项和各种形式的锻炼小组,不仅成为田间地头劳动生产的重要力量,也是各种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的主要力量。基层体育组织的建设也为妇女体育的开展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条件,不同程度地激发了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自此,各机关团体,后来发展到乡村集体,在工作休息时候做广播体操成为一种制度。乡镇、学校、企业、工厂和公社,甚至街道都办起来运动学校,运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董进霞,2005)。这一时期妇女体育运动,不仅传承自古代中国的传统体育、接续民国时代的新式体育,还结合苏联体育创造的具有浓厚政治意涵的集体舞蹈与体操,如秧歌、忠字舞、农作舞、劳动体操、广播体操、生产操以及集体运动竞赛等,都在城乡女性群体中得到普遍推行。高度整合、统一的社会结构为体育活动在妇女群体中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保证。
除了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支持以外,社会主义文化氛围也为体育运动在妇女群体中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条件。通过中央宣传和妇女基层工作者的努力,性别平等、男女相同等性别观念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封建文化对女性的限制也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主要目标。而妇女参与体育活动不仅成为解除妇女身体束缚的一种象征,而且也展示了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制度优越性,同时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因此无论从政府、单位、组织还是从社会成员来说,妇女参与体育运动都被认为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活动,也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就女性群体而言,一方面,她们把参与体育运动,尤其是参加一些体育比赛并获得成功,看成是自我解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很多妇女也通过体育活动的成功参与,获得单位和政府的肯定,成为一种政治资本(Xiong, 2008)。然而,正如中国妇女运动一样,此阶段妇女体育的发展基本上依靠的是至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国家干预,妇女自身在体育运动中的主体性、选择性、自觉性和自治性没能获得充分的释放,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她们对体育活动参与的主动性和持久性(Xiong, 2008)。
2 从“田野工厂”到“竞技舞台”:新中国妇女体育的政治使命
妇女群众体育在新中国初期的广泛开展,为中国女性走向国际竞技舞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女性不仅合理合法地进入到了体育领域,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也很快地撑起了“半边天”(Dong, 2003)。至此,妇女体育的社会功能不再局限于其为国防与社会生产、增强国民体质服务的范畴内,还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政治工具。中国妇女竞技体育的崛起,一方面是国家体育战略的促发,另一方面依赖于高度整合集中的体育训练制度,同时也折射出新中国对社会性别文化秩序的重构。
2.1 国际环境的改变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动力不仅来源于国家内部建设的需求,也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连,与世界格局息息相关。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广大劳动人民中普及体育运动是当时体育发展的既定方针。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并逐渐形成了“普及与提高结合”的新体育发展方针(熊晓正等,2010),开始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如何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不仅能在国内竞赛场上施展才能,也能进入到国际体育赛事中,争取在国际体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新中国面临的一项重任。
1952年7月29日,五星红旗在赫尔辛基奥运村升起,成为中国登上国际体坛的里程碑(熊晓正等,2010)。但是由于国际体坛制造“两个中国”的争端,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主权,新中国不得不中断与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单项体育运动协会的联系。然而,相对于其他更加封闭的社会领域,体育可以说是打开国门的一把特殊钥匙。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举行,还是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加入,还是“乒乓外交”创造的外交新局面,都是新中国开启国际交流的重要示范。随着1979年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也先后得以恢复,这也为我国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满足人民大众强身健体的需求,也需要走向世界,中国女性运动员成为走向世界的先锋队。
女性运动员能登上国际竞技舞台,闪耀她们的光芒,并不是个人或集体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妇女体育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妇女参与竞技体育从世界范围来看,走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现代奥运会的革新者顾拜旦认为,女性和体育比赛毫不相干,在他眼里,女性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唯一参与方式就是在运动场上为男人喝彩(Costa et al., 1994)。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体育理念,在整个20世纪给妇女体育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无论是“体育竞赛有损女性健康”的论断,还是“女性参赛者缺乏专业训练”的实际情况,都成为阻止她们站上国际竞技舞台的原因。虽然,早在1910年的卢森堡会议上,就批准了妇女参加奥运会的权利,但承认的项目仅有游泳、体操和网球。田径等体育核心比赛项目仍然向女性紧闭。虽然在多方的争取下,1928年,妇女首次被批准参加田径运动比赛,但也只限于5个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妇女竞技体育的发展更是步履维艰,那些运动水平表现出色的妇女甚至会被质疑性别而受到歧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奥运选手可获得金钱上的奖励。这一措施促进了运动员再创佳绩,也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更具挑战的比赛项目中,同时也延长了女性运动员的体育生涯,妇女在国际体育竞技比赛的成绩才得以关注。随着两位妇女代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妇女体育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国际妇女在竞技体育赛场上开拓的空间,也成就了我国妇女在国际舞台上的杰出表现。
2.2 新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酝酿与形成
我国女性运动员之所以能在进入国际竞赛体系后短短时间内取得骄人成绩,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在“缩短战线,保证重点”战略的指导下,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调整,基本形成了计划经济指导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也就是举国体制的雏形。在1959—1976年间,我国已经有13位女性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的头衔,占30.2%(董进霞,2005)。80年代,在奥运战略需求的刺激下,竞技体育通过强调重新分工、项目布局和竞赛分类管理使举国体制得到强化(熊晓正等,2010)。首先,从资源提供上,体育部门(体委)从群众体育转移到集中力量抓高水平竞技体育,这实际上也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了体育部门(体委)独家发展竞技体育的局面;其次是完成项目布局,优先发展奥运项目,加强对奥运项目的扶持与垂直管理,充分保证提高奥运项目竞技水平的制度力量;再次,通过竞赛的调控,使全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围绕“奥运争光”展开,从而达到“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目的(熊晓正等,2010)。
在举国体制的扶持下,无论是从参加国际比赛的项目,获得国际冠军的人数,还是从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来看,我国女性在竞技运动中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这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妇女体育的重视和人民对女子运动员的期望。1988—2011年,我国女子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1 419个,占这一时期我国获世界冠军总数2 410的58.88%。从1988年第24届奥运会到2016年第31届奥运会,我国共获得金牌212枚,其中女子获得121.5枚,约占总数的57%,夺冠项目主要集中于跳水、举重、摔跤、柔道、乒乓球、羽毛球和射击等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9)。可以说女子体育撑起了我国竞技体育成绩的“大半边天”。1981—1986年,中国女排取得了“五连冠”的辉煌成绩,更是让国民大为振奋。而女排精神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延续至今,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自豪感,其顽强拼搏的精神也鼓舞了各行各业人民的工作热情。
2.3 社会性别秩序的重构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形成与巩固加速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从性别来看,女子运动员的进步以及在世界比赛中取得的成绩要大于我国男子运动员。为何在同样的制度下面,我国女子体育竞技水平的发展更为凸显呢?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为“我国女性拥有传统的吃苦、耐劳”的美德(吕树庭等,1995);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对女性的期望阈值低于男性,传统“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造成了“阴盛阳衰”的错觉(卢玲,2010),但是都忽略了新中国社会性别文化秩序重构对我国妇女体育成就的重大影响。
随着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计划经济时期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也逐渐形成(蒋永萍,2012)。在这种治理理念中,个人的生老病死都被纳入政府管辖的范围。人民特别是妇女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共产党所倡导的革命和建设之中,女性某种程度上从家庭和私域范畴中被解放出来。公与私、家庭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边界,也冲击着“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男强女弱”的社会性别秩序(Yang,1999)。新中国社会性别秩序的重构不仅仅体现在传统男女分工模式上的,还体现在性别规范的同一性上。“男女平等”常常被等同于“男女相同”,男、女性别差异逐渐被抹除。女性不仅在公共劳动领域要按照男性标准要求自己,即便是在生理期,也会积极地投入生产劳动,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也践行着“消除性别差异”的理念。中性化、色彩单一的制服代替了五颜六色、款式多样的裙装,女性身体的曲线被宽大的衣服遮掩,从外形上打造了男女无差的身体秩序。在报纸杂志上,女司机、女技术员、女飞行员、女跳伞员等受到大量报道,成为时代的明星;“铁娘子”“铁姑娘”等强壮的劳动妇女形象受到赞誉(Croll, 1995)。这也正符合了当时社会“单一”的文化形态以及高度整合的政治环境。
从“男女有别”到“男女一致”,社会主义对性别文化秩序的重构客观上也为我国女性运动员的培养创造了适应的社会文化氛围。体育运动传统来看是彰显男子气概的场域(Messner et al., 1990),一旦女性进入到体育竞技场域,她会被要求符合这种性情倾向。然而一旦走出体育特定的场域,她们身上持续的男性气质和身体惯习就会与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的要求相冲突,而遭到歧视和排斥(Young, 2005)。由于新中国对社会性别文化的改造,体育场域内以男子气概为主导的身体文化与当时社会所打造的去女性化的意识形态是相一致的,因此我国女子运动员走出运动场后,不仅不会遭到社会大众的排斥,相反还应和了当时社会的性别规范。当女性有了像男性一样的体魄甚至超越男性的能力,地位也会相应提升。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很多年轻女性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体育训练和竞赛中。在“男女一致”的思想指导下,很多女子项目也采取男子化训练模式,要求女性运动员有男子的斗志、男子的素质、男子的动作、技术和打法(徐岩,1998),还提出女子运动队要思维意识男子化、团队管理标准化、队伍作风军事化(刘健,2009)。女性运动员的性别身份逐渐被忽略,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性别规范对女性运动员个体能力的束缚,促进了竞技水平的提升。
新中国妇女竞技体育,对外来说,促进了国家形象的提升;对内来说,巩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它不仅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政治工具,也成为时代的标记和民众的集体记忆。虽然从全局和整体来看,集中、整合、单一、单向的制度和文化(包括体育制度和性别制度)使我国妇女体育高效率地产出成果,然而从局部和个体层面来看,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机制下,妇女在体育运动中的主体性、自觉性、自发性、个体性被掩盖(熊欢,2013)。
3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投入”:改革开放后妇女体育的社会需求
无论是为投入国家建设还是为国争光,新中国领导下的妇女体育都履行了其时代使命。但是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外力推动,并没有真正地从更广泛的角度唤起女性内在的体育意识;社会文化对性别差异的抹杀,更确切地说是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抹杀,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女性集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Yang, 1999)。因此当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女性体育的参与呈现出动力不足、反复,甚至后退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进入全面、快速的社会转型时期,逐渐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我国妇女体育内生出新的动力,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
3.1 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妇女体育内生需求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不仅为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封闭、统一、单调的生活轨迹到开放、多元、活力、相对自由的生活空间转变,人们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成为驱动社会前进的新动力,也激励了妇女对体育的内生需求,而不再仅仅是外在要求。
1)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快捷,伴随而来的是体力活动的减少。同样,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身心健康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用体育活动来弥补体力活动的缺失和缓解压力,并将其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很多女性接受并付诸实践。除此之外,当妇女劳动力被推向市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其职业竞争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拥有健康的身体、姣好的体型和端正的外貌作为一种重要的身体资本,是女性能力的重要组成和外在表现,能帮助她们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也成为妇女参加体育锻炼新的增长力。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健康地生活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道德,这种文化风尚在大众媒介中得以传播和巩固,使运动逐渐变为女性竞相追捧的时尚。此时的妇女体育不再是国家/政府监督下的社会活动,而成为女性自我监控的方式和内化的社会(性别)标准。
2)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的增加,以及休闲方式的变迁在客观上为妇女体育运动的参与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是公共假期的增加,工作时间的缩短;另一方面是新科技以及家政服务的出现减少了女性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使得妇女有更多的余暇时间从事休闲活动。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发展,以公园、广场为中心的公共休闲娱乐区如雨后春笋般被建设和改造起来。这些公共休闲娱乐区为妇女体育运动提供了空间条件。除此之外,女性休闲方式越来越多元。她们的休闲已不局限于与家人、朋友间进行感情联络,而是更加注重个人的身心调节和精神追求,而体育活动正好满足了女性对休闲自由、释放和交流等综合需求,使女性暂时摆脱工作和家庭的角色,找回自我的存在感(熊欢,2014),这也生成了女性体育活动发展的内驱力。
3)在市场经济的浸润下,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崛起刺激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投资。围绕身体全部和局部所进行的美容美发、瘦身健体、保健调养等美丽消费成为女性个人消费的首选(韩湘景,2007)。改革前,妇女体育是一项免费参加的公共活动。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多种多样的针对女性锻炼健身的商业产品不断涌现,花钱锻炼,买健康的观念也开始传播开来。再加上女性自身对美丽消费的追求,体育消费逐渐成为女性生活消费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女性表示在经济能力允许范围内,她们愿意花钱参加体育运动,对自己的健康和美丽投资。在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女性的身体审美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曲线的塑造到肌肉的雕刻,越来越多的西方体育运动理念开始影响我国妇女的运动健身实践。同样,我国传统养生文化也逐渐被唤醒,与西方运动健身文化相互博弈、融合,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为妇女提供了更多选择。科学运动观的普及也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愿意购买专业的体育培训和服务。在体育商业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消费者的身份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是当前我国妇女体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3.2 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激励了妇女体育的自发性与多元化发展
妇女对健康、休闲、消费等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是她们参与体育的内在动力。但是没有一定制度环境的支持,这种追求是无法达成的。在单位制的背景下,体育锻炼活动都是至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监督和评估,这会造成体育活动单调且不一定符合女性的特点;女性没有自主选择参与的时间、地点、方式的机会;体育活动并不能满足女性个人的实际需求与利益。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促发了社会变革,刺激了社会的内在动力机制,妇女体育的发展也逐渐获得了可持续性的制度力量。
1)社会制度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两位一体”(国家-单位)的解构到“三位一体”(国家-市场-社会)的重构过程(杨俊,2008)。通过从单位制度到市民制度再到社群制度的转移,为缓解体育的政治功能,提升体育的民生功能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契机。首先在市场化和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很多单位无法承担多元的社会职能,休闲、娱乐与体育等被首先推向了社会和市场。其次,单位制度的瓦解逐渐使生产区域与居住区域分离,人们在工作之外的活动很难再受单位的管制,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体育活动也因此成为个人的选择而非政治任务。除此之外,社区服务体系逐渐取代了单位的主要社会功能。社区服务体系与单位制度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有效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服务的需求。同时,社区服务体系所带来的居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出现为体育规模化、制度化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熊欢,2012)。
2)在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我国体育制度的改革也开始启动。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导型的体育管理体制向体育事业社会分工、管办分离的体育管理体制过渡(熊晓正等,2010),一方面以市场配置为主、计划调节为辅,减弱了行政干预的力量,提高了体育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使体育发展主体多元化,打破了目标一体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目标格局,体育逐渐从“政治工具”变成“经济工具”,产生出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这种格局下,妇女体育制度的内生力量被激发了出来。例如,在职业化改革中孕育了一批有才华有能力的女性运动员,她们不仅在俱乐部和职业联赛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也为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整体发展贡献着力量。又如,各类国内外大小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女性创造了展现自我体育能力的场所,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普通妇女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体育,妇女体育的多元力量被潜移默化地塑造着。
3)新中国建立的性别秩序也在改革之后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国企改革和企业重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下岗潮,妇女成为被退回家庭的主要群体。为了使妇女退出劳动大军更合理化,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也开始强调妇女家庭角色和抚育责任的重要性。一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关系和思想观念回潮;另一方面,女性特征和女性文化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单极化、封闭的性别文化秩序开始向多元方向发展,这为妇女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社会对个人选择的包容度也有所提升。女性文化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甚至改变了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体育形式(熊欢,2016a)。特别是在市场驱动下,一些体育机构增加一些女性元素和个性化的设计,吸引、鼓励女性参与者。还有一些以男性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开始打破性别的禁忌与角色的束缚,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妇女也可以成为合法的传承人和参与者(Xiong et al., 2018)。同样,女性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比如广场舞影响逐渐扩大,也受到了一些男性的热爱。在社会性别文化多元化、包容性发展的背景下,体育性别文化边界也开始松动。
单位制度的退位,社区服务体系的出现,体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性别秩序的调整,为妇女体育的选择提供了一个自主、多元、个性化的空间。当国家干涉逐步减少,社会力量逐渐壮大时,女性在体育中的自主权得到充分发挥。她们有选择参与体育与不参与体育的自由,也有选择何时、何地参与的自由,更有选择如何进行体育活动的自由。如果说改革前,体育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规范、控制的途径,那么当今的体育运动对于女性来说则是一种身心释放、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当制度压力一旦释放,女性更易于表达以前被压抑的欲望与追求,这也点燃了她们对体育的热情。她们可以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回报,也可以在健身锻炼中追求身心愉悦和社会认同。
3.3 体育政策的调整为妇女体育均衡发展提供了方向
与新中国初期政策引导体育发展自上而下的路径不同,改革开放后,很多体育政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实际需求而制定的,是一个至下而上的过程。随着个体与社会对体育活动需求的不断增长,原有体育工作的目标和管理方式与现实需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特别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不均衡发展成为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从妇女体育的整体情况来看,也出现了这种不均衡的现象。虽然女性运动员在国际舞台表现杰出,但是妇女群众体育却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虽然有一定广度,但是深度和质量不高,专业设施和指导不充足等问题。因此,在体育领域形成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实际上造成了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与群众体育相对滞后的鲜明反差,而这种反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突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两个战略协调发展,但实际上一直偏重在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上。而对于群众体育,政府将它推向了社会和个人。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发展,全民健身计划与为国争光计划之间有了新的交汇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要求下,体育界开始反思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并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并不能代表整个国民体育的发展水平,而国民体育的发展程度却是竞技体育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体育政策的指针开始转向全民健身,国务院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构建群众性多元服务体系;协调各类体育,从竞技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以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体育政策的调整和深化为妇女体育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方向。从群众体育来看,首先明确了妇女群众体育是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体现,因此需要积极地培育和保护。其次,提供妇女体育发展的多部门合作模式。全民健身计划指出要把体育推进各个行业,调动了教委、民委、妇联、共青团、残联等部门办体育的积极性,也强调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体育活动开展方针,这符合妇女体育多样化、分层化的现实需求。再次,在妇女体育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推动下,全民健身计划为妇女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要让妇女体育走进社会、走入市场,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熊欢,2016b)。这一方面,解除行政的束缚,减轻政府的负担,顺应了社会改革的需求;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其无序、不均衡的发展。
竞技体育也开始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首先提出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观念,这为女性体育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思路。因为,随着女性文化的回归以及社会对女性外表的看重,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会比较慎重地选择做专业运动员,特别是一些女性群众基础较差的项目,选拔人才更是困难(马德浩等,2016)。因此需要结合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从下至上建立起竞技性运动在女性群体中的文化氛围和人口基础。其次多元化的竞技体育目标追求开始形成,可以从不同程度激励更多有运动天赋的女性主动投入到竞技体育和为国争光中来。再次,体育立法工作的加强为女性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也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日趋复杂的关系和矛盾。总之,体育政策的调整为妇女体育可持续、均衡地发展做出了规划,指清了方向,虽然在操作过程中还会存在着种种障碍,但是体育政策的调整从宏观上为妇女体育可持续、均衡地发展做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4 新中国妇女体育的发展经验
中国妇女体育走过的70年是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70年,它不仅见证了我国体育事业的跨越,也投射出了我国妇女地位从深闺中的“小脚女人”到撑起国家建设“半边天”的巨大变迁。我国妇女在体育领域中的一步步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为世界妇女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经验。
1)我国妇女体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经历。从动力机制来看,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妇女体育深刻嵌入到新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以及国家战略的转移、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之中的。与西方妇女体育的经验不同,我国妇女体育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与民族大业紧紧相连。因此,它的原始动力更多来自于至上而下国家力量的推动,也因此比西方妇女体育自下而上的争取权利,能获得更有力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从发展路径来看,如果说西方妇女体育运动的历程是白人精英女性的自我救赎,那么我国妇女体育则是党和国家领导下对广大妇女群体的集体赋权。虽然妇女个体对体育的接受度不同,自我意识的唤醒程度不同,但是这种普及行动为体育文化在女性群众中的扎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甚至改变了体育中“男强女弱”的性别结构。因此,当国家和政府撤出力量时,妇女体育并没有稍瞬即逝,而是从根植的这片土地中生发出新的力量,这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更是女性自发的群体力量,它波及面更大、生命力更强。无论是在健身房还是公园广场,无论是在学校跑道还是国际赛场,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女性挥汗如雨的身影,特别是那些散落在城市、乡镇各个角落空地锻炼健身的妇女群体,已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场景。
2)我国妇女体育的发展在主观上虽然没有清晰的、具体的体育理论指导,但在实践中却有较为明确的思想路线指引,自觉与不自觉地遵循了体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与西方妇女体育在发展道路上的自我探索、质疑、批判、否定、重构、分化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不同,新中国妇女体育实践一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的理论指针和路线,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男性不是以其生物性征而定义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体育是建构男女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同时强调公域活动(社会生产)和私域活动(生育)对女性解放同等的重要性,且强调要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打破现有的秩序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熊欢,2016a)。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对资本主义体育的阶级性和剥削本质进行了揭示,这让新中国的体育工作一开始就对旧体育进行批判和改造,强调了体育运动的大众性、服务性、平等性和生活性,及其对人全面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实践层面,新中国先解除了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结构性的束缚,让她们进入到生产领域,赋予她们更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这样在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创造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然后打造了男女一致的性别文化,解放了社会标准对女性身体的桎梏,特别是在体育领域打破了“男强女弱”的性别秩序。从物质基础到组织结构,再到意识形态形成了社会主义妇女体育的特色。改革开放后,在传统文化的回归、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新自由主义的浸润共同作用下,妇女体育的格局发生了一定改变,但是其总体的实践方向仍然是沿着为妇女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前进。
3)我国妇女体育是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融中所生成的身体现象和文化符号。身体不仅是人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实践的运载工具,身体在每一天的社会生活中被不断地系统制造、维持和表达着(Shilling,2012)。在参与体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我国妇女体育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不断地被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所塑造的身体秩序。它既体现了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秩序,又体现了促进生产、自我投资、刺激消费的经济秩序,还体现了身份认同、社会教化、网络建设的社会秩序,以及传统与现代、排斥与包容、保守与创新、迎合与反抗交互矛盾中的文化秩序。在身体秩序的建设中,妇女运动的身体也逐渐从国家规训走向了社会规训,并内化为自我规训。当然,妇女运动身体不仅仅是规训,也是女性欲望的表达和文化符号的传播载体。通过运动,让女性能从特定的角度看待生命、塑造关系、对生活做出应变。妇女运动的身体所传达出来的青春活力、性感美丽、健康向上等文化符号,也成为吸引更多的女性参与运动、消费体育的动力。
5 结语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妇女体育无论是对群众路线的开辟,还是精英运动员的培养,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政策的保证、制度的支持、时代的需求在宏观层面构成了我国妇女体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将继续推动我国妇女体育前行。然而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妇女体育仍存在一些限制,比如体育活动空间的挤压、体育项目选择的局限、女性体育组织的缺失、女性青少年从事竞技体育期望的弱化、国家财政投入的相对减少、女性参与政府决策的比例较低等。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不仅在政策上需要赋权女性,在体育运动实践中还要赋能女性;不仅在市场上要满足女性个体化、差异化的运动需求,也要在战略上整合女性集体力量为女性体育权益发声;不仅要开发妇女体育的市场价值和政治功能,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对妇女体育的关注,也需要充分发挥妇女体育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稳定与和谐。
董进霞, 2005.女性与体育:历史的透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冯文彬, 1950a.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J].新体育,(1): 8-9.
冯文彬,1950b.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J].新体育,(3): 3-4.
韩湘景, 2007.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蒋永萍, 2012.“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1): 1-6.
李汉林,2008.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J].社会, 28 (3): 31-40.
刘健,2009.对“女子技术男性化训练模式”的探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8(4): 64-65.
刘金伟,2013. “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J].理论界,(9):11-13.
卢玲,2010.我国竞技体育女性参与的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
吕树庭,王源,1995. “热线”中的冷思考:关于女子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反差的社会学启示[J].体育文史,(4): 13-15.
马德浩,季浏, 2016.我国女性竞技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应对策略[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35(3): 7-12.
荣高棠,1952.全国体育总会第二界代表大会报告[C].北京:国家体育总局.
汤尼·白露, 2012.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M].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童昭岗,孙麒麟,周宁,2002.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熊欢,2012.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女性休闲体育的兴起[J].体育学刊, 19(6): 16-21.
熊欢,2013.女性主义视角下运动的身体理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36(7):20-35.
熊欢,2014. “自由”的选择与身体的“赋权”:论体育对女性休闲困境的消解[J].体育科学,34(4):11-17.
熊欢,2016a.性别、身体、社会:女性体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熊欢,2016b.我国女性大众体育发展目标选择的思考[J].体育学刊, 23(4):68-73.
熊晓正,钟秉枢, 2010.新中国体育60年(1949-2009)[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徐岩, 1998.我国女子篮球男子化的训练应从小抓起[J].山东体育科技,(4):18-19.
徐英超,1950.论改造旧体育的两个问题[J].新体育,(1):10-11.
杨俊,2008.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5):4-1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1988.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9.运动员获世界冠军情况[EB/OL].[2019-8-21].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朱德,1950.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J].新体育,(1):7.
COSTA D M, CUTHRIE S R,1994. Women and Sport: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M]. London: Human Kinetics.
CROLL E, 1995.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M]. Lond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DONG J, 2003. Women, Sport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M]. London: CASS.
HONG F, 1997. 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M]. London: Frank Cass.
JOHNSON K A, 1983.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SSNER M A, SABO D F, 1990. Sport, Men and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M]. Champaign, Illinois: Human Kinetics.
SHILLING C, 2012.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ie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XIONG H, 2008. Urbanisation, women’s body image and women’s sport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1949-1979: A historical review[J]. Sport Hist Rev, 39(1):127-151.
XIONG H, DENG J, YUAN J, 2018. From exclusion to inclusion: Changes in women’s roles in folk sports and indigenous physical culture in China[J]. Int J Hist Sport, 35(15-16): 1603-1621.
YANG M M, 1999. Space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itional China[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YOUNG I, 2005.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ocial Dynamic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Women’s Sport over the Past 70 Years in New China
XIONG Huan
,,,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great achievements and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women's sports in China. Taking the social dynamics of women's sports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social systems, sports systems and gender systems have promoted women's spor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approaches, it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political mission, social needs and cultural symbols behind women's achievements and the sports reformation. The research thinks that from “physical liberation” to “national construction”, from “factory and field” to “international stadium”, from “passive participation” to “active involvement”, women's sport in China is instructed by socialist feminism and Marxist sports thoughts with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path. In addition, from policy incentives to endogenous needs, women's sport has inspired female power.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women's sports reflects the formation of an equal, pluralistic and inclusive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tinual advancement of women's sports in China needs to change from empowering women to enabling women, gather women's collective powers, respect differences with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ocial value of “humanistic care” in women's sport while developing women's market value.
’
1000-677X(2020)07-0031-09
10.16469/j.css.202007004
2019-07-11;
2020-06-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TY048)。
熊欢(1979-),女,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性别社会学,E-mail:hxiong99@126.com。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