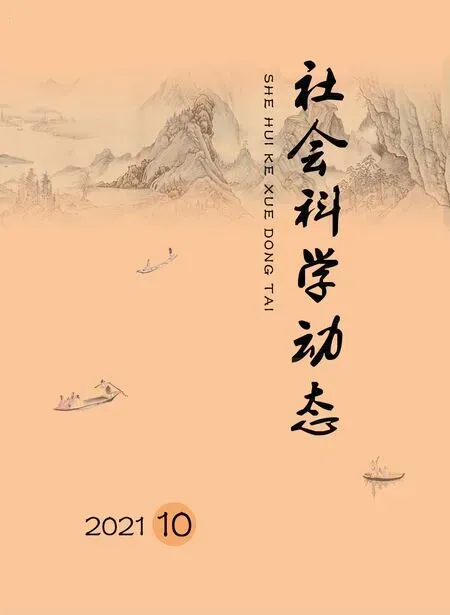当代文学研究的道与术
——张志忠教授访谈录
喻晓薇
编者按:张志忠,1953年生于山西太原,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分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先后获“庄重文文学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奖项,是莫言在中国最早的发现者和研究者之一,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首席专家。出版有《莫言论》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迷茫的跋涉者》 《1993:世纪末的喧哗》 《天涯觅美》 《卑微的神灵》 《90年代的文学地图》《求真之道》等著作。
一、关于问题意识
喻晓薇(以下简称“喻”):在做课题时您一直在强调问题意识。您能不能结合自己的治学实践来谈一下,您是如何把问题意识贯穿于具体的研究之中的?
张志忠(以下简称 “张”):好。做学问,从最基本的层面,就是我们讲“文似看山不喜平”。平铺直叙,一个是讲这文章不是好文章,再一个就是你不显山不露水,不能有效表达。要有鲜明的目标,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你的文章才能做出深度来。
还要有一种逻辑建构的能力。就是同样的一个题材,同样的一个研究,你怎么样去强化你的问题意识。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指导过的一个硕士研究生,菏泽学院的张建伟老师。当时她提出来说自己的硕士论文要做张洁研究。作家张洁有足够的份量成为一个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的选题,相关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作为后来者,怎么做出你的研究个性来?张建伟一开始拿出来的提纲,从张洁早期的创作一直到她后来的《无字》,把张洁的作品一网打尽,从头到尾写过来。我说,首先,你这从头到尾写过来的就是平铺直叙,是边走边看,边走边说,你应该从她创作的《无字》中提炼出几个问题来。 《无字》和她最初的创作,包括《爱,是不能忘记的》那一批作品,当中的反差太大了。我说你倒过来,从《无字》讲起,先把《无字》做一个标本,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再来追问,张洁为什么会写《无字》,她为什么会从《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样对爱情的无保留的歌颂,对男女主人公的不遗余力的肯定和称赞,写到《无字》的两性战争,写得那么残酷那么赤裸裸那么不管不顾,简直是像那一句古语“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作品中女主人公恨不得跟男主人公拼得同归于尽,仇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如果你从前往后写,你就是按照创作顺序,按照创作内在逻辑做过来,问题意识不突出。第二,就是这文章做得平平淡淡,平铺直叙。那么倒过来,先把《无字》确立在这里,为什么作家前后20年间的创作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她是怎么样一步步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走到《无字》?这就有了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很鲜明,把研究重心集中在《无字》上,其他的作品其他的文本都是在解答为什么会有《无字》。这样处理,问题意识就比较突出。
再比如我们课题组李晓燕的博士学位论文。她的导师是杨守森,我很早就认识,正好在高密开会碰到了。有一天晚上,杨守森把我请过去,把李晓燕也叫过来,要她来讲讲自己博论的想法、提纲,也要我帮着把把关,出出主意。一开始,李晓燕的设想就是靠田野调查来考察莫言小说当中的人物原型——她是莫言的高密同乡,有地利之便。按理说,这个选题不是不可以,我就说你这个选题没有深度,没有问题意识。因为你考察出来,余占鳌是张三李四王五几个人的经历,或者说张三一个人的经历为主综合起来的,现实当中的张三什么样、李四什么样、王五什么样。你这样的研究没有深度,没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我说你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呢?它应该有纵深感,现实当中的张三李四怎么样,作品当中的余占鳌怎么样,莫言怎么样把现实生活当中的张三李四通过艺术创造能力将其塑造成作品当中的余占鳌,这就有了三个层面了。这个问题意识就是,莫言怎么样把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和事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写到作品里边,形成艺术形象。他怎么写?为什么这样写? “为什么写”相对来讲好讲一点,他用什么方式来处理生活原型和艺术形象中的关系就难一些。这就是问题意识。一是要有问题,二是问题要有深度。
喻:您曾谈到“从一个倒置的结果出发追溯原因,发现其中的问题”,您有一篇文章①就是发现王安忆《启蒙时代》中的问题的吧?您那篇文章是不是就属于这类?
张:它不完全是。首先是讲发现问题,你要从问题的源头去追索开始,要去追索它的原因,因为你不可能在发现的问题面前展望未来,一定是要回望过去,这不是倒置,你发现了问题就一定要追溯它的来龙去脉。发现问题,这问题怎么形成,就像我讲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讲“市民社会”理论。再一个表现出小孩子对红卫兵的向往和崇敬,因为我这个年龄,包括王安忆,包括我近来正在做研究的徐小斌——我是1953年出生的,徐小斌和我同年,王安忆是1955年出生的——“文革”爆发的1966年,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进入中学,红卫兵主要在中学展开,所以大家当时就觉得没有当上红卫兵确实是一种遗憾,看着红卫兵威风八面叱咤风云心中好生羡慕。那么你因为年龄问题没有赶上这个潮流,登上时代舞台,在1966—1968年,在当时的语境下,你会觉得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失落,这就是王安忆为什么会在《启蒙时代》中用那样一种角度,用羡慕和崇拜的态度,去写已经是狂热消退之后的红卫兵,写他们新的思想追求。徐小斌有个短篇小说《末日的阳光》,也是充满这样的情绪。
喻:您还说过, “研究对象与研究结果成正比或反比,取决于问题意识”,能不能请您解释一下这句话?
张:这是讲,对于一个研究对象,你能从里头发现多少问题,我们做研究其实就是研究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怎么做工作呢?就是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我们的工作就得到了推进。做研究也是一样,你做文学研究,研究什么呢?就是要关注我们的文学处于什么样的现状,我们的作家作品有什么样的独特创造,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艺术个性,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什么新的元素,这就是问题。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问题范畴,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作家那里,它的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分解开来。
再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它的文学有什么特征?在哪些方面构成了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特色” “中国经验”?我们的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文学之间如何鉴别其异同。共性就是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表现真善美,表现人们真诚的爱情,或者这种理想信念,这种追求。当然也会讲痛苦,讲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讲人道主义讲人性,全世界的文学应该讲都在这个路径上走,那你说中国文学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当然到一个小的层面,那就是每一个作家都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比如王蒙、丛维熙,他们都是当年的右派作家,你看他们创作的路径是不一样的。王蒙的创作路径,我将其概括为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两种要素的交织交错,纠缠排斥,批判互动,矛盾冲突,也有说彼此情投意合,一起向前推进的时候。丛维熙就没有王蒙那么主流,没有王蒙的革命意识那么自觉那么强悍,他写的多是边缘性的知识分子,怎么样来证明他们对于革命的忠诚,像引起争议的《远去的白帆》即可为证。这就是发现问题。王蒙和丛维熙,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下,都是右派,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而且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在这样一个共同前提之下有什么各自的特征有什么追求?这就是问题意识。
喻: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课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研究,它应该也有一个问题意识贯穿的,您能不能结合这个课题谈谈您是怎么把问题意识贯穿到课题论证框架当中的?
张:你可以看看我的投标书。确实是如你所说,课题也是研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推动莫言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比如说莫言研究,每个人的研究都有每个人的角度和立场,但是在现有研究状况面前,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实现学术创新的?这就是讲,以学术创新研究的要求考察莫言研究的现状,发现它的不足,同时根据你自己对于莫言研究的了解,对于莫言研究的相关思考,提出你的目标,目标就是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没有被关注到、没有被充分地讨论到的重要问题,你觉得这个话题是可以实现突破、实现这种学术上创新的,就可以将其设定为研究目标。这份投标书里边提出了至少有十几个方面的问题关注,我们有四个子项目,每个子项目都有四到五个相关的问题。
我这里举其中一点,莫言怎么样把生活经验转化、升华为艺术精品,这个经验是苦难的经验,血泪斑斑。它不仅仅是莫言一个人的生命记忆,它又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有内在的关联性。莫言小小年龄,他的人生坎坷萃集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的、身体的各个方面,他有很多曲折,有很多心灵创伤。但是,莫言的文学并不是诉苦文学,并不是一味地痛哭流涕。现实生活当中,小小年龄的莫言,从生产队菜地里拔了一个萝卜吃,被生产队干部发现了,把他拎到大庭广众之下,在社员们出工的路口上,罚他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请罪,请完罪回到家中,又被他父亲暴力殴打。这样的故事,照实写出来就具有充分的“文革”时代的印迹。一个小孩子从地里拔了个萝卜,在那个年月要向毛主席请罪,要示众。鲁迅写的示众是阿Q的示众,莫言自己就是被示众的小孩。但莫言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苦文学,他对于曾经盛行一时的“右派文学”——倾诉右派苦难的文学很不以为然:这种作品只是控诉或指责,不是好的文学。从生活到文学,莫言怎么转换的?他把这种苦难记忆、创伤记忆的另一面发掘出来,就是:人还有一种超越苦难蔑视苦难的精神气。现实当中一个萝卜的故事,它分成了两段:一段写在《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小黑孩对透明的红萝卜的意象痴迷到了走火入魔,要到萝卜地里重新发现那个晶莹璀璨、熠熠生辉的美到极致的萝卜,它不是用来吃的,它是用来让人有一种审美迷醉;另一段在《枯河》里边,小孩受他父亲暴打,父亲打完了哥哥打,哥哥打完了母亲打,这个小孩不堪忍受人间的暴虐,自己走到河滩上,趴到河滩上死去。死,也是一种抗争,宁死不屈的抗争。这都是一种对于苦难的超越。这不仅仅是莫言个人带给我们的启示,它关乎到我们怎么处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创伤记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创伤记忆,怎么样能够变成具有超越性的文学作品?历史的苦难、创伤、血泪,怎么样能够产生出和历史的惨痛记忆、惨痛教训相匹配的精神的成果、思想的成果、情感的成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令人警醒的名言: “我只怕我配不上我经受的苦难。”我们经常提一个问题,中国有那么多惨痛的历史记忆,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在哪里?李泽厚讲,鲁迅并不能说是全球第一流思想家,他在我们民族的思想高峰上那是一个峰顶,但放到世界的大思想家行列中并不醒目。为什么我们会讲海德格尔,会讲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这都是世界超一流的大脑,但是你恐怕不能说鲁迅是超一流的。20世纪沉重的历史灾难、沉重的历史创伤,没有产生出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成果。我们现在仍然要回到五四的那样一种思想状况当中去,我们现在仍然在呼唤五四精神,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自己的思想,创造当代中国的思想高度?我们仍然走不出五四,我们也走不出五四的高度。五四并不是不可超越,并不是它有多么灵光,很多的问题它都没有解决。我们今天还仍然指望它要来解决今天的问题。
喻:这就是未完成的现代性吧?
张:是的。未完成的五四。我们现在仍然在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沉重命题,我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它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就不会有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么多的挫折坎坷、灾难血泪。用同样的逻辑置换一下,五四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五四如果能解决问题,我们20世纪的路不就很顺当地走过来吗?现在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五四精神受到打压、受到扭曲,所以未能解决后来的进程中遭遇的历史难题。那这种受打压被扭曲,就是讲你的思想力量,你没有足够的强度,你要强大到不可打压不可摧毁,不可扭曲不可扼制,这才可以成立。好比马克思受打压、受阻扼、受各种各样摧残,但毕竟他的思想曾经传遍全世界。我们现在也没有说回到马克思可以解决现实问题。那么五四的思想高度,比起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丰富性可以算得上非常薄弱。这就是讲历史的沉重灾难怎么样能产生出民族的、思想的、智慧的、高度的结晶。这就是问题意识,而且这个问题意识第一是从莫言出发,进入中国文学,再一步到进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想文化精神的生产。我经常会讲,我不仅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有所思考有所推动。
二、关于实证与心证
喻:您讲过这样一段话,就是“从事古典文学可以靠资料吃饭,做作家年鉴、史料长编、笺注、集释、会编、会校,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没有这么多优势、便利,它主要是面对文本、阐释文本的。实证研究,因为有切中学术时弊的意义,所以在今日值得推重,而心证呢,自有其轻灵生动、元气淋漓之用”。请问实证研究和心证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是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特点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之处?或者说二者就是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区别所在?
张:不能那么理解。心证研究是讲在场批评,同步跟踪研究,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心灵的互证,你这个研究者和作者作品的精神气象的互证。80年代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路子,出现什么新的作品,大家马上对作品进行阐释。它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讲,新时期文学初期,每个作家都不是有很长的创作历史,王安忆也好,莫言也好,他们都是80年代出现的新作家,你顺着他们的创作历程往前走做同步研究,从80年代走到90年代,走到2000年,仍然是一种心证研究。另一方面,有的人是从当下的莫言、当下的王安忆开始做起,回过头去追溯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用实证材料来说明的事情。具体而言,实证与心证是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如我们课题组李晓燕所做的《神奇的蝶变》,莫言小说当中从人物原型到艺术形象的过程,那实证研究的部分,就是讨论当年墨水河大桥伏击战是什么样的情况、余占鳌和刘连仁的比较、余占鳌和当年那两个国军首领的比较、或者讲《蛙》当中的万心和现实生活中莫言姑姑的人物原型的比较。讲现实当中的人物原型和艺术作品当中的艺术形象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就是实证研究。我后来跟她讲,仅仅是梳理A和B,A怎么样B怎么样,做这种平行论述,那你还仅仅是在处理你所面对的现象、材料,在做田野调查,是走完了第一步。你还要做第二步,就是A怎么样变成B,刘连仁怎么样变成余占鳌,姑姑怎么样变成万心,这个过程中莫言用了什么方式进行艺术的创造,那这就是心证。
讲实证,是因为2000年以后,强调当代文学历史化,强调当代文学已经有50年、60年、70年这么漫长的历史,莫言、王安忆这一代作家,他们创作了40年,回过头来梳理他们创作的历史脉络,廓清他们的创作和现实生活、他们的生活经验包括阅读经验和文学道路之间的关联性,现在这个方向可能也是一个文学研究的热点。
喻:2019年10月在山东举行的“新中国文学70年与莫言研究暨红高粱文学现象学术研讨会”,程光炜老师讲莫言研究缺什么,说到莫言的年谱,还有资料长编等等。这是不是您所说的实证研究?
张:任何现象都是一种概括,不能仅仅靠材料说话,并不是说你把材料摆出来就实现了你研究的目标,而是从这些材料当中去发现问题。程光炜老师相关的研究做了很多,他不但研究莫言,他们所谓“重返80年代”,其实也是在这个方向上用力,但是你看他自己做的“重返80年代”和他的学生所做的“重返80年代”,两者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能力、眼光。 “重返80年代”,不是说把80年代的材料挖掘出来,过去不注意,现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仅仅是这个过程。程光炜老师的文章,许多时候它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实证。他写得好的文章都是找一些实证材料来解决作品阐释中的问题。比如他有一篇研究文章,讲张炜《古船》中隋抱朴阅读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阅读《共产党宣言》,那样一种精神状况,他是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的。 《古船》问世的时候,很多研究者就提出,农村当中真有隋抱朴那样深刻的思想者吗?真的有人这样投入地读《共产党宣言》,而且读得非常有心得有体会、非常有情怀,有这样的农民存在吗?程光炜就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不是靠实证能够解决的,他是从张炜自己的思想历程、张炜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证研究也是要解决问题的。
喻:就是为问题服务,是吗?
张:对,为问题,要解决问题。
三、关于文学批评的天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
喻:经常听到作家说,写作是需要天分的。您说过,文学鉴赏也需要个人才情与悟性,那么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文学鉴赏是一种基础,那是否意味着文学批评也是需要天分的?另外,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文学鉴赏和审美能力是否也是一样重要呢?
张:这个是肯定需要的,而且讲文学创作也好文学批评也好,它是一种交流对话,精神的、心灵的、情感的交流和对话。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讲: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这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作者是情动而辞发,从情感的涌动中生发出文字,读者和研究者是从它的文字进入文本的感情世界。这是一种双向的心灵震动,作为读者和研究者,你一定要能够读出作品的精妙之处,读出作家呕心沥血的创造,而且还能捕捉它,而且还能够描述它,才算是合格。作为研究者,作为阐释者,就要把别人认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尽可能的用你的语言表述阐释出来。伟大的作家也需要伟大的阐释者。五四时期的鲁迅很伟大,如果没有茅盾、瞿秋白等人对鲁迅的阐释,鲁迅的传播、鲁迅的理解当然也会进行,但是能不能达到当时那么高的程度,在作品产生的同时就被经典化?这就是批评的重要性。像80年代,王安忆、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铁凝,他们的作品一问世,如果不是第一时间被批评家及时地捕捉、把握、阐释,而且阐释得非常精彩,他们能不能够像今天这样走得这么远呢?当然,一个文本可能有5种阐释或10种阐释,但不管几种阐释,这种阐释一定是有相当的高度,这才能够和作家对话,和时代、和文学对话,这对于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是非常高的要求,因为你仅仅讲思想脉络,讲历史背景,那文学就是社会学的材料、历史学的旁证。文学之成为文学,如果什么枝蔓都可以减掉,最核心的存在,一个是它内在的情感,一个是它外在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有情感的形式,意味就是情感的意味。我觉得对于解读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者你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同样是如此,鲁迅描述魏晋时期的文学“清俊” “通脱” “宏大” “华丽”,这就是一种高度的概括。 “清俊” “通脱” “宏大” “华丽”,它融入了魏晋文人的一种生活和精神风貌,又是魏晋文风的精彩表述。鲁迅讲“《红楼梦》一来,传统的写法都打破了”,这不是讲《红楼梦》的思想境界,而是讲它的艺术塑造、艺术追求。
喻:刚刚讲到,文学创作需要天分,文学批评需要天分,当然文学批评它还是不同于文学创作,它对批评者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理论素养,包括文学史知识有相当程度的要求,那么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在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这两种思维类型中,您认为两者所占的比重孰重孰轻?
张:我们当然希望说是两个方面都很强,两个方面都一半对一半,但是这样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理性思维、思辩能力在批评家这里显得更为突出,更多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是属于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通常讲 “别、车、杜”,别林斯基理性思维、抒情色彩和他的文学情调是相匹配的,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就是思辨性、思想性的方面更为突出。当然也有一条, “别、车、杜”也好,再早的赫尔岑也好,用文学的方式来批判揭露俄罗斯沙皇专制的黑暗、恐怖、苦难、血腥、残暴,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文学的战斗性就突显出来,文学的思想召唤功能就更为强大。我觉得,许多的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在这个方面,在理性思维和思辨能力方面更为强大。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文学史(我也主编过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谁能成为文学史家?我们大家都讲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学著作,这些都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路径。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思辨性很强的一种写作方式。真正说从审美的角度讲,李泽厚《美的历程》就是一个思辨性、历史感和艺术评判、艺术感受能力相互均衡,甚至还包括它的诗性文笔,就是表述的方式,都是我心目当中一个样板。这就是恩格斯提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但是,我们又经常处在一个巨大的矛盾当中:我希望我们的文学研究审美优先,强调体验性,强调贴近文本,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我们20世纪的文学一直到当下的文学,都是一种召唤社会民众,召唤一种民族情怀,召唤一种改变现实推动现实前进,这样一个功利性很强的文学。当然,文学永远不可能超功利,但是20世纪把文学的功利推到了极端。这也和我前面讲“别、车、杜”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今天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都已经很难做到,那要做别林斯基可能就更其艰难。
喻:就是说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具备思辨性与思想性这是基本的,然后像别林斯基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理性的思维、思辨能力、理论素养是一个人从事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准入资格,然后在此基础上要求有感性,你是这么认为的,对吧?我的导师樊星教授就特别强调感性。
张:我也强调感性。感性有几个层面,一个是基本的感受力和高级的感受力。没有基本的感受力,那你跟文学的缘份就很浅了。但是有了基本的感性,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沿着感性和理性并重的路径往前走,还是很多时候就会容易偏重理性思考这条路往前走。
喻:是不是偏向这条路就更容易获得成功呢?因为它是一种大家都会采用的方式,或者说主流的方式?从事文学研究首先就是理性的方式进入?
张:对,它跟创作相比,肯定是理性的东西更多……
喻:那是不是可以说,走这条路就更容易获得现实上的成功?
张:那也未必。因为各种才能的不均衡,高级的感受性、高级的审美体验的能力确实是很难用一种我们当下的教学体制的方式来加以阐述、加以传授,但是理论性的东西是可传授、可讲述的。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下,将学生引向理性思考。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论文有那么多理论八股的原因。而且还有一条,审美感受能力的培养相对比这种理论思考、理论传导可能更艰难更困难。
喻:这需要天分是吧?
张:需要天分,也需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所以比较起来它的难度更大。
喻:美育?是吧?美学里讲审美教育。
张:我前些天写了一篇小文章,讲我们现在已经懒惰到不愿意思考,不愿意进行一种深度的审美开掘、审美创造的平庸时代。就靠几个明星、小鲜肉来支撑,演个电影演个电视剧,告诉你有哪几个明星,甚至把20个明星、30个明星捆绑到一部电影当中去,资源过度挥霍,却是连一个好的作品名字都取不出来。当年翻译一部外国电影, 《魂断蓝桥》 《飘》 《蝴蝶梦》,这样的命名都有一种艺术情调在里面。现在,我就想不出《都挺好》这是说什么呢? 《我们都要好好的》这又是说什么呢?没有任何指向。
喻:它是不是代表一种市民的价值取向?
张:不是代表市民价值取向,是创作者的思维惰性。而且,即使代表市民价值取向,你也不能去追随它,不能去迎合它。文学艺术还有一种引导性,还有一种导向性,它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高度概括、凝炼,提升出来,不是说把我们艺术的语言变成大白话。 《都挺好》,是我喝的这个茶很好呢?还是这个正使用的录音机很好?还是讲我们坐的椅子桌子挺好?没有任何思想意蕴,没有任何艺术的含量。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好过日子、好好看电影、好好做游戏?
喻:它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
张:强调文学研究中的感性优先、审美优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尔库塞所讲的,建设新感性,要用丰盈的审美感性去改变现实中的人的工具性异化,对抗单向度的人,去冲击工具理性的功利至上和社会生活的同质化。这是个很大的理论命题,以后有时间再续谈。
喻:好的。谢谢张老师的指教。
注释:
①张志忠: 《误读的快乐与改写的遮蔽——论〈启蒙时代〉》, 《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