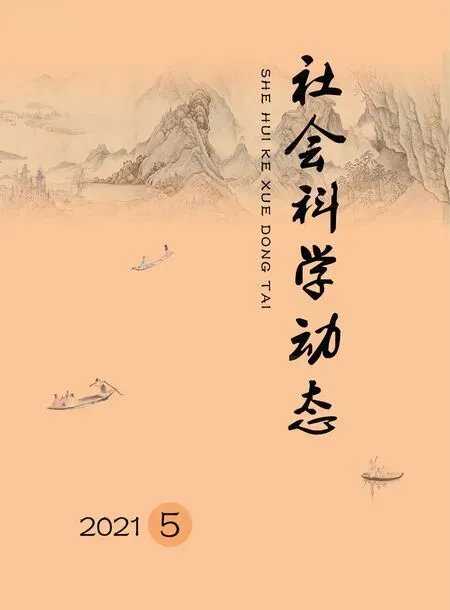疫中一堂“ 写作” 课:追忆与反思
张箭飞 陈 韬
编者按:2020 年2 月,武汉大学写作学专业2019 级博士生就 “学科前沿与治学方法”问题,对武汉大学文学院张箭飞教授进行了线上采访。为此,张箭飞教授系统地梳理了自己的求学、治学历程,追忆了诸多关乎当代学术气候的人与事,总结了一些宝贵的学术心得。时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箭飞教授有感于社会现实,对 “文学何为、学术何为”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教导学术后辈要关注现实、投身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陈韬博士将此次访谈内容整理成文本,以分享其学术思想。
一、 写作转向与文化气候
你们都是写作学专业的博士生,那我就从写作谈起,讲一讲我和这个专业的渊源。
我一直认为写作学和其它专业不太一样,写作学更加强调实践性。写什么?如何写?不能只讲不练,你得不断去写,才能领悟写作的技艺。正好最近弘毅学堂要开写作课,领衔的主讲教授是一位著名作家,讲“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al writing)”,作为助教之一,我有机会聆听作家本人谈论创作实践和“秘笈”。这一机会促使我去思考新文科体系中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和路径。当然,这并非我第一次接触写作教学。我曾教过学术写作,文学院硕博英语专业课,包括学术英语。有几年,我负责这门课文学部分,张延成教授负责语言部分。除了导读文献原著,还要讲解如何写英文提要(abstract),这一教学任务需要使用一些“八股范例”,比如有哪些常用动词、副词、句型,都是有章法可循的。
再往前溯,我教过武大作家班的《外国文学史》,也算一点微弱的写作学渊源吧。武汉大学一共办过三届作家班,我教过其中两届。作家班的课程设计及培养目标应该属于“想象性写作 (imaginative writing)”,与学术写作 (academic writing)有很大不同。作家们的写作课我是没资格教的,但是《外国文学史》的部分内容提供了想象性写作的经典样板,以至于有几个学生要求提交自己的作品代替闭卷考试,我没有答应,部分是出于一种预置的经典傲慢:你们的习作无论如何不能和巴尔扎克、卡夫卡放在一起比较打分。实际上现在来看,武汉大学作家班还是培养了不少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等。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光大了凌叔华、袁昌英、闻一多等人的遗产,巩固了武汉大学文学系作为作家摇篮的传统。
我与写作学产生联系的节点和国内学术热点的移动几乎同步。20 世纪80 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大学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带热了想象性写作;90年代后期学术写作渐成主流,从教师到学生,人人都在写论文、发论文,前途系于学术写作;再到最近,创意写作专业要么从原有的语言文学科系独立出来,要么嵌入传统领域再开新枝,这一变革又将非虚构写作推到前沿——看看本院《写作》杂志最近两年的关注热点,就能发现变革的速度和趋向。
写作学的三个侧重面,我接触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学术写作。它是我的从业技能,也是需要传给学生的技能。之前教英语,现在教汉语,语言不同,但是路数相近。我们的学术写作基本是依照西方范式展开的。如果沿袭《二十四诗品》 《人间词话》的路径写论文,显然和当下的论文规范无法对接,投稿给《文学评论》或是《文艺争鸣》,大约不会通过审核。西式论文,从摘要、关键词、正文、结论、注释、引用等都有一定之规。作为审稿人,必须按照一些公认标准来审核或评阅各种论文。这种规范的学术写作是存在问题的,这一点我稍后再展开讲。
广义地说,学术论文或专著,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往往列入非虚构写作范畴。我个人偏好的新历史主义、微观史学著作不少也称得上非虚构文学杰作,比如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作者曾是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因担任一部电影顾问而接触到关于真假马丁的档案材料,她通过出色的叙事技巧,重构了“16 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这本书写得轻盈活泼,我每年都要推荐人文班学生阅读。我经常想,如果我们每年审阅的学位论文能跳出几篇这样路数的写作,那该多么清新可喜啊!
以上是我与写作专业的渊源。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能反映出来,学术气候的变化在我个人的专业生涯中有很大影响。你们问到了我的学术兴趣变化,为什么从早期的鲁迅小说研究转向风景与文学研究,再到现在的植物与文学,似乎跨度有点大。其实转来转去,我并没有离开文学。包括我的博士论文是《鲁迅的诗化小说研究》,也可以说是鲁迅小说的音乐性研究,属于“音乐与文学”的范畴。总之,我感觉自己的兴趣不管怎么转向,都还没有离开文学,每次转向与时代的学术气候变化有关。
二、 七年之学: 恰遇文学年代
前面说到写作学的热点移动,第一个热点是文学创作,这和今天很不一样。当下的语言文学系,文学研究和批评占了课程主要部分,不少学生也有以学术为志业的打算,自然而逻辑地会选择读研深造,一路朝着文学批评家或文学史学家的方向狂奔,除非改换专业进入其他领域,比如法学、金融学。我读本硕那7 年,却是搞文学创作的同学最领风骚,备受仰慕。90 年代后期渐成学界中坚和权威的学者,谁没当过文艺青年啊?要说80 年代校园充满文学的空气,一点也不夸张。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之前断档缺货的经典名作,闻所未闻的文艺思潮,包括创作方法,不分时态地一起涌进国内,说是泥沙俱下也好,话语多样性也好,反正就是很丰富。有些在原产地快要成为“知识考古遗物”的思想也再次走红,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此书由傅雷先生翻译,1962 年首版,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翻译者已偕妻自杀。要到80年代,它才会鲜花重放,惊艳于国内读者群。
这让我想起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文集《重放的鲜花》。“文革”结束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把一些此前受到批判的老作家们的作品辑成一集,名为《重放的鲜花》,来呼应社会的文学阅读饥渴——我觉得这个书名非常好,富含“rebirth”之意。的确,当时我们赶上了一个开放时代,除了贪婪接纳外来文学,还饥渴地汲取曾被标为“毒草”的汉语写作精华——文学也好、理论也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解冻复苏的过程。此书一再加印,其中一版由著名诗人公刘作序,言简意赅:“多少寒冬!多少苦夏!/痛楚在历史的手掌中融化;/古莲子又复活了,冰山却轰然倒塌!”只有置身那个时代氛围(atmosphere),才能真切体会为什么“毒草”可以重新绽放为“鲜花”,而且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呼吸,塑造出他们的性格气质。后来,一些高校开始加入了这股解冻浪潮。记得当时国内大学敢办作家班的也就只有北大和武大。80 年代的武大在不少方面敢为天下先,中文系又特别活跃,说它引领风骚和思潮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英文系读书,经常蹭中文系的课程和社团活动,因此我也算是四面八方接受各种影响,从文艺理论到写作实践。
你们问到我为什么从那么多的理论流派中选择了新批评作为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原因很简单,我本硕念的是英美语言和文学,而英文系教学一直强调文本细读——可以说,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入手训练,看重批评者的语言学基础,这一点恰好是武大英文系的传统和四川外语学院的强项。我本科的学术导师聂文杞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受教于燕卜逊教授门下,而燕卜逊被列为新批评宗师之一,其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 与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构成我们的文学批评课程基础。在硕士阶段,我师从四川外语学院蓝仁哲教授,他是翻译大家,不少美国意象派名诗汉译就出自他的妙笔。其实,读研头两年,我的兴趣主要在语言学方面。当时的川外,研究生培养体系不像现在的武大强调专业界限和课程性质,我们可以随意选课,不拘主次。正好碰上两位很有意思的语言学老教授,他们的个人经历如果考据串联起来,就是应用语言学的时代坐标,翻译专业的战争风云,川外辉煌的校史。他们讲的东西我特感兴趣,比如句法背后的逻辑和思想,倒装句的“意义”呈现,介词使用的文化蕴含……可惜,那个时候也没便携式录音笔,如果当时记录下来他们的正课和闲谈,一定是非常珍贵的学术甚至历史资料!
有一阵子我想转到语言学领域,觉得语言学(linguistic)听起来有些“科学 (scientific)”的硬核,当然最后还是放弃了,重回文学方向。一来我是简·奥斯汀的铁粉,借做毕业论文可以好好与原著磨合一番;二来我觉得毕业后若在英文系任教,有的是机会实践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交叉”,不管是形式主义批评还是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到底离不开索绪尔的影响,而且它们也不断借光语言学进展,揭示作为语言作品的文学的美学以及文体特质。
讲到文本批评,我想到当下的研究生文学教育。我上课最大的困扰就是:很多学生文学原著读得太少,课程安排太满,不留读书的“余裕”。北大的一些老师也有同感,还专门写过文章讨论“解困”之道。反观80 年代青黄不接,不少该开的必修课都没人上,反而给了我们阅读的自由。到了你们90 后,学术训练密不透风,好处是训练有素,步步为营,坏处是系统性的定量投喂,疲于消化。课程论文、外语考试、出国申请、论文发表……压力之下,读书只能带着很强的目的性,搞不好就变成“精致的平庸”——这是某位清华教授的吐槽,指的就是那种流水线出来的论文,工序和技法无可挑剔,唯独没有个性印记。
杨孟庄排闸,孔深15m。闸基主要为第②上层壤土、③层壤土,地层厚度稳定。第②下层壤土,粉粒含量较高,夹砂壤土薄层,土质均匀性较差,7.8~9.7m呈软塑状,埋深较大,一般不影响地基稳定。
继续说我为什么对新批评情有独钟。除了外文学院英语系固有的教学传统熏陶,也与外聘的加籍教授洛伦斯基有关。他原籍乌克兰,属于俄罗斯形式主义批评的嫡传,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他流亡到加拿大任教。中国重开国门,老先生就被请来“传经”,因为蓝仁哲先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加的学者,多伦多大学毕业。洛伦斯基教我们英语诗歌批评,正是从他那里,我们对诗歌的语言试验获得特别的理解。他有很高的音乐修养,钢琴弹得很好。他上课不按流派概述、文体特征这类我们习惯的套路ABCD 一一进行,而是直接扭开音响,播放古典音乐,他一行行给我们读多恩、雪莱、叶芝……至于他们的诗歌有什么奥义,老先生似乎不屑深讲。他只在课前打印一叠讲义,标出韵律特点记号发给我们,要求我们细细品味轻重音,品味头韵、节奏之类的声音特点——说新批评派最宜诗歌解剖,大概是有道理的。当时蓝师门下有7 个研究生,之一就是张枣——每当听到武大文学院学生表白如何崇慕他时,作为他的川外同学,我真是又骄傲又惭愧——骄傲自己居然与一个载入文学史册的杰出诗人师出同门;惭愧自己当年没有史家前瞻眼光,记录点课堂内外掌故。洛伦斯基教授非常欣赏张枣的才华,与他交往甚密,似乎并无师生之别、内外之隔——这是我从某位诗人追忆张枣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的。但在我的印象中,张枣常翘老洛的课。其实,就连导师的课,他也会大翘特翘——这位诗歌神童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浪游、行吟、留情于重庆、成都两地诗人部落和粉丝堆里。蓝师也特别开通,由着门下几个写诗的学生时不时神龙不见首尾。
川外颇得巴蜀灵气霑濡,诗风尤盛,未遑多让北上广武等地的老牌名校。当时中国有两个诗歌中心:一个是以北京《诗刊》为中心,比较主流;另一个就是成都《星星诗刊》为中心,比较先锋,发表了不少蓝师现代派诗歌译作。值得一提的是:蓝师也是国内首版《托马斯·哈代诗选》的译者。诗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毕业之前我也得到了一本赠书。关于哈代,我此前只读过他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还乡》 《无名的裘德》等,自然当他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伟大的传统一环。经过蓝师的引介和点拨,我才对哈代诗歌的现代性和实验性略有了解。多年后,国内学界哈代诗歌研究“温热”起来,我更加佩服蓝师对原诗的风格感觉实在敏锐,能用同样气质的汉语节奏和韵律传达出来——当看到著名诗人牧南对蓝译诗选的高度评价,我一时不能自己:如果蓝师还能看到来自诗人读者的赞美,一定会很害羞地微笑吧。
在这种风气之下,川外星光熠熠,除了张枣,还有杨武能、林克、刘小枫、邓正来、杜青钢等人闻名于国内文坛译界——川外人的创作和翻译参与塑造了时代精神(zeitgeist)和文化氛围(cultural atmosphere),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洛伦斯基教授选择客座川外,与我们诗性逍遥的校园氛围特别合拍。这个老外还是一个川剧粉,曾在课上说中国艺术只可由川剧和金鱼代表,其余不过尔尔,杜甫诗歌充满廉价的情感——我很清楚地记得,一句“cheap emotions”激怒了我的雅安同学,他用四川调调的英语反驳了一番,大块头的老先生不以为忤,笑得十分豪放。当然,豪放,也可以说霸道——那是80年代,改革开放没几个年头,外教多多少少有点文化优越感和学术傲慢。有同学也吐槽他上课播放音乐时间太长,有磨洋工的嫌疑。但就我个人而言,特别感谢他给予我的音乐启蒙,使我注意到文学和音乐的关联。你们想想现代派诗歌,它要摆脱传统的押韵方式,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物,那就是音乐感。正如席勒说过,一旦诗歌失去了音乐感,它就不可能达到艺术臻境。所有的艺术最后都趋向音乐性,这也是作为现代派前驱的浪漫主义留下的一份遗产,后来的现代派颠来倒去进行各种激进的语言试验,无论是节奏也好,重音也好,还是意象之间的呼应也好,最终是为了音乐性表达。基于这个大语境,洛伦斯基教授格外强调诗歌的“可听性”,当然,他要我们理解的可听性并非等于“悦耳”“流畅”——就好比西方音乐发展到斯特拉文斯基时代,刺耳、粗暴、怪诞就是现代主义定义的和谐音。实际上,被誉为“前现代派”的哈代,在布罗茨基看来,其诗行“拥挤紧绷,充满互相碰撞的辅音和张着大嘴的元音……”,颠覆了我们已习惯的浪漫主义诗歌优雅顺滑韵律特点和节奏方式。
我们学外语的一般都会装备一台录放机。受洛伦斯基教授的影响,我买了不少音乐磁带,慢慢听出了一些名堂,逐渐对西方音乐有些系统的了解。这种“文学的耳朵”训练不仅铺垫了我后来的博士论文,还直接促成了我的室友职业选择——她后来进入四川音乐学院任教,译介了一些西方音乐资料。如果没有洛伦斯基教授的启蒙和熏陶,来自鄂西北山村和川西农村的“草根”读书人,大抵不会与西方音乐发生深度联系。
三、 博士阶段: 聆听鲁迅
硕士论文我并没做文学音乐性研究,而是选择了简·奥斯丁与启蒙运动哲学这个题目,涉及三个方面: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这篇略有学术野心的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的相当肯定。其中一位是熊正伦先生,年过八旬,是从西南师范大学请来的,该校后来升格为西南大学。这位与吴宓同事多年的英语教授鲜有人知,其实他真称得上是世纪老人——生于清廷变法新政之年,逝于中国改革提速之年,几乎全程见证了20 世纪中国历史。熊先生本科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又在美国工作多年,回国进入教育界,曾在好几所大学任职,还教过杨振宁——这个细节是熊先生在答辩“茶歇”时摆龙门阵讲的。那时候还在讲台的老教授,几乎每个人的人生都称得上波澜壮阔,他们共过事的或教过的学生不少都是名人。等我陈述完毕,熊先生点评,特别夸奖了我的英语文体,说没有料到会写得这么美。借他的吉言,我后来将其中一章翻译成中文《奥斯丁的小说与启蒙主义伦理学》,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 年第2期上。作为学徒工的“少作”,此文被引用量尚可。
说到我的英语写作,我是下过一些笨功夫的:在本科阶段,我每天抄写两大教材的篇章,New Concept English (《新概念英语》) 和 Essential English for Foreign Students (《基础英语》),前一套教材人人皆知,后一套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到了研究生阶段,我选择赫兹利特批评散文练习翻译,先翻译成中文,再根据中文回翻回去,两相对照看看差在哪里?异在何处?赫兹利特是浪漫主义时期批评大家,他的文风汪洋恣肆又华丽炫技,颇与我那时的品味合调。研二下学期,南京大学英语系解楚兰教授来川外,我有机会陪她游览林森官邸。解教授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多年担任范存忠先生的研究助手。武大毕业前,我还曾投考范先生18 世纪英国文选方向,不幸落选——连同我在内的三位候选人全部落选了。落选的内情,多年后从毕业于南大英文系的一位教授那里得知,不免遗憾:我辈晚矣,错过范门桑榆暮色,沾染不上先生治学的余晖。那时并不知情,只得怅然作别南大。不久,我接到解教授的来信,信中颇多鼓励之句,我回信感谢并告知自己已被川外收留。所以,解教授到重庆访旧,特意约我一见——这就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教养,细腻而优雅。听说我在模仿赫兹利特文体,解先生就建议我多读海明威,说他言之有物、简洁清晰的文体更要可取。她的苦心我要等到与鲁迅相遇,才会有些明白——说起来,简洁清晰,也是音乐性表达的特征之一。
硕士毕业后,我重返母校,选择进入中文系,岗位任务是给考研同学补习英语。到第二年,一位教外国文学史的法归老师突然跳槽,留下三分之二的课时无人接手。于是只念过英美文学的我顶了上去,不由分说地就从国别文学转到一个更大的专业领域,继而视野也被迫拉大。比如说,我讲到文艺复兴,就必须多线追踪,看看意、法、西、英、德,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文学这些线索如何交织成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那个巨大的存在。那次仓促上阵的机会迫使我打破了原来的专业设限。实际上,随着文学教育及批评的“跨专业跨语言跨文化”趋势逐年加强,一直严守语言疆界的国别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学——今日讨论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现象或一部作品的具体表现,恐怕都不得不在“越境、流动、贯通”的框架里展开。比如说,如果不懂日语,不了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换和文学传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初的很多问题只能搁浅在看得见的部分。教了几年外国文学史,我很幸运地成为陆耀东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经过几年伤筋动骨的“捶打”,我慢慢舍弃了原先对于华丽文体的偏好。博论开题,我选择鲁迅诗化小说,陆师有点担心:毕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研究经过多年深耕,成果密度很大,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包括我导师在内,太多杰出学者贡献了传世之作,留给我们这些迟来者的空白或缝隙似乎不多了。
这里,作为过来人,我贡献点体会。博论选题,不外两种选择。一是绕开经典大家,单挑比较冷僻甚至闻所未闻的作家,也许会有所发现,但有可能带来一个糟糕的结果,就是你不得不降低文学标准,在一个不那么好的作家或一些不怎么样的作品上面花四、五年时间,写出博士论文来。这种做法越来越时兴,大概因为学术从业人员太多,传统研究对象已经成为稀缺资源。第二个选择就是迎难而上,不畏险高。在我眼里,鲁迅才是中国的“文化昆仑”,对于我这样一个学英语的人来说,通过鲁迅,我可以好好补一补中国近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学。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史进程,跌入现代性深不可测的水域。1881 年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断裂、偶然、巨变,从洋务运动到文学革命再到前期抗日战争,鲁迅都全程见识和亲历,他被时代塑造,他亦在塑造中国的现代文化。研究鲁迅,就得深读鲁迅,进而进入中国的心灵。
但是,话说回来,鲁迅研究的确难以“出新”,几乎方方面面都被捷足者涉猎留痕。在恶补泛读了一批文献之后,我找到了诗化小说和音乐的文体关联,决定结合我原来的爱好,论证鲁迅文体是否有高辨识度的音乐性。早在1918 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既讲了小说“叫喊和反抗”的启蒙作用,又谈到了文体要求,包括力避行文的唠叨,务必读得顺口——这近乎是音乐性的要求了,直到现在,很多著名作家都未必做得到。找到这个结合点,我每天的功课就是边听音乐边读鲁迅小说,在打印出来的文本上划线字词句段,标记音节、音顿、顿歇、轻重、标点符号的“声音”功能等,揣摩他的语气、语调、弦外之音,我需要同时调动眼睛和耳朵——这种细读是比较技术主义的,而鲁迅这种大家也值得花上这番功夫。
我本来想把博士论文定题为“鲁迅诗化小说和音乐”,后来出于谨慎,改成比较稳妥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陆师请了北大和中国社科院几位鲁迅研究名家评审,包括钱理群先生、刘和教授、吴福辉教授等。外审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答辩会上,钱先生当场问我可愿把论文编入他主持的一个书系出版,并且约定其中一章交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我很欣慰,受到钱先生激赏的几篇拙文后来被一些鲁迅学术史综述屡屡提及,其中,“鲁迅小说的音乐性分析”入选王彬彬教授主编的《十年论鲁迅——鲁迅研究论文选(2000—2010)》——在我看来,这也算是对我转入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一个肯定吧。
当时也有如何写论文的宝典,我就买了朱光潜先生写的一本。说实话,我只大略翻了一翻,真正用心读的反而是该丘斯作曲法教程。我认为,写得好的论文应该有音乐的结构,如何陈述主题动机,怎么变化、发展、对比、章节的长度安排……总之写作和谱曲都要遵循逻辑和连贯性。现在的博士论文有种趋势,越厚越好。我个人倒觉得文学研究的monograph(专论),还是写得紧凑明晰更好。写完之后,务必朗读几遍,废话、病句、拗口的表达自然浮现,多余无用的节段格外扎眼。我自己审读论文,对于同义重复的车轱辘话也颇不耐烦。总之,作为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和学者,我们得为现代汉语“美的表达”而写,写得简洁、明晰、有节奏感。
四、 近年转向: 风景和植物人类学研究
《鲁迅诗化小说研究》的出版等于结束了我的阶段性任务。对我来说,鲁迅太伟大了,他不应该成为我的饭碗,而应该作为精神食粮继续滋养我的学术。我再次转向。这肇始于钱理群先生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在他的第二故乡安顺举行,而这次会议又是起因于钱先生自己的困惑:学院派的文学研究已与社会现实脱离,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遗产难以为继。说起来,学者定位的转换还是时代所致。80 年代人文学者大都以启蒙为己任,文学批评的现实介入感很强。到了90 年代,知识分子觉得思想启蒙属于the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之使命)。于是,几位著名学者发起了一场争论:一种声音主张仍然保持介入现实的姿态;另一种声音则坚持用学术规范收束80 年代以来众声喧哗造成的写作乱象。逐渐地,第二种声音演进为主旋律,与其同步演进的则是依托研究基金和核心期刊的学术评价体系。2000 年之后,进入学术界的“新人”基本由这套体系培养,并将其自动升级成写作操作系统,内嵌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中。其优点不言而喻:评价有据可依。论文是否抄袭,职称是否够格,都可导入这个系统检测。同时,规范也意味着有章可循,“某某主义或理论视野下的某某研究”的流行也证明规范的行之有效。钱先生意识到这种规范背后的危机,因而提出要阅读脚下的大地,并编辑了一本《贵州读本》,意欲以地方文学的特殊性打破某些批评公式或范式的“齐一性”。会上,我做了一个主题报告:“地方感与文学”,主要介绍国外在这一方向的探索。钱先生很感兴趣,问我能不能翻译一些原著,这就是译林那套风景译丛的起因。每本书都重点讨论了一个多学科交叉概念,比如风景与认同、风景与权力、风景与记忆等。
这套丛书中,马尔科姆·安德鲁斯的《寻找如画美 : 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对标贵州风景和《贵州读本》,为贵州风景的文化赋值提供了一些借鉴。译作出版之后,在主持贵州旅游规划的张晓松教授大力推介下,某些学术观点进入实务领域发挥一点作用。作为贵州旅游文化研究传播中心的特聘专家,我有机会参与贵州十年旅游规划制定、调研和培训,而这本书关于风景的发现、废墟崇拜、如画美的塑造与现场写生等问题的讨论发挥了观照现实的作用。期间,我发表了几篇较有价值的论文,其中的一篇《风景与民族性的建构——以华特·司各特为例》颇受同行关注,入选了爱丁堡大学司各特档案馆的研究文献目录。
随着参与度越来越深,我对风景美学的关注偏移到风景的重要构成要素——植物和植被上。最近几年,作为旅游大省的贵州省开始精准定位自己的风景优势,开发山地旅游的巨大潜能,不少村寨展开了美丽乡村运动,先从美化道路、庭院和田园开始,就要种树、种花,结果不可避免落入大江南北的绿化窠臼……花景的季节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几不可辨,曾经的“独一无二”的风景特质面临“千镇一面”“千村一面”危机。在现实问题倒逼之下,我开始琢磨起乡土植物与地方风景的关系:什么样的乡土植物能保持或突出当地的魅力?什么样的“植景”可以提供不可复制的审美体验?
我出生在中医家庭,从小生活在鄂西北山区。这个区域曾以植物多样性和观赏植物丰富性而著称于世界园林植物史。我对植物的热爱既是环境赐予,也有家传的基因,更有后天阅读的强化。就这样,兜兜转转地我回到少年最爱的事物上,并把热爱发展成学术兴趣。最近的几篇发表都与植物交换和美学有关,比如《宜昌报春花与大英帝国花境》一篇就是写于参与湖北生态旅游实验点考察之后。看见自己的文章能引燃当地有心人去重新发现地方的骄傲,作为研究者还是有点欣慰。
讲到这里,我简单做个总结。这次瘟疫几乎突然切断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学术生活和惯性写作。在最焦虑的日子,我问了自己三个问题:文学何为?文学理论何为?学术何为?正是出于一种回答的冲动,我改换了上课内容,将弘毅学堂的《外国文学史》的重点移到“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将汉语文学专业的《植物人类学》的重点移到“抗疫植物的传说搜集和整理”上,我试图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重新定位一个文学研究者与现实关注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对你们提出的问题的回应,非常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在一个特别的时期,让我回顾自己这40 年的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