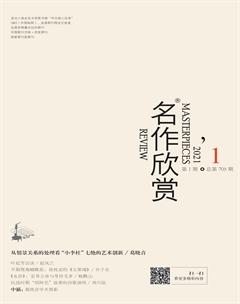范仲淹与他的朋友们(一)
周宗奇
小序
有的人生性寡淡,一辈子没个知心朋友,形影相吊,可怜兮兮;有的人性喜交友,二木成林,三木成森林,风过处哗啦啦一片涛声。
然而,交友之道,是一门人生大学问,蔚蔚然深矣!笔者琢磨:缘分运作,遇人也多。但凡你认准了其中一位或几位的真性情,特别是认准了他或他们的缺点、弱点,并且又愿意包容之,妥了,你就深谙交友三昧,有了自己一辈子的朋友了。
又然而,说好说,做难做。古来交友高人有几多?所传佳话并不丰盛。笔者又琢磨:北宋名士范仲淹一生的交友实践,全面又典型,极具借鉴意义。比如:有争议的朋友,怎么相处?有恩惠于自己的朋友,怎么相处?误解过你、伤害过你的朋友,怎么相处?得你恩惠的朋友,怎么相处?个性特强、脾气古怪的朋友怎么相处?朋友们共襄家国壮举,面对艰难险阻与失败怎么办?……范先贤都有示范,都堪称经典,都学而可受益终生。
于是,遂有拙文问世,不揣冒昧了也。
范仲淹与滕子京
天底下,人世间,既然人无完人,必定朋友无完朋友。你的朋友中,说不准就有惹是非、招争议的人物。
在范仲淹所有的朋友中,相识最早,相交时间最长,相知最深,始终都有笔墨与心灵交流,最后共同为后世留下《岳阳楼记》千古名篇的,就是滕子京。可这个滕子京呀,偏偏就是个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滕子京以字行,名字叫宗谅,河南洛阳人。他比范仲淹小一岁,与范大哥同登大宋祥符八年乙卯(1015)蔡齐榜,进士及第,有了同榜之谊。两个青年人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这关系可就从根上扎下了。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范仲淹还不叫范仲淹,叫朱说,怎么回事那得另外成篇。
滕子京的性格,与他范兄大相径庭。《宋史·滕宗谅传》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倜傥”者,言行卓异,不落俗套,豪爽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近义词就是风流潇洒、风度翩翩、风流跌宕之类。而“好施与”者,慷慨大方,仗义疏财,花公帑大手大脚,花自家银子也从不心疼,所以到死的时候,穷得家“无余财”。用今天的话说,滕子京就是那种个性极为张扬的人,我行我素生瓜蛋一枚,优点也好,缺点也罢,都一起抖出来给人看。这样一种性格,其实适合做行吟诗人或梁山好汉,放在宦海官场里,那就注定吃不到好果子。范仲淹对兄弟最是了解,感慨不已地说:“宗谅旧日疏散,及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他这话原是对皇上宋仁宗说的,也是他对老朋友的真实看法。“招人谤议,易为取信”,什么意思?谁要造滕子京的谣言,一般人都会信以为真,他就那副德行。这里只说两桩由他引发的历史公案。
第一桩:泾州“费公钱16 万贯”案。
泾州,就是现在的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泾州古城可了不起,城建史三千多年,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从商周至清末,它“控扼两陲之咽喉,边衢之门户,壮西服而控远夷”,一直起着“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的国防重镇作用。北宋时西夏“元昊攻宋”,这里更是生死攻防的前沿阵地。案件发生时,正是滕子京“知泾州”,是重任在身的地方长官。此时,他的哥们范仲淹经朋友韩琦举荐,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与韩琦同时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也在抗战前线,时年五十二岁。滕子京则刚过知天命之年,二人的友情已然绵延二十多年了。
泾州这个地方,是个边关阻隔、战乱频仍的兵家必争之地。西夏国大举攻宋,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知州镇守城池,手中并无多少兵卒,“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总算没有失守。为了抚恤和庆功,滕知州抡开大手笔,动用公款“16 万贯”,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花了个精光。为了不让下属承办官佐担责任,他“一人做事一人当”,发了点好汉脾气,“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滅姓名”,将所有账单付之一炬,想查账吗?查个锤子!这可就给自己惹下大麻烦了。有御史梁坚者,向皇上奏了一本,罪名是滕子京“费公钱16 万贯”,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挪用公款”罪。想想这可是在战争时期,又在作战前线,挥霍“公钱16 万贯”,足可买下你人头一颗。这样的钦犯谁敢为之说情?谁敢为他做无罪申辩?
患难之处见真情。敢为朋友两肋插刀者,也只有范仲淹了。此时,范仲淹的处境并不好,“予时待罪政府”,但仍不顾个人安危,连上奏折三道:《举滕宗谅状》《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应该怎样公正对待滕知州,范朋友有过这样一段话:
西戎犯塞,边牧难其人,朝廷进君刑部员外郎、知泾州,就赐金紫。及葛怀敏败绩于定州,寇兵大入,诸郡震骇,君以城中乏兵,呼农民数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缯募敢捷之士,昼夜探伺,知寇远近及其形势。君手操简檄,关白诸郡,日二三次,诸郡莫不感服。予时为环庆路经略部署,闻怀敏之败,引藩汉兵为三道以助泾原之虚。时定州事后,阴翳近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劳,霈然霑足,士众莫不增气。又泾州士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复抚其妻孥,各从其欲,无一失所者。
这才是事实真相,这才是真正的滕知州!包括皇上在内,你们明白了吗?梁坚之弹劾,昧于事实,是非颠倒了啊!宋仁宗还算是个比较通人性的皇帝,最后“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调岳阳任职,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有了“岳阳楼贪渎案”。
第二桩,“岳阳楼贪渎”案。
滕子京这性格,到岳州就消停了吗?那就不是滕子京了嘛。他前脚刚重修好岳阳楼,后脚就有人再告御状,弹劾他说:这个滕子京在岳州任上,并未做到“勤政为民”,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反而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况下,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技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瞧瞧,这回滕子京犯的可不是“挪用公款”罪,而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了,分明是个借工程捞钱的“大老虎”。
对于这位又惹争议的老朋友,范仲淹会怎么办?经过西北前线数年的战火洗礼,他们近三十年的友谊得到锤炼与升华。年近花甲的范老兄底气更足,他说:滕子京的问题,根本不是出在什么“贪渎成性”,而是出在他“尚气”且“好施与”的“倜傥自任”。他说话并非护短,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滕子京斥巨资重修岳阳楼,靠的并不是财政拨款,也没搞什么集资摊派,而是依靠催收民间烂账聚财,公私双赢。如此令人拍手称奇的妙招,实在是“非宗谅侠智而不能为”,连岳州老百姓都“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你说滕子京“自入者亦不鲜焉”,绝对不可能!假如修好岳阳楼尚有余资的话,照滕子京那喜欢排场热闹的脾气,搞个大型豪华庆功晚会,花大价钱请来著名艺人捧场,上点好酒好菜,把那点钱花个精光,这倒完全可能,他才不会惦记什么“自入”呢!不然的话,怎么会“及卒,无余财”呢?
有意思的是,比范、滕晚生近三十年的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闻》中这样记录此案:“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看来笔者这位河东先贤,所记貌似全面而又公正,其实却揪着“自入者亦不鲜焉”的小辫子不放,想做“帝王师”的他,是看不惯滕子京这种官品的,你能像我司马光一样清白吗?嘁!可他也留下了自相矛盾的把柄,滕子京既有贪渎,何以“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范仲淹浩荡一生,为国为民荐举了多少人才,几乎无一失误,怎么偏偏就对一个滕子京,花几十年功夫都看不透,倒不如你这个捕风捉影的后生晚辈?莫非你连朝廷查證“及卒,无余财”的正式结论都不信吗?你这个苛责他人的毛病真不好哦。
至于重修岳阳楼,是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还是在抢救文物,做一件利在后世的功德事,范仲淹心里当然明白。岳阳楼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最早,三国东吴大将鲁肃奉命镇守巴丘,操练水军,在洞庭湖连接长江的险要地段,建筑了巴丘古城; 建安二十年(215),他又在巴陵山上修筑了阅军楼,登临可观洞庭全景,一帆一波皆可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在两晋、南北朝时被称为“巴陵城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登临胜境,凭栏抒怀,记之以文,咏之以诗,形之以画,使岳阳楼成为艺术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滕子京被贬至岳州时,岳阳楼已经坍塌毁损,非重建不能保有千古胜迹……这些话范仲淹自己不说出来,是想留给后人评说,岂不更有说服力?他爽然应约,欣然命笔,绝唱面世,《岳阳楼记》中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八个字做引子,你们就去尽情想象贬官滕子京的岳州作为吧!
不出范公所料,公正评价滕子京者,当代就大有人在了。共识是: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饱经磨难,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棱角分明,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事实是:他在岳州三年,承前制而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件大事在在有记。故而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则称:“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苏、王与《渑水燕谈录》,都是与滕子京同时代的名家名著,其评价是很可取信的。至于后人之褒赞不绝,不可胜记也。
庆历七年(1047),五十七岁的滕子京病逝于苏州任所。五十八岁的范仲淹当时在邓州任上,正为朋友一件事累得身心疲惫,闻此噩耗几乎晕倒,星夜赴苏州奔丧。后来记之曰:“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迁知苏州,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
滕子京墓在安徽青阳城东,新河镇光荣村金鸡岭下。他是洛阳人,为何要安葬于此?这就牵出他与范仲淹曾经的“青春游”了。他俩自打成了同榜进士,信然订交,过从甚密。青阳有座“读山”,原名长山,少年范仲淹曾随继父朱文翰在此读书,后人遂改称“读山”。范仲淹中进士后,即偕同榜好友滕宗谅来此游玩怀旧。青阳县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南倚黄山,北枕长江,山灵水秀,气候宜人。唐代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文人墨客览胜吟唱,多有留踪留名。滕子京触物明敏,感情丰富,一下子就喜爱上此地的山水之美。后来,他被贬为池州榷酤(笔者按:专管酒业专卖)期间,又邀好友范仲淹到池州游玩,二人上九华、游秋蒲,再览贵池、青阳风光。《青阳县志》载有滕子京所著《九华新录》《九华图》为证。就是在这次游历中,滕子京流露出百年之后,希望魂归青阳的愿望,并把年迈的父亲和滕氏家族陆续迁入青阳。他病逝后,家人遵其嘱,安葬于青阳。《明万历青阳县志》载有范仲淹所作《宋滕子京墓志铭》,“诸子奉之丧,以某年月,葬于青阳邑东十里之金龟原,而乞铭于余……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云云。
说到范仲淹所作《宋滕子京墓志铭》,也是传世美文一篇,可惜篇幅过长,不便照发。且看以下用词:“少孤”,“性至孝”;“生平好学”,“积书数千卷以遗子孙”;“政尚宽易,孜孜风化”,“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在……四郡,并建学校”;“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重兴岳阳楼,刻唐贤今人歌诗于其上”……这就是范仲淹笔下滕子京的一生。一个读书人拥有如此忠孝节义、可圈可点的人生,“可不谓之君子乎!”滕子京瑕不掩瑜,是一位佼佼士君子,聱聱大丈夫!范仲淹用平生近四十年功夫,正面盖棺论定滕子京,绝对不会错!《宋滕子京墓志铭》的结尾一段如下,录之以飨读者。
铭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职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
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海不还,鬼神何意。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以降,干戈弗加。树之松楸,蔽于云霞。
君今已矣,复藏于此。魂其依欤,神其乐只。寿夭穷通,一归乎至理。